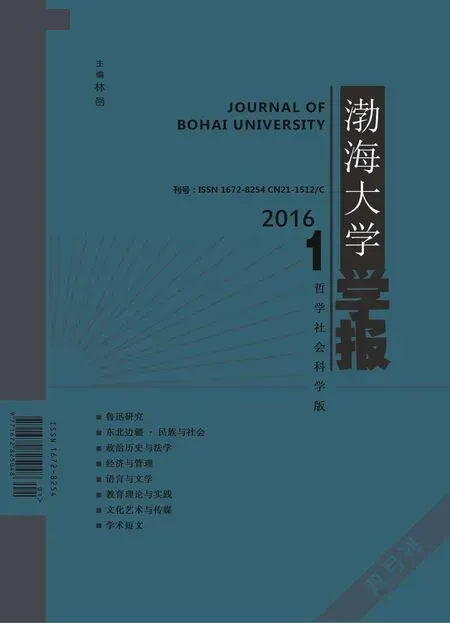隋唐营州的民族融合、胡风与葬俗
2016-12-16肖忠纯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辽宁锦州121013
肖忠纯 (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辽宁锦州121013)
隋唐营州的民族融合、胡风与葬俗
肖忠纯 (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辽宁锦州121013)
摘要:隋唐营州境内汉族、契丹、奚、靺鞨、高句丽、突厥、西域胡族等多民族杂居的局面促进了民族融合,胡族人大量接受汉族文化,但地域内在衣食住行方面仍盛行浓重的胡风。隋唐营州墓葬与中原地区不同,以圆形墓为主,不论墓主人社会地位高低,墓葬规模越来越大,并体现出较多的胡族文化因素。关键词:隋唐营州;民族融合;胡风;葬俗
隋唐营州处于东北边疆的前沿地带,所辖地域十分辽阔。《太平寰宇记》卷71《河北道》营州“四至八到”条记载:“东至辽河,南至大海三百四十里,西至平州(今卢龙)七百里,北至秦长城二百七十里,至契丹界湿水四百里。”不仅包括今辽西地区,还辖有今内蒙古东部和河北省北部地区。隋唐营州的治所位于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市老城),经济文化相对发达。随着朝阳市及其周边地区隋唐墓葬的发掘,关于隋唐营州葬俗的研究取得一些成果。但由于文献资料较少,关于民族融合与社会习俗的研究十分薄弱。本文主要从汉族文化的传播、胡风胡俗与葬俗三方面进行探讨。
一、隋唐营州的民族融合
隋唐营州地区除了汉人以外,还有契丹、奚、靺鞨、室韦、高句丽、突厥以及西域胡人等民族人口,各族居民大杂居、小集居,民族融合的程度日渐加深。民族融合以汉化为主流,但也会受到胡族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隋唐营州的多民族杂居局面
隋唐营州地区汉人主要集中分布在柳城,即今朝阳及其周边地区。其他地区驻扎一些汉人军队,总体来看,营州汉人人数并不是很多。营州大部分地区是为内附诸族所设的羁縻州县,如唐朝前期为契丹部落设立辽州、昌州、师州、带州、玄州、沃州、信州,为奚人设立鲜州、崇州(北黎州),为靺鞨移民设立燕州、慎州、黎州、夷宾州,为室韦人设立师州(以契丹、室韦部落合置),为突厥部落设立瑞州。各族居民大杂居、小集居,营州地区形成多民族杂居局面。
营州柳城虽以汉族人口占大多数,但多民族杂居局面尤为明显。城内与城外分布有许多民族人口,除了契丹、奚、靺鞨人外,还有内附的高句丽人、突厥人以及往来经商的西域胡人。历任营州都督、总管、柳城太守、平卢节度使之中即有一些是少数民族,如靺鞨酋长突地稽之子李谨行,唐高宗麟德年间曾任营州都督,据《旧唐书》卷199下《靺鞨传》,号称“部落家童数千人,以财力雄边,为夷人所惮”。还有出身于西域胡人的平卢节度使安禄山与高句丽人平卢节度使侯希逸等人。
根据目前发现的纪年墓葬,隋唐时期柳城有韩、蔡、张、杨、孙、王、勾、左、鲁、骆、高、李计十二姓19个家族。根据墓葬考古发掘和主要事迹,可知唐初内附蕃人有孙则、杨律、骆英、高英淑、尼大光明等5人,皆身任要职或为高官家属,其家族在柳城势力很大。可见,墓葬考古发掘反映出柳城城内多民族混居的人口构成状况。
隋唐营州地区多民族杂居的人口状况必然会促进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不断深化。
(二)汉族文化的传播
多民族杂居的营州地区,中原内地的儒学、典章制度、文字礼仪、佛教信仰以及服饰饮食等汉族文化因素逐渐为北方民族接受、吸收。相对先进的文化逐渐同化落后民族的文化,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隋唐时期,由于朝贡、和亲、质子、榷场贸易等形式,契丹、奚、靺鞨等族的中上层分子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不乏其人。契丹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先后朝贡20余次,肃宗至德以后,每年选酋豪数十人入京师长安朝会,其下属数百人则住在幽州馆驿中。至德、宝应年间朝献2次,大历年间13次,贞元年间3次,元和年间7次,大和、开成年间4次[1]。唐朝政府为了安抚契丹,对其上层分子实行和亲政策,先后以永乐公主嫁李尽忠的从父弟、松漠都督李失活,燕郡主嫁李郁于,东华公主嫁李邵固,静乐公主嫁李怀秀。所谓质子,也称侍子,一般都是契丹贵族子弟,在京师长期居住,如孙万荣就曾经到长安当过侍子。这些上层人士与汉族接触的机会比较多,他们对传统的汉文化倾慕向往,耳濡目染,文化水平得到较大的提高。
隋唐时期,接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契丹人,最典型的例子如李光弼,他是契丹酋长李楷洛之子,祖籍营州柳城。李楷洛在武则天时归附入朝,官至左羽林大将军,封蓟郡公,死后赠营州都督,溢号“忠烈”。李光粥平生喜读《汉书》,父死守孝,“终丧不入妻室”,遵从的就是儒家的孝道。在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与郭子仪齐名,可谓典型的儒将。其子李夤、弟李光进也都是汉化很深的契丹人[2]。张孝忠,《新唐书》和《旧唐书》列传都记他是奚人,“世为乙室活部酋长”。实际上乙室活是契丹部落,所以张孝忠应是契丹人。张孝忠“性宽裕,事亲恭孝”。在河朔藩镇割据之际,能够心向朝廷。贞元二年(786),河北闹蝗灾,张孝忠与部下同甘共苦,“人服其俭,推为贤将”[3]。其子张茂昭,受张孝忠影响,“约有志气,好儒书”;次子张茂宗,与公主结婚,为驸马;三子张茂和也颇有政绩。总之,张氏一门是个汉化较深、遵从儒家伦理道德的典型契丹族家庭。
安禄山、史思明祖籍营州柳城,安禄山为粟特人,史思明为具有突厥血统的胡人。二人通六蕃语言,为互市牙郎,从其经历来看,自必精通汉语,汉化较深。类似二人的各族中上层人士肯定还有很多,如大祚荣一家居于营州多年,后东走建立渤海国,也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
唐朝末年,还有一个汉化较深的契丹上层人士,即耶律阿保机的弟弟迭剌。他是契丹文字的创始者,说明他精通汉语和汉字(因契丹字是以汉字楷书偏旁为基础创制的),而且据说他能“播之以礼乐诗书”,“守之以道德仁义”,“达于理行,咸推其德”[4]。显然迭剌是一位精通儒家经典,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契丹王子。
当然,契丹、奚、靺鞨等“胡族”文化对于汉人的影响也是存在的,在社会习俗上必然会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只是由于各方面资料的缺略,难以详言。隋唐时期,汉人的华夷观念仍较浓厚,如将契丹、奚称为“两蕃”,所以不能将汉人“胡化”现象估计过高。
二、隋唐营州的胡风与胡俗
隋唐时期,各族人民虽然接受汉文化一定的影响,但在风俗习惯方面还是基本上保留了本民族的传统特色。如在文字方面,史书称黑水靺鞨“俗无文字”[5],而契丹“本无文纪,惟刻木为信”[6],即仍以刻木形式为记事手段。有关谣谚、歌诗、传说等,皆靠口耳相传,为口头文学。《隋书·契丹传》所载录的对死者祷词:“冬月时,向阳食。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就是以口头传诵形式流传到隋代。这篇祷词同时也反映出原始崇拜(包括自然、鬼魂、祖先崇拜等)仍是其主要宗教活动。
衣食住行习俗独具特色,是胡风与胡俗的重要体现。在服饰方面,髡发左衽,冬穿皮服,具有鲜明的北方民族特色。但各族也稍有不同,朝阳黄河路唐墓出土了两件辫发石俑,身穿圆领右衽长袍,与普遍采用的左衽长袍不同。男俑头发自前额两鬓向后梳起,至脑后编辫,辫上束带。浓眉大眼,注视前方,大耳下垂,颧骨突起,身穿圆领右衽长袍,腰束带。右臂屈肘,上立一鹦鹉,足系绳。左手提一前端呈圆曲状的棍子,足蹬尖头靴。女俑头发向两旁梳起,在头顶两侧梳成两髻,然后又在脑后结成发辫下垂,辫梢亦不扎结。浓眉大眼,嘴角微翘,面露微笑。身着交领窄袖长袍,腰束带,袍襟撩起系带内,露出长内衣,脚穿靴。腰带右侧佩香囊,身后亦佩两物,不识。双手置于胸前,作左手握右手拇指“叉手”状[5](1844)。从衣饰和发饰来看这两件石俑不是汉族人的形象,而是东北地区某个少数民族的形象。经过专家考证,这两件石俑属于粟末靺鞨人。
饮食方面,主要以肉乳类为主,辅之以粮食、蔬菜和水果。牲畜乳、肉及野兽野禽的肉是他们的主要食品,一旦畜牧业减产,契丹人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唐末,幽州节度使刘仁恭深谙此道。他整治契丹人的手段是“穷师逾摘星山讨之,岁燎塞下草,使不得留牧,马多死”。契丹人无奈,只好“献良马求牧地,仁恭许之”[1](6172)。
唐代高适曾经来过营州并写下一首《营州歌》:“营州少年厌原野,皮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盅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这首诗描绘了营州柳城的风物和民情,反映了胡族服饰饮食与生活方式的特色。
契丹人和奚人的居室,也与中原汉人不同。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宅,门皆东向。一直到隋唐时期的契丹人和奚人,大部分仍然是射猎居处无常,居住在穹庐中,并且居处东向的习俗一直保留到建国后。各游牧民族出行骑马,并有配备帐篷的穹庐车,以马、牛、骆驼牵引。
更具民族特色的是契丹和奚人的葬俗。契丹人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实行树葬和火葬,《北史·契丹传》载:“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这种丧葬习俗一直保留到隋唐时期。《隋书·契丹传》有相似的记载,《新唐书·契丹传》称:“死不葬,以马车载尸于山,置于树颠。子孙死,父母旦夕哭,父母死则否,亦无丧期。”奚人葬俗与契丹同,《隋书》卷84《奚传》记载:“死者以苇薄裹尸,悬之树上”。树葬又称风葬,是野葬习俗的一种形式,在北方信仰萨满教的诸民族中广为流行。
当然,唐代中期以后,北方诸族深受汉文化影响,葬俗也在逐渐发生改变,尤其是迁入营州柳城附近居住的契丹、奚、靺鞨等族。如目前在朝阳发现的孙则墓、杨律墓、骆英墓、高英淑墓、尼大光明墓都是汉化很深的契丹人墓葬[7]。另外,在营州边远地区的诸游牧民族也在悄然改变,契丹等族人先树葬,后火葬,最后土葬。在内蒙古的乌斯吐,曾发现一座土坑火葬墓,其年代约相当于唐代中前期。这座墓葬墓底堆放着骨灰和木柴灰烬,烧过的骨灰上盖有几层桦树皮,并以铁刀、铁匕、磨刀、陶罐、陶壶为随葬品,该墓被断定为契丹人火葬墓[8]。在内蒙古的科左后旗呼斯淖发现一座土坑竖穴墓,年代约为唐末。该墓以羊骨架、陶器、铁器、铜镜为随葬品,陶器中有一黑陶鸡冠壶。此墓主人可以定为契丹人[9]。契丹建国之后,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古老的树葬风俗遂逐渐消失了,普遍代之以土葬。
三、隋唐营州的葬俗
(一)隋唐营州墓葬的基本情况
墓葬的基本情况从以下几个方面分类说明:(1)从数量上看,据不完全统计,隋唐墓葬有200余座,近年来不断有新的发现,可谓数量极丰;(2)从分布地区上看,主要分布于朝阳市及周围地区;(3)从墓葬年代上看,绝大部分为唐墓,隋代墓葬只有贾善墓(开皇二十年,600年)和韩暨墓(大业八年,612年)等数座。唐代墓葬只发现一座安史之乱时期的墓葬——杨涛墓,下葬时间为公元761年,安史之乱以后的则没有发现;(4)从建筑材料上看,以砖室墓为主;(5)从建筑结构来看,以单室墓为主,墓道较短,墓室北壁或西壁有砖砌棺台;(6)从墓室大小来看,基本都是中小型墓葬,较大的有孙则墓,墓室长5.2米;(7)从墓室的平面形状来看,有方形、圆形、梯形墓,其中以圆形墓居多;(8)从随葬品来看,既有典型的中原输入的物品,也有区域特色和民族特色比较明显的随葬品。比较特殊的是朝阳地区墓葬中经常出土如墓龙、仪鱼、观风鸟等怪兽。这在中原地区的唐墓中很少见。
(二)隋唐营州墓葬与中原地区墓葬的比较分析
总体来看,中原地区处于唐王朝直接统治地区,墓葬具有较强的规范性、等级性和一致性,而朝阳地区则不同。
第一,在墓葬规范性方面,中原唐墓因社会等级的不同对应不同的墓葬类型。而营州地区地处边疆,多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影响,墓葬逐渐超越丧葬制度的束缚,墓葬规模越来越大。所以墓葬规模的大小并不代表官位的高低,这种现象具有营州地域特色。
第二,在墓葬外观形制方面,中原唐墓的墓室以弧方形、方形为主,终唐一代变化不大。而朝阳地区的唐墓在隋唐前期,也以弧方形和方形墓为主,但到了唐代中期以后,则以圆形墓为主,弧方形和方形墓消失。这种圆型和梯形墓葬具有鲜明的营州地域特色。
第三,在筑墓材料方面,朝阳唐墓不论墓主人社会地位高低均以砖砌为主,而在中原唐墓中,砖室墓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只有高等级墓葬才用砖砌筑,低级官吏和庶人一般用土洞墓。
第四,朝阳隋唐墓葬体现出较多的民族文化因素。营州地区有契丹、奚、靺鞨、高句丽、突厥等民族,因此营州地区的墓葬形式多种多样。其中弧方形墓和中原地区汉人墓葬保持一致,但墓主也不都是汉人,孙则、杨律、骆英、高英淑、尼大光明都是汉化很深的契丹人。圆形墓和梯形墓则是具有地方特色的墓葬形式。墓葬的随葬品中有铜铃,有的铃上铸有“日”字形纹饰,这与朝阳地区的鲜卑墓葬文化有很大的一致性,很可能是鲜卑族系契丹人或奚人的墓葬。朝阳地区墓葬随葬品中比较特殊的是经常出土如墓龙、仪鱼、观风鸟等怪兽,这也具有少数民族特色。
上述研究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而关于隋唐营州社会习俗方面的研究,比如婚姻习俗、节日习俗等问题,也有许多领域需要探究。
参考文献:
[1]欧阳修.新唐书·契丹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172.
[2]欧阳修.新唐书·李光粥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4597.
[3]欧阳修.新唐书·张孝忠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4769.
[4]李逸友.辽耶律琮墓石刻及神道碑铭[M]//东北考古与历史编辑委员会.东北考古与历史(第1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181.
[5]薛居正.旧五代史·黑水靺鞨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6:1844.
[6]王溥.五代会要·契丹[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457.
[7]田立坤.朝阳的隋唐纪年墓葬[M]//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122.
[8]哲里木盟博物馆.内蒙古哲里木盟发现的几座契丹墓[J].考古,1984(2):153.
[9]张柏忠.科左后旗呼斯淖契丹墓[J].文物,1983(9): 18.
(责任编辑单丽娟)
Yingzhou's National Am algam ation,Style of Northern Barbarian Tribes and Burial Custom in Suiand Tang Dynasties
XIAO Zhong-chun (College of Politicsand History,BohaiUniversity,Jinzhou 121013,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period of Suiand Tang Dynasties,multiple nationalities,including Han,Khitan, Hu (the northern barbarian tribes),etc.,promoted the national amalgamation in the region of Yingzhou.In particular,Hu peoplewere greatly influenced by Han's culture,butstill remained their own national style in food,clothing,shelter and transportation.The tombs ofpeople in Yingzhou,which are circular in shape and quit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people in Central Plains in ancient China,tend to be large-scaled despite the socialstatusof the tomb owners,which strongly reflects Hu's culture.
Key words:Yingzhou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national amalgamation;style of the northern barbarian tribes;burial custom
作者简介:肖忠纯(1969—),男,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副教授,从事东北民族史、历史地理研究。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隋唐至明清时期大凌河流域移民与城市发展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L15BZS003)
收稿日期:2015-10-12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254(2016)01-002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