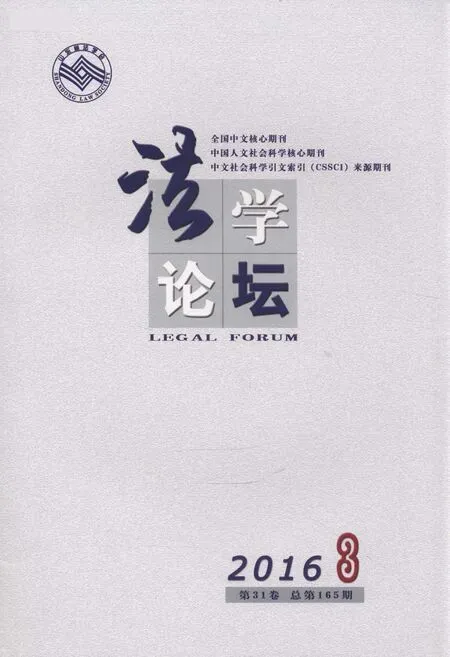破解暴力型精神病人管束困局刍议
——基于三部法律联动的视角
2016-12-16潘侠
潘 侠
(中国海洋大学 法政学院,山东青岛 266100)
破解暴力型精神病人管束困局刍议
——基于三部法律联动的视角
潘侠
(中国海洋大学 法政学院,山东青岛 266100)
摘要:尽管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刑事诉讼法》《精神卫生法》中均涉及精神病人问题,但并未使暴力型精神病人的混乱管束状况有大的改观。以“强制医疗”作为应对该特殊群体的主要举措是必要的,也具备正当性,但要使其发挥实效,当前条块分割、分类管理的方式并不足取。在程序之外,填补促使程序发挥价值的实体内容,建立统一的强制医疗输入、输出的机制,实现司法裁决,明确各方职责,完善社会保障,才是破解困局之正途。
关键词:暴力型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强制医疗所;强制医疗解除
“精神病”在近几年是个醒目的字眼。由精神病人制造的广西南平血案、云南大火案、北京家乐福超市持刀行凶案以及陕西男童遭受暴打案等,件件触目惊心,让人猝不及防。据报道,截至2009年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重性精神病患已超1600万。*参见陈泽伟:《研究显示我国精神病患超1亿 重症人数逾1600万》,载《瞭望新闻周刊》2010年5月29日。精神病人已然成为我国社会治安防控中不可忽视的对象。2015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做好对易肇事肇祸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服务管理工作,加强治安防控网建设。在此背景下,探索管束该特殊群体的具体方案对完善当前社会治理、创新治安管理工作具有积极意义。
一、暴力型精神病人的界定及管束概况
暴力型精神病人,俗称“武疯子”。严格来说,它并非精神医学上的特定称谓。“精神病”在临床医学上的规范表达是“精神障碍”。*为方便读者理解,本文依然采用约定俗成的称谓,即“精神病人”。所谓精神障碍,是指具有诊断意义的精神方面的问题,特征为认知、情绪、行为等方面的改变,可伴有痛苦体验和(或)功能损害。*参见郝伟、于欣主编:《精神病学》(第7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就精神医学的观点来看,它是个类概念,泛指各种由于大脑功能失调而产生的情感、意志、认知、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障碍,并以此为主要表现的一类疾病的统称。*参见黄丁全:《刑事责任能力的构造与判断》,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44页。根据病因学和症状学兼顾的分类方法,世界卫生组织编写的在国际范围内受到广泛认可的《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简称“ICD-10”)将精神障碍分为十个大类,并又依次罗列出对应的各亚类。从精神症状以及既发案例来看,有些疾病患者极易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例如,精神分裂症、持续妄想性障碍、双相情感障碍、反社会型人格障碍、(中度及轻度)精神发育迟滞等。这些患者往往易冲动、暴躁,有的存在被害妄想,敏感、多疑,具有攻击性,极易借助刀、斧等钝器实施极端恶性的伤人、毁物行为,给他人人身安全及社会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危害。因人类大脑活动的复杂性和医学探索手段的有限性,在精神医学实践工作中,只有10%左右的精神障碍病例的病因、病理改变比较明确,而 90%左右的病例则病因不明。*参见郝伟、于欣主编:《精神病学》(第7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版,第43页。加之有一些患者的精神病症很难在既定的分类系统中找到对应的医学名称,而只能被概称为“其他精神障碍”或“待分类的急性短暂性精神病性障碍”,*沈渔邨主编:《精神病学》(第5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年版,第1025页。但从司法精神病鉴定实例上看,此类患者又极易产生暴力侵害行为。所以,精神医学并不能提供现成的为我们所关注的“武疯子”的范围。本文以“暴力型精神病人”统称之,旨在通过对行为人的关键特征加以突出强调,表明研究对象为具有攻击性、易实施暴力行为而侵害公共安全或公民人身安全的精神病人。按照对社会造成危害的严重程度,暴力型精神病人在我国被区分为“肇事”精神病人(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和“肇祸”精神病人(行为触犯了《刑法》)两种。实现对这些患者的妥善管理是我国社会治安防控建设的重要环节。
据统计,1998年至2010年,我国安康医院累计收治肇事肇祸精神病人4万余人次,其中严重肇事肇祸的占30%,*参见张向宁:《强制隔离戒毒所、安康医院、戒毒康复场所的现状及未来》,载《人民公安报》2010年3月18日。给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严重危害。目前这些患者的数量仍在激增。但是,与精神病患数量不断攀升的强劲势头相比,我国对暴力型精神病人的监管却未能同步跟进,以致乱象丛生。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法律规范的不统一,另一方面则因既有的法律规定不明晰、配套机制不完备。
2012年之前,《刑法》仅在第18条提到,“对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在必要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细化规定,致使各地自行其是,做法纷呈。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宁波、无锡、武汉等地陆续出台了地方性的精神卫生条例,另有《天津市收治管理危害社会治安精神病人办法》《青岛市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管理治疗规定》《吉林省危害社会精神病人强制医疗若干规定》等。虽然这些地方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管理流程作了回应,但多数省市没有明确的操作规程。实践中,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进行管理治疗的安康医院在全国仅有24家,几近饱和的收治现状和安康医院所负担的治疗与维护社会治安的双重任务已使其再难承重负。所以,对于肇事或肇祸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除少数由政府予以强制医疗外,多数仍交由家属看管。由于不少精神病人家庭生活困难,在高昂的治疗费用面前,家属只能望而却步。而且,鉴于家属可对患病者实施监控的手段及监管精力都极其有限的现实原因,为防止病人出去招惹祸端,家属不得不对精神病人动用私刑,采取简单粗暴的羁押式看管,一关了之。有的家属干脆对病人不管不问,任其流落街头、在社会上游荡,放任精神病患者再次危害社会的行为发生。即便部分患者能够依照地方出台的这些规范性文件而被移交隶属于公安机关的安康医院接受强制医疗,有关送治和治疗环节的规定也相当粗放,加上地方规范性文件因有违《立法法》的法律保留原则而时常遭受合法性的质疑,暴力型精神病人在我国并未获得规范有效的管控。媒体频频曝光的“武疯子”事件恰是我国对这类特殊群体监管乏力的有力映照。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增加“强制医疗程序”规定,新出台了《精神卫生法》,以期通过规范强制医疗的方式为患者和民众带来福音。然而,两部法律施行至今亦未见我国暴力型精神病人的管理取得太大的进展,精神病人肇事肇祸事件依旧频发。据某学者统计,2013年7月仅媒体报道的疑似精神病人实施的暴力案件就高达10起。*参见张品泽:《强制医疗程序的实施与反思》,载《中国司法鉴定》2014年第1期。与此同时,学界围绕立法内容的适当性、确定性及体系的完整性提出了诸多批评意见,如强制医疗适用条件不明确、适用范围过于狭窄、检察监督可行性差、被强制医疗人的救济渠道不畅、两大法律互动性弱等,并认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拉低了这两部法律的实际价值。因此,继续修缮法条、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被视为解决暴力型精神病人管束问题的不二之选。笔者对此表示赞同。然而,在着手解决问题之前,务必要明确,把患者控制住不是最终的努力目标,在消除社会隐患的同时,促进患者复归社会才是根本目的。相应的,在破解暴力型精神病人管束难局的制度建构中,需秉持统筹的思想,既要从宏观上实现法律规范的统一适用,又要着眼于微观,查明导致管理不畅的症结并逐个击破,后者相较于前者更需要花费大力气。因为当前我国的强制医疗问题重重,除了在强制医疗的输入环节上,作为被强制医疗患者接受监管、治疗基本保障的执行场所和确保患者获得良好医疗服务的经费的承担主体及方式含混不清外,在输出环节,我国亦缺乏可操作的强制医疗解除标准以及患者复归社会的应对机制。这些障碍攻克不了,困局将很难破解。为此,本文将围绕强制医疗建构针对患者的输入、输出机制,形成良性的循环路线图,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入手破解暴力型精神病人的管束难题。
二、强制医疗的输入机制于破解管束困局之效用
暴力事件的发生虽然在客观上表现为精神病人的行为举动,但其系病理所致,行为人很难对行为的性质、意义有清晰的认识。在此情形下,依靠传统的惩治违法者或犯罪者的方式如教育、罚款、监禁等无益于再犯的避免,有效的防范举措是控制病情。因此,通过特定的机制让患病的行为人能够得到治疗是破解管理难题的首要步骤。
(一)强制医疗的门槛设定
2012年《刑事诉讼法》明确了《刑法》第18条提及的强制医疗的程序,但同年颁布的《精神卫生法》仅规定了“非自愿住院治疗”,*参见信春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89-91、100-101页。没有涵括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管理的内容。至此,我国暴力型精神病人被人为分成若干类并在《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精神卫生法》中被施以不同对待,分别为:第一,对于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进行强制医疗;第二,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有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等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时,不予处罚,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第三,患者被诊断为严重精神障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83条第2款规定,所谓严重精神障碍,是指疾病症状严重,导致患者社会适应等功能严重损害、对自身健康状况或者客观现实不能完整认识,或者不能处理自身事务的精神障碍。者,并具有“已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等情形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患者本人或其监护人对诊断结论有异议,而所要求的再次诊断依然持相同结论时,其可自主委托具备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医学鉴定。如果鉴定意见与前两次诊断相同而监护人仍然对住院治疗实施阻挠,或患者擅自脱离住院治疗的,公安机关有权介入并协助医疗机构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此即《精神卫生法》第30条第2款第2项、第32条及第35条规定所表达的内容。换言之,在应对精神病人暴力事件上,我国存在三种法定方式:通过司法裁决施以强制医疗;经由行政化手段交由家属看管、治疗;基于医学诊断或鉴定而开展非自愿住院治疗。
划定《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调整范围的主要依据是行为的性质,即是否达到入罪的要求,而罪与非罪的具体评判又涉及构成要件的考量。这是我们将两部法律加以区分所遵循并认可的基本逻辑。对罪与非罪的行为分别加以规制,一方面有利于明确执法者的权限,另一方面在于当无法遏制行为人的违法行为时,引导其能理性地选择对社会及他人最小危害的方式,从而避免最严厉的刑罚处罚。但对于患精神病的行为人而言,其既无力正确认识现行的法制度,也无法自如地选择其行为方式,更不能控制行为的后果。将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与行为及其后果相结合作为处罚依据的常规处理思路在意志不自由的精神病人面前根本行不通。精神病人实施危害行为完全系精神疾病所致,所以对症下的“药”只能是对患者进行治疗,而非通过惩罚末端的行为以期倒逼其适法而行。所以,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如何治疗。是强制医疗,还是交由家属看管、治疗,抑或其他方式?《治安管理处罚法》选择交给家属看管、治疗,《刑事诉讼法》则要求强制医疗。区别对待的主要依据仍在于对行为及其后果的判断。这里隐含了一个被认可的前提,即行为的危害性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呈正相关,由此决定有无接受强制医疗的必要。但笔者认为,二者不具有必然的因果联系。行为造成怎样的危害后果完全是概率事件。一旦确认行为人是暴力型的精神病人,就需采取对应的措施,防止危害扩大。加之现实中将患者交由家属看管、治疗收效甚微,所以无论危害行为怎样,一视同仁对待尤显必要。另外,《精神卫生法》规定的非自愿住院治疗的条件较为笼统,其旨在对《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之外的情形进行兜底,但实质上并未起到应有的效果。且不论《精神卫生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在规制内容上模糊不清,这也为有权机关选择性执法打开了方便之门,即绕过审查相对严格的司法程序而改为采用行政或医疗模式对患者采取强制医疗措施。
为防止公民“被精神病”而导致人权受损,也为避免患者得不到应有的治疗而引发更为严重的危害行为,有必要将上文所述三种违背患者意愿的治疗均纳入司法的轨道,并适用同一的准入门槛:即行为人具有严重的精神障碍,且发生了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并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在此当中,患者的人身自由权将不仅多了重司法保障,其还可获得诸多程序性权利,如接受司法鉴定、获得律师帮助及公平听审的机会、对证据材料进行举证、质证等。借由司法及其程序的约束,限制患者人身自由的强制医疗措施才可能不被滥用。当然,考虑到危害行为的严重程度与行为人人身危险性有一定联系,当行为未达到犯罪程度时,可适当简化收治程序、相对降低治疗期间对看管的严密程度的要求等,但强制医疗交由司法裁决的做法不容挑战。
(二)强制医疗的核心要素
强制医疗的门槛,主要解决能否“强制”的问题。当一切程序性规定为涉案人的人权提供层层庇护后,被推送到强制医疗体系中的精神病人,即将接受的对待是获得治疗。这是制度的根本,也是实现患者回归社会之最终目标的重要保障。由此,其必然绕不开两大核心要素——治疗的场所和经费。
1.强制医疗的场所。 关于强制医疗的场所,《刑事诉讼法》称之为“强制医疗机构”,但未指明具体所指。《精神卫生法》中非自愿住院治疗的场所为“医疗机构”,要求具备开展精神障碍诊断、治疗所需的精神科执业医生及护士、必要的设施和设备、完善的管理制度和质量监控制度,*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25条。既可以是精神病专科医院,也可以为符合前述资质的有精神科室的综合性医院。在此之外,公安部于2012年已开始起草《强制医疗所条例》,目前送审稿已提交国务院法制办审议,并在进一步征求意见中。该条例明确指出,“强制医疗所是强制医疗决定的执行场所”。*参见2015年《强制医疗所条例(送审稿)》第2条。尽管该条例处理的是刑事强制医疗的场所问题,而笔者主张扩大强制医疗的范围,不限于触犯刑法的精神病人,但对于场所的探讨具有共通性,故忽略其适用范围而放在此处一并讨论。概括起来,我国患者能够接受治疗的场所有:强制医疗机构、强制医疗所、医疗机构。但强制医疗所该如何定位,是否就是所指的强制医疗机构?它是一个全新的、待规划落实的强制医疗专属场所,还是对现有医疗资源的整合或改建利用?
自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因强制医疗场所指向不明,实践中做法比较混乱。有的仍交由当地负责处理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治疗工作的安康医院。但因全国仅24所安康医院,所以,有不少地方将经过司法程序的患者转到了普通的精神病院。然而,医院专司治疗,其没有强制性监管患者的权限,该权宜做法终非应对之良策。放眼域外,意大利设有六所专门对触犯刑律的精神病患者进行治疗的司法精神病院。日本则在《精神保健福祉法》外于2003年另颁行了《心神丧失等状态下造成重大伤害行为者的医疗和观察法》,并为此建立了由保护患者权益者、精神保健医师、精神保健审判员及参与者、指定医疗机构、保护观察所等组成的运作体系,强化了对患者自由的限制,以达到预防精神病人实施严重危害行为的目的。其中,指定的医疗机构是由国家和政府之外的人开设的精神病医院。只要其符合国家规定标准,医院的全部或部分可被指定为强制医疗场所。另外,德国柏林设置了隶属卫生行政部门的专门安置触犯刑法的精神病人的强制治疗医院,实行与监狱相仿的封闭式管理 。*详见信春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462、465、473页。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于经过司法干预的强制医疗而言,治疗的场所不仅要具备医疗条件,同时还需承载监管患者以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功能。因强制医疗既包含医疗的实质内容,同时还是法律中的一项执行行为,所以与普通的精神病院有别。在我国强制医疗场所设定上,有必要强调场所的双重属性,实现治疗与监管并重。至于场所的具体设置,是概称“强制医疗机构”也好,是划出特定的区域专称为“强制医疗所”也罢,利用既有的司法资源以及整合社会医疗资源是加快安置强制医疗患者、避免大规模兴建医疗机构的最低成本之法。笔者的基本设想是,将安康医院列为专门的强制医疗场所的一部分,对某些社会性医院进行全部或部分改造,使其符合监管的条件。鉴于目前法律规定不明,在强制医疗场所就绪后,为扫除其行使监管职能面临的合法性质疑,尚需法律的明确授权。
2.强制医疗的经费。 治疗的费用是强制医疗制度行使中面临的又一个现实问题。据了解,在医疗设施较好的精神病院,一个严重精神障碍者平均每月的住院费用约五六千元,整个治疗流程总费用可高达十几万元。即使就诊条件一般的精神医疗机构,每位患者一年的医治费用也需一万元左右。*参见潘侠:《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法治化研究——从中美两国对话展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9页。加之精神类疾病医治周期长、复发率高、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患者数量与日攀升,医治费用将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新《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并未提及费用问题,而《强制医疗所条例(送审稿)》第11条则规定,“强制医疗所经费开支单立账户,其修缮、工作人员费用、被强制医疗人员治疗、生活等所需经费开支,纳入本级政府财政保障”,意在将医治费用交由地方财政负担。在《精神卫生法》出台前,各地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医治费用基本采取的是由医保、患者及其家属、政府或其民政部门依次负担的方式。例如,青岛市关于《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管理治疗规定》指出,患者有工作单位的,医治费用按照公费医疗、劳保医疗规定负担;无工作单位的,由监护人及其亲属负担,其中,如病人系本市职工供养的直系亲属的,可由职工单位报销部分费用;当以上条件均不满足时,如患者具有本市常住户口,但没有生活来源、无依无靠的,由民政部门负担。*参见青岛市《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管理治疗规定》第10条。吉林省颁布的《危害社会精神病人强制医疗若干规定》也作出了类似规定。*参见吉林省《危害社会精神病人强制医疗若干规定》第15、16条。
抛开这些文件本身的合法性问题不论,就实践来看,由政府全部负担强制医疗费用的做法并不多见。笔者认为,在暴力型精神病患者基数庞大的当下,治疗费用的来源应予多元化,以避免强制医疗国家干预后给财政带来过重负担而影响强制医疗制度的长期有效贯彻执行。根据近些年的医改动向,在某些省市,一些常见的精神疾病已被纳入大病医保的范围。*例如《山东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工作实施方案(试行)》中认可的病种有“重性精神疾病”,具体包括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精神障碍、偏执性精神障碍、双相(情感)障碍、癫痫伴发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等疾病类型。另外,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意见》明确要求以发生高额医疗费用作为“大病”的界定标准。这些改革均为强制医疗费用多方负担方式的实现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本文建议,在患者接受强制医疗期间,每一工作年度的费用应首先由医疗保险承担,其余部分则纳入各级财政预算,由国家统一定额拨付。患者家属或监护人如要求自费为患者提供更高标准医疗的,由强制医疗主管部门进行核查,符合患者医疗利益时应予准许。当患者既无医疗保险、家属也无能力为其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时,由强制医疗机构在国家财政拨付范围内为患者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在此,有个实际问题需加注意,即依照相关医保政策,患者只有在出院时才能到定点医疗机构进行结算,从而享受医疗保险补偿。但精神病人治疗周期普遍较长,医治费用如长期不到位,医疗机构恐无力承受。建议采用分阶段报销方式,以确保医疗机构正常运转。
三、强制医疗的输出机制于破解管束困局之效用
完备的输入机制是激活强制医疗制度的基础,而输出机制则是强制医疗持续发挥制度价值的重要保障。在解决暴力型精神病人管束困局中,不能以找到应对之法即将患者交付“强制医疗”就万事大吉,为接受治疗的患者找到适当的出口也是防止医疗资源供不应求、破解困局的重要一环。
(一)强制医疗的解除
在强制医疗解除方面,根据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280条的规定,强制医疗机构认为被强制医疗人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接受强制医疗的,应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报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批准,即司法裁决解除方式。《精神卫生法》第44条关于出院的规定中,要求对于非自愿住院治疗的患者,医疗机构应及时组织精神科执业医师对其进行检查评估,评估结果表明不需要继续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应立即通知患者及其监护人,即医生单方决定解除的方式。鉴于被医治的患者非普通的精神病人,而是具有暴力倾向、易对他人或社会造成危害的精神病人,为避免草率决定而致不符合解除条件的精神病人流入社会再次致害,也为防止满足解除强制医疗条件的患者因医生滥用权限而侵犯患者本该享有的结束强制医疗、重获自由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在解除的裁决环节引入中立的第三方机构。对此,联合国《保护精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保健的原则》(以下简称《原则》)明确指出,“非自愿住院的患者可按照国内法规定的合理间隔向复查机构申请出院或自愿住院的地位”,或者“负责病情的精神保健工作者在任一时候确信某一患者不再符合非自愿住院患者的留院条件,应给予指示,令患者不再作为非自愿住院患者继续住院”。其中,复查机构是依国内法设立的司法或其他独立和公正的机构,负责审查患者非自愿入院及出院事宜,其“在作出决定时应得到一名或多名合格和独立的精神保健工作者的协助,并应考虑其建议”。根据《原则》的精神,解除强制医疗既倚重医疗人员对患者病情的专业诊断,也需要特定的机构对继续强制医疗与否作出最终裁断。为患者应否出院这一本属于医学领域所司事项另加一道过滤程序,旨在对患者的自由权利、附带的医疗福利与社会利益进行权衡,尽量将解除强制医疗后患者可能给社会造成的危险降到最低。由与治疗机构无利害关系的中立机关肩负最终的裁决工作,不仅是对患者权益的保障,其超然的形象也有助于提升裁判的公信力。笔者赞同解除环节依此而设。
在我国,强制医疗的解除宜统一交由人民法院裁决,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人民法院有无能力对患者是否满足强制医疗的解除条件——“已具备辨认、控制能力,不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会再危害公共安全或他人人身安全”作出恰当的判断?对人身危险性的评判目前仍缺乏一个确定的、可量化的指标体系,仅能借助就诊期间患者病情的进展、定期诊断评估的情况以及就诊前其一贯的行为表现等相关因素进行盖然性判断。其中,患者的病情状况无疑是最具含金量的一项衡量指标,而其只能由专业的治疗医师进行提供。虽然病情与人身危险性二者呈现的不是绝对的正相关,但如果患者痊愈,其人身危险系数通常被认为归零,人民法院作出解除强制医疗的决定也就相对容易。但如果患者并未痊愈,只是病情有所缓解且状况相对稳定,而治疗医师认为此情况下患者不再具有人身危险性时,实践中人民法院往往会碍于精神病易反复的特点,担心解除强制医疗后患者再次发生暴力行为,而使其作出的裁决遭受质疑并因此而担责,所以人民法院不会贸然作出解除决定。这无疑会堵塞强制医疗的出口。在笔者看来,人民法院作为外行,根本无力对医生提供的诊断评估意见进行实质审查。它存在的价值并非对患者的精神状态作最终的权威认定,而仅是确保强制医疗能够规范运行的“监工”。如在医疗机构未提出解除意见时,患者本人或其近亲属可向法院提出解除申请;或者,当医疗机构要求解除强制医疗时,从形式上审查其定期评估报告的制作是否合规,检查的事项是否全面,解除意见书的说理是否清晰、明了等。对于专业的医学问题,则交由专家辅助人把关。经审查如符合要求,人民法院就应采纳医疗机构的建议,准许解除强制医疗。当然,将解除决定机关作此定位的一个重要支撑在于强制医疗解除后应对机制的完备。否则,决定机关先前的担忧仍将存在,解除决定的作出也不会顺畅。
(二)强制医疗解除后之应对
精神病人一旦进入强制医疗场所,往往很难被解除强制医疗而回归社会。主要原因除了上文提及的决定机关怕担责而极少批准外,患者家属或其监护人也常以无能力、无精力照看结束强制医疗的患者为由,拒绝将患者领回。所以,在强制医疗输出环节,必须构建配套的输出之后续机制,以保证整个强制医疗流程有条不紊。
关于强制医疗解除后的处理机制,一些文件有所涉及,如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法院、公安局2012年联合印发的《关于强制医疗程序的实施办法(试行)》第28条规定,安康医院在接到解除强制医疗决定书后,应当立即通知被强制医疗人的近亲属将其接回,无法通知或者近亲属拒绝接回的,应当通知原送交执行的公安机关接回妥善处理。此外,2012年北京市公安局颁行的《办理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案件程序规定(试行)》第28条规定,当被强制医疗人无监护人、近亲属的,无法通知或者其监护人、近亲属拒绝办理出院手续时,由办案单位办理相关手续,将被强制医疗人接回妥善安置。2008年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措施管理办法(试行)》第15条均有类似规定,当监护人、近亲属拒绝办理出院手续时,由被强制医疗人实际居住地分(县)局办理并将患者接回交给其监护人或者近亲属;无监护人或者近亲属、又无生活来源且无劳动能力(简称“三无”)的患者,由实际居住地分(县)局将其接回妥善安置。然而,这些文件皆以“妥善安置”一笔带过,查找不到任何与此相衔接的制度设计。虽然有关强制医疗问题的最新文件《强制医疗所条例(送审稿)》第43条提到,“对被解除强制医疗的人员,强制医疗所应当通知监护人、近亲属的户籍地或者居住地社区卫生机构和公安派出所”,但仍缺乏可操作性的规定。
在强制医疗制度体系完善中,笔者认为,设计清晰的解除强制医疗后之应对路径应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总体的建构思路应为:统筹公安、卫生、民政、残联等部门,明确各自在患者回归社会中的职责。具体而言:首先,确定监护人。为方便对患者进行跟踪管理,在解除强制医疗时,应由监护人到场办理相关手续。监护人的确定按照我国民法的规定进行。对于“三无”的患者,应由民政部门给予救助,具体由民政部门所属的精神卫生机构进行接收。监护人因经济原因而无力照管时可向民政部门及残联申请救助,残联可采取向患者免费发放巩固治疗的基本药品等措施。对于无理由拒不承担照管义务的监护人,可赋予强制医疗裁决法院扣押监护人部分财产的权力,由法院有偿选任他人照管患者;其次,公安建档。由负责各片区的民警为被解除强制医疗的人建档,定期跟踪、随访,及时掌握其动向;再者,将患者纳入《精神卫生法》规定的社区康复体系,实现与精神卫生法制度的对接,达到资源共享。在卫生部门主导下,完成患者向社会的过渡。唯有建立环环相扣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管束困局方可疏解。
[责任编辑:谭静]
收稿日期:2016-02-26
基金项目:本文系青岛市博士后应用研究项目《刑事法视野下的强制医疗适用研究》(201482214249)、中国法学会2015年度部级研究课题《刑事强制医疗执行实践考察与探索》(CLS(2015)Y24)和中央高校青年教师科研基金项目“破解暴力型精神病人管束困局研究”(20141303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潘侠(1986-),女,河南济源人,法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讲师,研究方向:刑事法学、证据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003(2016)03-0112-07
Subject:Discussion on Breaking the Dilemma as to Manage the Violent Mental Patients —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nnecting Three Laws
Author & unit:PAN Xia
(Law & Politics School,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Shandong 266100, China)
Abstract:Although the Law on Penalties for Administr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in China involves mental patients' issues as well as the Criminal Procedural Law and the Mental Health Law, which two laws were enacted in 2012 one after another, there is little improvement to change the messy situation towards the violent mental patients' management. The involuntary medical treatment, which is chosen as a major response to deal with the tough thing, is necessary and legitimate. But to make it effective, the current mode of separate management is undesirable. It is the right path to crack the problem by perfecting the existent procedure, filling the substantive contents which can realize the procedure's value, establishing the uniform input and output mechanisms of the involuntary medical treatment and adjudicating by justice,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 opportunity of enforcing laws selectively is eliminated for law-executors.
Key words:violent mental patient; input mechanism; output mech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