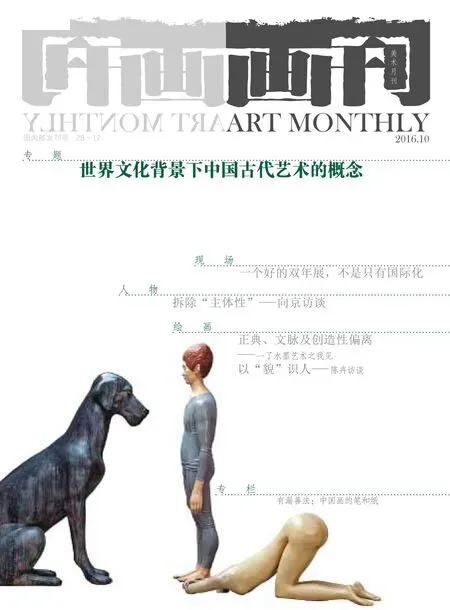正典、文脉及创造性偏离
——一了水墨艺术之我见
2016-12-08岛子
岛子
正典、文脉及创造性偏离
——一了水墨艺术之我见
岛子
在文化代群上,一了(朱明)属于“60后”艺术家,除了这一重文化身份,他还是一位结庐嵩山的禅者。一了曾在青年时代拜师禅门,修习佛法并钻研书法。20世纪90年代初期游学中原,转益多师,从事现代书法的理论与实践,不久则以其独特、鲜明的书风自成一家而鼎立书坛。
2004年,一了作为书法艺术家受邀日本文部省访学,此间,他和日本著名批评家海上雅臣结为知遇师友,亲炙井上有一书道,并深受启发,创作观念水墨“囚”。通过“囚”系列的创作,一了的水墨发生了脱骨换胎的变化,迅速摆脱了流行书风、抽象水墨影响的纠葛。

《语世》系列 一了 纸本水墨、丙烯 180cm×90cm 2010年
穿越书写、冥想和行动,一了的“囚”是一种冥化的书写,或谓书写的冥化。与当代艺术时下所标榜的“转换”不同,冥化是一个消除特定界限的过程。世界无所不“囚”——社会、人际、体制、性别,人生之生老病死、爱恨情仇,各有所“囚”。“囚”的象形隐喻在更广阔的境域中呈现出本来面目:大死大生、勘破生死即为冥化。以此理喻,《囚》是一个霹雳书写事件,它横空迸发,崩坏庸见陋习;它所昭示的生命的动能、流变之道,使书写本身回归书道正见,颠覆观念法则和形式法则,因此而获得一份额外的活法、额外的值域。诚如《圣经》所言:“那召你的本是信实,必成就这事。”
理解一了的艺术,断然不可脱离禅学。禅学正典认为:世界是流变不居的,而艺术应该是此运动的一部分,所谓“随处做主,立处皆真”。非二元性是禅的基本面貌和奥秘,慧能临终时传授三十六诀:“举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法,出没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性相。若有人问法,出语尽双,皆取法对,来去相音,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坛经校释》)其要义是以相对的、有无穷组合的两极来破除“我执”和“法执”,表面上不合理的最终仍有自己的逻辑,面对现象可以直觉、直观,不受对比规则的拘束,直指人心。传统的对比诸如意识/无意识、前景/背景、书写/涂绘、书旨/画诀、艺术家/素材、心智/身体、实物/虚空、艺术家/作品/观者、主体/客体,以及水墨的画科分类山水、人物、花鸟等,并不必然是相互分离或对立的,习惯性思维不敢超越对比,只是因为想象不能。
禅的非二元论思想,促成了不同类别的可能性融合、互补及折叠。而二元论的排他性与限定性,限制了自由与统一。
自达摩以降,在禅的诸多门派中,临济禅显然与艺术之间关系较为密切。冥想给予禅艺术灵感,而冥想的经验也在艺术中自然呈现出来。所以,禅及禅学不是一种仪式化、体制化的宗教,亦非纯粹的哲学,更多的是一种宗教哲学、一种方法论、一种人间智慧。禅的艺术表现方式,是关照式的、境界式的、启悟式的。但自由是禅的主要目的之一,缘此之故,禅乃自性清明、幽微之处的光明。
继之观念水墨“囚”系列,一了在2010年之后持续创作了《语世》系列。在此系列水墨绘画作品中,老虎作为灵兽的形象,生成了层出不穷的变体,演绎出无界限与周遭空间关系。灵兽在此是一个意蕴丰满的复合体,天地兽人鬼神,寓万于一,以少胜多,灵兽即艺术家主体之“独化”、主体性大化于灵境。
从风格来源看,老虎-灵兽的意象造型博采众长,有汉代画像石刻动物形象的灵动和神秘,也兼有摩崖石刻、石窟造像、史前岩画及草根民艺的有机综合与萃取。犹如《山海经》演绎的妄想怪诞世界,一了的笔下奔涌着横飞的翼虎、犄角鹿虎、鬼脸虎、虎头人身、人面虎身、虎神、虎身佛、虎王、虎群……林林总总,千奇百怪。从图像符号来说,艺术家凭着天才的想象力,借由老虎-灵兽之想象,构造了一个包罗万象的能指链,混沌的自我、社会畸变、隐遁的神迹,在非存在关系中,得以鉴别、澄明和启悟。
一了笔墨涵养的书写性,在其水墨语言中起到了意象造型的关键作用。
古典画论倡言“书画同源”“骨法用笔”,实际上是以书法墨线的运动态势、行笔力量及偶发笔触,随机营造意识和潜意识中的“象”,立象以尽意。从一了绘画的书写性,可以看到一种雄肆、浑厚、老辣、遒劲的汉魏碑学格调,还有民间书写不可遏制的放达、率性、变形。当其用之于绘画,一则放大了非文人书画的拙稚和奇趣;二则假借篆书、草书章法结构自由处理图形、图式,往往以倾斜、扭转、繁密、连缀一气呵成大块,自然天成,痛快淋漓。
一了的灵兽有灵气而常带有几分稚气、喜气、野逸之气,所谓“语世”,既关照人心世相,“知神奸、明戒鉴”,远离颠倒虚妄,疏离语言暴力,不合流、不粉饰、不矫情、不媚俗,不做庸俗社会学的哗众取宠;同时,敢于无情揭示自我和社会的虚假意识。在晚明画僧朱耷的题跋中,这种关照谓之“涉事”。因此,无论其老虎如何变相、变体、变形,都是以隐喻、转喻、直喻的交替变换方式,指涉人心腐坏、乱象危机,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我想:这是观者由衷喜欢他的水墨灵兽的缘由之一。直言之,水墨之畅神、写心、心印、移情、卧游乃至逍遥自娱,未尝不具社会功能,只不过功能有其关联域,因文脉、因时代、因地域、因个体之主体性而异而变,此四者中,后者是其核心。

左·《语世》系列 一了 纸本水墨、丙烯 85cm×578cm 2016年

右·《语世》系列 一了 纸本水墨、丙烯 85cm×578cm 2016年

上·《囚境》系列 一了 布面水墨、丙烯 800cm×260cm 2008年

下·《语世》系列 一了 纸本综合材料 68cm×68cm 2016年
从一了近期的诸多大尺幅作品看,其《语世》情怀更加深挚而富于激情,巨幛水墨《经幡》(2016年)笔力狂放、情势奇伟、关切深沉,不啻为其代表作。此作丈八四条屏,正面背面皆着图文。《经幡》之一、之二、之三的背图皆为线描千佛,正面为大写意佛释造像,自上而下,顺势运行,笔笔到位,一气贯之,见出画家一贯的宏恢魄力、老辣气度。佛尊或端坐莲花,或立地而升。佛尊形象多源自北魏塑像及唐末五代石窟壁画,悉心加以半抽象半写意的概括。在庄严悲悯的表情中,在斑驳陆离的历史迹象中,一种当代人的焦虑与无奈感浮现出来。其中一幅条屏,一只惊鸟戛然遗屎于佛尊头上,整个画面,由开始铺设的庄严神圣、澄净清凉的氛围,被递增的生猛涂鸦感所逆转,为之疏离、为之陌生,巨大的视觉张力油然而生。《经幡》之一、之二、之三分别题款为“佛头着粪”、“远离颠倒梦想”,这些题款书风,鉴取公案、民间书写及暴力标语,可谓方便了当、明心见性。及至《经幡》之四,以焦墨皴笔铺底,佛尊则以丙烯白线勾勒而出,仅存一个相对清晰的轮廓,如同影像负片,而背面是一片恍惚混沌。四幅条屏,是一个具有意蕴结构的诗章,正面反读,而背面正读;正面在反讽,背面在修正;正面与正面之间在聚讼、争执,牵连纠葛,构成相互解构的互文关系,其匠心别裁,无以复加。

1

2

3
1.《语世》系列 一了 纸本水墨 137cm×68cm 2016年
2.《语世》系列 一了 纸本水墨、丙烯 137cm×68cm 2016年
3.《囚境》系列 一了 布面水墨 246cm×450cm 2007年
从佛像绘画表现的历时关系上看,唐末五代初,众多的寺院壁画和卷轴画承袭“画圣”吴道子,执著于“笔力狂怪、纵横驰突、形制奇古”的佛像画创作,杰出者当属前蜀画僧兼诗僧贯休。据传,贯休所画水墨罗汉“状貌古野,特殊不为世间所传,丰颐蹙额,深目大鼻,或巨颡槁项,黝然若夷獠异类,见者莫不骇瞩”。贯休言,此皆为“梦中得之”。虽不可稽考来处,但无非出自对佛教信仰的虔诚感情,对人生苦禘的参悟与表现,及至文人画的书卷气和水墨程序化,宗教情感的虔诚和热情,庶乎荡然无存。反观当今画佛者,多是一些江湖画痞摇身一变,以画僧自居,观其修为和德性,实为沽名钓誉的文化蛀虫、皂隶之徒。
可见,宗教艺术及精神性艺术于今是冰火两重天,腹背受敌。“尽管上帝之信仰不受人之背信的干扰,但背信毕竟是背信。尽管上帝的悲悯包围和承载着尘世,但尘世毕竟是尘世。”(卡尔·巴特《〈罗马书〉释义》)
中西艺术史一再证明,真正伟大的艺术是具有宗教性的,艺术在其艺术创造活动之深处是宗教性的。在先知型艺术家身上,通过美和真实现了人对自然的直觉认知,“远离颠倒梦想”。实现对人的解放,开启了对超验的引入、对世界观念的改变。在创造中,有从“虚无”中来的本源,亦即从另一个世界的自由中来的因素。这意味着,最重要和最神秘的事物,最富有创造性的新东西不是来自唯物的“世界”,而是来自精神。而所有精神的创造,都是对人为教条的偏离。这也是古典画论将“逸格”视为终极品格的根本原因,而绝非应景酬唱的“工匠精神”云云。
一了是中国当代艺术“精神性转型”的优秀范式,他的思想和实践表明:水墨不只是一种艺术媒介,它还是一种与一系列社会性、历史性和文化性的语境有着复杂关联的社会能指,一个不断终结又重临的精神开启。当代性之于艺术家个体,是一种有尊严的、追求精神自由的选择,意味着在遭受启蒙现代性的独断与破裂之后,水墨艺术必然要跨越鸿沟,重建知识与生命的统一,价值、意义与理性的统一,也必然要重新认识自然与人的一元整体存在,重建人与神的关系。
丙申年中秋,于京郊回龙观
注:
展览名称:一了:恶世吞吐
展览时间:2016年10月15日—12月15日
展览地点:北京宋庄89艺术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