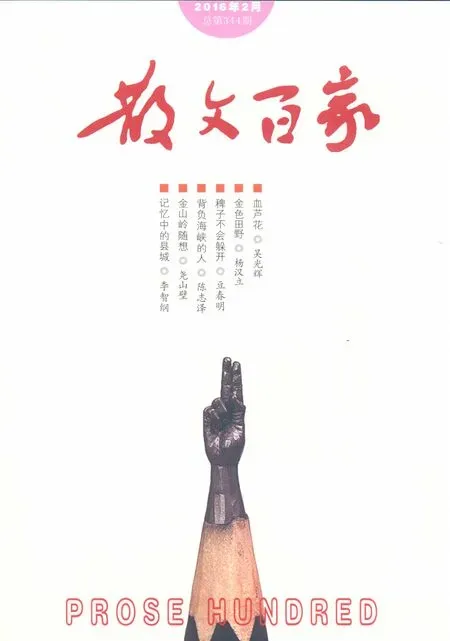失落的北方
2016-12-08朱宝杰
朱宝杰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失落的北方
朱宝杰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北方是悲哀的,艾青曾说。那是八十年前的事情了,年代的风霜刻划着广大北方的贫穷与饥饿,但他爱着北方,爱着悲哀的古老的国土。八十年一过,北方没有了穷苦,没有了悲哀,但悲凉和困顿却从未远离,那精神奴役的煎熬在打开了一把锁链之时又套上另一把锁链。我们物质的丰裕却阻挡不了精神的贫瘠和人性的日益泯灭,贫穷一扫而光,随之而来的又是什么?我从出生便生活在北方的这样一个很不知名不显眼的街道上,从南而北再而南回到出生处的街道对面,短短的几十米的距离我却走了二十年,还要过去多少年我并不知道。这条笔直的大虎街不过短短几百米的距离,承载着几百户人家的日常与梦想。他们在这虎滩最繁华的地段日夜存活、沉默或喧闹,悲喜和哭笑。而我所见的种种,无非是他们最惯常的表现、最平凡的生活,而那最一般背后的肮脏丑陋,在我年龄日复一日的增加时越来越重,变成大虎街穹顶太阳下的一片乌云,越来越暗,越来越多。
我在很小的时候,遇到过两个疯人。第一个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他是姓甚名谁,只知道他是外地人,认识他是因为他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夏夜爬进了我家的屋子。他没有双腿,只能用两个凳子撑着上半身行走,他就是这样爬进了我家屋子避雨,很简单的结果,爸爸发现了他把他轰了出去,后来不知何时他被弄到一辆车上和一群疯子一起被拉到了某个地方从此再也没有出现。他活跃的那段日子,我还是一个吃奶的孩子,我所知道的有关于他的这些事情都是妈妈讲给我听的,但我感受了和妈妈一起的恐惧,还对他印象极深。第二个疯子叫“会来”,我确确实实见到过他,一头长而脏乱的头发,脏而破旧的军绿色大衣,高壮的身体和凶神恶煞的样貌,他走路的气势更给他增添了让人害怕的资本。我记不清他活着的时候干过什么,听说他经常来我家饭馆捣乱,跟爷爷打过架,记得他死在一个水库里,人们说他是在在水边喝水时不小心掉进去淹死了,但现在想想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还是真的如人们所说有待考证,然而从没有人去证实过,因为关心他的生死。我真的还记得这两个疯人,在我还小时为数不多的记忆里这两个人占着一席之地,无论是想象中的无名氏还是记不太清的“会来”。现在想想,大概是因为他们体貌丑陋脏乱,让人厌恶和害怕,所以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人越是害怕和厌恶什么,越是忘不掉什么。而我对他们有过恐惧,却没有过厌恶,那个年纪我可能只会有由好奇心而产生的恐惧,至于去讨厌一个人,还没有那么真实和长久,现在我以一个承认的思维去回忆那些和私情,开始质疑人们对他们封以傻子称号是否有理有据,我越来越觉得他们不疯不傻,只是因为他们生活行为不同于一般大众,就被排斥为让人生厌的“疯子”。在我稍稍长大之后,大虎街又经常出现“傻大妮”,这个同样如疯子一般打扮的男人也不疯不傻,只是爱捡点东西,总是不说话一脸微笑着挨家挨户的要东西吃或要钱花。在我刚见到他的时候,也是会有点害怕的躲开,我总觉得他的笑不怀好意后来我懂得了又让你害怕或讨厌的东西你就躲开或不去看,而好奇总让我在他出现的每一次都禁不住地去关注他的一举一动。等我再长大一些,觉得可以打的过他,大到也可以和其他人一样驱赶他的时候,莫名的恐惧烟消云散,代之以莫名的如同他人的厌恶。直到每次爸爸总会忍不住去给他一些东西,直到我光明正大的去看着他坐在路的一旁吃着乞讨来的食物,直到我看见他经常拿着铁铲给街道清扫,我再也没有了厌恶的感觉,我开始敢去直视他的笑脸,甚至莫名的喜欢,几年不见,他不知身在何处。
我之所以经常遇到他们的原因还有就是我家在大虎街上开了三十年的餐馆,是他们愿意来的地方。三十年里,饭馆由生意红火到冷清,由小而大,在整个街道扩张,店铺不断更换的时候,我家饭馆一直保持较稳定的状态。由于我经常乱逛以及它的面积较小,我对大虎街的状况是比较了解的,而我较熟悉的店铺却无非就是周围这几家在几年里也渐趋稳定的店儿——南边的买粮油的老魏、买酒水的老林,北边与我们隔道大门的卖百货的老陈、卖粮油的老张、卖五金的老曲、修自行车的小李和修大车的老杨、开超市的老刘。至于街对面的店儿,我们基本没有过什么交集,似乎空间的距离和同行业的限制注定了这种情况。说白了,我最日常的生活圈子就是从南边十字路口截至到北边臭水沟中间这一段街道的同侧,再加上生活在院子里的统辖整块区域的老于家和我比较熟悉。这些年里,我和这些家庭打着交道,感受着大家彼此微妙的关系和人情冷暖。
大虎街上总会在平淡无奇的日子里发生一些并不无聊的事情,似乎每一个人都在闲来无聊时有事可做,在看完热战之后打几场冷战。多年来,我总结出几大哲理:
其一:人多必战,战久必伤;其二:热脸爱贴冷屁股;其三:惹不起但躲得起。
于是,在出现了许许多多莫名其妙的事情之后,我家餐馆在许多年后的现在终于可以安静度日,从一个热闹的大家爱来集会的茶馆变得安闲,我们可以静观周围的一切而不予置评,再也不用去到他们面前迎合,只需遇到的时候打个招呼微微一笑。
而我开始发现微笑并非又使人积极的力量,它掩盖了许多真相,暗暗涌动的恶意的冷箭会让人猝不及防。我想起无名氏和会来那凶恶的脸和大妮傻笑的面庞,他们最真实的外在和内心配合,无所谓着世人的言语。我不想再看到他们的笑脸,只想如当年不看或者躲开自己害怕的疯人一样不看或者躲开他们,可在这样一个狭小而熟悉的大虎街上,这些只能想想而已。
在一个闷热的夏日午后,我路过北边臭水沟时发现邻居的女儿和一个男子在隐秘的那侧衣衫不整的躲开,我假装没看见的走过。我想起邻居曾告诉我我家的小狗曾在臭水沟里挣扎着往上爬最后失败,我不禁又走回臭水沟旁,看见漂浮着的各种发臭发烂的垃圾和一个未被脏水污染的新鲜的白色套子,各样的蚊子苍蝇正在狂舞。突然我看见黑镜里浮现出一张张凶恶的笑脸,我吓出一身冷汗转身逃走。回家的时候,路过老张家门口发现几个男人女人在那谈笑风生的看到了我,我没看他们扭头走了过去。而我的面前浮现出他们在我身后鄙夷的表情和指指点点,又听见他们尖利的声音:“老魏家这几天一直带儿媳去看医生,听说怀不了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