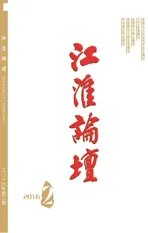国家壁垒及其对国际私法的影响
2016-12-08于飞佘发勤
于飞 佘发勤
(厦门大学,福建厦门361005)
国家壁垒及其对国际私法的影响
于飞佘发勤
(厦门大学,福建厦门361005)
国家间的私法冲突一直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因国家权力的自源性、独立运行与权威性而形成的国家壁垒。国家壁垒既是国家间私法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国际私法冲突难以获得有效解决的原因所在。即使各国为解决国际私法冲突进行不懈努力,还专门成立了“海牙国际私法会议”这样的专门组织,但通过分析该组织的成果,我们依旧发现国家壁垒还是国际私法发展中的主要阻碍因素。
国家权力;国家壁垒;法律冲突;海牙国际私法会议
与世界经济的飞速国际化相比,国际私法总体上的发展是滞后的。这种滞后状态有很多原因,如法律、政治、乃至文化上的差异,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因国家权力的自源性、独立运作与权威性而形成的国家壁垒。
一、国家权力的特殊性及其壁垒
(一)国家权力的特殊性
所有组织都具有权力的特征[1]63,无论组织规模大小,其科层结构决定有人负责决策、有人负责执行。在环环相扣的“决策—执行”体系中,决策者对执行者拥有权力,执行者对被执行者拥有权力。个体成员加入组织是为了某种利益,但为了共同的利益必须从事共同的行为,因此成员的行动及其意志将服从于组织的共同意志。这就意味着组织以一种权威影响其成员,成员则处于这种权威之下。这种权威以正式制度为前提,组织的内部制度确定了组织对其成员的权威。因此,组织具有典型的权力特征。
国家的权力特征是非常明显的,人们通常以国家权力为原型,来理解其他社会组织的权力结构。然而,国家权力具有特殊性,与其他组织的权力有着本质区别。
首先,在起源上,国家权力具有自源性。虽然很多西方理论用“社会契约”来解释国家的起源及其合法性,但是与其他组织不同,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国家的成立,是没有明确“契约”的。而通常的社会组织,总是通过成员之间的协议来建构组织体。在当代,几乎所有的正式组织都有“章程”就是最好的说明。这种基于成员同意而缔结的协议,构成了组织体内部权力的来源。然而在国家这个组织中,这种协议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人们很难将现代宪法理解为成员之间的协定。毕竟宪法的颁布并非基于每个人意志的统一,甚至在形式上都不存在这种统一意志。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国家权力本身就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力量,其来源实则为暴力。也就是说国家权力并不是来源于理想的社会契约,而是在社会自发的暴力过程中产生的。在实证上国家权力不以其他权力或权利为前提或依据,是自源的。这种权力来源上的自源性,是其他社会组织的权力所没有的。
其次,国家权力在运行中的独立性。国家权力在来源上的自源性,决定了其运行中不依赖其他权力或权利。国家权力最终是依赖其自身的暴力与权威性,而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这一点与其他社会组织的权力运行有着本质区别。其他社会组织的运行,最终依赖于国家权力。即使其他社会组织的权力可以来源于其组织成员的同意,但是在运行过程中也不能与国家权力相左。而且,当它们的权力运行遇到障碍时,最终需要国家权力的支持。
最后,在各种权力关系上,国家权力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国家权力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构成对其他权力的权威,并成为其他权力合法性的依据和基础。国家权力之外的权力存在与运行是以国家认可与支持为基础的,或者说,其他组织的权力及其运行必须建立在与国家合作的基础之上。这样的权力关系是因为相对于其他权力,国家权力具有绝对权威性,它以自己的暴力为基础,而不以任何权力或权利为基础。
(二)国家权力形成的壁垒
国家权力的自源性、独立性与最高权威性,决定了国家壁垒的形成。国家壁垒使得当代国家具有主权,在制度上普遍具有对内最高管辖和对外独立性。
首先,国家权力的独立性决定国家间的以邻为壑。在立法上,国家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独立、排他地颁布法律、法令。即使意识到与其他国家之间会发生法律冲突,在法律的选择适用上也是自主、独立的。在行政管理上,国家权力的独立性与权威性,决定了行政机关不可能适用其他国家的行政法规或行政命令。
其次,国家权力的最高权威性,决定了国家林立这一基本政治法律现状。每个国家的国家权力是最高的权威,相互之间不隶属,也不隶属于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众多国家权力的并存是客观现实。国家权力之间的对立导致国家之间不可避免产生矛盾与冲突,这就需要在这些最高权威之间进行协调。国际私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最后,国家权力的自源性为国家林立与独自管理提供了事实依据和正当性基础,也为国家壁垒的形成准备了充足的条件。国家权力的自源性、独立性与最高权威性,使得国家在其国内管理以及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足以保持充分的权力独立,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国家权力以邻为壑的政治法律现状。尽管国家间有合作,但是国家权力本质决定了国家利益至上,因而合作是有限的。
国家权力的这些特殊性及其产生的国家壁垒,是我们了解国际私法及其发展的最基本的要素,离开这个基础,我们对国际私法产生与发展的认识难免是片面的。
二、权力壁垒对国际私法影响的历史分析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私法产生于欧洲,简单回顾国际私法的历史,不难发现,国际私法在总体上经历了从“区际私法”到“国际私法”的发展。权力及其壁垒对这一过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基督教世界国家对国际私法产生的消极影响
在欧洲,罗马帝国及其之后的中世纪,都沉浸在一种世界主权的政治情怀之中。拥有世界主权的是教会,教会在精神与世俗世界两个层面,始终扩张自己的权力。到了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之后,罗马教会具备了近代国家的绝大部分的特征。[2]136此时,欧洲基本上形成了以教会权力为核心的世界国家。
罗马教会具有国家性,而世俗政权仅仅是教会治下的“地方政权”。尽管事实上存在大量的世俗政权,然而,制度意义上的世俗主权国家并不存在。虽然世俗政权拥有权力,也具备权威,但是与罗马帝国、罗马教会强大的权力完全不一样,地方世俗政权的权力与权威都是有限的,不能形成有效的权力壁垒。
当时欧洲实际上存在的各种世俗政权,它们具有民族性、地域性与权力。但是,因为“它们的所有成员,包括它们的统治者,在许多方面也要服从一种作为它们中心的教会国家”[2]137,因此,世俗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是教会。这就是说,当时的世俗政权即使在实践上具有强势权力,但其权力不具有自源性与最高权威性,其权力的运行要通过与教会合作才取得合法性。从当时的权力体系来看,只有教皇的权力才是自源性的,是最高的权威。当时的欧洲,罗马教廷具有中央集权、近代国家的性质。不存在国家林立,就没有国家壁垒,因此,当时的欧洲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间的法律冲突。
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间的法律冲突产生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公会”之后,作为和会的重要成果《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彼时欧洲各邦国“主权平等”与“领土主权”。有了平等的主权国家,才具有现代国际私法意义上的国家间的法律冲突。
(二)欧洲世俗政权下冲突法的产生
尽管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前,欧洲不存在并列的最高权威,没有产生最高权力之间的壁垒。但是,无论是国际私法理论、法律冲突现实,还是解决法律冲突的实践,都已经先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渐渐发展起来。这是因为权力割据的真实存在而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权力壁垒,从而导致了近代区际私法冲突。
在罗马教廷的集权之下,存在着并行的权力体系,尤其是世俗权力。虽然这些权力都不是自源性的,也不具有最高权威性,可它们是并行存在着的,并对各自治下的个人具有权威。最为典型的就是中世纪的意大利北部城邦国家。
14世纪意大利北部各城邦共和国,在名义上属于神圣罗马帝国,但是“皇帝在那里的权威纯粹是形式,因为实际权力都是掌握在城市的市政官手里。”[3]280因此,在权力体系上,各国城邦共和国都是相互独立的,并且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力与权威——名义上的最高权力与权威,实际上不对城邦共和国发生效力。当时意大利北部城邦的真实权力结构是:各城邦共和国自己享有真实的最高权力和权威,其权力是不受外来权力干预的;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力是名义上的最高权威;教皇的权力只是精神上的最高权威。
权力的实际状况决定了法律体系的实际状况:虽然罗马法作为普通法被普遍适用,但是各城邦共和国都有自己的特别法。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罗马法原则,通常处理纠纷时如果城邦有自己的“法则”,则适用自己的“法则”而不适用“罗马法”。这种法律制度状况与欧洲中世纪大多数时候没有根本性的区别,但是由于发达的贸易和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得在意大利北部城邦,跨界的民商事纠纷非常普遍。当北部城邦在处理涉及其他城邦共和国的民商事纠纷时,就会产生两个以上城邦共和国“法则”的冲突。解决跨界纠纷所带来的法律适用问题,超越了罗马法与自己城邦法则之间的关系,于是,近代意义上的“私法冲突”产生了。不过,这种私法冲突不是建立在国家割据与壁垒基础之上的,而是以城邦共和国的林立与壁垒为前提,站在神圣罗马帝国的角度来看,毋宁称其为“区际冲突”。
从权力的视角看,当时意大利北部城邦的“区际冲突”与现代意义上的“私法冲突”并不存在什么本质区别,都是以“权力”的排他性、各自独立与对立为基础。彼时的意大利北部城邦是独立的自治共同体,与欧洲当时其他世俗政权非常不一样:基于教皇的授权,它们独自负责后来被称之为“国家”的事务,构成了欧洲“最早的纯粹的世俗政治实体,是最早的近代世俗国家”[2]471。正是因为其具有独立的权力与权威,后世才称之为“城邦国家”。这说明了为什么是在意大利北部城邦产生了私法冲突及其解决的规则,而不是在欧洲其他地方。14世纪意大利北部城邦国家的权力还表现在这个政治实体拥有制定新法律权力的“议会”制度,城邦把自己看作是世俗的政治体,“并不要求自己去适用宗教法律”,“其使命首要地是扼制暴力和调整政治、经济关系。”[2]478这些权力运行与法律实践说明这些城邦国家之间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权力壁垒,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法律割据状态。
14世纪意大利北部城邦体系中的法律冲突及其解决方式,充分说明了国际私法的产生与权力具有密切关系。作为行为规范,尽管法律的产生可能基于很多原因和方式,但其实施与适用却离不开权力的支撑。因此,权威权力的存在是法律运行不可缺少的要素。权力因素的状态决定了法律运行的状态。当足以维持法律运行的权力出现并列的情形时,将导致法律运行中的冲突。这种基于权力并行与“割据”而产生的法律冲突是真实的,冲突的解决需要在这些平行权力之间建立某种机制。这种解决法律冲突的机制,实际上是每种平行权力体系都会遇到的。14世纪意大利北部城邦权力林立而形成权力壁垒,加上其发达的商业交易,产生了最初的私法冲突。国家权力林立只是平行权力体系的一种,国际司法的产生就源于林立着的国家权力所形成的国家壁垒。
三、当代国家壁垒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当代,国家壁垒不仅仅对国际私法理论与制度产生根本性的制约,而且对国际私法的进一步发展,也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
(一)国际私法理论与制度的国家壁垒基础
国家壁垒对于国际私法的理论与制度都产生重大影响,在某些方面甚至是根本性的原因。下面我们将从理论与制度两个方面来揭示国家壁垒对国际私法的深刻影响。
在理论基础方面,国际私法领域几乎所有的重要理论,都受到国家壁垒的制约。
首先,国际私法存在合理性的核心问题就是:一个主权国家为什么要适用其他国家的法律。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疑问,其潜在的理由是国家是有主权的,有权力不承认外国的法律。在我们的意识中这实际上就是:国家即最高的权威。正因为如此,最早也是最有名的适用外国法的理论基础——国家礼让学说,就是将主权置于无与伦比的地位,也即承认国家的最高权力与权威。一国法院适用外国的法律,不是外国的法律所体现出的任何权力或者正当性、合理性被认可,而是出于“礼让”——属于伦理道义的范畴。将法律制度的基础建立在道义的基础之上,这种苍白无力的理论,是面对国家权力最高权威性时,无可奈何的选择。在国际礼让学说基础上诞生的“胡伯三原则”,是美国国际私法的主流理论,同样坚持国家在其领土内的主权与专属管辖权、一国的法律不能约束不在其境内的人或物。“胡伯三原则”理论认为,一国法律在他国发生效力,是因为他国的明示或默示承认。这最终还是建立在承认国家权力最高性和主权不可损益的基础之上。同样,英国早期的适用外国法的理论——戴赛既得权理论,也体现出对国家权力割据的默认:法官只负有适用内国法的任务,不能直接承认或适用外国法。
其次,关于外国法律的性质:意大利、法国等少数国家和学者主张,外国法律在本国法院是法律;英美法系坚持认为外国法律仅仅是个“事实”而不是法律,尽管是个“特殊类型的事实”;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折衷立场,坚持外国法律既非单纯的事实,亦非绝对的法律,而是根据本国法律指定适用的法律规范。显然,英美法系将外国法律不作为法律对待,体现了国家的绝对权威与权力的属地性质,也反映出权力的割据状态。折衷学派也是将本国法律置于外国法律之上,之所以适用外国法律乃是基于本国法律的指定。这也体现出内国国家权力的至高性。
最后,公共秩序保留理论再次表明,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国家壁垒对国际私法理论的掣肘。适用外国法是以国家主权为前提的,而当外国法律被适用时,依旧不能离开国家主权的掣肘。当外国法的适用与内国重大利益、基础政策、基本道德观念或法律基本原则相违背时,将不适用外国法律。这一理论及在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制度,本身就说明外国法律在内国的弱势地位,外国法律的这种地位是内国国家权力绝对权威性导致的必然结果。正是因为内国国家权力的权威性,使得其在适用外国法上具有绝对的权威,因此,内国重大利益、基础政策以及道德观念和法律基本原则,都是内国主权之下的事项,完全由内国自己去判断。这种权力壁垒现状,使得这一理论顺理成章地在世界范围内通行。
在制度方面,国家壁垒构成了国际私法制度的重要基础,无论是冲突规范还是实体规范都是如此。
首先,之所以产生国际私法制度,是因为主权国家的平等性决定了各国的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具有同等效力的各国法律,如果对于同样的法律关系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就会导致法律冲突。而这种国家之间的法律冲突,与国内法律之间的冲突具有本质的区别。区别之一在于相冲突的各国法律没有效力上的等级之分,也就没有确切的规则来确定优先适用之次序。而国内法之间的冲突,通常以等级、优先次序来解决法律冲突。区别之二在于国家法律之间的冲突,其效力无法通过确定权力系统来确立效力上的优先次序,而国内法之间的冲突如果不能通过事先确立的优先次序来解决,那么总是可以通过特定的国家机关来解决。各国法律都具有独立于他国法律的效力,具有与他国法律同等地位的效力,构成了各国自己的法律制度系统。这些法律制度系统都是相互独立、具有绝对属地权威,形成了各国法律系统之间的以邻为壑。并存着最高效力的法律制度系统,是国家权力具有最高权威性的必然结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有必要解决壁垒带来的问题,国际私法才有存在的必要。
其次,法律冲突的解决是国际私法制度的核心,然而解决法律冲突的制度具有明显的国内法特征,各种典型的国际私法制度,在实质内容上具有重大的区别。虽然冲突规范具有相同或相似的逻辑结构,但是因为连接点的不同,使得各国的法律冲突规范迥然相异。如“属人法”这个连接点,有的国家理解为“国籍地”法,有的国家则将之理解为“住所地”法,也有理解为“惯常居所地”法。例如,同样的一条冲突规范——“婚姻当事人的婚姻年龄适用当事人的属人法”,如果A与B在不同的国家,他们的国籍、住所与惯常居所不一致时,就会产生不同的结论。这样的一种不确定性与法律规范追求确定性的目标,极其不符。而这些无疑都是源自法律背后的国家权力的最高性与独立性。国家权力的最高性与独立性,赋予了本不具有合理性的这些结论以合理性。这一悖论之根源就在于国家权力带来的国家壁垒。
最后,对于相同的冲突法原则,各国根据自己的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传统,予以不同的理解。条约国内解释主体直接涉及条约国内效力。[4]最为典型的就是在对“意思自治”原则的理解上,各国千差万别。对“意思自治”内涵、适用范围、构成限制的强制法律规范的性质与范围等规定不同,导致即使都根据“意思自治”解决民事或商事纠纷,也会产生不同的法律结果。而根据国家主权观念,这都是合理的。可见,国家主权及其构建的国家壁垒对国家私法的影响是实质性、根本性的。
(二)国际私法统一化的艰难
国家壁垒——国家权力并行与法律的割据状态,作为根本性的社会结构是现实存在的。时至今日,国际私法的发展与变化,始终是受到国家壁垒这一政治法律事实的影响。也正是因此,国家之间的合作才是必须的。当前,最具影响的国际私法领域中的国家间合作莫过于“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始于1893年,直到1951年才通过组织章程,正式成为政府间国际组织。虽然其目的在于“促进国际私法规范的逐步统一”,但其取得的成就远没有达到官方所称的“巨大贡献”,以下对相关统计数据的分析可以清楚表明这一点。
首先,无论是实体法、程序规则还是统一冲突法,几乎没有一项国际公约获得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一致批准。截止到2015年1月,“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共订立了39项公约,除了第一项公约《StatuteoftheHagueConferenceon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是其章程外[5]3-6,其他38项公约(指表1中02-39号公约,以下的所有分析都是以此38项公约为基础,不包括章程)都是直接关涉法统一的,或是统一程序法或是统一实体法。这38项公约里,11项未生效,1项已经失效。在已经生效的26项公约中,有17项公约的成员国少于30个国家,不足10个成员国的公约也有8项。而世界主要国家——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德国——同时批准参加的公约仅有两项:《关于从外国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公约》和《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合作公约》。如果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角度来看,则没有一项公约是主要经济体都批准参加的。
其次,从公约订立与批准生效的时间来看,我们也没有发现,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一体化,而加快了私法统一的脚步。已经生效的26项公约,从订立到生效,平均耗时约6年3个月。其中,1978年以来订立且已生效的9项公约,从订立到生效平均耗时约为8年4个月。而本世纪以来唯一订立且生效的一项公约,从订立到生效耗时为9年。截至2015年,本世纪订立而未生效的4项公约,最长的已经耗时8年多,最短的也耗时7年多了。可见,人类经济的日益一体化,并没有能够加快人类统一私法的脚步,反而有放慢脚步之嫌。
最后,国际私法的统一化在实现两大法系的统一方面的作用是严重不足的。“海牙国际私法会议”订立的公约中,已经生效的公约的成员国主要是欧洲和美洲国家,尤其是两个大陆中的大陆法系国家。就此而言,获得生效的公约,没有能够起到统一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作用。
在已经生效的26项公约中,5个主要的英美法系国家: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南非,分别参加9项、5项、10项、3项和5项。英国和美国都参加的公约仅有3项:《关于取消外国公文认证要求的公约》、《关于向外国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国际诱拐儿童民事方面的公约》。上述主要英美法系国家中,有3个以上英美法系国家都参加的也仅有5项:《关于遗嘱处分方式法律冲突的公约》、《关于取消外国公文认证要求的公约》、《关于向外国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国际诱拐儿童民事方面的公约》、《信托的法律适用及其承认公约》。
可见英美法系国家的参与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的工作根本就没有黏合好世界两大法系。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国际私法的统一化进程中,目前为止尚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因为法律制度的统一化,离不开两大法系的融合。
我们不能完全以法系的传统为理由来解释这一现象:两大法系的制度传统与文化传统阻碍了统一化进程。因为在英美法系国家内部,差别也是很大(见表2):澳大利亚批准了10项公约,而加拿大仅仅批准了3项。作为最为典型英美法系国家的英国与美国,共同参加的公约仅为5项,而英国与大陆法系的法国,共同参加的公约却达到7项。显然,法系制度与文化的影响并不是主要因素。更有说服力的是《信托的法律适用及其承认公约》。信托是非常典型的英美法制度,但公约的批准国中没有美国、南非,却有意大利、瑞士、荷兰这样的大陆法系国家。因此,阻碍统一化进程的主要因素并非法系本身制度与文化上的差异所带来的,我们认为国家权力及其壁垒才是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综上所述,世界范围内国际私法发展的滞后,不能从经济与法律传统上获得解释,而是明显受制于国家壁垒这一政治现实。下一节对欧盟的分析会给我们提供很好的正面佐证。
(三)欧盟的启示
欧盟的私法统一进程明显超过“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的步伐。2007年欧盟通过《罗马条例Ⅱ》,即《非合同法律适用的条例》(RegNo864/2007([ 2007]OJL199/40)),2008年,又通过《关于合同法律适用的条例》(即《罗马条例Ⅰ》)(RegNo593/ 2008([2008]OJL177/6))。这两项重要公约将欧盟范围内的私法冲突问题予以解决。欧盟所有国家有关法律冲突法的规定都不得与之抵触,实际上,这两项公约都已成为欧盟成员国的国内法。
为什么欧盟能够缔结对成员国具有如此强制约束力的公约,我们只能从欧盟的组织体系中获得解释。欧盟作为一个从国家间组织向超国家间组织发展,其发展过程恰恰反映了国家从权威林立与割据的状态走向建立一个处于国家之上权力权威的状态。也正是因为欧盟具有打破国家权力壁垒与垄断的超国家权力,法律的割据与冲突才能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得以解决。国际私法领域的统一,实际上仅仅是欧盟法律统一中的一部分,他们在许多重要的实体法领域也实现了统一。[6]276-308
与国际私法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举步维艰形成鲜明对比,欧盟取得引人瞩目的进步。这都源自在欧盟范围内,欧盟的强大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国家权力,进而逐步击破国家壁垒。欧盟在相当程度上打破国家壁垒,也许就是国家权威盛极而衰、国家壁垒松动的征兆。这或许意味着人类已经步入从国家形式向更高级形式转变的历史进程。
通过上述历史的考查与现实的分析,我们相信作为当前国际政治与法律现实:国家壁垒——这一来自国家权力最高权威性的客观存在,构成了国际私法产生与发展的最根本原因,也是当今国际私法发展陷入瓶颈的决定性因素。
[1][美]肯尼斯·阿罗.组织的极限[M].万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63.
[2][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M].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136.
[3][英]德尼茨·加亚尔.欧洲史[M].蔡鸿滨,桂裕芳,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
[4]冯寿波.论我国条约解释主体制度的完善——以修订我国《缔结条约程序法》为视角[J].政治与法律,2014(9).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公约集[Z].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6][法]德尼·西蒙.欧盟法律体系[M].王玉芳,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丹若)
D99
A
1001-862X(2016)02-0109-007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www.jhlt.net.cn
于飞(1962—),女,陕西佳县人,法学博士,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私法;佘发勤(1973—),安徽庐江人,法学博士,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法与法律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