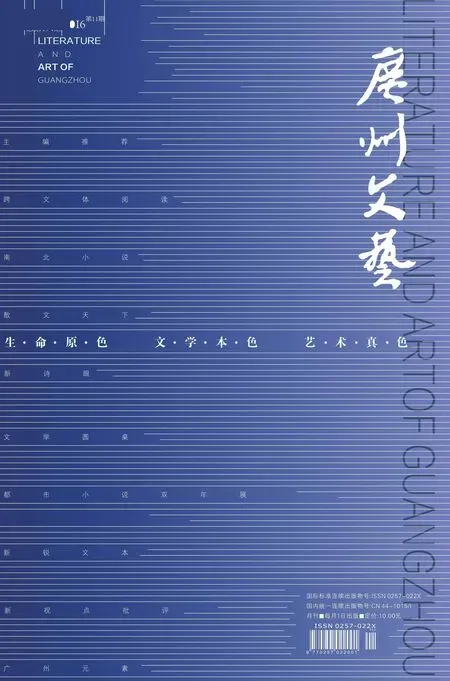路线图
2016-12-08肖达
肖达
路线图
肖达
1
杨桃从楼上往下看,大雪。漫天白雪成团连片,白花花的世界自天而降,密不透风。
在城市里,雪的大小总是被我们忽略,往往我们一抬头,看到的是雪的城市,而不是雪飘落下来。城市的所有建筑阻隔了我们投向天外的视线,我们眼睛里看到的,往往是结果,忽略了过程。因此,那天我们看到的,的确是一片白色的城市。
相信那个风雪的傍晚,走出校园的杨桃感觉到了城郊的校园外,暗藏着阴冷杀气。天宇苍茫寂寥,树木坚硬如刀。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走在雪地里的杨桃都出奇矮小。听一个同事说,他看到矮小的杨桃缩肩拢臂,背着一只酷奇包,在纷飞的大雪里走出校园。那个同事说,他看到穿着白色羽绒服的杨桃不一会儿就淹没在白雪之中了。
现在,我们可以确信,杨桃的酷奇包里装着讲义、优盘、手机,还有手提电脑。
这之前,杨桃在学校的单身宿舍里住了一周,是借了学生的一间宿舍住的。学生宿舍在东宿舍楼。这栋楼外是一片平原,
站在楼内向外一望,除了远处一个村庄,便是一望无际的原野。有一条国道斜穿过那个村庄,如一把匕首由宽变窄,生硬坚硬地刺去。国道这边的另一端,是一家新建的工厂,工厂没有工人,只有几排厂房被围在灰色围墙里。有人问起为何几年也不见开工,看门的答道:为了占地。为了占地的工厂离校园不远,北侧,近邻国道,185郊线车的对面。
去年,一个来自于南方的学生穿着毛衣毛裤,在冰天雪地里,瑟缩于车轮之下。意外时有发生。
杨桃提着她的包走进学生宿舍,身后跟着抱着被褥的学生。宿舍里有相对的两张双层床,上下四个铺位,四个铺位都是绿垫子。身后的学生将一床被褥替杨桃铺好,杨桃说,谢谢你。
后来,有同事问起杨桃在学生宿舍住得怎么样,她淡淡地说,挺好的。
杨桃有来头的家世,让所有教工们对她另眼相看,她便显得孤单,噤声敛气,温婉恭谦。除了大家一起出去聚餐时主动埋单之外,她很少说话。同事中有好事者问起杨桃的哥哥是不是在省里做高官,杨桃矢口否认,表情上略带厌烦。久而久之,背地里就有些微辞了, “又求不着她,看把她吓的。”“真能装,故弄玄虚。” “干得好不如生得好啊!看看人家杨桃生在高官家里。”还有更难听的:“说不定是哪一路的哥呢?没准是干哥。”
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事多,杨桃只装作听不到,回家跟母亲说这事,母亲也说,就当没听到,做好你的工作就是了。
有一次,系主任把杨桃叫到她办公室,大谈自己的儿子。拉拉扯扯半个小时,最后说儿子考了三年公务员,今年终于考上了,可就怕面试出问题。杨桃坐在系主任对面,让头发挡住半边脸,嗯了一声。
系主任又说,“要是有人替我们说一句话,问题就解决了。”杨桃还是嗯了一声。
系主任见杨桃如此冥顽不化,脸色在好看与不好看之间游移变换,声音像枝头上唱歌的鸟,婉转顿挫,腔调渐现隐忍,“能不能让你哥给市里打个招呼?我这辈子也没什么奔头儿了,就这一个孩子,所有希望都在孩子身上,这事就求你帮忙了。”
杨桃更深地低了一下头,目视地面,回答却非常干脆,“我帮不上忙”。
走出系主任的办公室,杨桃在心里嘀咕:“家兄从未帮过我,又岂能帮你?”目光尽是蒙蒙雾气。
从此,系主任不爱搭理杨桃了。打电话给她,或者不接,或者对杨桃说, “这事你别找我,找你们教研室主任去。”
杨桃向学校报精品课的材料报了三年了,每一年都在系里压下来,系主任这样解释: “每年省里只给咱们学校一个精品课的名额,你觉得你的材料报上去能批吗?既然不能批,为什么要报?”
大家只知道住在学生宿舍的七天里,杨桃好像一直在写什么东西,写的是什么,谁也不清楚,只觉得七天来,杨桃神志恍惚,丢三落四,面色惨白如纸。
杨桃在傍晚离开校园的那一天是周五。班车在四点一刻开出校园,而杨桃离开校园的时间是班车离开的半个小时之后。
她匆匆下楼,直奔校门。这个时间,天色已晚。
2
行政楼上宽大的电子屏在傍晚时分的暮色里,是一块黄色的闪光。这闪光里滚动着文字,不必看,杨桃也知道上面写着的字。这些字,滚动了一周了,是申报精品课的通知。
杨桃路过那些字,走向校园的大门,大门外的旷野,雾一样的青白,阒寂寥寥,寒风卷处,她不得不把自己缩小。
以往大门外近处的小广场上,会有一些黑出租车,是当地小镇上的人往市内跑私活赚外快的。杨桃很少坐这种黑车,她有时自驾车,有时乘185郊线车回市内。偶尔,她也会坐上叫作快客的小型面包车。这种快客车终点站是火车站北站,杨桃家住城南,从火车北站到城南,刚好是这座省城的直线长度,太远。这个傍晚,杨桃选择坐快客回家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杨桃站在185郊线车站点跺脚,出奇冷,雪不见小,迎面打来,如张牙舞爪的子弹,弹弹坚硬。路上的车子开始打开了前灯,灯光扫进雪地,一溜橘黄的河流冲开雪道。一辆快客飞速驶过招手的杨桃,杨桃跳着脚跟着快客奔跑了几步。
时间变得难熬,一分一秒地膨胀,杨桃陷落在难熬的时间里,眼神有些迷离,嘴唇抖动发紫。
一个黑车司机顶着一顶白色的绒线帽缩着背蹁着腿小跑过来,鼻和嘴呼哧呼哧喷着白气,似簌簌作响。说,“大姐别等郊线车了,上我的车,现在车里有三个人了,就差一个,你上车就走。”
杨桃竟没有迟疑,跟着那个黑车司机跑向小广场的另一端。那辆白色的捷达车窝在雪堆里,突兀出一个雪包。
杨桃在上车之前向车里扫了一眼,后座上有三个人,男的,五大三粗,眼光凛冽,表情僵冷。不是学生,不是教工,她看到了一只瘦骨嶙峋的大手用力按着坐在中间那个男人的腿上。杨桃略有犹豫,随之感觉到咚咚心跳。这时,出租车司机已经坐进了驾驶室,他向杨桃挥手,咧嘴大喊:“上车啊上车啊!”
杨桃向185站点看了一眼,又顺着国道向更远处望去,她没有看到大客车。一面灰白色在远处里,那家工厂,死一般沉寂。司机开了车门探出半个身体说,大姐啊,你行不行啊!还等185?你要是没钱,老弟给你出,快上车吧。
杨桃坐到副驾驶位置。
学校大门的门卫在这个时刻刚好向门外探出头来,从大门的照明灯里,他看到杨桃老师蹚着雪跑向小广场的一个黑出租车,她的前面,一个男人戴着一顶白色帽子。门卫看了一眼对面墙壁上的石英钟,五点半。
他该下班了,于是收拾手套和帽子,把钥匙交给接班的年轻人。走出门时,看到那辆黑出租在眼前一闪而过,扬起一堆雪粉。
这个时候,天色完全黑了下来,迎面看不清对方的五官了。门卫自语:这雪恐怕是要下一宿了。
3
杨桃屏息侧目,一路上双手抱包一声不出。车窗外的原野快速融进黑色里,偶尔有一两盏昏黄的灯,在远处越来越近,
随之被甩到身后。
身后那个喷着酒气的男人突然开始语无伦次,“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不管这个男人如何喊叫,其他两个乘客一声不出。黑暗里,沉默比叫喊更加可怕。那个刚才对杨桃快言快语的司机,也不作声,两眼死盯着前方的路。
杨桃先是听到了身后有金属的撞击声,接着是肢体搏斗声,这些声音混杂在男人们粗粝的喘息声里,咕咚咕咚响。杨桃座位的后背上,不断被硬物撞击,在车子的颠簸中,深一下,浅一下地顶进后腰上。杨桃将身体前倾,但她闻到了血腥的气味游丝一样,丝丝缕缕从身后飘来,弥漫了身前身后的空气。
身后的三个男人安静下来了,有那么一刻,杨桃在这安静而温暖的出租车里充满爱怜地想到了前男友,一个长着一对竹竿样长腿和扁脸小眼的男人。说不上是谁抛弃了谁,杨桃厌倦了前男友撒谎时紧眨不止的眼睛,还有搁在自己身上如竹竿一样干瘦的白腿。
或者与那个前男友结婚了,孩子也能打酱油了吧?杨桃有时候会这样问自己。
之后,前男友再前男友,十年的时间,三五个总是有的,长则一年,短则半个月,走马灯一样换人。有一次,摩肩擦踵的人群里闪出一张油汗的脸和肥厚的嘴唇。他惊讶地说,“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还好?”杨桃一怔,想不出对面的人是谁,便说,“还好还好。”那男人笑道:“我们约会过。”接下来眼神里的暧昧添杂龌龊。杨桃嗯嗯两声,拔腿便走。过后想,不知道是对方认错了人,还是自己认错了人。
当然,杨桃有时候也是很可爱的。有一次,她在半夜里打电话给一个男人,那男人在睡眼惺忪中问,哪位?杨桃说,是我。我想跟你说一句话,男人说,大半夜的,闹鬼啊!杨桃便冲着手机嘻嘻笑,说,咱们谈恋爱吧。房间里四下寂静无声,杨桃听到养在窗台上的玫瑰叭的一声开了,床头这边萦绕着一股香水的甜味。男人在电话那头嘿嘿笑着说,我追了你八年了,怎么今天半夜里想起来要跟我恋爱了?杨桃半天没出声,说,我的玫瑰花开了。
爱情本是好东西,可用得多了,也会腐败变馊。现如今,人们总是用新的记忆覆盖旧的记忆,尥腿向前跑,谁能说痛比记忆还长久?
远远的,蜿蜒的灯光沿着河岸逶迤着兜了个圈,由远及近。过了一道铁道的闸口,路变宽,前面一排重型货车堵了路。有人影从前面向这里走来,探头看看,挥着手臂比划着,出租车司机嗯嗯使劲点头。身后一个粗着嗓音的男声叫:“上土路上土路。给油给油!”司机还想分辩些什么,一段白亮的硬物从司机的后颈逼过来。杨桃忙把目光转向车窗,身后那个男人又说:“兄弟对不住了,救命要紧。”
车子箭一般冲进一片雪地,拐上土路。杨桃只觉得整个身体上颠下簸,每根筋骨都断得七零八落。
时间变得漫长又短暂,一列火车鸣着长笛,驶过来,又奔过去,进入黑隆隆的原野。
杨桃看到了璀璨的城市,宛如闪光的湖,四周是黑色的岸。
身后一个人喊,停车停车,人快咽气了。一家诊所的白色牌子竖在眼前,身后的两个男人搀扶着瘫软的另一个人跌跌撞
撞冲进医院的玻璃门内。
这里是哪儿?杨桃问了一句,司机说,谁知道这是哪儿啊,司机东看看西看看,背对着杨桃说,这是城北。
杨桃的包不见了,走出很远,她才发现那个在茫茫雪地里独行的身影如刀削一样空空荡荡。包没有了,手机就没有了,所有录在手机通讯录上的电话号码,一个也记不起来。她觉得大脑的所有皱褶,平坦得如一块运动场。
4
杨桃没有止步,她追逐着一盏灯,在灯的尽头好像有更多灯隐约闪现。雪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仿佛雪本身就是夜晚,夜晚本身就是雪。风从前面来,一会儿又从后面来,包裹着她,考验她的脸颊会不会比风还硬。
如果她埋头走路的话,她看到的只是脚下一片乱轰轰的脚印,这些脚印或深或浅,有长有短,却没有一枚是清楚的。如果她在风里抬起头看看前方的路,她马上就看到了那盏变换着大小光圈的灯,还有更远处许多时隐时现的光亮。
杨桃期望这时有行人路过,老远地,她也会紧跑几步冲过去,或结伴而行,或打听一下路线,她无法在这个寂静的路上独自辨识方向找到一条捷径。有一刻,她站在原处,四处张望,没有人经过,比四处里的黑色更让她胆颤心惊。
几个人走过来,背着包,提着杂物,杨桃问,请问这里是哪里?
那些人走近了,一个人在灯光下嘻嘻笑,说,我们也是赶路的,不知道路。
杨桃再问一句,没人回答,呼啦啦从她的身旁急冲冲走过去。
杨桃跟着他们后面走,大约十米,然而,他们越走越快,离她越来越远。
她看到了路边有一个烧烤摊,一个中年男人在收摊。他重重地把家什搬到脚蹬三轮车上,低声咒骂一只扬头听他训斥的大狗。气光灯下,男人脸皮粗糙,眼神凶恶,他停了手里的活儿,冲着马路骂天气,满腔仇恨。
后来,骑着三轮车的男人从后面赶上来,超过去,又折返。嘴上的烟头一明一灭。
“要不,我带你一段?”
“不用。”
三轮车就跟着杨桃的身边慢行。
“车费你看着给,我不多要。”
“我打车。”杨桃转脸看了这男人一眼,说。
男人粗鄙地笑:“这里你能打到车?做梦吧。轻轨站不远,坐轻轨吧。轻轨比地铁好。”
“为什么?”
“轻轨在地上,地铁在地下。”
“地上和地下有什么分别?”
男子哈了一声说, “地上是做人,地下是做鬼。”
杨桃便不说话了。
男人对三轮车里的狗说,“人家瞧不起咱这破车,不坐拉倒,咱不上赶着,上赶着不是买卖。谁比谁差哪儿了?都是三顿饭一张床,都是爹生娘养的,都有生老病死,你当官的有退休那天,你发财的有破落那天。站着比谁高,躺着一样高,最后都去阎王爷那报道。有啥了不起的!”
男人在身后高一声低一声跟他的狗说话。说倦了,突然嗷地喊一嗓子,像夜空被刺了一刀,又被撞回来,咕咚一声落到雪地上。接下来是歌声,听不出是什么词,听不出什么调,每到停顿,那只狗便呜噜一声,和一下。那男人的嗓音像是受过专门训练过的美声。
到了轻轨站,那男人在身后大声跟狗说:“就当今晚咱学雷锋了,她瞧不起咱,咱也送她一程。这叫仁义。”
杨桃进了轻轨站浑身哆嗦,视力突然模糊。她甚至想回身跟那个一路跟在后面的男人说一声谢谢。
橙红的轻轨在地下轻轨站台的灯光里,颜色十分耀眼。杨桃一时无法适应这种颜色,坐到座位时,举目望出去,空荡荡的车厢里,有两个年轻人低头看手机,一个中年妇女系着一条花色繁杂的丝巾,抬脸正向她张望,沧桑、憔悴,心事重重。
轻轨车厢进出的门上方,有一块路线牌,杨桃走到跟前去,眼睛却一时看不清站名。她只能看到一条条线在那张图上纵横交错。喇叭里报着站名,用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昏沉的灯光下,这两种语言像灯光一样含糊不清,仔细听,广告语的声音甚至比站名更清楚——是在卖一种药。
杨桃发现她脑袋里的一张地图不见了,她用力想,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把那块牌子上的线路与脑子里的地图联系起来,只觉得熟悉,却没法判断。她站在那块牌子前很久,望着窗外黑影幢幢的楼宇一闪而去。
杨桃转过身向车厢里的两个年轻人求助,她问这是哪儿啊?
年轻人说,你要去哪儿?杨桃说,我要回家。
年轻人相视而笑。接着,他们都下车了。杨桃跟着他们下车了。
5
雪停了。
杨桃站在十字路口上,四处有车有人有灯光。耀眼的灯光,打得她满脸满衣,金光灿烂。杨桃坚定地站在那儿,仿佛缩小成一粒沙粒,迷失在一个巨大而璀璨的时间沙漏里,茫然失措。因为十字路上的任何一条路的方向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勾引着她。这样看来,不是雪迷失了某个方向。
杨桃向出租车招手,竟没有一辆车子停下来的。
闹市啊,繁华的地方啊,怎么会打不到车?
杨桃向前走了一会儿,她看到一个寂静的公车站,广告牌上的一个男子手里举着一座楼,冲着她笑。站牌上有一排站名,她在密码一样的字里找不到她通常乘坐的车号。
一个穿着深色衣服的人从马路的对面向这里跑,跑到近前,对杨桃说,我看你在这里转悠半天了,你在干吗?
杨桃想了想,还是回了话,说,等车。
那黑衣人说,夜半三更,你等不到车了,车都回家睡觉去了。车需要休息,路也要休息。休息的时候它们在思考,决定把哪一类人送到哪一条路上去。当然,走在路上的人更需要思考。你回头看看你身后那些人,那是不懂思考的人。
杨桃便看到了一条马路的左侧酒店里走出来的一群男女,他们嘻嘻哈哈笑,一
声比另一声还高,夜空里便是一片诡异的笑声。
杨桃说,我脑子里的路线图不见了。
黑衣人说,你确定是现在不见的?你能肯定不是很早以前就不见了?
杨桃说,我没注意到是什么时候不见的,但现在肯定是不见了。
黑衣人说,以前你的路线图就不见了。但你不是一直还在走路?所以,路线图见与不见都不影响你最后的方向。其实大家最后都会走到一条路上去的。
从酒店里走出来的那伙人路过他们,黑衣人自语:“终日拈火择香,不知身在道场。”
黑衣人点了支烟,没有要走的意思。黑衣说,你从哪儿来?杨桃说,我从单位来,黑衣人又问,那你要到哪儿去?杨桃说,我要回家。
黑衣人说,回家这个概念有点含糊。杨桃问,那你从哪儿来,要到哪里去?黑衣说,我从应该来的地方来,要到应该去的地方去。
杨桃突然就笑了,“废话。”
黑衣说,大家都说废话,我为什么不能说?
他们都在那里无声地笑。
杨桃正正经经地说,我要到自由大路去。可我脑袋里怎么也找不到路线图了,丢了。
黑衣人说,你的心太急,急而不定,不定而不静,不静不能安,不安何以能虑?你脑子里的路线图丢了很正常。不过,没有路线图没关系,无非是多走走路。多走路多见风景。比如你吧,你要到自由大路去,那你知道不知道从现在站着这个位置起步,你得先找到解放大路,沿着解放大路走,你才能走到自由大路上去?是很长的一段路呢。
杨桃说,没关系,我有的是时间。
黑衣人点头说,我知道你有的是时间。时间就是用来打发路的,人是用来打发时间的。但谁也打不败时间,只能把时间当成恋人。
杨桃说:我们是顺路吗?你能陪我一起走吗?
黑衣人说:不顺路,我刚从自由大路回来。现在我要去飞跃路。我不能陪你一起走,我不是那个陪你走路的人。
杨桃说:你能给我一个提示吗?比如我何以以最短的时间走到我的目的地?
黑衣人说:不能,所有的提示都不靠谱。我现在不给你提示,别人的提示你也不要相信。就像雪,你相信了它,雪融了,是水。
杨桃说,你像是在给我布道。
黑衣人说,这个世界没有道,只有心。若无心,人则不人,物则非物,道何来之有?
黑衣人转身淹没在黑色里,像一片巨大的镜子深处投进了一个背影,越陷越深,直到幻成一面镜子。
杨桃举头望向夜空,寒星闪着冷光,如钉在一件巨大深蓝褂子前襟的无数纽扣,又刺穿了那件褂子,想透露真相。杨桃觉得自己快步走进了那个真相,四处里金星炫目。
6
绵细的雪里,飞扬着风,杨桃素面白
衣,发丝一缕缕飘到半空里,衣袂飘然,容颜姣好。她站在突出的一块悬崖处,把自己站成了披枝盖叶的玉树。
可是,稍一低头,杨桃便看到深不见底的深渊。更远处,天与地接壤,云涛汹涌,天地相合,无半点纰漏。身后的那个人只差半步,感觉到他局促的呼吸。杨桃说,如果你拉住我,你会跟我一起掉下去,或者我们站成两棵树;你如果打算逃离,眼下为时不晚。
这梦醒来时正值医生说话,他靠着病床站着,说病人被人送进医院来已是凌晨,轻度昏迷。又用安慰的语气说,这种病患我们经常遇到,生命既脆弱又顽强,没事没事!
眼下,杨桃的病床在十四楼,单间,靠窗。在落地窗敞开式的格局里,杨桃最先看到了一片苍色天空,无云,无风,满天明亮。接下来,她看到了一只放在她枕边的男人的手,骨节包在细白的皮里,指甲修剪整洁。男人的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沓打印纸,上面的字迹清晰明了。男人掂着那沓纸说,这个故事好,最上乘的。又说,我来接你回家。
杨桃脑子里的路线图哗地一下子展开,一抹阳光穿过玻璃照耀在那张路线图上,又轻盈又温婉。
现在,从我们这里看过去,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杨桃与一个女子擦肩而过。那女子的相貌与衣着打扮与杨桃一模一样,女子越过杨桃的身体,走进色彩鲜明的人群,她们之间便有一条汤汤流淌的人河,把两个人越推越远。
不知道杨桃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女子,但我们看到,就在杨桃与那个女子一错身的当口,她的手紧握住另一只手,她的脸,美艳如花。
但是,很快,我们又发现,这张脸消失不见了,转瞬间,诞生一张新脸。
我们知道,大学教师杨桃,家住南环路市府西街,伊甸园花园小区13栋2206号;我们知道,那个偌大的伊甸园花园小区隐藏在一片树林里,楼房依四面缓坡错落其间,缓坡推下来的深处,是一片变化莫测的湖水;我们知道,杨桃在傍晚时分经常站在自家窗前注视着湖面,看别人在小桥上自此岸到彼岸来往穿行,但自己从未通过那座桥;我们还知道,自此以后,再没有人在那个小区里见过杨桃。
杨桃到哪儿去了呢?!我们无所知晓。
责任编辑 杨 希
肖 达
某高校文学教授。90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以创作都市题材中篇小说为主。出版中篇小说集 《上邪》,长篇小说 《一张碟》。著有长篇散文 《途经秘密》,文论 《文学的味道》等。中篇小说曾多次入选年度选本,多次入选 《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等文学选刊。曾多次荣获各类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