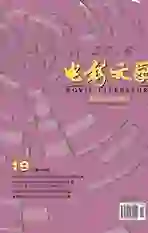《荒野猎人》的影像表达
2016-12-07李拜石
李拜石
[摘要]《荒野猎人》在2016年伊始成为影视界和大众文化领域的热门话题,其诗意的影像表达、极富震撼的视觉冲击,是导演伊纳里多的拍摄理念与摄影师卢贝兹基摄影美学的契合,也是影片反映出的美学格调。其长镜头的娴熟运用,强烈的影像风格,对生命的书写和诠释,光影营造出的寒冷意象,丰富了影像表现的可能性,穿插的梦境画面构图也拓展出更深层次的意蕴。用镜头剥去文明的层层体面,求生的原始本能里,人和野生动物一脉相承。
[关键词]《荒野猎人》;长镜头;生命;影像
2016年伊始,《荒野猎人》成为影视界和大众文化领域的热门话题,一举获得第73届金球奖剧情类最佳电影奖、最佳男主角奖和最佳导演奖后,又斩获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和最佳摄影奖,在国内上映三天票房即飚过两亿。暴力、血腥、残忍、极富震撼的视觉冲击,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多导演的野心之作,在艺术与商业上都获得了成功与认可。当然,就叙事本身来说,《荒野猎人》的故事线有些松散单一,其情感的传达也大多依赖文化语境,对史诗的构建亦是过于克制、欲语还休。除却莱昂纳多可圈可点的出众演技外,本片最为人所称道的还是其影像的表达,长镜头的娴熟运用,使得奥斯卡最佳摄影奖实至名归。
一、长镜头的美学格调
《荒野猎人》的摄影师艾曼努尔·卢贝兹基,以擅长运用一镜到底的长镜头著称。巴赞根据自己的“摄影影像本体论”提出和蒙太奇概念相对立的理论,确立了长镜头的必要性。巴赞认为,长镜头能最大限度地表现时空的连续性,是保证电影逼真的重要手段。在《荒野猎人》中,唯美、恢宏而又逼真的长镜头画面为观众提供一种浸没式的观影体验。同时尽可能用最少的剪辑完成最流畅的镜头,这也是导演亚历桑德罗拍摄理念与摄影师卢贝兹基摄影美学的契合。
在《荒野猎人》中,长镜头确为其保持了时空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在镜头的运动中实现空间的自然转换,实现局部与整体的联系。作者电影的表现力和空间感在一系列长镜头段落中呈递得淋漓尽致。从大广角甚至天远地阔的超大广角至人物本身,再转换至人物周边,流畅完美,一镜到底。广角镜头下,洛基山脉的壮丽风光一览无遗;镜头平缓地将物静与人动串联,天地人自然一体;摄影机在山林河流之中随着人物跨越奔走。大广角在尽可能远阔地摄入了风景之后,又给了主角格拉斯不少广角特写,由他的面部延至以外的景会随着光学畸变而弯曲,造成一种有些眩晕的美学感觉。
全景长镜头美学一般极富现实的表现力,《荒野猎人》的长镜头里表现的空间是实际存在着的真实空间,这些镜头充满了张力,体现了娴熟的场面调度能力,清晰地交代了故事所处环境以及人物的基本特征,展示出一种雄浑开阔的空间感,将电影的荒野气氛调动得非常到位。银幕前这些浸淫成长于工业技术时代的观众,被拉回到一个机器悄然起步的时代,那个时代还处处书写着蛮荒,自然和荒野之光笼罩影院。电影以其特有的语言表达出美学诉求,摄影艺术的美,存在于自然的韵律,存在于社会的法则,存在于摄影师自我追求的美学格调之中。卢贝兹基的镜头美学是将人置于野生动物的旁观视角,随着叙事的推进保持追踪。
二、原始的生命影像
“在画面的造型问题上,真正的影像化表达不是运用花里胡哨的电影手段,而是写实地(虽然也是有选择地)运用所产生的价值。风格不需要改变现实,而应该选择现实的特定方面加以呈现。”《荒野猎人》有着强烈的写实影像风格,甚至学习和趋近于纪录片的影像表达,鲜血、搏斗、撕咬、伤口、死亡,每个场面和细节都逼真得让人触目惊心。影片对自然环境的描绘,从不吝画面,几乎与人物角色平分秋色。空镜头其实并不“空”,这里其作用并不仅是艺术性地烘托气氛,还丰满了几乎占一半表述空间的主题。山林、莽原、厚雪、河水……这些蛮荒少人烟的自然条件,一方面让格拉斯的生还与复仇增添了许多艰险;另一方面又让他借助这些自然元素逢凶化吉,展现出人类生理动物性的状态,食生肉,吃生鱼果腹,以熊皮和马尸取暖求生。在这里,就生命的原始状态和求生本能而言,人与动物似乎并无二致,以极本真的姿态融入了荒野。
主人公本来台词就不多,情节设置中又因为被熊抓伤了喉咙导致声带受损,干脆让其处于失语状态,发音基本都是喘息和呻吟声。除了这些声音的补充,影片的影像就显得尤为重要,大部分需要画面来说话。语言本来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明显标志之一,更是文明的象征之一,可即使正常人,在危及时刻也可能会出现失语的情况。当生存成了第一需要,身而为人再次回归动物本性的时候,喊叫和喘息便成了身体与自然连接,向外界唯一能发出的求救信号。
无论是印第安人还是白人的队伍,在森林和旷野中骑行的时候,都似乎成为另一种野生动物的群体。曾经有人指出生命也是一种“混沌”状态。人类对自我物种的认识在其赖以生存的植物和动物世界里是完全独立,区别于其他物种的,但更多的是基于理性和“文明”社会的判断,仅就其血肉之躯而言,退回到生命的无知之幕背后,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人与那些所谓低等的生物仍然是一脉相承的。“影像的功能,诚如果戈里所说,是在表现生命本身,而非生命的理念或论述;它并不指涉或象征生命,而是将它具体化,表现它的具体风貌。”卢贝兹基用镜头剥去文明的层层体面,生命的原始欲望里,人和野生动物并无本质不同。
三、光影营造出的寒意
《荒野猎人》的时空设定是冰天雪地的寒冷季节。片中对自然场景的调度自如,森林与雪原中光影的捕捉和运用,都展现出明显的特点,为影片打上鲜明的创作烙印,从头至尾寒气逼人。这种寒冷是两个层面的:自然景观环境的寒冷;主人公生存与复仇的彻骨寒意。
《荒野猎人》的舞台是大自然,主要取景地是在加拿大阿尔伯塔以及阿根廷南部,雪山、流水、冰森林都是百分百的原生景地。风景极美,但拍摄条件艰苦。据剧组称,拍摄地点遥远,冬天下午3点就会天黑,剧组只能每天选择下午1:30到2:45这个时间段进行拍摄。因为完全依靠自然光拍摄,并且所有场景在野外-30℃的冰山和野林中实景拍摄,画面展现出清冷的黑灰色调,分分钟让人感受到那种在极寒天气中拍摄的艰难与痛苦。Collide网站曾发布过对卢贝兹基的采访,他说:“在排练中我们逐渐意识到,我们想用比较清透的镜头,让人自始至终能够看清故事发生的周遭环境,让人能一直与演员的内心世界、内心挣扎以及自然环境的外部力量产生联系。”
导演的镜头很开阔,叙事却极为克制,极强的画面带入感,阴郁的冷色基调,直抵人的感官本能,将观众置于彻骨的寒冷之中,让银幕中的人物在饥寒交迫之中,在危机四伏如同猎物的恐慌笼罩下,甚至让主人公格拉斯亲眼目睹儿子被杀,自己被背叛丢弃,在深深的绝望之中,去体会角色的残酷命运。
从陨石坠落划过天际到壮观的雪崩,从基督教堂遗迹的壁画到格拉斯仰望牛骨堆,拍摄者在摄影内容和形式上形成了一股追求自我意识、实践人对精神家园的寻求、坚持信念的思想。这是个性化的摄影观念建构与叙事方法的塑造,显现出一种对表达的话题更为敏锐的洞察力与更加流畅运用的把握能力,找到属于自己的视觉语言,不仅让自己的影像具有独特的内涵和视觉面貌,同时也丰富了影像表现的可能性,拓展了“寒冷”更深层次的意象。
如同《与狼共舞》中对白人西部拓荒的反省,时隔多年,《荒野猎人》旧瓶装新酒,以寒冷和荒野的意象演绎出印第安人的神秘气息,展示出其与西方文明对撞时遭受的冲击。利用视觉表现力来表达一个关于生死、关于复仇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镜头中表现出了静态的美,同时还有万物的浩瀚和苍生的无力。
镜头下冷漠沉静的“野地”能提供生命的另一种向度、一种超越时空和经验的能量,那是一个清冷而安详的空间,似乎和亿万年前没大区别。当人深处于寒冷的腹地,离所谓人类的文明社会越遥远,时间和环境就仿佛凝固了。广阔、缥缈等仿佛就在灵魂深处回荡,那种古老和原始的生机给人的震撼越发显出其大。
四、梦境的画面构图
电影是一门造型艺术,影像以画面来传达,影视画面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综合体,是全方位立体于矩形平面的展现,构图、光影、色彩、角度都集中在这个综合体上,这个方框世界要把这些要素表现在无穷尽的变化组合之中。电影艺术走向现代,其表现模式也已突破了在固定模式的画幅之内完成画面造型任务的局限。构图的前提是构思,而观众对画面的审美思维也由封闭式思维转向开放式思维。多元化的思维、意识的流动、开放的构图形式,是突破画幅固定局限的有力手段。
《荒野猎人》的故事简单,除了将观众带入主人公逃生的艰险经历,在主体叙事里又插入梦境,让电影的节奏时不时跳出线形情节演进,进入一种抒情性的意境。恰恰是“跳戏”的梦境流露出导演强烈的主观表达欲,梦境的画面仿佛主人公的内心独白,经过了精心的布局和构图,也就有了更深层的寓意。
电影摄像是动态的,但在《荒野猎人》中穿插的梦境画面、镜头的移动缓慢,和主人公在现实中的奔逃、与黑熊的生死之搏等境遇形成反差,区别开来。主人公现实生活中的大特写和强烈动感充满了残忍血腥,镜头切换节奏较快,而梦境的“静”则是轻声却坚定的呓语,无论是人物出现,还是教堂景观,都带有宗教般的圣洁和心灵安抚的意味。在梦境的影像中,起落幅的动态变化节奏较慢,因此,即使定帧,画面也很好看,每一幅都充满了油画般的美感。
开场的梦境中,用了斜拉对角线的构图,画面的重心是右侧这端格拉斯的背影望向对面,中间有一棵枝叶繁茂的树,左侧有留白,而树似有若无地将妻子和孩童时期的儿子隔开在那一端,三个人形成一个三角形状,儿子似乎正在向妻子那边跑去。妻子和儿子的人像都很小,背后是茫茫的云天和黑沉沉的大地。整体逆光拍摄,没有人脸,人物与环境色彩一致,并毫无违和感地融入环境。画面有一种强烈的艺术张力,反映出主角记忆中一家三口的幸福时光,但同时也由梦境中的这一幅图提示出格拉斯与妻儿在生命的此岸和彼岸隔世远望。
在格拉斯梦里反复出现的妻子常常是用仰拍的镜头,仰拍一般多为褒义,会让被拍对象有了庄严、高大的形象,在感情上起到升华的作用。在这里表达出格拉斯对妻子的感情,同时也流露出拍摄者的创作意图,以拍摄角度赋予格拉斯的印第安妻子天使的形象。妻子遇害后的俯拍构图则有种普世的悲悯情怀,自然光打在她的脸上,妻子表情安详地躺在地上,与大地融为一体,胸口飞出的鸟儿,更让她的逝去有了通灵的意味,似乎灵魂去向了另一处乐园。
“影像的技术载体,与其社会作用一样,始终在演进。电影是在摄影摄像的复制和传播、新观赏形式(活动画景)和快速运输新手段(铁路、汽车)的出现改变了与可见现实的关系的时刻发明出来的。电影影像因其与时间的关系和‘记录性可信度而具有明显的现实印记。”荒野是人类以外的众多生命样态的家园,曾经是独立于文明之外、一种广袤纯粹的自然成就。在影片的尾声中,格拉斯努力地喘气,镜头逐渐模糊,远处只有模糊的太阳穿透出少许光线,格拉斯的呼吸声从四周包围而来,依旧是辽阔的长镜头,天地一片安寂宁静,如初创世时。当复仇的信念远去,万物仍在,荒野之中,每一种生命都有其特定状态,都会以自己生命固有的形式顽强存在。
18世纪以来,荒野在美国文化传统中一直处于神秘、特殊的地位。从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现实中的美国人爱国热情高涨,急需寻求精神慰藉的家园,找到一种能蕴含美国精神,体现美国特色的文化元素。直面荒野的艰辛,也是对人类原罪的救赎,人与自然本身亦不可分割,于是孕育万物、自由而原始的荒野即成了美国新大陆文化的象征之一。18世纪以前那种认为自然和荒野是粗俗、落后、危险的观念逐渐退场,文学和艺术纷纷把视线投向荒野,将其作为文化和艺术灵感的源泉。这一母题取之不竭,不断演进,《荒野猎人》以唯美诗意又独到的镜头记录下了美国文化这一寻觅的过程,表达出笃定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