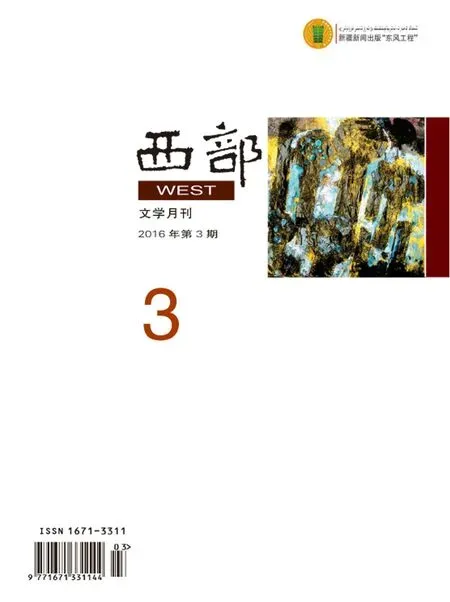跨文体风物小记
2016-12-07赵瑜
赵瑜
跨文体
风物小记
赵瑜
之一:寒同山道士
山下有果子吃,桃子,杏,色泽好。
桃子脆甜。入口时犹如古筝曲子的第一声弹奏。几乎是不约而同的,我们都说,呀,这桃子,吃了会成仙的。是啊,这么好吃的水果,就长在这神山下面的田地里。
山不高,叫寒同山。“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说的就是寒同山了。寒同山在旧时本就叫“神山”,因为相传山上的神仙洞为张果老和吕洞宾二位仙人所造。
只是传说,当不得真的。果然,晚上回到宾馆的房间,查看莱州杨黎明先生的文章,知道寒同山上的修道洞穴乃是莱州道士宋德芳所修,是依照了他的师傅刘长生的意愿。
山上有道观,需要介绍的是,道观的主人姓王,叫合林。他们世代居于此道观,到了王若林这一代,已经是第八十九代掌门人了。说是掌门人,却并没有徒弟侍奉。世俗生活将道教的信仰慢慢融化,上得山来,看到的第一个招牌,是毛笔大字:雪糕。
王道士有六七十岁的模样,挽着发髻。清冷,仍然是世外的模样。同行的人介绍他说,整天在山上生活,王道士一身的功夫,上山下山几乎可以飞檐走壁。
王道士带着我们看神仙洞,一口地道的莱州方言。这方言让我们对道士的生活充满了好奇,从元代开始,王姓家族一直更替住在这座山上。道士多是清居的,而王道士是火居的。火居,自然是要食人间烟火居住的意思。相当于佛教中的居士,在家修行,可以结婚生子。所以,王道士成家,是一个亦道亦俗的修行者。
王道士介绍了造洞的简单经历。在旧年月里,在山上凿出一个可以居住的大洞来,这几乎是有悖于生活常识的。为什么不能在半山坡修建一所房子呢?就地取木,岂不是节约许多?然而,道家讲究的是脱离日常的欲念,作为一种修行的方式,仪式感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这历经辛劳修成的神仙洞,完全摆脱了老百姓日常居住的理念,让前来跪拜的信众生出敬畏。甚至参与修建神仙洞的群众,因为积了这功德而有了好运,也会成为当地百姓相互传说的内容。
王道士给我们介绍洞里的石刻。两条龙,从旧有的光阴里来,盘在那里。那是有“神情”的两条龙,仿佛经历了数百年岁月,居住在墙上。人来的时候,就安静地贴在石壁上,等到夜深无人,两条龙就会在山林里飞翔,或者到不远处东海龙王的神庙里,聚会,议事。一切都不可知。
两条龙深镌在石头里多年,早已有了生命。
王道士介绍完两个山洞,又带领我们向山上走。他走得快,在前面停下来,看着我们相互讨论。他每天都带着不同的客人上山,有分辨的能力,大抵也知道我们的来处。
山上有风,风吹来鸟的鸣叫,又或者是更远处大海的波涛声。王道士向着山的远处看,每一天,他都会站在不同的地方向着山的远处看。他比我们更熟悉世间的事,风向,季节的更替,树叶的颜色,以及由此带来的世事人情的变化。
山上居一日,人间已一年。这是比喻。而在山上,看得更远,能听到更为清澈的风声,能看清楚更多云彩奔走的方向,甚至能更早一些摘到星星。这林林总总的感受,可不就是山上一日,丰富过人间平庸窘迫的一年。
一直想安静地在王道士家里吃饭,看他在田里干活,看他查阅家谱、记录收入,看他在世俗与道家之间如何平衡。这是日常的,也是哲学的。这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
在王道士清风明月的气质里,我仿佛看到道教的清修对于世俗中人的影响。我看到了矛盾出现时,道家火居士的挣扎。世事简单又复杂,而王道士的仙风道骨,绝不仅仅是被山上的风吹的,而是他内心的生活一点点造就的。
之二:仙叠岩的冬天
这里只有风。
风吹来涛声,便有惊涛拍岸,这样也好,倒让人觉得有一股苏东坡的诗意。
远处有工人在悬崖边上修栈道,有幽远的声响传来,叮叮当当的,总想站在他们近处,看他们一会儿。或者只想听到石头发出的清脆声响,那声音最终会跌落在深海里,消逝。
渔船在海里打捞近海种植的海菜,要么是紫菜,要么是羊栖菜,总之,渔船上的人是喜悦的。
若是逢了夏天,台风来了,仙叠岩的石头会发出鼓声,风一直弹奏着一曲无人能懂的乐曲,整个小城都得失眠。
这才知道,原来,这些石头是乐器,等着风从海上来,在合适的季节奏响。
春天的时候呢,想来是婉约的,草绿月柔,只能在虫子安静的时候,才会有风轻拍石壁,奏出一曲高山流水的雅调。夏季自然要热烈的,风卷起浪花,击向岸边这高耸的岩石,除了爱意,更多的时候,这音乐和内心的追逐有关。或是梦境里虚幻的桂冠,或是生活里诱人的奖章。这激烈而轰动的声响,每一年都要发作一次,提醒日常生活的人,活着不能过于平庸,要有叙述的高潮。
而这是冬天。风夹着大海睡眠的气味,石头上的草枯黄着,一场音乐会已经散场的模样。我和友人往灯塔处走,曲折处看到石壁上的摩崖石刻,觉得像是看到古人的留言。
古人喜欢在石头上刻字,他们信任石头最为坚固,能将他们的心思传递给后人。而之所以选择在一些名山大川刻字,是觉得,这些名山也好,大川也好,不过是一个“网址”,会吸引不同的人前来观看,甚至回应。这样一想,古人在石头上的留字,竟然和现在的人在微博上发言一样。
终究是因为有些寂寞需要出口。
而从海上到来的风在这里找到了出口。沿着山路下行,回望,可见仙叠岩叠成记忆的石头。
风将石头刻成了画,刻成了古旧的图书,或者一段漫长的时光。总之,时间停在这些石头上,时间就停在石头与石头之间。时间茂盛着,时间又荒芜着,就这样,时间长出了草,时间又生出了游人的赞叹。
天若是晴好,站在仙叠岩的灯塔附近,可以看到海对面的基隆港。这也是旧时光的一种,这里曾经是驻扎了军队的。和对岸的人对峙着,保卫着一种信仰。
和友人往山洞里钻了一下,幽暗,寂寞,我感受到的不是军事基地的神秘感,而是夜晚风吹动海浪的声音。这些声音执著而激动,把人的内心湿润,让人失眠,想起陈年的旧事,或伤心不已,或寂寞难耐。总之,这样封闭的空间里,实在想象不出,人该如何抵挡夜晚的风声,以及冬日石头的凉。
仙叠岩的冬天,除了风,还是风,是风与风的叠加。除了海水,还是海水,是海水与海水的叠加。除了涛声,还是涛声,也是涛声与涛声的叠加。夕阳的光铺过来,更是时光与时光的叠加。站在仙叠岩斑驳的石头上,往山顶看,看到三三两两的游客往小庙里走。
在这里,只有庙宇烧着的香火是温热的,其他的,都被寒风吹彻了。
游客们在风中拍照片,描述着这些石头的样子。他们把仙叠岩石头的样子带走,却带不走这里的风声,也带不走海浪拍打岩石的声音。只有站在这里,静静地听,才能听懂这些风说了什么,而那些浪又应答了什么。
仙叠岩的冬天,孤独。来到这里的人,总会被刻在那岩壁上的时间叫醒。看着那时光深处的静谧,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夏天,需要热烈的事物。
之三:南长街的夜
似乎,南长街的夜色和无锡的黄酒类同,透明,温和,差不多,小口喝下,有想要跳舞的感觉。
在此之前,我刚刚坐船赏了南长街古运河的景致,和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相比较,这里安静,甚至幽深。船过清名桥,停在一片古老窑址边。是旧时专门给城墙烧制金砖的一些窑口。那时,筑城墙,每一块砖上都有印记,年月久了,损了破了,便会根据那砖上的印文找到生产这砖的窑口,照着旧有的尺寸,再重新烧制。
旧时的风物,总是充满了出处。那是我们文化的根部,只要根部的文化是健康的,繁华自来。
回来,便看到夜色中的黑陶。我们之前见过两次,喝过茶,谈论过夜色。这一次,我竟然来到了他的家乡。
茶馆的名字在灯笼上,红红的。临河,就着这古运河的水,我们忆念起旧事。南长街适合回忆过去,这旧式的建筑是一个磁场,一进入,我们就被时间软禁,不得不说起从前。
黑陶要了宜兴的红茶,宜兴,一把紫砂壶就可以代表。黑陶的父亲,便是一个老窑工,是一个懂得火候的人,正是他,将黑陶烧制成一个诗人。
我们说起了诗句、书法、文学的元素,包括适于泡在茶水里的古镇。黑陶喜欢背包四处游走,有时候,他到一个地方,会记下那里的广告,然后写在文章里,寻人启事,杀猪启事,治疗性病的启事,等等,这些文学细节,无法虚构,却又像是虚构的一样。
南长街原本是无锡最为穷困的一条老街,拥挤而热闹。因为临水,早些年也是商业街,剃刀铺,打铁铺,杂居,仅想象着,便能闻到《清明上河图》里的气息。如今,这条街道,成为这座城市里最有年代感的生活标本。城市建筑的同质化,让这条古街的气质慢慢显露。而外出旅行的城市青年,被北京后海、成都宽窄巷子,又或者是丽江古城、凤凰古城一类的风景启蒙。回到自己的故土,才发现,原来,南长街两岸,才有最动听的音乐。
正是因为城市发展的迅疾,才有了城市人的怀乡病。可以说,古镇的复苏,是治疗城市人病态的一味中药。
但是,这味药却充满了审美。比如,我和黑陶兄选择的这家茶馆,从布局到设计都充满了文学的元素。这家茶馆的老板是江南大学的美术教师。
差不多,到这里来喝茶的人,也被茶馆老板的审美所熏陶。审美的,必然是让人愉悦的。城市单调而乏味的物质生活,比起这慢悠悠的喝茶时光,便显得粗鄙而苍白。
一起喝茶的还有作家王曼玲,一个“曼”字,让这个夜晚曼妙起来。黑陶的爱人写散文,却热爱读小说。四个写作的人,对着夜色,念着这座城里还有钱锺书,便又觉出一座古桥的好处。是啊,人只有过了桥,才能走得远一些。
在此之前,我喜欢喝祁门红茶,不浓不淡,养胃,醒神,是我最近几年喜欢上的。而宜兴的红茶呢,多了一味厚道,比祁门红茶的味道迟缓一些,比福建红茶要淡一些,但却耐回味。
宜兴的茶,如果配上宜兴的窑口里烧制的陶杯就好了!我相信,那是绝配。
茶喝完了,夜已深。和黑陶退出小茶馆,在南长街上慢慢走回酒店。
路边的小店里还坐着不少年轻人,安静。灯光在运河里摇曳着,如同一部金基德电影的开场。
我对黑陶说,在这样的夜色里,应该醉了,才能走。是啊,如此安静的石板路上,没有一个醉酒的人,实在是一篇庸碌的小说。
在这样一个秋夜,无锡,南长街,风软,月凉,一个写作者,不论醉不醉酒,不论喝不喝茶,不论吟不吟诗,都是幸福的。而且,还有好友相伴,还可以谈论音乐,美味的食物,以及可以反复阅读的文字。
这些,都是极好的。
之四:梵净山云朵
缆车上一个背着相机的师傅,温和地看着我们,不语。他将手上捏着的红色收据收好了,放进兜里。
他已经随着缆车走了一圈了,该下来的时候,他拿着收据对着工作人员说,我和你们的王总说好了,我要坐两圈,才能拍到云海。
云海。我们记下了。
梵净山一年四季的景色不同,所以,常有旧地重游的客人。
我们上山的时候晚了一些,山脚下的雨对我们的行程造成了困厄。等我们走到半山腰的时候,雨停了。山里的气候,谜语般难猜。
坐在缆车上,从雾岚中穿过,我们觉得正走在一首唐诗里,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吟出:“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以前只是理性背诵着这样工整的句子,现在,我们意会到了这景致中的微妙。云深,不知处。不仅仅是不知道采药远去的师傅的位置,连我们自己的位置也丢失了。
有关云彩的模样,我写过诗句的。但大体是仰视的角度,云彩通常在高温的气候下浓郁,透亮。在海南,我见过厚度不等的云彩。在去三沙的船上,我看过风将云彩吹散后的霞光。在北方的村落里,我记得雪后的天空突然堆起来的云朵。这些都是迷人的记忆。云彩是天空永远不变的剧情,几乎,除了日月,它就是天空的别名。
而梵净山的云彩是可以采摘的果实,和我们日常仰望到的云朵不同。梵净山的云朵是流水,是山里的溪水,是一场雪,是雪后的几声鸟鸣,是涂在我们眼帘上的画,是永远也擦拭不掉的一缕感动。
缆车走到半山处,左侧的舷窗打开了,我们突然看到了云海。云在山与山之间奔跑着,像是喜悦的,又像是哀伤的。树丛的绿色在云朵的深白色映衬下变成了黛色,或者紫褐色。云朵比我们的眼睛要宽阔,比我们的想象力要跑得快。
看起来它们并没有流动,可是只一会儿,它们便向着幽远的暗角涌去,仿佛有人正收拾它们,一块一块地折叠它们,将它们随手扔在了某处幽暗里。
山在云彩里隐藏着,树也是,流水声也是,在半空中,俯身看着这浪花般的云层,觉得呼吸也突然通畅起来。仿佛经络里的某处开关,在瞬间被打通。吞吐的同时,也就融入这云彩的开放与流动中。
在飞机看到的云层也漂亮,但那是高空中的铺排,几乎是雪域,是梦境里永远无法走出的一次惊吓。
而在梵净山所看到的云朵,是织物,是舞蹈的女子在舞池边刚刚摆下的造型,是婉约的词句,是中国画里工笔的部分。
梵净山是一座佛教名山,和凡尘的距离,就用这样一池云锦隔开了,仿佛,山与山之间的这些云彩是几声晨钟,是几声鹤鸣。
我们将要到山顶的时候,看到远处的云彩里透出一束光,光照下的山林迷人,让人觉悟。
云里雾里,常常指代人所处的观看世事的位置。而这一次,我们穿过世俗的云层,来到了梵净山的顶端,端坐在空中,看破了云里的事,雾里的事,看透了云中的水,林中的鸟。在半山处看云,竟然有一种顿悟的错觉。
从云里雾里出来了,我们伸手,便触到了真相,本质的自我,甚至是陌生的念头。
是真的,看过梵净山的云之后,我觉得以前放不下的心事,明澈了许多。没有做完的一些琐碎事,曾经让我焦虑的利益,都在那云朵的恍惚中变得轻浅,甚至无足轻重。
下山时所看到的云海与上山时不同,大概是云彩的流向不同,所呈现出来的气象也有差异。下山时遇到的云内敛、谨慎,像是得道的佛。
而我却更喜欢上山时看到的云,浓郁有时,浅淡有时,畅快有时,暗淡有时,像是在红尘中经历了挫折的人,有了进步,获得了理智,总是得体而自由的。
我们习惯赞美需要仰视的物事,月光的缠绵,阳光的浓烈,风奔跑的速度,以及雨来临时的畅快,却从不知还有在半山腰可以踩在脚下的云。
梵净山的云,这开在深山的花朵,这安定灵魂的乐曲。我想隐居在这里,种花,养蝶,做三年的梦,并吟诵长长的佛经。白天的时候,如果有人来寻,我会泡茶招待,让他看云彩的舞蹈。夜晚的时候,我写字,看书,有人来觅,便留字条:只在此山中。至于云深不知处,那是觅者的事情。
那该多好。
之五:塘河
过一座小石桥,船慢了下来。阳光藏在桥的另一侧,藏在水里,被船荡漾着,又顺着水波爬上船。船上的人都伸了伸腰肢,沿着光,向外面看。桥上晒满了被子,驳落着,油画一般。这是温州城的日常生活。
有少妇在桥边的石阶上洗衣服,差不多,这注释了河水的质量。船已经出城了,房屋变矮,岸边小路上的汽车也少了许多。城市仿佛在一条河的衬托下变得慵懒了。就在刚才,在出发的码头那里,城市还拥挤不堪地关注着道路信息,以及生存的种种。现在,城市被水流冲洗干净了,四周有了鸟鸣,有了果园和庙宇。
这是温州市郊的村庄,差不多每隔一里水路,便有一座庙宇。有的庙宇沉稳些,是旧时的建筑。有些呢,刚刚装饰一新,有一种主动出示的庄重。这些庙宇占地不算小,在城市日益物质的时代,它们盛放着本地人的灵魂。
船上有来自内陆省份的友人,用手机不停地拍水的波纹。城市里的河水不比山间的川流热闹,塘河的水安静温和。总觉得,温州这个名字的来历和一条心情静谧温和的河流有关。塘河,几乎容纳这个城市里所有的争吵和市声。不仅仅如此,入夜的时候,这流水也会将人世间嘈杂的心事带走。
早些年,温州的交通多从水路走,塘河两岸的人家是最早醒来的。醒来便意味着听流水的声音。凭着那水流的声音,这些临水居住的人便可以推测出风向,以及天气的好坏。阴雨天时,出门的人少,船就泊在岸边,谁家孩子淘气,在水里抓了几条鱼,不拿回家,偏要扔到别人家的船舱里。这户人家,便能听到船舱里的鱼的蹦跳声。去捡了来,便将鱼吃了。这也是常有的事。
说起鱼,塘河的鱼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遇到了灾难。城市化的过程,意味着城市人口的增加,意味着物质的丰富,意味着生活被拉长,而自然被破坏。那么,鱼类遭了殃。“河里的鱼虾都死绝了,被污染后的河水就连拿来洗刷马桶都嫌脏。”这是我在一则新闻里看到的话。
我们对一条河犯了罪,河水自然也会报复我们。他们报复的方式简单,就是发出臭味,提醒我们。
河水由清澈变污浊,又从污浊变得清澈。这个过程我并不陌生,有时候,在一些公众的场合,我会因为水的污染和别人辩论。我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我喜欢安静的东西,如果非要发展,我喜欢缓慢地发展。显然,我是同河流山川站在一起的。有时候,我把自己当作河中的一条鱼,想象着自己在水变得污浊的时候,呼吸困难,痛苦,直到死亡,便会想,若是有人能救下我,多好。
现在,我们一群人坐在船上,看着塘河水泛着生命的光泽,岸上的景致映在水上,云朵也是。河水里的鱼被救了。被救的还有我们自己。我们为这样的深秋上河图所陶醉。被洗衣服的人,被在桥上晾晒衣物的人,被伸出头来和路边人说话的临河人家的女人,被划着小船打捞水面上漂浮物的工人打动,我们被热爱这条河流的人打动,也成为热爱塘河的人。
河的另一岸有一片果园,不用说,栽种的是瓯柑。农夫打扮的人从果园里将一筐筐绿色的柑橘运出来,放到船上。也有黄澄澄的,温州友人说,那是成熟的。青涩的果子呢,也是甜的,果农们摘下来可能就是为了多放几天。
没有热闹的收获场景,这条河上的生活差不多像一场黑白电影。只是这场电影不需要票,没有剪辑。一条河将他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有了可以观看的意趣。
若是盛夏,河水里定然有游泳的人。温州友人说起河里的鱼,是最近刚刚放到河里的,还小。所以,岸边不见钓鱼的人。在旧时,每每下雨天,塘河岸边便聚集了钓鱼的孩子。差不多,这条河盛放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
友人又说起龙舟的事,以及早些时候,结婚时的船队模样。想想便让人欢喜,这些在唐诗宋词里住了很久的事情,温州的人一直做着,没有间断,这便是历史的况味,也是文化的传承。
在白塔寺的墙上,看到宋代温州诗人叶适的诗句:“有林皆橘树,无水不荷花。竹下晴垂钓,松间雨试茶。”这几句诗描述的便是塘河两岸的生活。
橘树如今依旧,茶园也是有,只是河里的荷花不见了。若不然,经过盛夏的怒放,如今已经成了残荷的画面,一定会让这条河有水墨画的韵味。
用水墨来形容这条河的风情,倒是妥当。在塘河的两边,除了刚刚修葺一新的庙宇,更多的是留下来的两层旧式的青砖黛瓦的临河民居。若是下了雪,河与民居形成黑白风格的构图,定是格外好看。
有一些破败的民居被本地人开成了颇有意味的茶馆,入夜以后,会有不少城市里的人前来,临着街,就着茶水,说说生活里的琐碎。就这样,听着流水声,日常生活的烦恼便烟消云散。
曾在北京短居,在北京的胡同里来回穿行,总觉得那是时间的证据,我们在那样破败的胡同里闲走,就是为了看看时间的留言。后来,又去过一些古城和小镇,甚至城市里被保存下来的古街。成都的宽窄巷子,无锡的南长街,南京的秦淮河,北京的后海……这些被人们当作怀旧对象的景点,虽然已十分商业化,却仍然留有让我们内心柔软的风物和信息。
在塘河的船上坐着,从城市的闹市区出来,一点点远离中心,渐渐走到疏离的郊外,再走到僻静的白象塔。我感觉像是已经走了很多年。一船的友人在嬉笑间,突然白了头发。
这只是幻想。我们在这样安静的水面上行走,磁场断断续续,内心里最为强烈的念头是能向旧时的某座桥上走一走、某首诗里走一走。凑巧,同行的人中,很有几枚诗人。我甚至也从他们的眼睛里借到了几句诗:
塘河,我只有简单的背包
装不下你深处的甜
你的滋味,是一声鹭鸟的浅吟却足以将整个橘园里的梦唤醒
跨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