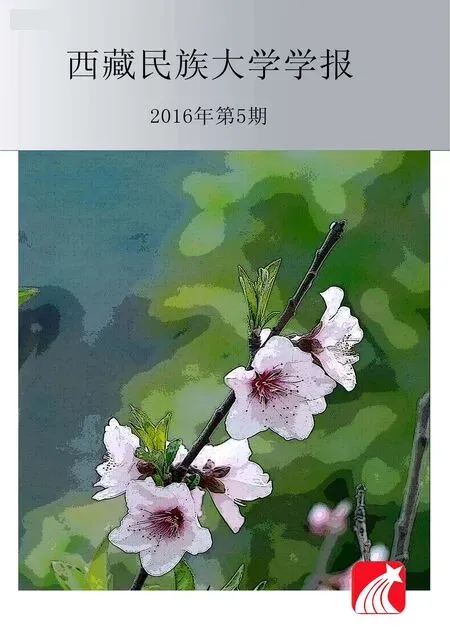论《后汉书》李贤注的文学文献价值
——以东汉文学研究为中心
2016-12-06高明
高明
(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论《后汉书》李贤注的文学文献价值
——以东汉文学研究为中心
高明
(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初唐李贤《后汉书注》为现传最早的范晔《后汉书》注释,该书补充疏证《后汉书》史事,保存了一些重要的文学文献。李贤注汇集大量东汉文学作品,为确定后汉作品文本提供了重要参考,是文学作品辑佚的重要来源。李贤注重词句训释、典故疏解,许多后汉文学作品的最早注释即源于此。同时,李贤注还可以为文学研究提供一些珍贵资料。《后汉书》李贤注的文学文献价值应该得到进一步重视。
后汉书;李贤注;文学文献;东汉文学
今本《后汉书》120卷,“纪传”部分为刘宋范晔所撰,“志”部分为宋人取梁刘昭注晋司马彪《续汉书》“志”汇入范书。最早为范书作注的为梁刘昭,继之而起者为唐章怀太子李贤。李贤注充分吸收刘昭注的精华,调整补充了注释重点,详刘注之所略,在疏通文字语句等方面下了很大工夫,对阅读研究范书大有裨益。
范晔《后汉书》是了解研究东汉历史文化的基本材料。从文学角度看,无论是作家作品,还是时代背景、文学思潮等文学研究的重点问题,在《后汉书》中均有大量涉及。李贤注既有刘昭注补充史实的成分,又有疏通文义,方便阅读的功效,自然对《后汉书》中所蕴含的文学材料有所阐发。有关《后汉书》李贤注的研究,多关乎史学,鲜有掘发其文学材料者。本文即以此为切入点,力图揭示李贤注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文献价值。为讨论问题的方便,本文将论述范围限定在东汉一代,对李贤注中其他文学材料,暂不涉及。
一、东汉文章的汇辑
文学文献的核心是历代文人创作的大量文学作品。作家艺术风格、不同文学流派以及创作理论的研究都建立在作品分析研读之上。作品保存的是否完整,制约着文学研究的深入。就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唐宋以下的作品保存较为完整,汉魏六朝文学作品散失严重。东汉文学作品的保存主要依赖总集的编纂、别集的刊刻和类书及注释等其他文献的引用。
东汉以后,随着文学创作的进一步繁盛,总集和别集应运而生。据《隋书·经籍志》,从晋挚虞《文章流别集》后,唐代初年存世的总集,共计107部,
2213卷。如果加上其间散失的,总数可达249部。《隋书·经籍志》收录后汉留存及亡佚别集共69部①。唐宋以后,绝大多数汉魏六朝以来编纂的总集均已散失,完整保存至今的,仅有《文选》、《玉台新咏》等几部。到明清时代,汉魏别集也基本全部散佚。今天流传的汉魏别集,均非原貌,多为明人重新编辑刊刻。清人顾千里在明活字本《蔡中郎集》十卷后跋:“东汉人文集存于世者,仅此一种,尚是宋以前人所编,其余无之矣。”[1](P353)《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集部别集类”《蔡中郎集》提要亦曰:“其集至隋已非完本……《宋志》著录仅十卷,则又经散亡,非其旧本矣。”[2](P1272)蔡邕为东汉著名文人,其文集命运尚且如此,其他汉代文人别集的流传情况可以想见。
由于总集和别集的散失,唐宋以后类书及注释等其他文献中采录的大量文学作品,在总集和别集的重新编纂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辑佚取材的重点。如唐代编纂的《艺文类聚》,因为收入大量汉魏六朝作品,“隋以前遗文秘籍,迄今十九不存,得此一书,尚略资考证。”[2](P1142)注释著作中如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等也在辑佚中被广泛采用。李贤的《后汉书注》引用了大量东汉文献,在文学作品汇集中也有一定作用。
李贤注《后汉书》引用多部东汉别集。例如《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传》附班固传载其上东平王奏记:“弘农功曹史殷肃,达学洽闻,才能绝伦,诵《诗》三百,奉使专对。”[3](P1332)其中的“殷肃”后,李贤注:“《固集》‘殷’作‘段’。”[3](P1333)这里,以《班固集》的异文,解释《后汉书》中涉及的人名,提醒读者注意《后汉书》资料来源的多样性。再如《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传》:“自去史职,五载复还,乃设客问,作《应闲》以见其志云。”[3](P1898)李贤注引《张衡集》云:“观者,观余去史官五载而复还,非进取之势也。唯衡内识利钝,操心不改。或不我知者,以为失志矣,用为闲余。余应之以时有遇否,性命难求,因兹以露余诚焉,名之《应闲》云。”[3](P1898-1899)此处紧扣“应闲”,利用《张衡集》中文字为之作释。据统计,仅《后汉书·张衡传》一卷,李贤注共引用《张衡集》达17次之多。
李贤注引用的东汉别集还有许多,甚至包括一些今天文学史中很少提及的作家别集。如《蔡邕集》5次,《马融集》4次,《冯衍集》8次,另外还有《崔骃集》、《崔瑗集》、《孔融集》、《黄香集》、《朱穆集》、《傅幹集》、《陈琳集》、《王粲集》等。
除明确标示外,李贤注暗引文献,也极有可能来自东汉文集。如《后汉书》卷二八下《冯衍传》:“惟天路之同轨兮,或帝王之异政;尧舜焕其荡荡兮,禹承平而革命。”[3](P992)李贤注引班固曰:“仰天路而同轨。”[3](P993)又卷五九《张衡传》:“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秽累而票轻。”[3](P1920)李贤注引班固《幽通赋》:“矧沈躬于道真。”[3](P1920)上引班固两段文字,均出自其《幽通赋》。李贤的引文来源可能就是当时流传的《班固集》。这一推断,是否可能成立?且看《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传》:“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3](P2006)李贤注引《班固集》云:“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3](P2007)此引文为班固对司马迁《史记》的评价,更容易得到的材料无疑应该是《汉书·司马迁传》。李贤注舍《汉书》而用《班固集》,说明做注时对《班固集》的重视。
李贤注在东汉作品汇集中有重要作用,有时,这种作用具有唯一性。也就是说,从辑佚材料的来源上看,有一些作品,如果没有李贤注的保存,可能就会失传。例如《后汉书》卷三四《梁统传》附梁竦传:“竦字叔敬,……既徂南土,历江、湖,济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骚赋》,系玄石而沈之。”[3](P1170)李贤加注,引《东观汉记》所载《悼骚赋》全文。梁竦的《悼骚赋》承骚体赋之余韵,表达了怀才不遇的感叹,有一定文学价值。本传中说他:
以经籍为娱,著书数篇,名曰《七序》。班固见而称曰:“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梁竦作《七序》而窃位素餐者惭。”[3](P1171)
能得到班固的高度称誉,其作品可同孔子《春秋》相提并论,梁竦在当时文苑的地位可见一斑。而据严可均《全后汉文》,其流传作品仅此一篇。如果没有了这篇赋作传世,是否能够在东汉文坛为其争一席之地,恐怕很成问题。另外,梁竦作《悼骚赋》的记载,见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唐宋类书,但各种类书,都没有具体收录这一作品,李贤注是现传保存《悼骚赋》的唯一文献,其作用不可
替代。
李贤注产生时,抄本仍然是文集流传的主要方式,李注所引抄本均早于流传至今的各种刻本。深入挖掘这些材料,也能发现相关文本校补的新材料。
如《后汉书》卷四三《朱穆传》:“穆又著《绝交论》,亦矫时之作。”[3](P1467)李贤注谓其集中载此文,并略引其文,共计235字。朱穆《绝交论》,在唐宋类书中多有保存,但文本差异较大。《艺文类聚》卷二一引后汉朱穆《绝交论》曰:
世之务交游也,甚矣。不敦于业,不忌于君,犯祀以追之,背公以从之,事替义退,公轻私重。[4](P397)
《太平御览》卷四一〇引后汉朱公叔《绝交论》曰:
世之务交游也,甚矣!不惇于业,不忌于君,犯礼以追之,背公以从之,事替义退,公轻私重。[5](P1893)
《册府元龟》卷八二九载朱穆作《绝交论》事,并在附注中略引其文,其文字同于《后汉书》李贤注。可以推测:《册府元龟》的引文正是出自《后汉书》李贤注。显然,从朱穆《绝交论》文本的完整性看,李贤注优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且早于《册府元龟》。严可均在辑此文时,正是使用李贤注提供的材料。
文集流传中字句异文,在李贤注中多有保存。如《后汉书》卷五九《张衡传》:“所考不齐,如何可一?”[3](P1903)李贤注引《张衡集》“考”字作“丁”。[3](P1904)又卷八〇下《文苑·祢衡传》:“《激楚》、《杨阿》,至妙之容,台牧者之所贪。”[3](P2654)李贤注:“诸本并作‘台牧’,未详其义。《融集》作‘掌伎’”[3](P2655)。又卷二八上《冯衍传》:“杀人父子,妻人妇女,燔其室屋,略其财产,饥者毛食,寒者裸跣。”[3](P966)李贤注:“毛,草也。臣贤案:《衍集》‘毛’字作‘无’,今俗语犹然者,或古亦通乎?”[3](P967)李贤注保存的这些异文,未必一定就是原作之貌。但因其时代早于现今流传的各种版本,在各家文集的校勘整理中仍不无价值。
二、东汉文章的早期注释
《隋书·经籍志》:“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6](P1089-1090)别集、总集的产生,是东汉以后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时代较近,语言文化还未造成阅读障碍,魏晋南北朝时期总集、别集的注释数量不多。直至今日,汉魏文学作品的注释,数量仍然很少,而且多为明清以后人所做。如在文学上成就较高的曹植,唐宋以后其集已非旧貌,而流传至今影响较大的注本,大多也是明清以后出现的,如清丁晏的《曹集铨评》、清朱绪曾的《曹集考异》及近人黄节的《曹子建诗注》等②。其他汉魏文人作品缺少注释,也在情理之中。
文学作品的注释,汉魏时期就开始出现。《诗经》和《楚辞》作为特殊的两类文学文本,其注释西汉即有数家,毋庸赘言。其他各类文学作品的注释也大多从这一时代开始。考《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经籍志》,发现早期的作品注释主要是以两种方式展开:一是汇集赋等特殊文体的作品,集中做注③。二是以《文选》注释的面目呈现。从注释的内容看,有的侧重释义,有的侧重注音,也有两者兼顾的。
《隋书·经籍志四》“总集”类收有《杂都赋》十一卷,其下原注:
《二京赋音》二卷,李轨、綦毌邃撰;《齐都赋》二卷并音,左思撰;……亡。[6](P1083)
同卷还收有《杂赋注本》三卷,其下原注:
梁有郭璞注《子虚上林赋》一卷,薛综注张衡《二京赋》二卷,晁矫注《二京赋》一卷,傅巽注《二京赋》二卷,张载及晋侍中刘逵、晋怀令卫权注左思《三都赋》三卷,綦毌邃注《三都赋》三卷,项氏注《幽通赋》,萧广济注木玄虚《海赋》一卷,徐爰注《射雉赋》一卷,亡。[6](P1083)
以上所记各书,梁代以后,陆续亡佚。但像薛综的《二京赋注》、刘逵的《三都赋注》、徐爰的《射雉赋注》等,为唐人李善《文选注》采录。借助《文选注》,可以窥见各注的基本面貌,大致是以训释词语、阐发文义为主。同时,以上赋注多以“音”来命名,成为文学注释文献的新类型。《旧唐书·经籍志》著录班固《幽通赋》一卷,最早的注释为曹大家,即其妹班昭。如果此说可信,则赋注东汉中期就已形成。
《文选》注释大量出现,成为早期文集注释的另一个突出特点。《隋书·经籍志》集部总集类有《文选音》三卷,萧该撰。《旧唐书·经籍志》还收有公孙罗、李善、释道淹等人的《文选》注释著作。因《文选》中收录了大量东汉文章,这些注释可以看做是东汉文章的较早注释,直至今日,对阅读研究东汉文学,仍有重要价值。
从内容上看,李贤《后汉书注》对东汉文章的注释,基本沿袭了魏晋以来文集注释的基本特点,突出在释词义、通文意、揭典故、补史实、明语源等几个方面。如《后汉书》卷八十下《文苑·郦炎传》为例,该传收郦炎诗二首,其一为:
大道夷且长,窘路狭且促。……富贵有人籍,贫贱无天录。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陈平敖里社,韩信钓河曲。终居天下宰,食此万钟禄。德音流千载,功名重山岳。[3](P2647-2648)
李贤注共为这首诗出注6处。其中“窘路狭且促”后注:“窘,迫也。”[3](P2648)是以训诂来解释词义。“富贵有人籍,贫贱无天录”后注:“富贵者为人所载于典籍也,贫贱者不载于天录。天录谓若萧、曹见名于图书。”[3](P2648)是通过串讲来疏通文句的意思。“陈平敖里社”后注:“陈平为里社宰,分肉均。里中曰:‘善哉陈孺子之为宰也!’曰:‘平宰天下亦犹是。’见《前书》。”[3](P2648)是引用《汉书》来解释史实。
东汉文章,因别集、总集的散失,注释本就缺乏,李贤注因而就成为这些作品的重要注释来源,有的篇章注释甚至会是流传至今的唯一古注。《后汉书》收录东汉作品众多,如此大规模地为作品详加注释,李贤注在提供文章早期注释方面的价值不容忽视。
将李贤注和李善《文选注》加以对比,更可凸显出李贤注在东汉文学作品注释方面的价值。从时间上看,李贤注释《后汉书》大约开始于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六月,完成于上元三年(676)十二月,历时一年半左右。④而李善《文选注》的完成时间,一般确定在唐高宗显庆年间(公元656-661),稍早于李贤《后汉书注》。
从总体数量上看,《文选》所收作家,在《后汉书》中有传者共12人,即班固、张衡、班彪、班昭、马融、孔融、朱浮、王延寿、崔瑗、蔡邕、傅毅、史岑等⑤。《文选》共收作品30篇,其中2篇为李善采录旧注,其余各篇均为李善汇集各种材料重新作出的新注释。同样是这12人,《后汉书》收文篇目和《文选》有很大出入。现将其中班固、张衡和蔡邕三家统计对比如下⑥:

显然,单纯就收录作品并加注的数量来说,《后汉书》李贤注和《文选》李善注差异较大。《文选》中选录的大量文学艺术性较高的作品,在《后汉书》中未予收录。同时,许多东汉作家及作品,《文选》未予收录,《后汉书》中却多有记载,李贤注均有详略不同的注释。
如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卷五《汉诗》共收录傅毅诗歌2首,其中《迪志诗》即来自《后汉书》,李贤注也有较为详细的注释。《傅毅集》,《隋志》二卷、《新、旧唐志》均记载为五卷。北宋《崇文总目》无记载,大概当时已经散佚。因此,李贤为《迪志诗》
所作的注释,应该是这首诗最早保存的注释。
再如孔融《报曹公书》,《文选》未收,《后汉书》卷七十《孔融传》中收录,李贤注也有详细的注释。《孔融集》,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收录,但也仅有原文,可见,直到明代《孔融集》仍没有精良的注本。1991年吴云的《建安七子集校》在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孔融的作品并加注释。1994年,路广正的《孔融集校注》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2013年夏传才主编的《建安文学全书》中有《孔融陈琳集校注》,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样,孔融作品才有了比较详细的注释。李贤注对孔融相关作品的注释,远远早于以上几部著作,虽然注释的作品数量有限,但作为孔融作品的早期注释,其价值仍应重视。
三、东汉文学研究的重要线索
秦汉文学研究,面临多重困难,其中作家和作品界定的困难与史料的缺失相互交织。⑧文学研究的出发点是文献材料,由于秦汉文学材料保存的特殊状况,深入挖掘和分析材料,对秦汉文学研究而言,就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从微观的角度看,一篇遗文的发现,一则史料的挖掘,都有可能改变文学史的部分论述。扩大史料搜索的范围,珍视“只言片字”,注重揭示文献的深层含义,这些都将有助于秦汉文学研究的深化。《后汉书》李贤注中包含大量东汉文学发展的微观材料,可以为研究东汉文学提供相关线索。
东汉文集,唐宋后大多散失。其篇章组成,更不得而知。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作家及其创作的理解和认识,也给汉魏别集辑佚造成了许多困难。《后汉书》李贤注广引文献,相关注释有助于理清散失文集的构成情况。
如《后汉书》卷二八下《冯衍传》:“所著赋、诔、铭、说、《问交》、《德诰》、《慎情》、书记说、自序、官录说、策五十篇,肃宗甚重其文。”[3](P1003)李贤注:“《衍集》有《问交》一篇,《慎情》一篇。”[3](P1004)又注:“《衍集》见有二十八篇。”[3](P1004)《冯衍集》,《隋志》别集类著录,共五卷,《新、旧唐志》亦著录为五卷。宋元以后典籍没有记载,大概在北宋中期已经亡佚。明张燮《七十二家集》中辑入《冯曲阳集》二卷,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收入《冯衍集》(一名《冯曲阳集》)一卷,共有作品十七篇。严可均《全后汉书》卷二十共辑得冯衍文二十九篇,其中包括一些残句。显然,从宋代到明清,《冯衍集》已非原貌。李贤注依据当时见到的冯集,确定《问交》和《慎情》为其中两篇,对辑佚材料的编排有一定帮助,为恢复冯集原貌提供了重要线索。
知人论世是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作家生活时代,作品创作背景,是文学研究的基本材料。《后汉书》记载东汉历史,关系东汉作家群体生活样态。许多历史细节的记叙,都成为理解作品、研究作家的关键。李贤注补充史实,细化历史,常常可以提供文学作品创作的具体背景。
如《后汉书》卷四三《朱穆传》:“穆又著《绝交论》,亦矫时之作。”[3](P1467)李贤注略引《朱穆集》中《绝交论》原文,共235字。《绝交论》采用主客答问的形式,表现了作者宁受人疾,而不愿与世俗交游的高尚节操。但文章并未紧贴“绝交”二字。朱穆“绝交”,是针对当时浇薄的社会风气而发,还是有其具体对象,《后汉书》原文并未明确,李贤注所引《绝交论》中也找不到端倪。这一疑问不能解决,会直接影响对这篇文章的理解。李贤注引朱穆《与刘伯宗绝交书》:
昔我为丰令,足下不遭母忧乎?亲解缞绖,来入丰寺。及我为持书御史,足下亲来入台。足下今为二千石,我下为郎,乃反因计吏以谒相与?足下岂丞尉之徒,我岂足下部民,欲以此谒为荣宠乎?咄!刘伯宗于仁义道何其薄哉?[3](P11468)
又引朱穆《与刘伯宗绝交诗》:
北山有鸱,不洁其翼。飞不正向,寝不定息。饥则木揽,饱则泥伏。饕餮贪污,臭腐是食。填肠满嗉,嗜欲无极。长鸣呼凤,谓凤无德。凤之所趣,与子异域。永从此诀,各自努力。[3](P1468)
此书及诗,均应来自《朱穆集》。刘伯宗,与朱穆为友,后汉文献无其事迹。从上引诗文可以看出,刘氏本人贪欲无极,爱慕虚荣,反复无常,有违儒家仁义之道。这正是刺激朱穆写作《绝交论》的
直接原因。当然,朱穆在《崇厚论》对东汉“风化不敦”亦有针砭,对“虚华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纯笃稀”的社会风气慨叹有余,这也是《绝交论》创作的大背景。《朱穆集》唐宋以后已散失,刘伯宗在东汉文献中无迹可寻。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李贤注所引用的文献,《绝交论》的创作背景很难完全理清。
文学研究中,常有许多细节问题,诸如作品署名的真伪,作者的生平等。这些微观问题,是文学文献研究的重点,也是文学史宏大叙述的基础。将这些问题考证清楚,才能最大程度保证文学史叙事的准确科学。李贤注在这方面也可以提供一些非常宝贵的线索。
严可均《全后汉文》卷四五收入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严氏注明辑佚来源:“《古文苑》。”[7](P719)《古文苑》相传为北宋人孙洙得于佛寺经龛中,《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集类《古文苑》提要谓:“其真伪盖莫得而明也。”[2](P1691)严氏依据《古文苑》辑出所谓崔瑗的《河间相张平子碑》,是否真实可靠。《后汉书》卷五九《张衡传》论:“论曰:崔瑗之称平子曰‘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3](P1940)李贤注:“瑗撰平子碑文也。”[3](P1941)范晔论中所引“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正见于严可均《全后汉文》从《古文苑》所辑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李贤作注时代,早于《古文苑》的发现,李注所依据的应该是当时还流传的《崔瑗集》。李贤注虽寥寥数字,但从一个侧面解决了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的作者和真实性,也为《古文苑》真伪问题的考证提供了新的材料。
经历南北朝,汉魏文献大量散失。李贤注处于抄本向版刻转化的关键时期,当时文集开始流散,但损失还不像后代那么严重,李贤作注时仍然能够见到为数不少的汉魏文集抄本。许多汉魏时代的文章,因李贤注的引用,被保存下来,使文集的重辑更趋完善。李贤注对《后汉书》所载作品的随文注释,成为编排新的校注本的重要参考。能否充分挖掘李贤注中的材料,仍直接影响着校注本质量的高低。李贤注还能为文学史研究提供一些关键线索,在许多微观问题的解决上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总之,全面探讨《后汉书》李贤注,认真分析其中的具体问题,可以推动东汉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后汉书》李贤注在东汉文学研究中的文献价值还有待一进步挖掘。由此引申:包括李贤注《后汉书》、颜师古注《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郦道元注《水经》等众多注释文献,由于时代较早,引用文献众多,深入挖掘这些注释材料,对先唐文学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注 释]
①依据《隋志》“集部别集类”统计,取其中属于东汉的别集,包括注明梁代亡佚的别集。
②关于《曹植集》的流传,可参葛兆光《古诗文要籍叙录》中《曹植集》的介绍,中华书局2005年,页208-211。
③有关东汉赋注的深入研究,见踪凡《东汉赋注考》,《文学遗产》2015年第2期。
④参见周晓瑜《李贤注〈后汉书〉起讫时间考》,《文史哲》1991年第5期。
⑤东汉作家的确认,标准依据曹道衡、沈玉成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中华书局1996年版。
⑥《后汉书》收文的统计主要依据严可均《全后汉文》。“文章”取广义概念,即包括纯文学作品和应用性文体。各文的题目依严可均书。
⑦括注为文章在《后汉书》中出处。
⑧参见刘跃进《秦汉文学史研究的困境与出路》,载《文学遗产》2003年第6期。刘文谓:“研究秦汉文学,面临的最大困惑还不是史料的匮乏,而是如何确定研究对象的问题。”其实,研究对象的不易确定,除了同文学观念相关,史料的匮乏更增加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1]顾广圻.顾千里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5]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6]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7]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责任编辑 池万兴]
[校 对 夏 阳]
I206.2
A
1003-8388(2016)05-0121-06
2016-06-13
高明(1970-),男,陕西西安人,现为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典文献学、中古汉语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