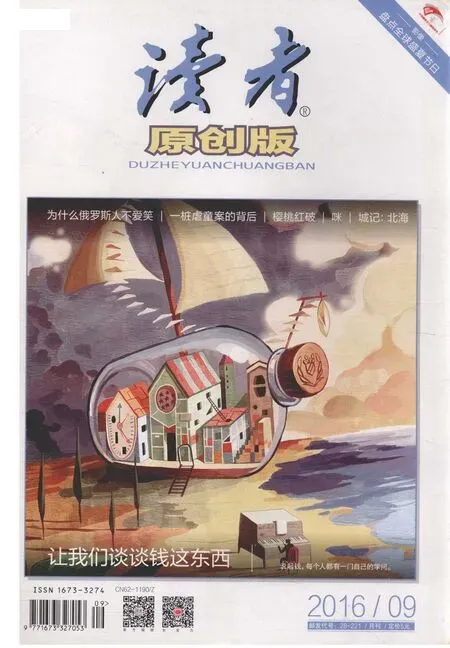人情与金钱
2016-12-05文_多多
文_多 多
人情与金钱
文_多多
一
成家后第一次与父母爆发激烈冲突,是在弟弟找工作时。
弟弟那年在南方某985大学计算机专业读研究生三年级,职业理想就是留在学校所在的城市做程序员。这份工作收入可观,他的想法也具有可操作性,全家人都很支持。
谁也没想到,2013年就业形势那么严峻,弟弟一次次碰壁。有一次他深夜打来电话,失声痛哭。
我没有告诉父母—对已经退休的老两口来说,再担心儿女的事情,恐怕也帮不上忙吧。但我们不说,不代表他们不知道。
突然有一天,老妈悄悄告诉我,爸爸托了表姐夫的哥哥,认识了一个老伯伯,隔三岔五要带着礼物去拜访一下。原来,那个老伯伯的儿子是某国有银行的高管,老爸想通过这层关系,让弟弟参加银行在当地的招聘考试。
我一听就头大了。
且不说他们自作主张有可能打乱弟弟的人生规划。我太了解父母,在他们的生活圈子和60年的生活经验里,人情高于一切,这样急着贴上去求人家帮忙找工作,必然要花钱来搭建、维系这份人情。
果然,认识一个多月,老爷子住了两次院,过了一次生日,再加上平常串门,爸妈几个月的退休工资花出去了。
平时精打细算、连买把青菜都要在菜市场走三遍的老两口,面对这样的人情花费,毫不手软。但这份“慷慨”让我心疼。
我坚决反对父母再去打人情牌、拉关系。我的想法是,弟弟的工作让他自己搞定,父母过度干预,是对他的不信任。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我不相信人情,更不用说是这样临时搭建起的“人情”。
我自读大学起,就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小城,也终于逃离了盘根错节的人情网,读研、找工作,我相信并依赖的是商业社会的法则。这在我看来,公平且高效。
但在当时,我和父母,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件事情最终以弟弟进入一家互联网公司告一段落。那时,那家银行的招考甚至还未开始,但父母从不认为自己花了冤枉钱。
也是,在他们大半辈子的人生经验里,为人情花的钱,是一定要花的,没有值与不值之分。
二
自记事起,人情往来的花费就是我家的一项重要开支。
从我成年后与闺密交流的情况看,我们很多人的家里,都有一本人情账,记录着每笔人情往来的礼金。在我家,那账簿上的内容也是父母常在饭桌上交流的话题。
“老张家快要嫁闺女了,我们得包个红包。”
“嗯,就比照上次老王家娶媳妇吧,几家关系都差不多。”
“好。唉,这个月又要超支了。”
这样的对话,几乎每隔几天就会在我家餐桌上上演一次。我看到了出身农家的父母小心翼翼地搭建人脉、维持生活体面的不易,也看到了身为工薪阶层的他们“宁可亏自己,绝不亏别人”的捉襟见肘与坦然。我的人情往来的观念、与人交往中分寸感的把握,多半是经由这样的对话建立起来的。
我刚结婚时,父母来我生活的城市玩,无意中翻到了婚礼上的礼金簿。爸爸大为惊讶:“份子钱真少!”当时在这座城市,两三百元便是正常的人情往来,同学、同事之间有什么事情,互相捧个场,这算是拿得出手的数字,也不会对生活有什么影响。
而在老家,稍微近一点儿的关系,500元才是“起步价”,父母几十年苦心经营,朋友、同学、同事、邻居……各种关系都有不同的价位,虽不是明码标价,但大家心照不宣。
与此相对应的,是人情往来的种类繁多。结婚,生小孩,孩子升学,老人生病、去世,乔迁新居,买车,都有相应的宴请,自然都有份子钱。
听起来就头疼,但父母乐在其中。他们在名目众多的宴请理由中,衡量着自己与他人关系的远近,亦享受着给人帮忙张罗的被需要感,在这过程中,一次次强化“人情大过天”的观念。
三
这两年,父母一直在帮我带孩子,于是自然而然地将他们对人情世故的看法,带到了我的小家庭。
孩子生病,我和先生带着他去三甲医院排队挂号、取药,打吊瓶时没有床位,孩子就躺在楼道的加床上;孩子要上幼儿园了,我家附近只有一所公立幼儿园,硬件好,师资强,价钱便宜,但入园非常难。
每逢此时,父亲就一再念叨:“我早就说了,你们就是不听,人在社会生存,要有两方面的关系,一是医院的,二是学校的。花一些钱,跟人家保持好关系,没什么不好……”
跟亲戚通电话时,他不止一次唠叨我和先生“舍不得那一点儿小钱”。
知道他的一番苦心,但对我们而言,还是听听就算。
我们当然知道,在看重人情的社会,办事情时有熟人的便利性。但对我们来说,这一点儿便利与搭建关系时要付出的时间、精力相比,代价未免太大,老一辈人看重的要花费的钱财倒在其次。
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或者说有敢于不拉关系的底气,还是来自于方方面面规范的建立吧。我相信这规范,并从中受益。
四
弟弟是工作第二年买房的,那时他生活的那座南方城市,房价已经升至一个天文数字。父母拿出大半辈子的积蓄,也只够首付。
对此,弟弟和弟妹觉得很不好意思,那毕竟是父母的养老钱。好在他俩收入不错,每个月的房贷光是公积金就够还了。他俩计划把每月的工资都存一部分,尽快把钱还给父母,父母年纪大了,有钱傍身总归好一些。
他们这么懂事,我也很欣慰。
没想到,过了没几天,父母又给弟弟打过去一笔钱。
我们都很惊讶。原来,不少亲戚朋友家的孩子买房时,父母都或多或少有所表示,帮他们贷低息贷款,或是借一笔钱给他们,大家都很感激。我当年买房没有跟家里伸手,大家都觉得过意不去。这一次,亲戚朋友各家拿出一些钱,说让弟弟他们少还一点儿利息。每家给的钱不算多,但凑在一起也相当可观了。
我和弟弟相当感慨。
对于房贷,我们这一代人视为理所当然,不像上一辈人,觉得房贷没还完就始终不能心情畅快,所有消费都要靠边站。而且,公积金利息相对较低,每月还贷,压力也不大。对我们来说,更怕欠的是人情债。何况,现代人不敢借钱给别人,除非已经做好了不要这笔钱的准备。
没想到,父母从亲戚和朋友手中拿到这笔钱,却是轻而易举。
我和弟弟从重视人情的家庭中长大,自小见证了父母为人情世故所累,一向视人情为“不能承受之重”,成年后拼命逃离故乡,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我们向往更有规则感的都市文明,小城的熟人社会在我们眼中,落后且低效。
但没想到,正是这份人情,让我们感受到久违的温暖。
世界观决定金钱观。父母塑造了我们的世界观最初的形状,却终因时代、环境的变迁,我们的世界观和金钱观,与他们的有了很大的不同。
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好在,我们都能在各自的环境中自在生活。
这样,就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