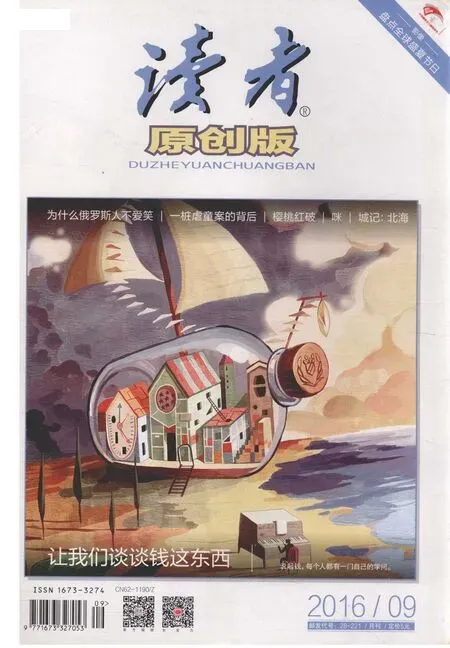财富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意义
2016-12-05DidiWu
文_Didi Wu
财富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意义
文_Didi Wu
一
我好像是个经常“破财”而非擅于理财的人—刚开始工作的几年,攒下的钱本来就不多,所以干脆都用来旅行和培养兴趣爱好。升职加薪之后的几年,终于有了一笔存款,这笔钱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可能也就勉强够一套小户型的首付,于是我干脆在29岁那年把它全拿了出来,让自己去英国重新读一个真正喜欢的专业,算是送给自己30岁的一份生日礼物。
所以30岁的自己突然又变回了20岁时穷学生的状态,当“朋友圈”里在晒旅游、美食和孩子的时候,我的生活却经常是为了下个学年的学费和生活费,用学习以外的时间去接活儿或打工。这个暑假也是这样,虽然6月初学期就结束了,但我接了一个刺绣的活儿,每天从大清早忙到半夜两三点,连着绣了快两个月,手指关节肿得厉害,不贴膏药连拿针都困难。然而,就是这么辛苦地赚钱,本以为解决了下一学年一部分的开销,却不想因为英国突然公投脱欧,导致英镑大跌,这个暑假赚的钱因为英镑跳水全部搭进去了,等于整个暑假的工作都白做了。就在我感叹时运不济的时候,学校发来邮件告诉我说,他们决定下学年给我一笔奖学金,相当于一半的学费。这在把教育当产业的英国,特别是在英国艺术院校绝对算是破天荒的恩赐,这个特大的惊喜让我一秒钟从沮丧中回到天堂,有种“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感觉。
在英国的这一年虽然辛苦,但绝对值得,每一个困难真的都会变成学习和感悟的机会,虽然物质生活远比不上当白领时潇洒,可我一点儿也不委屈,因为我之前从事的并不是自己喜爱的工作,升职加薪并不能给我任何成就感。而现在当真是朝着自己想做的事情迈进,剥离了很多曾经拥有的物质之后,我反而觉得特别踏实。“我是谁”不再关乎公司头衔或者穿什么样的衣服、背什么样的包,而是我正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探索什么样的问题,这样的存在感是根植于自己内心的,而不是印在标签上的。
二
最近翻到20岁那年,还在读大学时给好朋友写的邮件,里面大言不惭地写道:“10年后我30岁,那时候应该已经存到人生的第一个50万或者100万了,这笔钱该用来做什么好呢?是不是可以环游世界了?”现在的我读到这里,着实吓了一大跳,完全不记得自己还有这么个阶段。不过,如果当年20岁的自己穿越到现在,估计也会被当下的我吓一跳。年少的时候看亦舒的书,印象很深的是喜宝说她想要很多很多爱,如果没有爱,有很多钱也是好的。如果两者都没有,还有健康。当时的自己是很赞同这样的想法的。
我也有过爱情大于一切的那种年岁,在校园时,一半时间用来努力读书,另一半时间全花在恋爱和失恋的各种纠结上了。后来进入职场,大都市白领的生活繁忙又复杂,导致真爱难寻,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令健康大打折扣,结果真的只剩下了钱,于是消费便成为最惯常的解压和取悦自己的方式。然而,这种方式换来的欢愉也不过就短短一阵,而且越来越短,然后就买越来越贵和越来越多的东西。现在时髦的吃素、练瑜伽我也尝试过,身体素质有没有变好我没感觉,但心底里一直存在的一种不安与隐隐的空洞却完全没有被救赎。
过了25岁之后才慢慢发现,虽然这三样东西确实重要,但并不是我人生最重要的课题,因为不管有没有爱人、身体是否健康、是否富有,我都会被同一个问题不断地敲击,那就是—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来到这个世界要做什么样的事。这更像一个关乎存在的追问,与吃饭、喝水、睡觉一般属于根本性质,而爱情、健康和财富更像是生活的附加值,有很好,如果没有就慢慢培养,但并不是我生活的全部意义。
三
毛姆写的《月亮与六便士》里提到,很多人出生后的各种配置其实都是错位的,不仅是地理上—生活在不适合自己的城市,更是一种生活状态的错位,比如做着一份不痛不痒的工作,维持着一段鸡肋般的感情,过着不好也不坏的日子。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这么凑合着过下去,总有人要起来反抗这并不理想的“配置”。故事里以高更为原型的男主人公就是如此,终于有一天,他抛弃了自己之前拥有的一切,从头开始学习画画,跑去了遥远的岛屿当一个画家。
我并不赞同毛姆笔下的主人公与过去一刀两断的决绝的方式,但那种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并为之努力的决心,我完全能够感同身受。在我看来,这并不只是向往自由的表现,更是一种向内挖掘自己和探索人生本质的行为。
我本来以为自己在这样的年纪做这样的选择很离经叛道,到伦敦之后,发现以我这样的年纪重回校园读书再平常不过了。在我的同班同学里,有两个退休的英国大婶,已经50多岁,照样不介意拿自己的退休金来重新读本科学位,而且立志要当面料设计师。
其实仔细想来,这样的人不只是欧洲或者小说里才有的。在我10岁的时候,有一位住在同一个小区的老太太来我家找我奶奶,因为她经常看到我奶奶在家教我弹钢琴,所以想让我奶奶也教她。她说她一直想学钢琴,特别喜欢莫扎特和肖邦,但以前没有机会学,现在想从零开始。老太太那时候已经快70岁了,我奶奶担心她的身体状况,而且购置钢琴还需要不菲的费用,但老太太相当坚持,认为自己有时间和耐心,而且完全不介意动用自己并不多的存款。
当时我觉得她不会弹很久,因为要弹到她喜欢的那些作曲家的作品,之前需要的是长达几年大量重复的枯燥练习。上了中学之后,因为上的是寄宿制学校,我弹琴越来越少,高考前自然而然地完全放弃。就在我上大学的某个暑假,我回到那个旧小区,经过老太太住的那幢楼的时候,被窗口传出的阵阵熟练的钢琴声吸引住了,她正在弹肖邦!时隔10年之后,她真的做到了。
我仍然记得自己当时的震惊,更多的则是感动。她那一代人,经历了那么多的动荡和社会巨变,而她选择用自己余生里的整整10年去练就那一曲肖邦,不会是为了任何其他的人,只是弹给自己听。这样的一位老太太,在我心里的分量比所有社会精英、成功人士都要重。因为人生到最后,账户里不论是几百元还是几亿元,都会变成一个带不走的零,而可以不留遗憾地离开的人,一定是找到了并且没有辜负内心深处那个最本真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