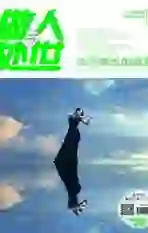寻找失去的记忆
2016-12-03叶子豪
叶子豪
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人
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母亲在生下我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另外一座城市了,这座城市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平城。平静祥和,万世长安。我曾一度以为平城就是我的故乡,但母亲总是摇头。她亦不知自己生于何处,她的记忆似乎出现了差错,将来到平城之前的记忆全部遗忘。
很多年后,母亲垂垂老矣。毕业后我曾参军,后来成了一名神经植入专家,负责管理和记录患者的记忆。彼时神经学的研究进入大脑皮层的最深处,我们已经可以将患者的记忆下载备份,根据患者个人意愿选择回放或删除部分记忆。
我一直致力于研究进入人脑记忆的项目,经过20年的漫长研究,我终于在大脑右叶中找到一块区域,我将其称之为“记忆复苏区”。我研发出一款芯片,将芯片移植到大脑中,我便可以通过磁共振进入患者的记忆之中。但这项技术尚未成熟,风险极大,需要试验。正当我为此焦虑的时候,母亲打电话给我,说她愿意成为第一个试验者。一年前母亲罹患癌症,如今癌细胞不受控制地扩散,她清楚自己时日无多,她想在离世之前找回自己缺失的记忆。再三权衡,我最终同意了母亲的要求。
我将芯片植入母亲的大脑中,和她一起坐在记忆转换器中。随着一声轰鸣,机器发出炫目的白光,而我在极速的旋转中昏迷过去。再醒来时,我发现自己重新回到了十八岁的样子。周围残屋破瓦,硝烟升腾。我手上的年代手表告诉我,我身处60年代末的越南,正是越南战争进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倏地,我看见一架战斗机从上空掠过,直直地扔下一枚炸弹。正当我茫然无措的时候,一只手拉住了我,迅速地将我拽进防空洞,很快,我听见炸弹爆炸的轰鸣,掀起一层热浪。
心有余悸的同时,我转过身,看见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女孩,面色清亮,是那种健康的麦色。我的直觉告诉我她就是我的母亲。我用越南语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她叫羽生,那正是母亲的名字。母亲告诉我,这个地区已经被敌军封锁,每天都会有这样的轰炸。她问我是否会用枪,我点头。她便递给我一把军式手枪,她说男人们都被征去打仗了,女人们得自己保卫家乡。当洞外的世界安静下来时,她紧紧握住手枪,拉着我走出防空洞。洞外的空气依然弥漫着硝烟,我们急急地走过一个街道,打开一个下水井盖,跳了进去。下水道里有很多人,都是老人和小孩,还有一些持枪的年轻女子。我想这里大概就是她们避难的地方了。
我很快就安静下来,开始思索如何从这段记忆中回到自己的世界。母亲找到我,坐在我旁边,她用平静的语气对我说:“你不是这个地方的人吧。”我先是一愣,而后点点头,轻声道:“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来到这个地方的。”她顿了顿,发出一声叹息,说道:“你说,这仗什么时候才能打完呢?”她望着下水道白色的墙壁,神色迷离。那个晚上,她告诉我,她的父亲和几个兄弟都死于这场战争,和她相依为命的母亲也在一次袭击中丧命。她说:“我已经是个没有家的人了。”彼时我看着她眼底的悲伤,忽然想告诉她我就是她的女儿,可我终究没有这么做。
这场保卫战打得异常艰难,每天都有人死去。我和母亲在战场上并肩作战,在枪林弹雨中打游击,打巷战。但我们很快被美军包围,面临着弹尽粮绝的境地。
我记得那一天,敌军占领了这座城市,把所有人都赶到广场上,如有人反抗,当即被枪决。这些畜生般的东西!我和母亲趁着营地守卫换岗的空隙,逃了出来。我们很快被发现,母亲拿着枪一个一个击毙追捕的士兵,带着我逃到了山顶的小屋。她把我藏在地板下,嘱咐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出来,便一个人跑了出去。
我蜷缩在地下,感觉到一阵阵疼痛。很快,我听见门被破开的声音,母亲的尖叫声,衣服被撕开的声音……我捂住嘴,尽量不使自己发出声音,眼泪顺着我的脸滑下。
母亲怀孕了!
一个月后,盟军把这座城市解放了,母亲和我重新回到了田间劳作。母亲很卖力地种地,因她知道,多一分收获,军人们就多一份口粮。越南夏季多洪水,连年的战争早已将堤坝毁灭,于是母亲就和留守的女人们一起用双手建筑新的堤坝。我们在烈日的暴晒下搬运水泥和沙石,一点一点垒成了大坝。只是老天似乎是刻意要考验我这位苦难的母亲,那年夏季发了一场特大洪水。洪水来的时候,我们正在海岸线旁。我们很快被巨浪淹没,就在我即将失去知觉的时候,母亲用尽全力将我推向岸边,我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昏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回到了自己的世界。母亲坐在我旁边,看着我,泪光盈盈。我轻轻地抱住她,泣不成声。
母亲终于找回了她的记忆,而我,也终于找到了我的故乡。
指导教师 黄忠 李红梅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