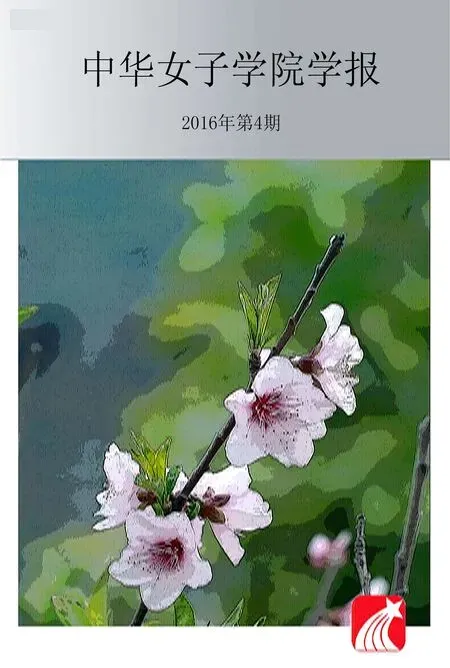生育政策调整目标实现的困境及破解
——基于女性个体发展视角的分析
2016-12-02张慧霞
张慧霞
生育政策调整目标实现的困境及破解
——基于女性个体发展视角的分析
张慧霞
主持人语:继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后,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再次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然而,要顺利实现从一孩向二孩生育模式的转变,仅有生育政策的调整是远远不够的。“单独二孩”政策启动之初,就有专家呼吁关注生育政策调整与生育主体特别是妇女之间的相互影响,建议完善相关法律,出台配套措施,加大社会服务供给。至今,“二孩”政策遇冷的现实似乎已初见端倪。出生人口不升反降的事实,急切要求以更为深入的研究为基础的应对策略。为此,本刊编辑部集中编发一组文章,分别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视域、女性个体发展的视角和生育成本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等不同角度,深入探讨“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以期对推进这一重大国家发展政策与战略提供一定的依据。
张慧霞提出,单纯的生育政策调整并不能对当前女性生育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必须正视独生子女时代形塑的生育价值观念、工业经济催生的工具主义生育理性、男女平等意识对女性生育行为的影响,补偿女性因生育行为所产生的损失,构建女性个人价值与生育的社会价值相统一的社会政策环境。王善英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女性社会作用、社会地位以及解放条件等基本理论分析,认为当下中国职业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其在全面自由发展的道路上依然存在较多的不利因素,生与不生的两难境地以及种种不利因素可能会降低职业女性生育二孩的意愿。任义科、郭玮奇、赵谚慧等人分析了“单独二孩”政策和“全面二孩”政策下生计资本对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得出结论:无论是在“单独二孩”政策下,还是在“全面二孩”政策下,生计资本都对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有着重要影响。由此建议,提高流动人口的收入,减轻流动人口的住房压力,提升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
“全面二孩”政策对于双重转型中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构建有利于生育主体、特别是妇女生育的社会政策体系是破解难题、摆脱困境的关键因素,为此,学界还需继续努力。
女性的生育行为是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的落脚点,然而单纯的生育政策调整并不能对当前女性生育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独生子女时代形塑的生育价值观念、工业经济催生的工具主义生育理性,有效地抵消了生育政策调整的预期效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女性更重视个体发展和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得到强化,而与家庭的关系趋于弱化,然而生育行为易导致其个人发展陷入困境。由此,生育政策调整若要实现预期目标,需要补偿女性因生育行为所产生的损失,从社会政策体系方面构建有利于女性生育的环境,否则只是单纯地放宽生育子女数量和适度延长产假,无法激励女性生育,更无法改变女性生育于自身个体发展方面的不利现状。
生育政策;女性个体发展;工具理性;社会承认
目前,我国生育政策由独生子女政策调整为普遍二孩政策,政策实施的目的可归结为:继续增强“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效用,解决人口结构老龄化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危机,调整性别结构以缓解婚姻市场压力。以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为生育政策调整的目标,离不开政策实施对象特别是育龄女性在行为上的响应。广义而言,社会政策不同于传统的文化、观念或制度,它们被制定和落实是为了解决已经存在或即将产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问题,即政策具有较强的工具理性特征,追求实施效果。但是,政策的具体执行过程面临复杂的社会环境,它时常与积淀已久的文化或观念不一致,有时甚至产生冲突,若要实现预期的政策效果,就需顺应现行文化、观念或习惯,关注被执行对象的行为特征,如果只是强制推行,将会大大增加执行成本。由此推论,作为社会政策之一的生育政策若要实现目标就有两种路径:顺应现行的文化推行,或依靠强制力落实。控制生育行为使人们少生可强制推行,但若要求其多生,强制推行路径似乎不可行。故而就只有一种路径:顺应当前现行育龄女性生育行为的价值理念,从而提升生育政策调整后的实施效果。
一、生育政策调整中女性生育行为的价值理念
(一)“一孩”政策奠定了育龄女性生育行为的价值理念
当前育龄女性生育行为的价值理念是由历史积淀而成的,并不轻易随政策调整而立即改变。以2012年“双独两孩”全面放开为时间截点,当时全国15—49岁且孩子为独生子女的育龄妇女有1.52亿[1],她们的出生时间为1963—1997年,20—29岁最佳育龄期的女性出生年份为1983—1992年。
回顾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1962年我国提出限制生育政策,196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倡晚婚,1964年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开始提出节制生育,1970年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1982年把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当1963年出生的女性达到20岁时为1983年,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已被作为“政治任务”开始严格强制实施。当前的最佳育龄期女性(1983—1992年出生)是在“晚婚晚育”、“只生一个好”、“少生优生才能幸福长久”、“男孩女孩一样强,长大都能做栋梁”等宣传独生子女利好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商品经济发展、市场经济改革的社会背景下,“丁克家庭”在我国开始出现并流行。夫妻双方追求“丁克”状态,一方面是由于孩子带来经济负担或影响夫妻事业发展,另一方面是受到独生子女政策的宣传影响,如“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市场竞争压力大”等,使一些夫妻认为生产易而养育责任重大,自身无法兼顾事业发展与生育孩子,不生育反而是一种负责任的社会行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本来是为了改变当时家庭喜多生子女的传统观念,但政策一经长期严格强制实施和广泛宣传,即在当前15—49岁的育龄妇女观念中落地生根,如今允许其生两个孩子的政策理念与她们已经固化的生育价值理念产生了冲突,从而导致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并没有立即带来预期效果,甚至相关政策在曾经的一些人口大省也“遇冷”。
(二)生育行为呈现出更大的工具理性特征
中国传统家庭追求的是多子多福、“四世同堂”,强调男性后继有人、香火不断、老有所养,即对家庭而言,多子女拥有较高的经济效益。长期以来,一些地区的农村家庭允许生育两个孩子,但农村家庭养老问题却日益凸显,多子女家庭尤其多儿子家庭养老矛盾突出,代际的付出与回报呈现出不对等性,多是父代付出,子代却不能或不愿反哺回报,多子女已经显现不出预期中的经济效益。并且随着子女增多,其带给家庭的经济边际效益反而下降,这意味着即便完全放开生育政策,现代家庭也不一定会回归传统,去追求多子多福。
生育行为受工业社会与市场经济影响,由理性决定,延续香火和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已经开始淡漠,无法再继续影响家庭生育行为。西方发达国家对生育行为不实施政策控制,部分国家宗教反对堕胎,但西方的生育率随着工业经济发展逐年下降。为此,这些国家颁布政策提供经济保障以鼓励生育,但多生子女仍以穷人为主,穷人生孩子也主要是借助政策对生育的保障措施来获取更多的家庭收入。工业经济已经使传统上通过人口数量来获取经济发展的优势逐渐丧失,生育政策调整已经不适用于快速发展的工业社会或市场经济。对于家庭而言,多生一个子女意味着增加负担,影响子代人口素质和父母个人的发展。对国家而言,人口增多带来的经济效益很难以绝对人口数量的增长去衡量,应对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发展危机和调整性别结构以缓解婚姻市场压力可以成为国家生育政策的目的,但尚不足以构成个人生育行为的合理动机。
(三)生育对女性发展的不正义特征
若生一个孩子已形成一种备受推崇的价值理念,则多生对家庭不利,更对女性长期发展不正义。传统家庭中经济生产和人口生产紧密相关,农业社会尤其明显。但工业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改变了家庭的经济功能,使其转变为纯粹意义上的人口生产和情感关怀的组织。婚姻曾经“是一个被法律所支配的经济关系,比关怀更多地关系到财产积累、劳动组织和资源分配”。[2]139但是,“就家庭职能而言,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取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个体由自然经济条件下的自主生产者变为社会化大生产机器的零部件,传统上具有生产职能的家庭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沦为主要具有消费职能的社会组织。”“就社会结构而言,正是由于家庭生产职能的萎缩所带来的家庭成员互助功能的弱化,个体越来越受到遵循着‘有利/不利’二元代码逻辑的经济系统做任意摆布。”[3]338随着社会保障制度日益完善,个体的生育、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需求均可被政府组织或非政府组织所满足,个体由此可以脱离家庭成为单独的社会公民,而非必须成为一名家庭成员。
家庭日渐成为以情感关怀为主的组织,组织内部情感关怀导向的资源分配原则不同于市场,它以按需分配作为原则,即家庭组织中弱势者最应得到相应的情感关怀,以及立足于情感关怀而衍生出的相应的经济需求。例如,家庭情感与经济资源最先分配给需要照顾的老人、孩子、生病的配偶。婚姻家庭中,为了孩子健康成长,父母需要付出时间、精力、金钱、情感和自己事业发展的机会。为了家庭特殊成员的需要和整体利益,这种不求回报的付出往往由女性供给。少数较为富裕的家庭可以通过金钱购买其他女性的时间来提供所需照料,但最终会导致另外的家庭照料更加缺失。
家庭组织内部的按需分配原则与市场经济的按劳分配原则不同,为家庭付出较多的女性一般很难如市场参与者一样获得相应的回报,她们在人生发展最关键的时期失去积累财产和提升竞争能力的机会,甚至部分女性还会被迫离开她为之付出无限情感关爱的家庭组织。以“有利/不利”二元代码的行为逻辑来评判,家庭财产立足于个人的工资和薪水收入的分配原则,使得在家庭中进行生产和养育活动对女性长期个人发展而言是不正义的。此处不正义指涉的是女性无法继续拥有在市场中同男性一样的发展机会,其对家庭的付出经常无法得到相应的回报,从执行程序和分配结果两个方面均呈现出不正义。这种不正义是生育政策不能落地生效的根本性原因。
二、当前我国女性发展困境的实证分析
(一)劳动力市场需要女性更长的工作时间
女性的时间是一定的,当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工作中,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生产和养育活动。依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对比2007年和2013年城镇就业人员两性调查周的平均工作时间可以看出,调查周工作时间为48小时以上所占的比例两性均有所下降,这部分归因于2008年实施劳动合同法的缘故。但周工作时间为41—48小时所占的比例女性高于男性,40小时两性差异不大。39小时及以下的比例女性虽然仍高于男性,但二者的差距由2007年的6.6个百分点降到4.8个百分点,此段的整体百分比也在降低。在此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女性调查周工作时间为41—48小时的比例比2007年有所上升,并且高于男性上升的速度。这意味着女性的工作意识逐渐增强,投入工作的时间逐年延长,女性工作之外的时间缩短。

图1 2007年与2013年不同性别调查周工作时间分布(%)
(二)生育行为成为导致女性失业的重要诱因
依据中国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样本数据(抽样比为0.822‰),女性生育年龄主要集中在25—29岁,占生育总体的39%;其次为20—24岁,占生育总体的32%;排在第三位的为30—34岁,占生育总体18%。三者合计占生育总体的百分比达到88.6%。若加入城乡因素,女性生育年龄在25—34岁的比例应更高。

图2 女性生育年龄分布
劳动统计部门目前把城镇失业人员的失业原因分为离退休、料理家务、毕业后未工作、因单位原因失去工作、因个人原因失去工作、承包土地被征用和其他等七个原因。据此分析年龄处于25—29岁、30—34岁和35—39岁的城镇失业人员的失业原因,从表1可以看出,这三个年龄阶段近五年因料理家务导致失业占全部失业原因的比例呈上升趋势,尤其以30岁以上表现得更明显,据六普数据统计,城镇女性初育年龄为27.9岁,由此推测女性生育行为易导致女性失业,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相应的男性数据却没有呈现逐年增长的明显趋势。

表1 2009—2013年城镇失业人员因料理家务导致失业占全部失业原因的比例
2013年,女性因料理家务而失业占全部七个失业原因的比例为36.8%,男性则为4.1%,女性远远高于男性。在不同学历层次,料理家务占七种原因的比例呈现出学历越低男女性别差异越大、学历越高差异越小的趋势,但女性一直高于男性。具体分布见图3。

图3 2013年因料理家务导致失业占全部失业原因的比例(%)
在纯粹由于料理家务而导致失业的人群中,文化程度同样存在着影响。尽管长期以来,女性在家庭劳动上投入时间高于男性,但文化程度越高,在料理家务方面性别越平等。根据图4可以看出,文化程度为专科及以上的男性因料理家务而失业的比例反而略高于女性。高中文化程度二者差距不大,初中文化程度的性别差异大,女性因料理家务而失业的比例远高于男性。小学及以下男性又略高于女性,其中原因可为低学历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在城镇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从事低端、低报酬的服务性工作,甚至非正规就业。
女性仍旧是料理家务的主体,育龄女性因料理家务而失业的比例仍旧居高不下,高学历女性虽然也会因料理家务而失业,但在七个失业原因中所占比例远低于低学历女性,她们更多的是因为个人原因而失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层次的两性对料理家务的付出差异并不大。这意味着高学历两性生育行为具有较强的理性,他们往往不会多生育子女,料理家务往往不是高学历女性失业的重要原因。

图4 2013年不同性别和文化程度因料理家务导致失业的比例(%)
(三)生育保险政策与生育调整匹配度不足
生育是一种理性行为,于个人、家庭和社会均产生价值。随着养老、医疗、工伤和失业保障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生育对个人和家庭的价值减弱,对社会的价值明显,但对于生育的社会价值进行直接回报的政策体系供给力度目前仍显不足。
生育保险待遇虽不能直接决定生育行为,但却对生育行为有影响。比较2006—2014年人口出生率和生育保险待遇享受人数的增长量可以看出,人口出生率的上升并没有带来待遇享受人数相应的增长,特别是2013、2014年人口出生率上升,但生育保险的待遇享受人数并没有相应增长。这主要是因为生育保险只适用于就业人员,由于生育政策放开,部分高龄女性由于生育而离开工作岗位,无法享受生育保险,导致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人数减少,由此也间接证明女性生育对其个人职业发展的不利影响。

图5 2006—2014年人口出生率与生育保险待遇享受人数增长量分布情况
生育保险一般支付女性怀孕、生产、短时间的养育(生育津贴或产假工资)、流产和计划生育费用,但流产和计划生育费用由于报销额度低并受传统观念影响,不少女性会放弃享受这类生育保险待遇,因此生育保险支付项目实际主要为孕检、生产和短时间的生育津贴,其中生育津贴为生育保险费用支出主体。以北京市生育保险支出为例,2014年北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6463元①参见新华网:《2014年北京职工月均工资6463元》,http://www,bj.xinhuanet.com/tt/2015-06/06/c_1115530736.htm.,若依据2016年之前的生育保险政策规定,北京城镇女性就业人员参加了生育保险,可报销生产的检查费用和医疗费,其标准为产前检查费用最高限额1400元,生产费用自然分娩依据医院不同,一般在2700—3000元之间浮动。生育津贴规定为女性的产假工资,发放标准为其工作单位当年的职工平均月缴费工资,平均缴费工资值的范围为上一年北京市社会月平均工资的60%—300%。一般企业晚育女性休假为128天。若把2014年北京市社会月平均工资作为女职工的生育津贴标准,则自然分娩的女性产假为128天,其产假津贴为27575.47元。医疗费用占生育保险费用支出的比例约为14%,即86%为女性的产假工资。假如把女性的生育保险费用全部作为女性产假工资,从全国2006—2014年生育保险人均支出占当年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比例可以看出,产假工资所占比例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女性生产后其待遇逐年降低。

图6 2006—2014年人均生育保险待遇支出占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比例(%)
女性产假工资降低不仅意味着下一年的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变低,还最终影响了女性个人养老保险待遇的提高。因此,生育政策调整后生育保险政策的改革并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来激励女性生育。
(四)婚姻、家庭结构变迁对女性生育不利
在中国,婚姻是合法生产的前提,养育以家庭为基础,女性生育需要长期稳定的婚姻和家庭组织,两性在婚姻、家庭中对子女的付出需要相应回报,否则婚姻、家庭就失去可持续的动力。
依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女性的平均初育年龄为25.9岁。[4]84同年数据显示,女性离婚者主要集中在35—49岁,其中40—44岁离婚比例最高,占离婚总体的19%。[4]89由此可推测,有子女家庭一般在子代9—24岁之间特别是14—18岁之间最易离婚,因为此年龄段的子女一般不再需要过多的家庭照顾。婚姻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对家庭子女付出9—24年在离婚时应得到多少经济补偿,但可以推测女性在此过程中损失较大。依据上文可知,女性在生育后因照料家务而失业的比例相对较高,为家庭和子女付出也较多,因而对个人发展影响较大,男性表现则不明显。这种婚姻、家庭因生育而于女性不利,从2005—2014年的结婚和离婚数据可看出,离婚率逐年上升,结婚率却相对下降。二者长期相背而行将导致婚姻家庭及其孩子的数量持续下降。

图7 2005—2014年结婚与离婚分布情况(‰)
从2001—2014年法院判决离婚占总离婚对数的比例逐年下降的趋势可以看出,协议离婚所占比例逐年上升,女性的独立意识逐年增强。女性不再以婚姻与家庭为其个人价值的重要体现,独身成为一种可以并愿意接受的生活方式。有知识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中具备竞争力的女性独身人数逐年增多。2010年全国六普数据显示,在全部未婚人口中,女性所占比例为42.7%。[4]86其中未婚女性主要分布在城镇,约占女性大龄未婚人口总数的65.3%。上过学和小学文化程度的30—44岁未婚男性大部分居住在乡村,比例分别为79.2%和80.1%,而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的30—44岁未婚女性90%以上居住在城镇。[4]87-88农村低学历的男性因在婚姻过程中无法提供经济保障而被婚姻市场挤压,但城镇高学历未婚女性则更大程度上是由于无法匹配到与自己等价的男性。婚姻与家庭构建的经济基础一旦失去,未婚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状态。
离婚率逐年上升,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竞争力逐年增强,与此相对应的法律或社会政策却没有针对这种变化做出相应调整,故女性不婚、不育的人数逐年上升也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图8 法院判决离婚占总离婚对数的比例(%)
三、女性发展与生育和谐所需的社会政策环境
生育政策调整后若要产生预期效果,就需要构建一种促使女性个人价值与生育的社会价值相统一的社会政策环境。个人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现为女性个人发展机遇与男性平等,生育社会价值的实现则有赖于社会政策的完善,需要摆脱单纯依赖“糟糠之妻不下堂”、“孝顺”等传统道德文化来激励女性生育的境况。家庭萎缩与社会的兴起缘起于公民社会权利,立足于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起个人与社会的直接关系,弱化了个人与家庭之间的互助关系,使女性与男性享有同样的社会权利,拥有对物质财产同样的摄取权和占有权,两性在财富、声誉和社会地位、权利和人格方面均可平等竞争。传统的道德文化无法保障女性独立于家庭而立足于社会,但工业经济发达的国家,两性被要求或自觉追求同样的个人价值。虽然为家庭牺牲自己是一种美德,但对大部分女性而言则是一种于己不利的非理性行为。女性个体的存在超越了家庭和社会的存在,其基于自身偏好而选择社会生活,放弃家庭生活,日益被社会认可、尊敬和推崇。“传统的由男性负担家计的家庭正在消逝,生育率正在下降,生命历程日益‘非标准化’。”[5]4若要改变女性“非标准化”的生命历程,以有利于两性和谐发展、子女健康成长、国家人口可持续发展,就需要以正义来构建社会政策,用社会保障措施来承认女性生育行为的社会价值,调和女性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使其摆脱困境。
(一)女性生育行为需要建立社会承认机制
女性生育需要良好的社会服务和慷慨的生活保护,生育价值同工作价值一样需要被市场和社会承认,否则女性就会因生育行为增加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风险。“现存的社会保护制度与不断产生的需求和风险之间的分裂在不断增加。究其原因,是缘于家庭结构的变化(如单亲家庭的增多)、职业结构的变化(专门化增强、变动性加大),还有生命周期的变化(生命周期越来越显示出非线性和非标准化特征)。”[5]9这三种变化导致了众多的不确定性。女性生育需要经济、社会地位和声誉的承认,没有对生育价值的社会承认,针对女性怀孕、生产、哺乳的保护政策都无法真正落实,甚至可能成为劳动力市场产生性别歧视的缘由。女性生育价值的社会承认需要以构建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为前提。计划经济体制曾经建立起来的社会服务体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已经被逐步消解。当前的生产和养育的服务体系立足于个人或家庭的收入或财产,女性生育行为变成了一种“昂贵”或“高成本”的消费行为,由此导致女性甚至整个家庭对生育望而却步。国家需要在市场经济中重新构建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使女性愿生、能生和敢生。
(二)女性生育过程中需要获得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随着高等院校女大学生增多,甚至超过男生,全国有知识的女性人口日益增多,两性平等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共识。高等院校的女性更承认能力而非性别在个人发展中的作用。高校学生生活在优秀者聚集的群体中,他们能更清晰地感知到身边女性的优秀潜质和才干,更易于认同“女性的能力并不比男人差”,“女人完全可以像男人一样独立而有成就”,在领导岗位的两性比例上,更少坚持“领导男女比例应该大致相等”的观点,而强调能力才是硬性指标。[6]目前,社会兴起和社会保障制度均立足于个体的资产、资本、劳动报酬,物质财富的获取除代际传递或赠予外,更多地来源于劳动力市场中个体通过劳动获取的劳动报酬。劳动报酬的高低取决于劳动力价值。工业时代的劳动力价值并不体现在生理上,而是更多体现在受教育程序上。教育资源,特别是能够提升个体竞争力的教育资源一般又受财富多少的影响。女性与男性共处同一劳动力市场,需要共享教育资源,在生育过程中两性均需要投入养育工作。这意味着职业指导和职业培训不能只针对失业人群,应扩展到所有在生产和养育过程中有提升自身竞争力需求的女性,从社会政策层面承认女性生育的付出并给予相应的保障。事实证明,社会政策对女性生育行为保障力度越大的国家,其贫富差距越小,两性越和谐,家庭和社会越稳定,人口生产和经济生产能力也越强,瑞典和德国为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三)女性生育需要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
市场经济处理的是人与物、人与人资源的再分配的关系,人立足于经济,又需要情感多元化的存在,即人除了需要经济保障,还需要情感保障。优生优育需要良好的情感基础和稳定的家庭环境。一个社会人若要获得构建良好情感的能力,需要生长在稳定和谐的家庭中,需要经济相对富足、各阶层之间贫富差距相对较小、文化多元而相对宽容的社会环境。国家强有力的竞争力和经济的富足需要有创造力的多样化的人才,人才的形成需要立足于多个家庭经济的富有和多元的文化培养,因此只有以人为本的价值体系才能使社会稳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单一的市场经济文化或工具理性不利于一个社会人的成长,更不利于激励女性生育。家庭、用人单位和政府均应强化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在追求国力强大、财富不断积累的同时关注人的存在。
四、结论
中国“多子多孙”和“继承香火”的传统并没有随着新文化运动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立即销声匿迹,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它仍旧影响着部分家庭及其女性,独生子女生育政策对这部分群众的需求是压抑的。现代社会的高风险导致“失独”家庭增多,许多家庭恐惧失独风险,生育政策调整也满足了人们降低家庭风险的愿望。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劳分配原则、男女平等意识、强化个体存在感的个人主义等也深深影响着育龄中的女性,从价值观念、经济分配原则、女性追求自身价值的角度而言,生育对女性均是不利的。故只是简单地调整生育政策,并不会影响一部分女性的生育行为,而这一部分女性将越来越成为育龄女性的主体。国家若要激发女性的生育欲望,就需要改变当前生育行为与个人发展无法和谐共处的困境,努力达成家庭与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和谐一致,即市场资源的分配或再分配需要把生育的家庭作为一个平等的参与者和分享者,而非仅仅针对个人,生育家庭不但参与初次分配,还应参与再分配。
[1]翟振武,张现苓,靳永爱.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J].人口研究,2014,(2).
[2]冯颜利,贾可卿.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与多元正义述评[A].邓正来,郝雨凡.转型中国的社会正义问题[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3]孙国东.试论社会主义与法治转型的社会理论逻辑[A].邓正来,郝雨凡.转型中国的社会正义问题[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4]杨玉静.中国女性的婚姻与生育状况[A].谭琳.2008—2012年: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报告[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5](丹麦)戈斯塔·埃斯平-安德森.黄金时代已逝?——全球经济中福利制度的困境[A].戈斯塔·埃斯平-安德森.转型中的福利国家[C].杨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6]魏国英.高校学生男女平等价值取向及其群体差异[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5,(5).
责任编辑:董力婕
Dilemma and Solution of Realization of Fertility Policy Adjustment——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Individual Female Development
ZHANGHuixia
Female behavior is at the center of China’s fertility policy adjustment,despite its apparent impact.The onlychild policycoupled with economics effectivelyoffset the expected impact ofadjustingthe fertilitypolicy.Under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focused on individual development and valu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weakening family relationships,fertility behavior can cause long-term problems.Thus,policy adjustment needs to compensate women for any loss in terms of social policy construction,or simply relax the number of births and moderate extension ofmaternityleave toencourage fertility.
fertilitypolicy;individual female development;instrumental rationality;social recognition
10.13277/j.cnki.jcwu.2016.04.006
2016-06-30
C913.68
A
1007-3698(2016)04-0032-08
张慧霞,女,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劳动与社会保障。10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