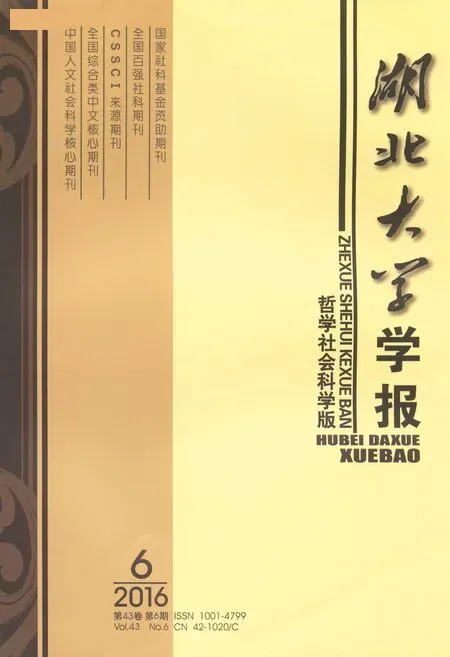法律论证的认知规则
2016-12-01徐梦醒
徐梦醒
(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法律论证的认知规则
徐梦醒
(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法律论证的规范性条件不但包含形式推论规则,还要突破形式结构主导的语义系统,走向论辩主体的认知意图和言语行为。论辩认知的规范性将论辩情境、策略和目的统一起来,分析主体意图与态度等要素,以及据此受到认知规则约束的论辩话语;论辩对话规则将主体间既有的认知共识作为分析论辩规范性的基础,根据论辩进程中的“承诺集合”的变动建构意义的传递、理解和交互。结合民法当中情势变更原则下论辩主体认知模式的分析,可以看到法律论证的逻辑规则与认知规则总是共同发挥作用,而并非独立运行。
法律论证;认知规则;情势变更;论辩意图
法律论证的逻辑和语用分析构成了目前该领域研究的核心视域。论证诉诸言说,而言说的表述与意义,源于论辩主体整合多重语境元素而组织语义符号的过程。因此,本文强调论证领域中的互动式论证,从多主体论辩的角度来分析推进论辩规范性的认知路径,而在谈及法律论证时,主要强调的是主体在证成立场当中的论辩思维。语义符号纳入到论者的认知系统、假设情境和论题识别过程中后,构成规范性引导下的对话前提。认知规范性强调一种从因果关系,或者假设情境导出的相关关系。关联论辩语境中可被适用的有效依据,意味着对论辩效果多元的可能性空间保持开放态度。论者本身具备的内在的个性化元素,在融入言语行为中的同时也在重构论辩效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目前学界鲜有从认知视角分析法律论辩规范性的研究,但这个问题对于建构论证有效性的意义不容忽视。
一、认知规则在法律论辩中的定位
(一)认知规则的定位
认知规则在法律论辩中的意义,即依据情境识别、信息组合、论题变迁与效果认同而形成论辩认知的规范要件,及其在对话规则的检验中如何反馈和调整。认知规则对论辩行为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更加直接、具体和鲜明。论证效力评价需要依据对语境——通常情况下是某种利益格局——的认知模式和期待为前提。通过这些认知要素,可以引导进一步的认知和行为[1]110。认知规则应对特定情境的被动性,决定了其结构表达主要依赖于“如果——那么”的条件句(if……then)结构[2]2,事实上,条件句可以涵盖任一规则的规范模型,以涵盖规则确定者的规范性期待。在假定该预设条件句为真的情况下,Shimanoff认为,规则通过特定的道义逻辑变量,可以指称特定场域在应然性层面上是“应当”、“必须”、“可以”发生,来对应论者针对该情境的认同程度或者其他可能影响其变动的态度。认知层面的论辩言说规则,主要涉及主体面对现实情境的信息处理方式。
法律论证认知规范性的前提,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动态语境下的关联要素具有多元性乃至无穷性。即使如此,论者仍然要预先确立某种程度的情境共识作为确认前提效力的“承诺集合”;第二,法律对话中对论辩规范性的认知,不但检验他们对语境回应的能力,还需要通过条件句的假设性感知,预测对方回应因循的认知的模式;第三,对论辩恰当性的评价,通常涉及论者对论证规则识别、认知与遵循状态的评价。论者可能遇到对方态度转变和议题偏离的意外情形,从而引发裁判者的打断甚至误解等论证互动的谬误类型。
(二)法律论证规则对认知语境的依赖
1.主体的个体属性与论辩规则体系。尽管法律论辩强调规范性和一致性要求,以及论辩话语的严谨与审慎,论者自我深受文化积淀等影响的性格或品质等要素仍然无法忽视。它们使论辩规则的认知可能具备极具个性的表现。例如,坚守礼仪原则的论者,通常将话语表述的友善性视为比逻辑性和思辨性更加重要;内向或者害羞的论者可能更倾向于回避尽管具备有利于己方的,具备更强说服力,但却可能包含激进性、进取性甚至侵略性表述的依据或者理由;信仰功利主义的论者可能对策略性论辩的言说模式抱有更加宽容的态度,从而认同某些可能引发诱导效应的方式,等等。引导论辩思维的规范性要求,显然无法回避上述个体属性的影响和干扰。如果在研究当中忽视或者省略这些要素,就无法切实和完整发掘认知规范性引导在法律论证当中的意义。强调论者的个性化认知风格在言说互动当中的,有助于区分和辨明理性与非理性的论辩陈述以及信息模式对论辩意图的影响。
2.规则适用频率和顺位。论辩规则体现和反应出来的问题模式,如果频繁地或者首先为论者视为关键对象,那么该项规则通常能够得到主体共同接受。也有学者认为最近适用(recency)的规则相对来说具有情境性优势[1]111。这种近期效应能够优先地,或者对论者的规范性认知和理解发挥激发效果。论辩情境的变动通常引起论者注意力的转移,而最近的变动最能引起主体在期待某种规范性效果的时候的关注。比如当论者被对方指出存在多重问题谬误时,论辩效力推进中的反驳重点可能会倾向于对隐含前提的检验。
3.预设或假定情境的认知模式。作为规则基本陈述模式的条件句“if……then”要求假定情形的判断符合规则预设的情境要件。在司法裁决针对特定事实作为小前提的演绎推理当中,这种情形依赖证据的完善性、充分性、相关性和合法性予以重构,并在共同确认的法律规则诠释和理解前提下确认合法裁判结果。然而,事实情境和假定情境在商谈互动当中,两者之间并非完全相符,而总是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对应不同向度的差异之处。在法律商谈的语境下,规则对应假定情境的吻合程度决定了该规则的适用价值。比如诉诸情感和诉诸人格的论证,往往是在假定情形为证据重构之后,在小前提建构上已经达成共识之后才有更大的适用空间。
二、意图对论辩规则的构成性
论者对情境的感知是论辩的前提条件,在时序上也首先发生。这种情境对应论者意图和该意图对应的论题及其前提,决定了论者需要面临的主题属性。例如,当论者需要证成命题Q:“S有罪并且应当受到刑事处罚。”他必须要将R:“主体S已满十四周岁”作为前提之一予以证成,尤其是其认定标准存在争议时。显然,对情境及其对应论题的确立,需要遵循相应的认知规则,其中包含着对特定价值权衡、主题脉络和期待整合的过程。正如在上例之中,R作为证成Q的前提(有时是认定主体犯罪行为唯一需要求证的前提,即R为真,则Q为真),成为超脱先前论辩主题的更为重要的主题。特定主题关联涉及其属性的情景要素,和证成其真值或者恰当性的相关依据。这就需要进一步诉诸主题的延伸,如若要证成R,则需要证明P:“S的户籍材料内容属实”为真,等等。
显然,论者诉诸论题情境这一思维过程需要论者感知、诠释、分析、解读论题情境属性,亦即依据论辩意图通过反思与整合发掘出证成Q需要明确的,相关的所有前提R1、R2、R3……并就其中存在意见分歧或者需要进一步予以证成的前提作为新的论辩主题;接下来,论者诉诸进一步探讨的认知规则被激发;目标A因而成为需要首先证成的主题。在Wilson看来,简单案例和复杂案例不同[3]。简单案例能够轻易获取前提性的论题,并且不需要面对过多的未曾意识或者隐含的不确定性。疑难案例通常面对模棱两可,甚至矛盾的情形。由于含混甚或对立的内在线索,认知规则无法单一地、纯粹地和确定地予以适用。规则当中的if条件句对特定结果的规范性指涉,也很难完整和简单地对应该论题情境的要素体系。与日常对话不同的是,相对于情景要素的多样性、系统性和变动性来说,法律论辩言说通常将问题、论题、焦点或者说议题作为论辩情境的内在核心。在融贯性原则的引导下,问题之间的逻辑网络引导着证据探寻,证据链的确立和证据网络的建构。
论题关涉的目的,可以通过内在和外在两个层面反映认知规则的运作,并将对方目的划分为不同类型[3]。支持性目的(supporting)和攻击性目的(attacking)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很少被论者从内在说明性出发予以隐含;后者有时包含着试图伤害对方感情或者形象等意图,或者放任此种结果发生的内容,因为考虑到合作原则的要求,通常不会外显于言说当中。当然,立场和意图能够通过论辩主体之间涉及的利益分配关系,得以清晰地辨识。在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中,作为控方证人的一名日本陆军少将田中隆吉明确指控了九一八事变即“满洲事变”以及皇姑屯事件的主谋以后,电影版本中的日方律师怒问田中:“你是日本人吗?”例子中的听者在答还是不答,如何回答的权衡上不但需要考量其回应对于先前坚守的论证观点可能的削弱甚至颠覆,还面临着对方预设理论的制度、伦理、道德乃至舆论等方面的压力。这种压力的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识别为攻击性目的。
内在目的和外在目的的分野与呈现,表征了论辩对话当中的语用向度,以及对话语言外之意的隐含性及其意义的识别。论者对支持性目的的追求,在于试图确立听众对该支持关系的理解和认同。攻击性目的隐含性的深度源于合法性要求的约束。显然,隐含性目的未必都具有攻击性,但攻击性目的通常都具有隐含性;外显目的未必都具有支持性,但支持性目的未必都诉诸话语而呈现。论辩在包括法律领域在内的所有情形,都依赖特定目的而展开。论辩主体的真实意图反映在合法性框架当中,具备专业性、法律性和范畴性表述模式。论辩目的内在的框架性和鲜明性,减轻了基于策略性隐含的意图、期待、目的在法律论辩当中的语用意义。例如,实践当中存在的“公益诉讼”,像针对损害结果提出一元钱赔偿的目的,对于原告方来说,案件判决的影响力或者后续的社会效果,才是原告作为证成特定立场合法性的真正意图。这些目的可以直接依据要求的损害赔偿数额判断出来。然而,为了确保论辩互动在特定法律程序当中的公正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尽可能确保真实意图呈现的客观性,或者内在目的和外在目的表述的一致性,对于缓和论辩当中发生的欺骗、掩饰、引诱等情形,推进论辩恰当性尤其是真诚性,具有关键意义:论辩真实意图和呈现的意图应当具有一致性。
主体根据目的的转换,可以将论辩信息进行检验、核对与调整,其中论者主要遵循的是论辩互动的共识内容和情境基础。迈耶(Meyer)将认知结构区分为情境—行动的结合,与行动—结果的结合[4]71~90。通过假定条件句的因果构成,论者可以预见采取特定行动的原因和根据,以及特定行动引发的结果和成效。而论辩的展开从特定情境模式(situation schema)开始。这种情境模式的认知的呈现[5],在当下看来,并不符合某种应然或者理想状态的特定利益协调或者分配格局。这种格局也包含在论辩当中涉及言说规范、理由表述、证据要求等层面的并非完善的状态。依据日常对话或者过往的论辩互动模式的分析,论者可能诉诸熟悉的经验整合出相对抽象的情景模式体系。并且,对论辩规则在认知层面上的认同和证立本身,并非必须作为论辩开展的确定前提。阿列克西认为:“它们到底应如何具体应用,这必须交由论辩参与者(来决定)……这些规则,部分是在讲话者群体中实际发生效力的规则,部分是已经暂时得到证立的规则。(论辩)不绝对按照已经证立的规则来进行,这并非是不符合理性的。”[6]233显然在他看来无法要求论辩可以直接诉诸完整、有效和即成的论辩规则。如果论辩在根本上是秉持理性态度,或者论辩程序本身要求这种理性反思原则贯穿始终的话,那么首先根据其自身尚未得到证立的规则展开论辩,也符合理性。从这个角度来说,论者意图是法律论证规则有效性共识的构成性条件。
论辩初始的理性预期,无论是在规则尚未证立的情境中,还是存在言说规则直接发挥作用的情境中,都包含着初始情境模式的特定核心目的的认同。这种认同在存在意见分歧甚至对立立场的论辩初始情境中,并非体现为特定论辩结果实际效果的共识,而是论辩各方都将这种效果确认为某种互动模式,或者利益分配格局,从而和论辩内在的互动性和多主体性相连贯。可以说,初始目的是一种构成性要素。论者有意或者无意地将初始情境予以“标签化”,并据此推进可能的论辩信息的呈现。Meyer指出:“一旦特定规则预期被激发,该模式能够组合或者构成言说者关于该情境的感知,并据此形成前意识层面上,对在该情境中具备恰当性的言说行为。”[4]75该认知过程一方面体现出论者对语境的被动反应,以及依据批判性反思形成的论辩推进规划;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论辩规则在后期证成和体系化中的建构性作用。
举例来说,在2009年底的李庄案庭审中,被告人李庄提出庭审人员集体回避的要求,理由是被控伪造证据、妨害作证,两项妨害司法的“受害者”都是当地法院,因此当地法院与他有明显的利害关系。主审法官则指出,由于“法律未就集体回避有明文规定”驳回了李庄的请求。李庄利用指令性语用行为较高的真诚性条件给法院施加了一种压力,或者说,李庄通过既定的“语言游戏”规则,为法院应当如何取舍和协调关于刑事诉讼程序当中的“回避制度”和“管辖制度”提出了一个难题。法院是否支持李庄的请求本身并不重要。问题的关键在于突破规则的语义范围,使原本超出预想的事实状态通过另一种基于最初命题态度的语用行为表达出来,或者说标示出预期的命名在真实的语言游戏当中的实际意义[7]。法律概念体系通过专业法律思维的重构功能,将论证模式导向法律话语当中。这并不代表此时的论证语境走向了绝对的、静态的和独白的专业话语体系。初始语境的影响仍然存在,而且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干涉法律商谈的走向。论者可能要求特定言语行为的导出,如涉及侵权责任的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声誉等等;或许仅仅是强调某种相对宏观的目的,如公平、效率、福利、自由等等。论者依据初始语境引发的论辩目的,或者说未经过法律概念重构的意图表述在具体和抽象层面上的构成,指涉并引导着该目的相对应的“情境—行动”结合。在遵照既有法律程序要件的前提下,论辩言说的操作性、规程性、融贯性依赖于论者整合先前在类型模式论辩言说当中的归纳。思辨性规范整合的进路,表征为“if……then”的陈述结构。法律论辩中认知规范性的判断,也需要将言说导入这种结构中展开。if引导情境属性语句,then引导规则指引的可能行动,体现为对论证语境(作为非现实或者假定模式的情况下)的规范性表述。
三、情境感知中的论辩规范性
(一)论题明确化作为共识性前提
从思辨进程来说,法律论辩需要弄清几个问题:即论辩对象的明确化、支持论题依据或者理由识别,这些理由的类型及其相互关系等等。正如前文所述,假定主体S的抢劫行为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据证明,唯一留下争议的是该犯罪嫌疑人S的年龄尚未确定。由于出生证明或者户籍登记的不一致,可能导致该问题在认定标准和定罪量刑上存在难度。从该案的情形来看,S的年龄认定就成为关键论题。或者说:对论题相关的关键要素,其是否成为新的争议焦点,需要论者就此达成共识。
这种共识的基础,在于论者意识到议题A的解决,离不开议题B的解决。如果论者相信论题C更加有助于解决议题A,那么他需要就此予以证成。此时,B或者C既可以作为说明A的理由,也可能是基于某种相关性、识别度、目的性或者期待内容,以及由于论辩效率的考量而走向新的问题的解决当中,从而使“如果不讨论B(或者C),就不可能说明A”,甚至“解决了议题B(或者C),就意味着解决了议题A”成为共识。事实上是否真的如此,尚且需要作为阶段性议题,使论者中断原有的思路予以明确。比如,针对同性婚姻合法性的问题,是否可以诉诸基于婚姻目的的期待性考量,本身也可以作为论辩的对象,也就是说,对P:“同性婚姻合法性”的论辩等同于对Q:“婚姻本身的目的”的论辩,这一判断本身可能使论者在期待诉诸其他说明或者证成思维的时候,转向对Q的反思当中。当论者最终确信:如果不讨论Q,就不可能说明P,对Q的论辩才能顺利地进展下去。我们可以就此例子通过图表展示出来:

当由P到Q的跨越得到论者认同之后,就Q的探讨才能够说得通。论者如果就婚姻本质理解与同性婚姻合法性之间的说明关系存在疑问,就需要证明其反驳的合理性,从而阻却进一步的论证展开。倘非如此,论者就不得不针对议题Q展开不同立场如R1、R2、R3……展开。法律论辩当中涉及的社会关系,通常与特定社会问题(例如同性恋、堕胎、死刑存废、安乐死等)、社会指标(性别、年龄、职业或者社会阶层等),或者其他社会现象相关联。这些对象的阐释,在结合社会主体的交互性意图之后,能够推动其所赞颂、肯定、发扬、期许或者贬斥、否定、扬弃、规避的价值、品质、道德、伦理观念的明确化。通过相对抽象的,由特定价值秉持支持的理由,通常在此处能够获得说明性依据,并进而和规范性要件相对应,确保特定结论的可接受性与合法性。
(二)论辩情境识别对论辩意图的影响
尽管在Meyer看来论辩始于言说者追求特定目的,但情境感知则是目的确立,甚至是论题确立的前提。依据特定利益考量或者价值判断,论者在论题当中确立自身态度和立场,从而形成相对具体的目的(goal)。从语内行为来看(通过说某事而做某事),论者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证成特定立场,或者从新修辞学角度要求听众的实际认同;或者从非形式逻辑角度要求证成其依据的相关性、充分吸和可接受性。从语外行为来看(通过说某事时做某事而造成某事)[8],论者通过证成其立场,其实是希望确立某种社会性或者规范性效果。这种效果隐含或者明示于论辩目的当中,表征为论辩意图的实际描述状态。这种效果超出了言说意义构成,但没有超出论辩互动主体的理解范围。意义构成以外的实践效果,就是得以证成的,言说行为以外的对某种新的互动预期的证成。从这个角度来说,语外行为包含了对特定言语行为理解范围以内的实际结果,因而不同于Austin意义上的,包含以理解目的以外的特定策略为内容的语后行为(perlocutionary)[9]。举例来说,2014年9月1日正式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了四种上下班途中工伤情形。工伤的认定通过工作原因、工作时间、工作场所进行统一认定。依据该规定的解释,下班途中到市场买菜,然后再顺路回家属于“合理时间”与“合理路线”上下班途中发生意外认定为工伤的情形[10]。关于上班时间以外的工伤情形的新认定标准,有的人认为该标准更加宽松,更加具备人性化;有的人则认为这种规定有可能会加剧用人单位和职工之间的矛盾,并且使工伤的认定难以获取确定标准,存在执行上的困难。对新出台法规的争议,主要是针对该规定对特定问题的认定和处理模式是否得到了公众的认同,是否获取了在实践层面上的可接受性而展开的。这种探讨如果包含认同该规定不断更新和调整的可能性,则属于对听众来说可以理解的,并非包含在论者策略性意图当中的言语行为。因为针对特定论题诸如某规范性文件的合理性的判断,需要论者在证成其立场的过程中,收集和发掘出有效的理由和依据。其对于论者立场的解释,能够使听者理解立论的证成意图,而不需要根据该意图推导语后行为当中隐藏的策略性目的。
论辩目的内在地包含在论辩的初始阶段。该目的使论者对初始论辩情境的认知和重构具备了某种独特性,从而激发了情境—行动的论辩走向。情境感知有时先于这个阶段,从造成某种事态的主体初期预估的结果,这就决定了预期性感知对后续互动情境的识别和评价。例如,故意杀人者可能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前,就预计到自己被判处死刑的可能性。这在后期的司法审判当中可能成为公诉方或者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的论辩议题。这种可预期性要求论辩目的贯穿始终的特性,从而为初始情境的造就者以及识别该情境的论辩主体,提供稳定的、可知的和有效的回应机制。论者对特定情境及其变动走向的感知,会调动其相关价值立场、态度和论辩能力等主观要素。显然,每项依据和理由都指涉特定互动结构的影响力。生活世界的多重维度自发地依据证成依据作为语境要素而展开[1]115。论者需要将每一重情境感知在真实性或者正确性上予以推进,从而导向其论辩目的。当然并非每一个目的仅仅需要单一路径予以证成,动态化语境以及主体互动对必然性和偶然性因素的灵活掌控,使通向特定有效性结论的路径有可能具体如“涉及最新的调查数据”,抽象如“做出好的论证”。
目的引导和建构者论证走向,其中包含着对依据整合难易程度与可行性的差异。例如主体对对方违约行为的追诉可能求助司法审判,也可以通过仲裁机构予以解决。依据特定利益状态的分析,以及有意收集的信息的属性,论者对特定论辩互动情境的预期,或者其目的实现及其程度的可能性估算,影响着当前论辩规划。行动-结果组合的关联性预估,就反映了这一点。该认知模式或者思维表述的呈现,如“倘若我妥协,就失去了获取遗产的机会”;“假定我承认自己的罪行,家人会对我失望”等等。特定结果作为可能发生的,使论者深感遗憾的检验性预期,呈现出论辩当中论者不得不权衡和考虑的问题。论辩目的在言说互动中的情境化,使论者向不同对象呈现其立场的表述模式也存在不同。当然,公诉机关将同样信息向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和法官分别进行传递,显然包含着不同回应模式的预期。这也体现出论辩规范性评价的公共性与识别标准的差异性,而“失去公共性的语言规则直接颠覆了语言中语词用法的一致性以及语词与对象之间的指称关系”[11]。论辩规则在认知层面上的分析,不但将论辩情境的变动性和阶段性考虑在内,而且兼顾了论辩主体针对情境感知,并对论辩规范性提升论辩规则体系的形成发挥了积极意义。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认知规则对具体问题和抽象问题的分野不够重视,同时也容易将论题作为论辩对象的思维实质,与论辩进程的操作模式融合起来。对此问题的重视,有助于法律论辩主题走向的明确化和论证效力的清晰化。
四、认知规则的运作模式——以情势变更原则为例
主体在认知网络当中确立可行的互动目的,其中包含着多重的和恰当的互动规则。而正是这些规则预设的假定条件,决定主体可能诉求的情境。这种规则模式可以表征为“如果论辩情境具备属性X,那么就可以追求目的G”[3]。论辩情境很有可能遇到意外的变动,论者的回应因循其认知范式和关注的视角而导向不同认知规范性理解,进而使他们适时调整论辩意图和预期。互动情境异动之所以能够给论者带来显著的影响,主要在于该异动使当下利益交互模式,和已经获得认同的利益分配模式受到了新的情境要素的影响。民法中的情势变更原则,就反映和确证了这种异动对论者预期协议的利益分配模式的影响。
在民法中,情势变更原则是合同在有效成立之后,因为不能归责于任何一方当事人的缘由发生了情势变化,导致合同基础动摇或者丧失,使合同继续维持原有效力将造成显失公平结果的情况,而允许当事人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6条的规定:“合同成立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解除。”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适用情势变更原则需要审慎结合相关条件予以论证。合同赖以存在的客观情境是否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否无法预见;是否不可归责于任何一方;是否发生于合同成立之后,履行完毕之前;以及继续履行是否会丧失合同目的或显失公平等。这些问题可以构成确认该原则适用的前提性论题“集合”。同时,情境识别和关联原则可以确立情势变更原则的语用学依据,认为情势变更本质上是言说互动背景的异动。关联原则认为作为协议形成与执行模式的商谈互动本质上属于认知过程,在共同的认知心理基础上,人们才能实现认知主体和认知对象,以及认知环境和交际意图的协调。关联原则能够激发法律人在全面分析案件事实与规范要素的互动中的判断智慧,他们可以结合推理效力预期和前提要素的多重发掘,从而有效提升语用推理的可接受性、正当性和合理性。
交际意图在由于特定关联要素的意外缺失,可能引发交际意图无法彻底落实或者只能部分落实的时候,就要求言说者调整对情境的认知模式,开展基于当下情境的新一轮商谈。新的协议如果无法限制在当事人认同界限,就有可能导致第二重基于法律规定的语用效果,那就是合同的撤销,即合同目的已经超越了仅仅是显失公平的结果,而无法在变更后的情境中得以行使。“一般而言,意图只能靠推理,而不能进行解码”[12]18。情势变更作为事态性信息,能够有效帮助当事人辨察其中包含的和其合同权利密切关联的要素,同时此信息在达成共识意见的情况下,将此意图传达给对方当事人,使其推导出对方当事人可能具有的变更或者撤销合同的意图。这种意图本身可接受性与有效性的论证需要建立在新情势对于当事人缔约期待落空的程度,以及双方对这种落空认同形成的判决或调解方案的理解方式和效益评估,因此需要尊重当事人意思的自治原则,确保当事人针对新形势中的利益协调,以及选择最佳方案的自由。
假定某协议缔结的语境基础集合中CN有C1、C2、C3……Cn几种情境要素涉及合同目的能否完整实现,其中任何情境要素的实际发生就都有可能使当事人不得不重新考虑原有合同中权利义务关系是否需要存续下去。作为情境基础的互动前提,是否和个人意图具有关联性,需要从交往主体的互动目的以及双方的共享知识背景的理解为前提。例如,可以从以下几种可能性中予以考察:
P1:情景要素C1根本未曾在缔约以及合同履行中被当事人考虑、预估或意识到;
P2:情境要素C2在缔约时被考虑到,但当事人保有该情境A稳定不变的确信;
P3:情境要素C3及其可能的变动情况在缔约时被考虑到,并根据预估与计算,各方当事人相信缔约后以及履行完毕前,该变动不会对合同效力及其目的的实现产生任何影响;
P4:情境要素C4及其可能的变动情况在缔约时被考虑到,并根据预估与计算,各方当事人相信缔约后以及履行完毕前,该变动会对合同效力或者目的的实现产生影响,但仍然约定回避对该变动的影响的回应,坚持按照合同原有内容予以履行;
P5:情境要素C5及其可能的变动情况在缔约时被考虑到,并根据预估与计算,各方当事人相信缔约后以及履行完毕前,该变动会对合同效力或者目的实现产生影响,约定变更合同内容,使缔约在关照各方当事人交易预期的基础上,更加符合变动后的情境……
从上述判断可以得出,情景要素是否包含在或隐含在作为缔约基础的初始语境当中,和初始语境的关联性程度,以及初始语境得以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延伸进度的考察,需要建立在缔约人的认知基础之上,尽管当事人对未来权利义务关系基于情势背景的走向未必完全精准,至少都反映了他们的真实意图。事实上,P1到P5这几种可能性都发生在缔约过程中,它们都深刻影响着当事人在合同开始履行之后是否约定适用情势变更原则。P1到P5作为缔约互动模式的可能客观走向,为事后情势变更效力的裁判提供了语用推理的前提,和理解合同履行中异动事件的整体性影响的参照性(inferential)依据。因此它们决定的不是单一的语境,而是一系列的可能语境[13]141,异动要素的具体提取和合同约定相关要素的关联性是对合同情境特定部分予以重新理解、商谈及处置的根本依据。从直觉上来判断,关联理论涉及话语效力、思维现象及其推断结果。因而,情势变更成为主体进行推论的外置信息,结合其导入判断内置的情境类型实现对特定语境含义的理解。
从认知科学的角度分析法律论证规则问题,目前在国内外学界鲜有探讨。本文从法律论辩规范性入手,通过论者主体的个性、论者意图的建构意义和论题识别与认定等分析尝试着手此论题。如上文所言,对于理性言说主体来说论证情境的异动和逻辑规则的协调,必然和论者自身意图结合在一起,实现意义诠释和理解[14]608。这就对法律论辩整合语言使用与论者心智状态提供了切入点。论者的认知模型如何遵循论证的规范性,如何进一步通过逻辑学的形式化对参与各方的心智状态,在基于法律原则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的界定与描述,从而在外部论辩对话与内部认知状态之间搭建起规范性的桥梁。本文提出这些问题,是期待整合法学、语用学和认知科学的理论精髓,为法律论证规则的研究提出新的思路。
[1]DaleHample.Arguing:Exchanging Reasons Face to Face[M].New Jersey: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 Publishers,2005.
[2]Shimanoff.Communication rules:Theory and Research[M].Beverly Hills,CA:Sage Publications,1980.
[3]S R Wilson.Development and test of a cognitive rule model of interaction goals[J].Communication Monographs,1990,57(2).
[4]J R Meyer.Cognitive influence on the ability to address interaction goals[M]//J.O.Greene.Message production:Advance in communication theory. Mahvah,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ion,1997.
[5]J P Dillard,D H Solomon.Conceptualizing context in message-production research[J].Communication Theory,2000,(10).
[6]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言说理论[M].舒国滢,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7]徐梦醒,张斌峰.法律论证的语用逻辑重构[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4,(5).
[8]Jürgen Habermas.On the Pragmatics of Communication[M].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8.
[9]J L Austin.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M].Oxford:Clarendon Press,1962.
[10]工伤“新规”众议[EB/OL].http://fbgl.fyfz.cn/b/823762.
[11]郑友奇,熊明丽.从语言批判到哲学批判——维特根斯坦私人语言论证及其哲学意蕴[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
[12]何自然,冉永平.语用与认知——关联理论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13]Sperber.D.Deirdre Wilson.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Second edtion)[M].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1995.
[14]Lawrance R.Horn and Gregory Ward.The handbook of pragmatics[M].London:Blackwell Publishing,2006.
[责任编辑:马建强]
D90
A
1001-4799(2016)06-0098-07
2015-12-20
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5130
徐梦醒(1986-),女,河南许昌人,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法律逻辑学、法学方法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