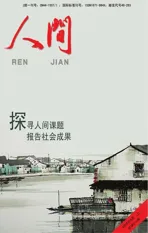浅析《齐物论》中的“吾丧我”
2016-11-29任晓娜西藏民族大学陕西咸阳712000
任晓娜(西藏民族大学,陕西 咸阳 712000)
浅析《齐物论》中的“吾丧我”
任晓娜
(西藏民族大学,陕西 咸阳712000)
摘要:《齐物论》是《庄子》内篇的一篇,篇幅较长,且晦涩难懂。开篇通过南郭子綦与颜成子游的对话引出“吾丧我”。主要讲述了通过“坐忘”和“吾丧我”以追求绝对的自由精神,空虚寂静,最后达到忘我的“物化”境界,真正领悟到“道”,以实现万物与我为一。其中“吾”、“丧”和“我”各有不同含义,且与“天籁”、“地籁”、“人籁”有着密切关系。
关键词:齐物论;吾丧我;物化;天籁
庄子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道,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批判了世俗社会的礼、权、法。认为懂得“大道”的人,不应该受世俗的限制,一味地因自己心中的执着,去看重世间的是非观念,看重生与死。庄子认为人们应去追求“天地与我齐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世界,万物与我一样,为道所生,并且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是绝对的精神自由,不仅不依靠任何外物,内心也不受任何限制。那么对于“吾丧我”,我们应当分两个层次来理解。一个是世俗世界的“我”,即“俗我”;一个是绝对自由的精神世界的的“吾”,即“真我”。
一、何为“吾丧我”
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汝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庄子在《齐物论》的开篇中,通过南郭子綦与颜成子游的对话引出“吾丧我”。 从语法看,“吾”、“我”皆是第一人称代词。两者不同之处在于,“吾”只能充当主语,不能用于宾语。而“我”既可当主语,又可以用作宾语。从词义来看,“吾”是第一人称的普通代词,起陈述作用。“我”是第一人称的特殊指代,表明自身的的特殊品质,是一种情意性的表达。维基百科中,认为“我”是指人的“成心”,会随着言语,不断往外追索;“吾”是人的“超越主体”,庄子称为“真宰”,人心应回复到最自然的虚灵状态。
从文章中理解,“吾”为精神世界中的我,“我”为世俗中偏执的我。中国魏晋时代哲学家郭象曾这样释义,“吾丧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识哉!故都忘内外,然后超然俱得。”文中从忘物到忘形,从忘形到忘我。忘物,不仅要忘掉具体事物,还要忘掉伦理纲常;忘形,使形如槁木,忘掉生与死;忘我,忘掉自我所执,是自己的精神与天地精神自由往来。“吾”即“真我”,不执著于区分是与非,长与短,认为万物虽然多种多样,但从道的角度,道的世界来看,万物都是一样的.“真我”,既不执著于生,也不厌恶死,一切顺其自然,不偏执,不为世间万物去“劳”自己的“神明”,超越世俗的生活,超越世俗的一切束缚和限制,在精神上追求最大的超越和自由。而“我”即“俗我”,看重生死,迷惑于世间万物,受礼仪制度的限制,看重万物表象的多样性,并且努力区分万物的不同。
为了更好的解释“吾丧我”,庄子在《齐物论》中以“天籁”、“地籁”、“人籁”的比喻来阐述“吾丧我”。子游曰:“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籁。”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耶!”郭象注,夫天籁者,岂复别有一物哉?即众窍比竹之属,接乎有生之类,会而共成一天耳。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人籁,人吹竹管发出的声音;地籁,“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指风吹各种孔窍所发出千差万别的声音,以形象的语言描述各种不同的现象,千变万化。同时为下文的“与接为构,日以心斗”做铺垫,进一步描述了世俗社会中人们勾心斗角的心理状态。郭象以自己“独化论”为核心,注解《庄子》。独化,一个绝对个体的活动变化,自生、自存自由的状态。他注解,夫天籁者,岂复别有一物哉?天籁并不是一个具体事物,而是一个境界,要超越人籁地籁,要“坐忘”、“丧我”,忘掉知识、礼乐、仁义,不看重生死,不妄执,要通过精神修养的“心斋”,即为心灵净化而进行的斋戒,才能到达“无己”、“吾丧我”的境界,也就到达了天籁的世界,达到了“大道”的绝对自由的精神世界。
二、为何“吾丧我”
庄子认为,道是万物存在的根本,万事万物都是从道派生出来的,道是“自本自根”的,即道的存在是第一性的。从具体事物来看,有的分散,有的聚集;有的消失,有的形成。万物的差别是相对而言的,而且万物总是处在不断的生灭转化中,这些差别总是暂时的。但从道的角度看,这些都是道的表现,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而要到达“道”的精神境界,则需要通过“坐忘”,进入到“吾丧我”、“无己”的境界。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郭象注解,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曰芒。“芒”,芒昧也,迷昧不知之意。万物虽异,至于生不由知,则未有不同者也,故天下莫不芒也。因为自己心中的偏执,追究万事万物的区别,而不知万物表象千差万别,其本质一样,一直区别事物,只会“劳神明”而已,正如“朝三”与“暮四”实质上是一样的。在世俗社会中,“我”即“俗我”,容易被“芒”所遮蔽。而“吾”即“真我”,要达到“真我”的世界,则需要“俗我”去掉“芒”,忘掉世俗的我。
庄子要破除人们心中所执迷的“有待”而进入到“无待”的绝对自由的精神世界。身体不受任何限制,也不受世俗礼节的约束,真正达到了“吾丧我”的世界。
三、如何到达“吾丧我”
“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说是,则莫若以明。”郭象注,小成者,谓仁义五德,小道而有所成得者,谓之小成也。世薄时浇,唯有仁义,不能行于大道,故言隐于小成,而道不可隐也。庄子认为执著偏见的人,凭借自己的主观意见分析“大道”,“大道”则被掩盖;不明事理的人,靠浮华的辞藻分析真理,则真理被花言巧语所遮掩。所以才有了儒家和墨家的是非之辩论,双方各自认为对方所认定错的是正确的,对方所认定对的是错误的。想要肯定对方否定的,否定对方肯定的,要以“明”观之。劳思光认为儒墨各囿于成见。而欲破除彼等之成见,则唯有以虚静之心观照。虚静之心,即认为事物不分彼与此,不分是与非,破除事物之间的相对,超越事物之间的相对。以此明彼,以彼明此,跳出自己的偏见。大道,自本自根,道的存在是第一性的。道,是万事万物的根本,是万事万物的来源。
“丧”又有丢掉、失去之意,所以“丧我”就要丢弃“俗我”,破除心中所指,那么“真我”就会与大道合二为一,体悟到
绝对自由的精神世界,在“真我”看来,万事万物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没有是非区分,也没有彼此区分,从而达到“齐万物与我为一”,达到“无己”的境界。其中“齐万物与我为一”中的“我”为“真我”,已无“芒”、无“成心”即已无偏执之心。
四、通过“吾丧我”所要达到的境界
庄子的《齐物论》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齐物”之论,另一方面是“齐”之“物论”。庄子在《秋水》一篇中,这样写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从大道的角度看,万物没有贵贱的区别;万物从自身出发,都觉得自己贵而别物贱;从世俗的角度看,万物的贵贱不在自身。而庄子同样也在《齐物论》中这样说到,“莛与楹,厉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中国魏晋时代的哲学家郭象注解,理虽万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为一。即理一分殊,万物各自有理,但事实上万物各自的理最终只是一个理,各物的理都是相同的,没有任何区别。无论草茎还是屋柱,无论丑女还是美女,也不管宽大、奇异、狡诈,一切差别,从道的角度来看,是没有差别的,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彼此相通,这就是“齐”。道是一个整体,贯通万物,而万物也统一于道。“道通为一”,是从道的角度讲万物的统一性,道为一,万物为多。“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事物没有什么形成,也没有什么毁灭,从道的角度看,成与毁是相通的,一样的,这便是“复通为一”。无论是与非,成与毁,丑与美,都没有准确的标准,人们不应该执著于区分事物的差别,虽然它们表象不断变化,但实质上都是相同的,没有差别。庄子在《齐物论》的最后,讲述了庄周梦蝶的故事,“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不知道是庄子梦见自己成为蝴蝶,还是蝴蝶梦见它变成了庄周。其实庄周就是蝴蝶,蝴蝶就是庄周,两者是一样的。同时与庄子的主旨相同,与“天下万物与我为一“相呼应,天下万物和我是一样的,这里的“我”为“真我”,我与万物没有差别,这就是“物化”,也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我”同“万物”一样,都是道所生,这样就到达了“道”的境界。
“物论”则是人们关于事物的理论。对同一事物,不同的人因为心中所执,即“成心”,对事物有着不同的看法,以自己的“所是”为标准。然而事实上,并没有是非标准,因而也没有是非。比如庄子在《齐物论》中写到的,“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我和你一起辩论,你赢了我,我输给你,你果真是对的,我果真是错的么?从大道来看,是与非没有标准,也没有是非,万事万物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差别。庄子将这一观点也引申到儒墨之辩上,认为儒家墨家都是执自己“所是”,而去辩论,以至于不能达到“道”的境界。
参考文献:
[1]白瑞芬:“吾丧我”庄子心灵自由的绝对境界[J],湖北社会科学,2012,(05).
[2]郭齐勇:中国哲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罗安宪:庄子“吾丧我”义解[J],哲学研究,2013,(06).
[4]祁涛:《齐物论》中“三籁”问题的再探讨[J],华夏文化,2013,(09).
[5]张一:从“吾丧我”解读庄子《齐物论》[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4,(07).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6-0038-02
作者简介:任晓娜(1991-),女,汉族,山西临汾人,现为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级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