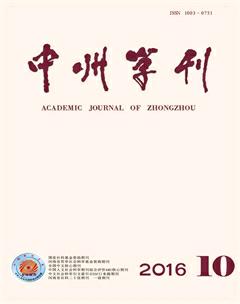艺术创造的转化与美学转向
2016-11-26席格
摘要:当下,艺术创造作为概念,俨然已被文化创意所替代。其原因主要有三:现代技术的革新、审美经济的勃兴和艺术自身发展对“美的艺术”观念的打破。在艺术创造向文化创意转化的过程中,对艺术创造形成内在规定性的美的神圣性并未得到有效延续,从而使艺术审美中潜藏的审美悖论凸显出来:艺术是呈现真理、引导本真生存还是创造“美丽学”之“美”;艺术的价值取向是注重审美价值还是追逐经济价值;艺术审美活动对人的主体性是审美超越与还原,还是审美满足与强化。由此,艺术创造转化客观上带来了现实感性的充盈,同时也造成文化垃圾的充斥。这两者无论在审美实践层面,还是在美学理论层面,都引发了诸多问题。在20世纪早期,西方诸多理论家已对此关注并深入反思,尤以海德格尔、本雅明为代表。虽然两人理论的基础、进路等存在着根本性差异,却从不同维度对当下如何突破艺术创造转化所造成的理论困境提供了启示。这种启示在于,重树美的神圣性对艺术创造及文化创意的内在规约,实现美从认识性对象到生存方式的转换,促成美学学科由认识论美学向生存论美学的转向。
关键词:艺术创造;文化创意;海德格尔;本雅明;美的神圣性
中图分类号:J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0-0148-07
20世纪初,文化工业的兴起,实则已经开启“艺术的产业化”和“产业的艺术化”。这也意味着艺术创造转化的开始。时至当下,随着审美经济的蓬勃发展,无论是原本属于“美的艺术”的音乐、舞蹈,还是在艺术疆域拓展后纳入其中的影视、动漫、设计等,似乎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应有构成。那么,艺术何以成了文化创意?除了技术革新、审美经济推动的现实动因之外,还有艺术自身发展致使艺术观念发生深刻变革的理论动因。如果说艺术与文化创意之间具有天然的内在性关联,那么其桥梁便在于艺术创造向文化创意的转化。该转化在促成现实日常生活中感性充盈的同时,也导致艺术与美走向泛化,并凸显了艺术审美自身所潜藏的审美悖论。尤其是文化创意向文化垃圾的转变,更进一步彰显出美的神圣性对艺术创造及文化创意内在规定的不可或缺。但艺术创造与文化创意的关联性问题,目前在美学维度并没有得到系统深入的研究。如文化创意纳入美学理论研究的合法性问题,便鲜有论及。有鉴于此,本文将重点梳理和探讨艺术创造向文化创意转化的动因,以及转化所凸显出来的艺术审美悖论,进而通过对海德格尔与本雅明关于艺术创造转化理论回应的考察,审视文化创意与美学理论发展的根本路径所在。
一、艺术创造向文化创意转化的动因
艺术创造,在内涵方面主要与想象力、原创性、天才、自由等概念密切关联。根据塔塔尔凯维奇的考察,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创造性”字眼才开始出现;到18世纪,“创造性”才在艺术理论中频繁出现;“及至19世纪,艺术脱胎换骨,一反先前的世纪那等不敢承认创造性为其本质的面貌”①;到了20世纪,“创造性”的使用范围则是超出艺术领域,扩展到科技、文化领域。文化创意概念的出现,某种意义上亦可视为“创造性”使用范围扩大的一个结
收稿日期:2016-08-01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文化创意维度的美学原理变革研究”(2014BWX008)。
作者简介:席格,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郑州450002)。
果。作为艺术创造的一个替代性概念,文化创意主要与想象力、创新性、产业化等概念密切关联。就现实发生而言,文化创意萌芽于20世纪早期兴起的文化工业,正式提出则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换言之,艺术创造向文化创意的转化,是在文化工业向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递变过程中逐步达成的。如阿多诺在《文化工业述要》中对“文化工业”一词进行解释时,明确指出它是“把家喻户晓、老掉牙的东西加以熔汇,产生出一种新的东西来”②。而要达成此目的,必须诉诸艺术思维,诉诸创新、创造与创意。到了文化创意产业阶段,更是直接将诸多艺术形式纳入产业化模式之中,文化创意替代了艺术创造。可见,艺术创造的概念转化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段。这一过程,不仅具有强大的现实推动力,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动因。
就现实动因而言,首先在于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传播技术的不断革新。艺术自诞生之日起便与技术具有内在性关联,在创作与传播两个层面都深受技术水平的影响。关于现代技术变革对艺术的影响,本雅明曾指出:“一九〇〇年前后,技术复制所达到的水准,不仅使它把流传下来的所有艺术作品都成了复制对象,使艺术作品的影响经受最深刻的变革,而且它还在艺术的创作方式中占据了一席之地。”③显然,本雅明既看到了艺术传播技术的革新,又看到了技术变革对艺术创作的影响。事实上,新技术不仅诱发了传统艺术形式创作手段的新变,催生了新的艺术形式,而且为艺术作品传播方式的革新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可能。所以,在技术革新的推动下,艺术与生活的融合走向深入,并以文化创意的形式促成了现实感性的充盈。
技术进步为艺术创造走向“艺术生产”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支撑,特别是艺术创造依托新技术所形成的新艺术形式,本身就是艺术创造向文化创意转化的产物。例如:“电影放映机起初是记录运动的机器,后来被戏剧、梦想、休闲所利用;本来只有通讯价值的无线电报机,后来也轮到它被游戏、音乐、消遣所利用。”④尽管在原有“美的艺术”观念中,电影、电视早期并不属于艺术的行列,但随着“美的艺术”边界的打破,它们早已被纳入艺术的领域。正是新技术对艺术创造及传播技术条件的革新,强化了艺术作品的可复制性,使艺术具有了产业化发展的可能。在艺术创造技术手段逐步革新的过程中,艺术创造自身的个体性、唯一性、崇高性等特征被消解,最终走向大众化、可复制、媚俗性的文化创意。
其次,在于体验经济对资本介入艺术创造的强化。20世纪中叶之后,技术进步在西方引发了社会的全方位变革,对艺术创造的影响主要在于:人们因生产技术进步而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得到相当程度的解放,闲暇时间大幅度增加,且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由此,人们对用于消磨闲暇时间的娱乐对象的形式、内容及审美品质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化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加剧,为了提升竞争力,文化工业之“产业艺术化”的发展方向受到推崇,文化工业得以逐步向“体验工业”转变。尽管前者重在文化产品的审美价值,而后者重在文化产品的经济价值,但由于文化产品经济价值的实现要以其审美价值为内在前提,所以提升文化产品审美品格自然成为文化工业发展必须直面的问题。为此,文化工业既要强化对艺术创造的运用,又要不断实现技术手段的革新。而强化艺术创造力的运用,便要吸引高层次的艺术人才乃至艺术家加入文化生产者的行列,自然要求加大资本投入;技术的研发、创新与运用,更是需要大量资本作为基础和前提。这就共同导致文化工业逐步强化了资本本身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相应地,文化工业先前被赋予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意识形态色彩逐步被淡化,得以向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产业转变。在资本大量投入的状况下,艺术创造需要满足人们休闲娱乐的审美消费需求,并由此在产品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但追求个性化、唯一性与非功利性的艺术创造,根本无法适应体验经济的资本逻辑,因而只能转向大众化、可复制性与功利性的文化创意。可以说,体验经济、审美经济的发展,对艺术创造向文化创意转化起到了催化作用。endprint
就理论动因而言,则在于艺术自身发展对“美的艺术”边界的打破。20世纪初,艺术自身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反审美、反艺术的特征,“美的艺术”的观念随之被打破并不断被泛化。1917年,杜尚《泉》的展出,以“现成品艺术”的形式,宣布了对“艺术品”与“普通物品”之间区隔界限的打破。由此,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分野随之被突破。费瑟斯通在论及20世纪初艺术自身发展的特征时曾直言,“在一次世界大战和本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的达达主义、历史先锋派及超现实主义运动”,“这些流派的作品、著作及其活生生的生活事件中,他们追求的就是消解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⑤艺术观念的泛化乃至泛滥,在某种意义上是因对艺术作品中“物因素”的凸显与强调而触发的。就文化创意而言,它虽强调了艺术创造创新性的特征,却极大地降低了艺术创造基本技能的门槛;虽拓展了艺术王国的疆域,却造成了艺术自律性、神圣性的消解,促使艺术与生活、文化的边界日趋消融。这为艺术创造向文化创意的转化提供了契机。
从艺术创造转化所带来的双重影响可以看出,艺术创造与文化创意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换言之,艺术创造在向文化创意转化的过程中,虽展现为艺术的泛化、艺术功能的转变和艺术概念界定的含混,但其实质则在于艺术创造丧失了之所以成为艺术创造的内在规定性。文化创意虽然在概念上替代了艺术创造,但它并不完全等同于艺术创造,其具有自身的时代性特征。大致而言,两者的共同之处主要在于:都强调运用艺术思维,都注重发挥审美想象力,都强调创新性。不同之处主要在于:艺术创造具有神圣性,重在对主体性的消解而实现自由生存方式的审美还原,而文化创意凸显的却是世俗性,重在对主体性欲求的满足,结果陷入了理性与感性冲突的生存悖论之中,遮蔽了自由;艺术创造的创新是具有鲜明的艺术家个人气质的独创,而文化创意因为资本逻辑的驱动,在追求创新性的同时又强调标准化,形成了创新性与标准化、模式化的矛盾;艺术创造重在强调艺术内容的独创,而文化创意则是着重对文化资源内容与形式的双重创新;艺术创造的范围主要限定在艺术领域之内,而文化创意既包括传统的艺术创造,又包括对生活的创造。如贾斯汀·奥康诺便明确认为:“如果创意产业生产文化价值,那么从一个宽泛的意义上来说,很明显,‘艺术是创意产业的一部分。在那种意义上,太多的‘艺术不能归入——是一种补贴或者相反——创意产业的范畴中,因为它们已经包含在创意产业的范畴之内了。”⑥正是艺术创造向文化创意转化过程中自身产生的变革,使艺术审美(包括文化创意所关涉的审美)凸显了自身原本就潜藏的审美悖论。
二、艺术创造转化对艺术审美悖论的凸显
艺术创造向文化创意的转化,在现实层面具体展现为艺术家向艺术生产者的转化、艺术作品向文化创意产品的转化。这三个维度的转化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并直接催生了艺术审美活动的变革,艺术审美追求的位移,从而映射出现代人精神生存状况的剧变。艺术作为人与世界关系建构的一种方式,承载着引导人们在精神生存维度实现自由和谐的重任。但随着艺术创造、艺术家及艺术作品的转化,艺术审美的境界追求在文化创意审美中并没有得到有效延续,而是发生了从自由和谐之生存境界向世俗性审美需求满足和创意产品经济价值最大化的位移。尽管我们可以认为资本与艺术的深度结盟对此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就根本原因而言,却在于艺术审美本身就潜藏着悖论,为审美追求的位移提供了可能。只是艺术创造向文化创意的转化,为艺术审美悖论的凸显提供了契机,并通过审美追求的位移集中呈现了出来。简言之,所凸显的艺术审美悖论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关于艺术对美的追求,是以呈现真理、引导本真生存为美,还是要展现“美丽学”之“美”。艺术以何为美,也就是在艺术创造过程中依靠什么引导和规约艺术创造力。艺术之所以被赋予神圣性,关键就在于真理、自由和谐的生存境界对艺术创造力的引导和规约,促使艺术致力于呈现真理、引导本真生存。相应地,艺术审美,便是诉诸艺术审美活动来引导人们体验真理、体验本真性的存在,实现自由生存。显然,该审美效果的达成,首先取决于艺术作品自身所能达到的境界,也即取决于艺术家的境界及其艺术创造力,并不取决于艺术作品的外在形式。换言之,就人的感官判断而言,艺术作品外在呈现形式的美与丑并不影响艺术作品本身对最高审美境界的追求。需要强调的是,以“美丽”“漂亮”“动听”等为标志的艺术作品,虽在形式上能给人带来一定程度的审美满足,但这并不是艺术创造的根本性追求,也不是艺术作品价值判断的根本性依据。相反,以视听为代表的人的主体性审美欲求,恰恰理应是艺术创造要超越的内容。当然,就审美发生而言,外在形式与人们感官审美欲求相契合的艺术作品,更易于在精神维度与人相接相交。所以,艺术创造力,由于能够呈现真理、引导自由和谐的生成方式,而被奉为“天才”,被赋予了神圣性、非凡性。
艺术创造转化为文化创意之后,受资本逻辑的推动,“天才”观念在文化创意中被严重淡化。因为,文化创意既不致力于对真理的呈现,也不试图引导自由和谐的生存状态,而是注重人以视听为主的身体感官体验需求的满足,强调“美丽学”意义上的“美”的塑造,以实现文化创意产品经济价值的最大化。这导致在文化创意中真理被悬置,精神审美追求让位给感官审美欲求;对社会的批判转向了媚世,即对一些审美风尚、审美趣味的迎合,甚至于积极主动地献媚。即便是被启蒙主义者赋予的启蒙大众的责任,在艺术创造转化为文化创意之后,也已不再被强调,而是走向了娱乐大众。正是在此背景下,贾斯汀·奥康诺认为:“当‘艺术天才的观念被艺术史和文化研究抛弃时,‘创造力呈现为一个新的、普遍的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⑦尽管文化创意在社会经济维度获得较大发展,并被认为有力推动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但人们的生存境界实质上并没有从中获得提升,因为大多文化创意产品所追求的“美”主要在于“美丽”“漂亮”“动听”等外在形式。
第二,关于艺术的价值取向,是崇尚审美价值还是追逐经济价值。艺术自身承载着多重价值,如审美价值、文化价值、伦理价值、经济价值等。但就艺术作为人生在世追求自由和谐生存境界的审美路径而言,其最大价值就在于通过艺术审美活动对人的非本真生存方式的超越,来实现人生存境界的提升。换言之,艺术自觉之后,审美价值便在艺术诸价值中位于首要地位。相较而言,艺术的经济价值在相当长的时段内并未受到普遍性的高度重视。直到20世纪,受技术革新和文化工业发展影响,随着艺术创造向文化创意的转变,艺术的价值重心才发生位移,即从审美价值向经济价值过渡。这必然对文化创意产品的审美品格造成深刻影响,使之缺乏应有的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与神圣感,展现出碎片化、平面化、世俗化的特征。阿多诺对此曾批判地指出,“文化工业调制出来的东西既不是幸福生活的向导,也不是有道德责任感的新艺术”⑧。他的论断虽有过激之嫌,却准确地指出了艺术作品成为文化创意产品之后,两者价值追求的差异。endprint
如果说艺术作品的价值追求,是艺术家通过充分发挥自身“天才”的艺术创造力,为真理的自行置入提供契机,或者是逐步引导人们超越主体性而实现自由和谐的本真生存状态,从而凸显出审美价值;而文化创意产品,则是艺术生产者通过运用作为一般性资源的创造力,追求新奇、震撼、媚世等,以满足大众表层感官审美欲求,提升创意产品在文化市场的竞争力,最终凸显的自然是经济价值。价值追求的差异,直接关涉艺术作品与文化创意产品审美品格的评判。就艺术创造而言,对审美价值的追求,内在地要求其审美品格,既要与人们的审美需求具有契合度,又要求超越现有审美需求以引导人们提升生存境界,从而对人们形成审美教育。就文化创意而言,对经济价值最大化的追求,注定其审美品格主要限于对大众审美需求的满足,对精神与现实生存的超越性便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进而言之,文化创意产品的审美品格,实则是在审美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张力之间摆动。当对经济价值盲目过度追求时,文化创意产品的审美价值会受到极度挤压,文化创意便会堕落成为文化垃圾。但是,当文化创意充分尊重审美规律、追求审美价值、追求自由和谐的生存境界时,却在客观上会促进经济价值的追求与实现。这样的文化创意产品并不常见,可谓是经典性的创意,与经典的艺术作品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第三,关于艺术与主体的关系,艺术审美是谋求对主体性的审美超越与还原,还是注重满足主体性的审美欲求,进而强化主体性。艺术作品,作为“人工制品”,具有认识的向度。这使其很容易被置入主客二分的模式中,被视为满足人主体性追求的路径。但就人追求本真生存的维度而言,艺术的最高审美追求在于通过审美活动实现人的本真生存。这就内在地要求艺术审美必须促使人认识到主体性生存方式的不足,逐步超越人主体性的外在追求;同时,让人在超越主体性的过程中,逐步向本真生存还原。因为在审美活动中,对主体性的超越与还原乃是“一体两面”同时进行的,艺术审美同样如此。也正是基于主体性的消解,人在艺术审美中方能与本真世界一体,天、地、神、人实现合一,也即艺术追求审美价值,追求呈现真理、引导本真生存,最终都是指向主体性的消解。
与此相反,在文化创意中,由于注重“美丽学”层面的形式审美,也即对大众视觉、听觉、味觉等主体性欲望的满足,强调对经济价值的追逐,最终指向的乃是主体性的强化。在艺术审美中,虽然并不否认艺术作品能够满足一定的主体性审美需求,但最终是要超越主体性审美,走向互主体性审美甚至无主体性的审美。文化创意对审美价值不同程度的牺牲,对大众审美的满足乃至迎合,注定其与呈现真理、引导本真生存的审美追求相背离。这也就不难理解,经典的文化创意十分少见,文化垃圾却到处充斥。另外,由于高新技术在文化创意发展中发挥着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文化创意的主体性倾向。因为,“在以技术方式组织起来的人的全球性帝国主义中,人的主观主义达到了它的登峰造极的地步……现代的主体性之自由完全消溶于与主体性相应的客体性之中了”⑨。文化创意审美对主体性的强化,不仅影响精神生存境界的提升,而且会影响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身心关系的和谐,影响到人对自由本真生存方式的建构。
整体来看,文化创意对艺术审美悖论的凸显,实际呈现为艺术和美的泛化、滥用,艺术审美品格的降低。当然,这并不否认在文化创意实践中,由于对艺术创造之神圣性的坚守,能够以美的神圣性去规约文化创意,最终生产出了一些优秀的文化创意产品。但更应该看到,文化创意与文化垃圾之间区隔的模糊性,对美的神圣性、艺术创造之于文化创意的重要性的凸显。所以,在艺术创造向文化创意转化早期,阿多诺就严厉批判文化工业的负效应:“文化工业有意地自上而下整合其消费者,它把分离了数千年,各自为政、互不干扰的高雅艺术与低俗艺术强行拼合在一块,结果是两者俱损。”⑩当然,艺术创造向文化创意的转化,在客观上打破了艺术精英主义、艺术推动了艺术民主化的发展,推动了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催生了“新感性”,从而促使感性在日常生活中处于充盈状态。艺术创造向文化创意转化的这种双重性,是艺术创造与文化创意之间具有内在关联的明证,基于此,将文化创意纳入美学研究领域获得了合法性;艺术创造转化催生了纷繁复杂的审美实践,并向传统美学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
三、关于艺术创造转化的理论反思
艺术创造向文化创意转化所引发的美学理论问题,概言有三:一是如何理解与界定艺术美。艺术创造转化所凸显的审美悖论,实质上乃是如何理解艺术美的问题:艺术是以对真理的揭示与呈现为美,还是以外在的“漂亮”“美丽”等为美。进而言之,则是如何理解美的问题,关乎对美的本质的探讨。二是美学学科的艺术哲学定位。当艺术作品转化为文化创意产品,艺术与生活、文化日趋融合时,便意味着自黑格尔以降的美学作为“美的艺术的哲学”学科定位,在介入文化创意产品时失去了应有的理论有效性,必须进行理论调整。三是关于美学作为感性学的理解。文化创意勃兴推动了感性的生产,也促成了感性的充盈状态。在美学维度重新审视感性,是将其作为人生在世主体欲求满足的路径,还是将其作为向自由和谐生存状态回归的路径,直接影响着美学如何向感性学回归的判定。
这三个维度的理论问题,特别是其中包含的艺术与技术的关系、何谓艺术、艺术美的界定等问题,其实在20世纪早期便已经开始引发诸多理论家、艺术家的关注,如布莱希特、阿尔都斯·赫胥黎、海德格尔、马尔库塞、本雅明、阿多诺等。他们从不同视角对艺术创造转化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应,大致可以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根本层面转变理论视角,从存在论哲学出发进行审视。如海德格尔基于现象学,通过解释学循环对艺术作品的本源进行了追问。另一类则是在传统的主体性哲学框架内,对艺术创造转化所引发的变革采取或批判的态度(如马尔库塞、阿多诺),或肯定的态度(如本雅明)。但在意识形态观念弱化、审美经济发展占据主导的境遇中,对文化工业的理论批判并未阻碍其向文化创意产业的转变与发展,当然也没有阻碍艺术创造向文化创意转化的现实进程。不仅如此,文化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在艺术与非艺术之间形成了连续性,从而推动艺术与生活、文化走向深度融合,促使美学由艺术哲学向文化哲学转换。相应地,对文化工业的理论肯定,如本雅明关于机械复制技术对艺术影响的论断,得到了进一步的理论延展。结合当下美学发展所面对的历史境遇来看,海德格尔与本雅明所作出的理论回应,无疑具有巨大的理论包容性、启发性,为当下探讨美学学科转型问题提供了方向。endprint
先看海德格尔。他在1935—1936年间结集出版的《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在“物与作品”一节针对艺术作品的“物因素”问题进行了讨论,进而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作品与真理”“真理与艺术”。对海德格尔而言,艺术作品与普通物品都是真理现身的通道,只是艺术作品更便于说明真理现身的过程。所以,他没有选择一双普通的农鞋,而是选择了梵高的名作《农鞋》。尤为重要的是,海德格尔在论述中明确地指出了艺术与美的关系:“艺术的本质就应该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置入作品。可是迄今为止,人们却一直认为艺术是与美的东西或美有关的,而与真理毫不相干。产生这类作品的艺术,亦被称为美的艺术,以便与生产器具的手工艺区别开来。在美的艺术中,艺术本身无所谓美,它之所以得到此名是因为它产生美。相反,真理倒是属于逻辑的,而美留给了美学。”在这里,海德格尔明确指出了艺术的本质在于“存在者的真理自行置入作品”,那么,作品自然便是真理现身的一种重要方式。依据这一论断,如果艺术放弃了对真理的呈现,艺术便将不再成其为艺术。同时,海德格尔在这里已经指出了艺术的美在于真理在艺术中的现身。对此,他在“作品与真理”一节中进行了明确表述:“美乃是作为无蔽的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
当然,海德格尔也直接对艺术创造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反思,即在“真理与艺术”中对器具之制作与作品的创作通过溯源进行了解释。他指出:“无论是作品的制造,还是器具的制造,都是在生产中发生的,这种生产自始就使得存在者以其外观而出现于在场中。”可见,作品与器具在生产方面具有相似性,但作品之所以不同于器具,关键就在于作品制造的过程乃是真理涌现的过程。“我们就可以把创作规定为:让某物作为一个被生产的东西而出现。作品之成为作品,是真理之生成和发生的一种方式。一切全然在于真理的本质中。”真理的生发内在地规定了作品之所以能够成其为作品,也赋予了作品区别于器具的本质所在。所以,海德格尔说:“当生产过程特地带来存在者之敞开性亦即真理之际,被生产者就是作品。这种生产就是创作。”他通过现象学的追问,强调了艺术得以成为艺术的本质所在,即艺术与真理的内在性关联。简单地说,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就在于它具有使真理敞开的神圣性。同时,海德格尔在现象学框架内对艺术作品本源的反思,实则是建基在人与物的非对象性关系之上的,即他否定了艺术创造是对真理的主体性的认知,而强调真理的“自行置入”,超越了认识论的模式。因此,如果艺术创造在向文化创意转化过程中,依然能够将真理置入敞开领域,那么,便不会坠入对主体性欲求的满足与强化。或者说,真理涌现所赋予艺术的美的神圣性,对艺术成为艺术具有内在的规定性,确保着艺术(包括文化创意)的审美品格。
再看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5—1936)中,本雅明明确指出了技术变革对艺术作品“本真性”的影响,即本真的艺术作品的价值根基已经从“礼仪”过渡到“政治”。相应地,艺术作品的价值,则从膜拜价值向展览价值转变:“随着艺术作品的技术复制方法的多样化,它的可展览性也大为增强,以至于两种极端价值之间的量变——如同在原始时代——突然成了艺术品本质的质变。就像原始时代的艺术作品由于绝对推崇膜拜价值,首先是一种巫术手段,而后才渐渐被视为艺术作品,今天的艺术作品由于绝对推崇可展览性,成了具有全新功能的塑造物。”从膜拜价值到展览价值的转变,意味着艺术作品本身神圣性的消退,也即本真艺术作品之“光晕”的消失,而人之主体性地位在艺术审美中却得到提升。在艺术作品这种价值的转变过程中,美在艺术作品中成为一种强制性概念,排挤艺术作品中所蕴含的宗教价值、政治价值、伦理价值等,而逐步走向一种满足人主体性审美需求的价值,同时,也潜藏着经济价值进一步放大的可能。这主要体现和得益于本雅明所言的“消遣”:“消遣在所有艺术领域中越来越受推崇,崭露头角,它显示了统觉所经历的深刻变化,消遣中的接受在电影中找到了真正的练习工具。电影通过震惊效果来迎合这种接受形式。电影排挤膜拜价值,因为它不仅让观众持鉴定者的态度,而且电影院中的鉴定者的态度不要求全神贯注。”
本雅明亦充分看到了技术革新对艺术创造的负面影响,他在注释里引用了阿尔都斯·赫胥黎的论断,即“技术进步……导致了庸俗化……一种重要工业应运而生。有艺术才华的创作者却很罕见:其结果是……无论何时何地,绝大部分艺术产品都很低劣。而当今的艺术总产量中所含渣滓的比重之高是前所未有的”,只是本雅明认为“这种研究方式显然不是进步的”。本雅明更强调新技术对艺术创造所带来的积极意义,所以肯定了照相、电影两种新形式。但是,他并没有指出如何解决文化工业发展所造成的文化垃圾问题。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仍然是在认识论哲学框架内考察技术变革的影响。本雅明对以照相、电影为代表的机械复制艺术的肯定,实质上指向了艺术的产业化、生活化发展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文化创意推动了艺术疆域的拓展、艺术时空传播的提升和艺术感性呈现的革新,也带来了艺术的过度泛化、世俗化、肤浅化等问题。同时,本雅明在论证过程中虽然看到了人类生存方式的变化、感知世界方式的变化,进而据此强调了大众对艺术的影响,但他没有看到人类对本真自由生存方式的追求并没有变化。相反,本雅明肯定了大众在电影欣赏中对震惊效果的主体性需求,以及电影创作对该需求的满足。这种对主体性需求满足的创作,显然无法形成真理的自行置入,即无法展现真理涌现的本真之美。换言之,美的神圣性在这种创作中被悬置,失去了对文化创意的内在性约束和基本性规定。由此,文化垃圾的大量出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从海德格尔和本雅明对艺术创造变革的理论反思中,可以见出,其哲学基础、问题视角、理论进路等存在着根本性差异,所以对美的理解也根本不同:美作为一种存在者之真理涌现的方式,还是作为一种认识的对象。若就艺术作为人生在世追求本真生存的一条路径而言,艺术创造的过程也即人与世界建构关系的过程,也是人的精神生存展开的过程。那么,艺术创造向文化创意的转化,实则意味着人与世界关系建构方式的转变,人的精神生存指向的转变。文化创意发展及相关审美实践已充分证实:随着“天才”的艺术创造力转变为普通的创新力,文化创意重在追求“美丽学”意义上的“美”的创造,追逐经济价值。这就强化了人的主体性,自然也强化了人的主体性的非本真的生存方式。当下审美实践中涌现出的肤浅化、碎片化、世俗化等问题,也充分暴露了本雅明在主体性的认识论美学框架内理论反思的局限性。相较而言,海德格尔借助艺术与真理关系对艺术作品本源所进行的现象学追问,所呈现的生存论美学路径,更具有解决美学学科当下发展困境的可能。针对文化创意发展所带来的美学理论挑战而言,要避免文化创意向文化垃圾的堕落,提升文化创意的审美品格,便需要重新赋予文化创意以美的神圣性的内在制约,即向艺术创造回归。这实则意味着,将艺术创造视为一种“去蔽”的活动,一种对主体性进行审美超越与还原的活动;将美视为一种存在方式,而非一种认识对象。相应地,美学学科的定位则须由认识论的美学转向生存论的美学。
注释
①[波兰]塔塔尔凯维奇:《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刘文潭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256页。②⑧⑩[德]西奥多·W·阿多诺:《文化产业述要》,赵勇译、[美]曹雅学校译,《贵州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③[德]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王炳钧、杨劲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62、289—290、278—279页。④[法]埃德加·莫兰:《时代精神》,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页。⑤[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95—96页。⑥⑦[英]贾斯汀·奥康诺:《艺术与创意产业》,王斌、张良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188、135页。⑨[德]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108—109、20、40、43、44、46页。美国西北大学教授彼得·芬维斯(Peter Fenves)2014年10月底至11月初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了短期课程《美学的发现与再发现:1735—1935》(《The Invention and Re-Invention of Aesthetics:1735—1935》)。其中,在美学的再发现部分,他围绕对艺术的重新理解展开论述,明确强调了海德格尔与本雅明对黑格尔美学思想的超越,认为二人构成了美学学科再发现的起点。尽管论述角度不同,但芬维斯教授以1935年作为时间点,将海德格尔与本雅明作为美学学科再发现起点的论断,对本文成稿启发较大。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