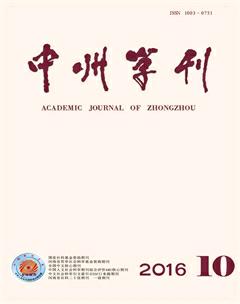再论清华简《筮法》与数字卦诸问题
2016-11-26张朋
摘要:清华简《筮法》能够给数字卦问题的讨论提供可靠的资料和进一步深入的契机。数字卦不是卦象符号的起源,清华简《筮法》篇能够给这一论断提供十分有力的支持。清华简《筮法》揭示了筮法问题的复杂,不仅对成卦方法研究需要考虑到各种可能,而且对解卦方法的研究也要考虑其多样性。在总体上,清华简《筮法》占筮系统与《周易》占筮系统有着很大的理论差距,前者应该不属于三《易》系统而属于民间杂占一类。特别是就一种民间流行的占筮系统而言,清华简《筮法》与《左传》《国语》中《周易》解说22例所反映的官方易占系统差异明显。
关键词:清华简《筮法》;数字卦;筮法;成卦方法;解卦方法
中图分类号:B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0-0102-06
2013年年底清华简《筮法》篇发表之后很快形成了一个易学研究热点,几年来各种相关研究文章不断出现。笔者近日重新拜读了李学勤先生的文章《清华简〈筮法〉与数字卦问题》①,又把清华简《筮法》篇反复翻阅,对于数字卦等问题有一些想法不吐不快。愿以此文附李先生骥尾,敬请方家指正。
一、数字卦不是卦象符号的起源
同李先生一样,对于清华简《筮法》,笔者最为关心的是数字卦问题,即数字卦是不是卦象符号的起源。如果说数字卦不是卦象符号的起源,那么在考古发现中不断出现的林林总总的数字卦又该给予一个怎样的合理解释呢?在这一点上,清华简《筮法》确实能够给数字卦问题的讨论提供可靠的资料和进一步深入的契机。
清华简《筮法》中所出现的筮卦都是六位卦,共114个,而且都是两两相对,并无一例单出。这就说明按照当时的占筮惯例,人们总是以“筮卦对”的形式进行贞问和筮占,或者更加准确地说,当时人们总是以“筮卦对”的形式对贞问和筮占的结果进行记录。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笔者在几年前对数字卦问题所做的一个基本判断:关于数字卦的考古材料中并列的两串筮数不是一次占筮的记录,即不可以像张政烺先生那样将其解读为一次占筮所出现的本卦和之卦,而只可能是两次占筮的记录,即每一个筮数串都必须解读为一次占筮所出现的本卦以及之卦(如果有之卦出现的话)。并列的两串筮数是关于同一件事情的两次占筮——这两次占筮可能是占筮操作的人不同,或者是占筮时间、方法稍有差异。②那么,为什么古人一定要以“筮卦对”的形式进行贞问和筮占,或者说为什么一定要以“筮卦对”的形式对贞问和筮占的结果进行记录呢?这样操作的具体原因很可能是因为《礼记·曲礼》所说的“卜筮不过三”,即占筮是古人生活中一件非常庄重的大事,就同一件事情最多占筮三次。这是在应对重大事件时为了防止差错,保证占筮结果准确的措施。所以在占筮的实际应用中,往往是三人并占,就一件事情三个人同时开始占筮,以占筮结果相同的两个人为准。这就是《尚书·周书·洪范》中所说的“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当然在实际操作中也有可能是两人同时占筮或者连续进行两次占筮。所以在考古发现中的两个并列的数字卦是就同一个事
笔者以上这些推断无疑得到了清华简《筮法》的有力支持。因为在清华简《筮法》出现的57对六画卦中的每一对都是就一个问题所进行的两次占筮,不可能是一次占筮的本卦和之卦。具体来说,首先,这些“筮卦对”绝大多数都是只有“一”和“∧”,而且还有两对数字卦其中并立的两对数字串完全相同的情况,即第十六节《战》的“九八七六五四”“九八七六五四”和“四五六七八九”“四五六七八九”这两对数字卦③,这就在根本上排除了按照本卦和之卦来解说这些成对出现的筮卦的可能;另外,从《筮法》第一节到第十九节对于命占的各类说明中,都是以“筮卦对”的形式对某一命占问题进行的举例说明。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114个筮卦中除了最常见的“一”和“∧”之外,还有“九”“八”“×(五)”“四”四个数字,虽然其出现频率很低。这样就有了如下一种推断:既然“九”“八”“×(五)”“四”是筮数,那么“一”和“∧”也应当是筮数,二者并非是阳爻和阴爻。特别有力的一个证据是:《筮法》中的《爻象》一章以“子午”配“九”,“丑未”配“八”,“寅申”配“一”,“卯酉”配“∧”,“辰戌”配“×(五)”,“巳亥”配“四”,这足以说明“一”为“七”,“∧”为“六”,“一”和“∧”也必然是筮数,这似乎确定无疑。
这种推断乍看起来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六十四卦符号出现之后,在实际操作中用以书写阴阳卦画的“一”和“∧”已经具有了阴阳内涵。就是说,由于清华简《筮法》所处的战国时代,当时六十四卦符号和《周易》文本都早已经形成,《筮法》中任何包含着“一”和“∧”的字符串都具有双重性质,既可能是表示最终占筮结果的六十四卦符号,也可能是表示占筮直接记录的数字卦。
进一步来说,一方面,正是因为“一”和“∧”具有数字的性质,所以它们可以直接代表数字,与其他筮数“九”“八”“×(五)”“四”一起组成代表着占筮直接记录的数字卦,并与其他筮数“九”“八”“×(五)”“四”一起和十二地支对应起来并具有筮法上的独特意义;另一方面,因为“一”和“∧”具有阴阳的内涵,是阴阳卦画,它们所组成的符号串可以直接表示六十四卦符号,代表着占筮的最终结果,在既有的114个卦象符号之中居绝大多数。
那么,“一”和“∧”在什么时候代表着阴阳卦画,又在什么时候代表着筮数“七”和“六”呢?首先,类似于《周易》文本的情况,被各种形式的卦辞以及爻辞解说的六位符号串一定是卦象符号。其次,必须承认,脱离文本环境单独就一个由“一”和“∧”所组成的六位符号串而言,确实难以遽然断定其究竟是数字卦还是卦象符号,但是究根揭底,数字卦是占筮的直接记录,通过对占筮具体方法的讨论和分析,可以将其归结为占筮的最终记录,即卦象符号。
对于清华简《筮法》筮数系统的讨论,可以参考《周易》占筮系统中的变爻法则做如下一番分析。
在清华简《筮法》筮数系统“九”“八”“七”“六”“×(五)”“四”之中,“七”和“六”是不变之爻,在实际占筮中将其记为“一”和“∧”,并直接带入到卦象符号的书写之中;而“九”“八”“×(五)”“四”是变爻,所以《筮法》第二十九节专门对“九”“八”“×(五)”“四”的“爻象”进行了论述:endprint
凡爻象,八为风,为水,为言,为飞鸟,为肿胀,为鱼,为罐筩,在上为醪,下为汏。
五象为天,为日,为贵人,为兵,为血,为车,为方,为忧、惧,为饥。
九象为大兽,为木,为备戒,为首,为足,为蛇,为曲,为玦,为弓、琥、璜。
四之象为地,为圆,为鼓,为珥,为环,为踵,为雪,为露,为霰。
凡爻,如大如小,作于上,外有吝;作于下,内有吝;上下皆作,邦有兵命、灾怪、风雨、日月有食。④
这里所谓的“爻象”含义很明确,就是指八之象、五之象、九之象、四之象,是指这四个数字所代表的物象。很明显,因为“七”和“六”是不变之爻,所以这两个筮数没有爻象,不需要对其进行说明。另外,此段文字还对爻的“作于上”“作于下”“上下皆作”三种情况进行了说明,观其言下之意就是爻还有上下都没有“作”即不发生爻变的情况,而不发生爻变的情况,也就是六个卦位中只有“七”和“六”而没有“九”“八”“×(五)”“四”。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推断:在清华简《筮法》中,凡是有一个或数个“九”“八”“×(五)”“四”出现的筮数串就是数字卦,它们是占筮的直接记录,需要对其变卦情况进行讨论后才能够与卦象符号对应起来,而没有“九”“八”“×”“四”出现只有“一”和“∧”的筮数串虽然也含有数字卦的意义,但是其可以直接解读为六十四卦符号。
在已知的《周易》大衍之数占算系统中,六、九是变爻,一定要发生爻变,即六变为七、九变为八;而七、八是不变爻,可以直接写入卦画。七、八在很多考古文献的六十四卦卦形中被写为“一”的形状和“八”的形状,比如马王堆帛书《周易》和阜阳汉简《周易》。这就可以说明,西汉时期的马王堆帛书《周易》和阜阳汉简《周易》很有可能是受到了大衍之数占算系统的影响,所以其六十四卦符号中的阴性卦画都呈现出“八”的形态。类似的,清华简《筮法》之中六十四卦符号阴性卦画都是“∧”的形制,这明显是受到其特有的占算系统的影响,导致其六十四卦符号的阴性卦画都是数字“六”的形态。
这样一来,就可以得出一个很有趣的推论,古人在记录六十四卦符号的时候,其中的阴性卦画既可以是“八”,也可以是“∧(六)”。“八”与“∧(六)”在六十四卦符号之中都表示着阴性卦画,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虽然二者所代表的数字决然不同,分别是“八”与“六”。比如对于江陵王家台十五号墓发现的秦简《归藏》,其最初的整理者就认为其中的阴阳卦画符号有一、六、八三种:“卦画都是以‘一表示阳爻,以‘六或‘八表示阴爻。”⑤这样的观感很容易引出对于卦象符号的其他理解和各种揣测,特别是关于数字卦是易卦符号起源的一些猜想。这里的关键之处在于就六十四卦符号的书写而言,阴爻无论是写成“八”还是写成“∧(六)”都没有区别。就秦简《归藏》六十四卦符号的具体书写而言,无论是运笔认真还是笔迹潦草,无论是把阴性卦画写成中间分开的“八”字形状还是写成中间连接的“六(∧)”字形状,其书写形状都足以与阳性卦画“一”明显区分开来,就六十四卦符号而言这就足够了。
所以秉持着“《周易》的卦形是由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数字卦逐渐演变而来的,到战国秦汉之际才定型成符号卦”⑥这一观点的季旭升先生所指认的数字卦演进过程,即“春秋、战国时代则向一、六、八集中。到西汉时期的马王堆帛书和阜阳汉简《周易》,全以‘一、八来表示”⑦,是根本不存在的,其观点根本就没有证据支持。
基于以上讨论,现在可以重申笔者的论断:数字卦不是卦象符号的起源,从殷商中期到战国时期广泛出现的数字卦不能够作为易卦卦象符号演进的依据。在得出这一结论之后,对考古文献中出现的数字卦具体含义的探求才可以继续下去,而这种探究必须结合占筮的各种可能方法做具体分析。
二、清华简《筮法》中的成卦法
一般来讲,广义的筮法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是成卦法,第二是解卦法,而清华简《筮法》对二者皆有涉及。由于清华简《筮法》对成卦法没有直接论述,所以只有根据其中所记载的占筮记录来揣摩其成卦法。在清华简《筮法》114个筮卦中,全部由“一”和“∧”组成的筮卦高达89个,而“一”“∧”“九”“八”“五”“四”杂见的则只有25个。就卦画而言,114个六画卦共684个卦画,“一”和“∧”的出现次数高达631次,而“九”“八”“五”“四”一共才出现53次,且高度集中于几卦之中。按照常识,就一个完备的占筮系统而言,在样本比较充足的条件下,作为地位平等的“一”“六”“九”“八”“五”“四”6个筮数出现的频率应该大致相等,不应该相差如此巨大:114个六画卦684个卦画位中,七共出现308次,出现频率高达45%;六共出现323次,出现频率高达47.2%;九共出现23次;八共出现10次;五共出现13次;四共出现7次。上文已经涉及,对此种差异的一个解释就是这些六画卦之中的“一”和“∧”已经是阳爻和阴爻,所以清华简《筮法》中绝大多数筮卦都是六十四卦卦象符号,而出现了“九”“八”“五”“四”四个数字的符号串则是记录占筮直接结果的数字卦。在原则上,这些数字卦都可以进一步写作六十四卦符号。这里的关键问题就在于这些数字卦发不发生爻变,如果发生爻变的话那么又应该如何发生爻变。
比如在筮法之中没有设置爻变的情况下,《筮法》第十六节《战》中的第一个数字卦“九八七六五四”按照数字的奇偶性可以转化为“一∧一∧一∧”,这是离下坎上的既济卦。按照《筮法》对坎离方位的独特定义(与《说卦》的坎北离南的方位恰好相反),离在北为水,坎在南为火,内卦离水克制外卦坎火。这能够给“凡是,内胜外”这句说明以非常有力的支持。同样的,在筮法没有爻变的情况下,《筮法》第十六节《战》中的第二个数字卦“四五六七八九”按照数字的奇偶性可以转化为“∧一∧一∧一”,这是坎下离上的未济卦。按照《筮法》对坎离方位的独特定义,离在北为水,坎在南为火,外卦离水克制内卦坎火。这同样能够给“凡是,内胜外”以有力的支持。endprint
那么在筮法设定爻变的情况下又会如何呢?比如按照笔者假设的如下这种变爻方法:
“九”“五”是阳性变爻,发生爻变,变为“六”,记为“∧”。
“八”“四”是阴性变爻,发生爻变,变为“一”,记为“一”。
这样一来第十六节《战》的“九八七六五四”这个数字卦就会变为“∧一一∧∧一”,这是巽下艮上的蛊卦。按照《左传·僖公十五年》的记载,秦国与晋国开战之前占筮就遇到了蛊卦,卜徒父的解说是:“《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其中明显是把内卦巽对应于己方秦国,而把外卦艮对应为敌方晋国,风落山,巽克艮,占筮战争时遇到这一卦象那么吉凶就非常明确,所以卜徒父的结论是:“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这与清华简《筮法》第十六节《战》中所说的“凡是,内胜外”完全契合。对于第十六节《战》中的另外一个数字卦“四五六七八九”,按照上面的变爻方法就会变为“一∧∧一一∧”,这是震下兑上的随卦。按照《筮法》对方位的定义,兑在西方为金,震在东方为木,兑金克制震木,外卦克制内卦,这也就与第十六节《战》中的“凡是,外胜内”完全契合。
很明显,虽然参照《周易》大衍之法考虑到了《筮法》中占筮方法发生变爻或变卦的情况,但是这仍然不足以充分说明清华简《筮法》中“一”和“∧”几乎各自占一半的出现频率以及随之带来的绝大部分卦象只有本卦而没有(或者完全不考虑)之卦的问题。当然,这里还必须要考虑到这种可能:《筮法》中绝大多数易卦卦象都是《筮法》作者为了讲述的方便而虚设举例,实际上并没有进行占筮,而因为是虚设所以简单方便地直接写成了卦象符号。对照之下,那些出现了“九”“八”“五”“四”4个数字的符号串则很可能是对实际占筮结果的记录。但是为了讨论的继续深入和逻辑上的完整,这里必须引入一个假设:清华简《筮法》中除了包含有发生爻变的占筮系统之外,还可能包含有《归藏》筮法,而《归藏》筮法是没有变卦或变爻的。
根据王家台出土的《归藏》残篇,《归藏》没有爻辞而只有卦辞,所以使用《归藏》进行占筮时只有本卦而没有之卦。必须说明的是,这里其实还隐含着一个问题:已经亡佚的《连山》是不是也是没有爻辞而只有卦辞,其占筮系统也是只有本卦而没有之卦呢?根据《周礼·春官》关于“大卜”有“掌三《易》之法”的记载,周代是《连山》《归藏》《周易》三种占筮方法并行不悖的。但是一方面由于关于《连山》筮法的资料极度缺乏,另一方面李学勤、廖名春等学者早已经指出清华简《筮法》与王家台出土的《归藏》文字上的关联⑧,所以目前以“清华简《筮法》可能包含有《归藏》筮法,其占筮方法中不发生爻变”为基础继续展开讨论是必要的,也是合适的。
三、清华简《筮法》中的解卦法
清华简《筮法》实际上揭示了筮法问题的复杂,不仅对成卦方法研究需要考虑到各种可能,而且对解卦方法的研究也要考虑其多样性。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关于数字卦的讨论可以说在一开始就陷入了这样一个困局:对于周代筮占的成卦方法我们只知道《周易》的大衍之法,而对于《连山》《归藏》的成卦方法几乎是一无所知;关于周代筮占的解卦方法只有《左传》《国语》中《周易》应用22例可资凭借并从中提炼出“八卦取象比类”的解说方法⑨,对于《连山》《归藏》的解卦方法同样几乎是一无所知。好在现在有了清华简《筮法》的出土,可以在筮法的多样性方面做一下差强人意的弥补,特别是其中对于解卦方法的举例说明就显得特别珍贵。
既然“清华简《筮法》可能包含有不发生爻变的筮法”这一假设基本可以肯定下来,那么接下来就可以对清华简《筮法》中的各种解卦方法(解卦法)进行讨论。对于《筮法》解卦法的讨论,可以与《周易》的解卦法进行对比分析,其中往往要涉及对清华简《筮法》中数字卦的解说。
首先,清华简《筮法》中的解卦法是针对相对独立的两次占筮结果以“筮数对”的形式进行分析和讨论,这与《周易》卦爻辞的言说内容明显不同。在占筮的情况下,《周易》卦辞是针对一个六十四卦所做的解说,而爻辞则是针对以本卦和之卦为关系的两个六十四卦所做的解说。⑩解说内容的不同决定了清华简《筮法》第一节到第十九节中的解卦方法绝大多数都不适用于《周易》解说,二者在总体上没有相通性。这里面比较特殊的就是上文提及的第十六节《战》中的两个例子。因为“九八七六五四”“九八七六五四”和“四五六七八九”“四五六七八九”这两对数字卦每对都是彼此一致,而且所谓的“凡是,内胜外”和“凡是,外胜内”只是涉及了八卦卦象,所以其解说方法和《周易》卦辞的解说方法类同。
其次,清华简《筮法》中的解卦法是八卦和爻二者并重,所以其没有单一的理论核心,没有做到解说方法的前后一贯和理论上的融通完备。
八卦是三《易》共同的理论基础,即如《周礼·春官·大卜》所载:“(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清华简《筮法》中的很多解卦法都是以八卦为基础的。除了第十六节《战》之外,应用八卦理论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第一节《死生》中的“三吉同凶”“三凶同吉”,第二节《得》中的“妻夫同人”“三左同右”“三右同左”“三男同女”“三女同男”,第七节《售》中的“三男同女”“夫妻相见”,第八节《见》中的“三男同女”“三女同男”,等等。其中男、女的八卦取象是采用了《说卦》中的解说,即“乾天也,故称父,坤地也,故称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但是为什么“三男同女”或“三女同男”就是判断占筮结果的固定格式呢?“二男二女”这个格式为什么就不可以呢?清华简《筮法》显然没有给这些理论问题以任何解答。除了八卦的男女卦象外,《筮法》中还有四位、四季吉凶、左卦右卦等具体解说方法,这些无疑都可以从八卦基本理论中生发而出。
清华简《筮法》中除了以八卦为基础理论的解卦法之外,还有一些解卦法则以“爻”及“爻象”为基础。比如第一节《死生》中的“六虚,其病哭死”“五虚同一虚,死”,就是把两个筮卦之爻叠加,叠加之后如果是六个阳爻就是“六虚”,那么“其病哭死”,如果是五个阳爻就是“五虚”,断辞为“死”。第一节《死生》中还出现了指认五、九为“恶爻”的情况。无论是六爻叠加还是五、九恶爻,在已知的《周易》占筮系统以及八卦理论中都找不到任何根据,应该属于杂占之类的解说方法。清华简《筮法》中以八卦为基础理论的解卦法与以“爻”为基础的解卦法彼此独立,在某种情况下又可以互相补充,比如第一节《死生》中有以八卦为基础理论的解说“三吉同凶,待死”,还有二者合勘的“三吉同凶,恶爻处之,今焉死”。endprint
需要注意的是,清华简《筮法》中的“爻象”定义(上文已经引述过)并不能够给上述关于爻的解卦法以任何支持。具体来说,在第一节《死生》两个筮卦之爻叠加的过程之中,默认的是阳爻叠加阳爻结果为阳爻,阳爻叠加阴爻结果为阳爻,阴爻叠加阴爻结果为阴爻。实际上阳爻是七,为奇数(这里即使把阳爻所代表的数字扩充为九、五、七,也一样都是奇数,并不影响结果),那么阳爻与阳爻叠加就不是奇数而是偶数,偶数所代表的是阴爻而不是阳爻,所以这种六爻叠加法实际上与筮数的奇偶性相违背。另外,在“爻象”定义之中五的基本爻象为天,四的基本爻象为地;九的基本爻象为木,四的基本爻象为风。与四、八的爻象互相对照,五、九的爻象没有明显的“善”,也没有明显的“恶”,所以“恶爻”这种说法也不能够在“爻象”定义之中找到什么根据。所以清华简《筮法》中的“爻象”定义不能够给上述两种关于“爻”的解卦法以任何支持。进一步来看,清华简《筮法》中的“爻象”定义就本质而言是筮数之象,不直接涉及阴阳属性,也没有直接涉及阴阳互化,其中列举的各种物象缺乏系统性,逻辑上也不完备,远不能和《说卦》中的八卦理论相比。
进一步说,就《筮法》中的“爻象”这一种解卦法而言,如果说仅仅根据其中列举的39种物象就可以断定多数占筮结果的吉凶,这是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这一点恐怕《筮法》的作者也认识到了,比如其中所罗列的八、五、九、四4个筮数各自所代表的物象在《筮法》第一节到第十九节中的各种具体解卦方法中没有得到任何应用,而其所陈述的“凡爻,如大如小,作于上,外有吝;作于下,内有吝;上下皆作,邦有兵命、灾怪、风雨、日月有食”也只能够作为一种独立的解卦法而存在。
严格地讲,在《周易》占筮系统中只有发生变化的数字所代表的阴阳爻才能够叫作“爻”,不发生变化的数字所代表的阴阳爻就是卦画。《易传》之中就非常强调“爻”所具有的“动”“变”的特性。比如《系辞上》有:“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这是强调“爻”的“动”的特征内涵。“彖者,言乎象也。爻者,言乎变者也。”这里的“爻”是指爻辞,而爻辞的言说内容是爻之“变”。“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这里的“爻”也是指爻辞,而爻辞的描述内容是“天下之动”。《系辞下》有:“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这里所谓的“爻象”也是在强调“爻”和“象”共同具有“动”“变”的特性。“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抛开了“象”,这里再次强调“爻”所具有的“动”的特征内涵。“道有变动,故曰爻”,这是把“爻”的“变动”特征与“道”这一重要概念做勾连。通过以上讨论可以看出,“爻”为“动”为“变”,这是“爻”的首要意义,“阳爻”首先是指由阳变阴之爻,“阴爻”首先是指由阴变阳之爻,这是《周易》占筮系统中阴阳爻的基本含义。现在看来,“爻”具有“动”“变”的特性,这种概念在清华简《筮法》筮数系统中并不一定适用,特别是对于《筮法》中所谓的“爻象”而言。
从易学史来看,清华简《筮法》中所说的“爻象”是在某些非三《易》筮法中适用的一种特殊定义,与易学中一般意义的爻象断然有别。比如现今比较通行的“爻象”定义是:
爻象征的事物。阳爻象阳,象天,象君,象君子,象大人,象父,象男人,象奇数,象刚,象健,象动,象一切阳性事物;阴爻象阴,象地,象臣,象民,象小人,象母,象女人,象偶数,象柔,象软,象静,象一切阴性事物。
这里所说的爻象无疑就是指阳爻之象和阴爻之象,而阳爻之象和阴爻之象总是相对而出,分别象征着对立统一的两个事物,比如男女、刚柔、天地、奇偶等,与清华简《筮法》中的“爻象”含义截然不同。
四、结语
在总体上,清华简《筮法》占筮系统与《周易》占筮系统有着很大的理论差距,前者应该不属于三《易》系统而属于民间杂占一类。特别是就一种民间流行的占筮系统而言,清华简《筮法》与《左传》《国语》中《周易》解说22例所反映的官方易占系统差异明显,但是其对后者也有一些继承。当然除了八卦的应用之外,这种继承性也体现在《筮法》“十七命”对《周礼·大卜》“八命”在内容上的扩展和在主题上的生活化改换。
注释
①李学勤:《清华简〈筮法〉与数字卦问题》,《文物》2013年第8期。②张朋:《数字卦与占筮——考古发现中的筮法及相关问题》,《周易研究》2007年第4期。③④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四),中西书局,2013年,第102、120、78—79页。⑤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文物》1995年第1期。⑥⑦季旭升:《古文字中的易卦材料》,刘大钧:《象数易学研究》第三辑,巴蜀书社2003年,第18、16页。⑧廖名春:《清华简〈筮法〉篇与〈说卦传〉》,《文物》2013年第8期。⑨⑩张朋:《春秋易学研究——以〈周易〉卦爻辞的卦象解说方法为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1—72、71页。张其成:《易学大辞典》,华夏出版社,1992年,第355页。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