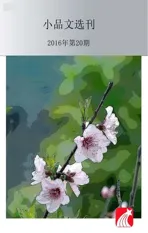以《西洲曲》为例浅析南朝民歌特点及其传统与延续
2016-11-26高云飞
高云飞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00)
以《西洲曲》为例浅析南朝民歌特点及其传统与延续
高云飞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00)
南朝民歌,是中华民族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西洲曲》作为南朝民歌的典范代表作品,具有南朝民歌最典型的艺术特点。南朝以其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形成了独特的市井文化,民歌在这种环境中也发展出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与语言感染力,勾勒出一幅幅绮丽、淳朴,富有生活情趣的生活画面,并影响了后世(尤其唐代)许多诗歌大家诸如李白、杜甫等人的诗歌创作。
《西洲曲》;南朝民歌;语言特点;结构
南朝民歌经过几千年流传,今保留下来的题材以情歌为主。它以清丽缠绵,自然活泼的手法更多反映了古代人民真挚的爱情生活,抒发了南朝都市生活里女性的心声与情感。以《西洲曲》为例,从这篇集南朝民歌艺术精髓的作品出发,探析南朝民歌的艺术特点,并追溯南朝民歌的题材成因以及其对后世文人写作的影响和发展。
1 语言运用
《西洲曲》是一首经文人润色且艺术成就最高的南朝乐府民歌,用缱绻含蓄的语言生动塑造出一位想念情人的思妇形象。全诗文笔流畅,辞藻华丽,具有独特的语言特点,作为南朝民歌的代表作品,我们不难从其中领略到南朝民歌的独特语言魅力。
1.1 双关隐语表意丰。南朝民歌中对语言的巧妙构思,最重要的体现在于双关隐语的运用。例如《西洲曲》中“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一句,表面勾勒少女拨弄莲子,莲子如水澄清的画面,实则以“莲子”谐“怜子”,“清如水”谐“情如水”,表现出少女对男子清澈纯洁的爱慕之情。再如“莲心彻底红”,表面写莲心颜色,实则以“莲心”谐“怜心”,“彻底红”一语双关表达出“怜心”的火热。大量使用双关隐语,看似言景,语语目前,实则写心,字字入木。
再观其它的南朝民歌,对双关语的运用同样比比皆是。《子夜四时歌·夏歌》中“清荷盖渌水,芙蓉葩红鲜。郎见欲采我,我心欲怀莲”四句,前两句一语双关,既写芙蓉,亦写女子,而后两句则运用谐音字(“采”谐“睬”,“莲”谐“怜”)表现出男女之间暗生的情愫。[1]《子夜歌》第三十五首中“雾露隐芙蓉”,“芙蓉”谐音“夫容”,刻画出男子难以捉摸的内心世界。南朝民歌的谐音字中,使用最多最具代表性的是“以莲写怜”“以丝写思”,当然,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双关语大量存在。江南缠绵的地理特点造就了其含蓄缱绻的表达手法,双关隐去锋芒,由此不难看出,南朝民歌的语言经过其独有的新奇巧妙构思,将委婉二字诠释得入木三分。
1.2 顶针蝉联衔接细。沈德潜曾在《古诗源》中评价《西洲曲》:“续续相生,连跗接萼,摇曳无穷,情味愈出。”[2]通篇读来,《西洲曲》韵律自然,环环相扣,其一大原因在于,运用了大量顶针手法。“忆郎郎不至……垂手明如玉”一段,句句顶针,首尾相连,通篇顶针的修辞让这首南朝民歌节奏紧扣,连绵不绝,朗朗上口,成为《西洲曲》的主要特色之一。
关于顶针修辞的运用,最早源于汉乐府《平陵东》:“平陵东……劫义公。劫义公,在高堂……两走马。两走马……心中恻。心中恻……卖黄犊。”[3]伴随顶针,整篇文章语句自然相生。此后,顶针普遍的被运用于各种诗作中。魏晋曹植的《赠白马王彪》中,使用了5次顶针修辞,唐代无名氏的《忆秦娥》,元稹《估客乐》等,皆是顶针的运用。
2 谋篇布局
2.1 时令划分结构。细品全诗,可以发现《西洲曲》中很多词语、俗语在暗示时令节序。如“折梅”—早春,“单衫”—春夏之交,“伯劳”—仲夏,“莲花”—夏末秋初,“莲子”—仲秋,“飞鸿”—深秋。通过这些词语的贯穿,按照诗意可分为春、夏、秋以及梦境四层,以词语为衔接点划分诗歌的意思,又以季节顺序层层递进,使诗意层次分明而又连贯。这种诗意与韵律的双结构让《西洲曲》表里相依,声情并茂。
南朝民歌的另一代表组诗《子夜四时歌》,更是以四时为内容,由二十首春歌,二十首夏歌,十八首秋歌和十七首冬歌组成,将时令节序与女子形态动作等紧密结合起来,分别表现女子在春、夏、秋、冬四季中的眷恋、相思等情节。
在后代的作品中,也曾出现过这样的写作方法。李白曾仿《子夜四时歌》写就了《子夜吴歌》四首,春夏秋冬娓娓道来。其《长干行》中“五月不可触,……八月蝴蝶黄……坐愁红颜老。”一段则是模仿了《西洲曲》中景物时令结合思妇动作的手法,以景观与俗语暗指时令节序的发展,通过五月、八月两个时间段思妇及其周围环境的变化,将一位惆怅闺怨的商人妇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
2.2 叙述视角多重。有关《西洲曲》的叙述角度问题,一直被相关研究学者称为诗歌中的“哥德巴赫猜想”。不同的名家对其叙述角度有不同的理解。游国恩先生认为,《西洲曲》只有末四句是女子自道心事,其余皆为男子语气;叶玉华先生认为全诗都为女子口吻;余冠英先生则认为末尾四句为女子语气,在这之前为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4]。笔者更认同余冠英先生的分析视角,但在末尾四句的理解上略有出入。《西洲曲》全诗写忆,其前面大部分的视角可以归结为现代文学作品中常用的“上帝视角”,从旁观者的角度讲女子的行动、表现,而结尾四句则为个人心意表白,其实结合全诗大义,也可理解为男子了解到女子内心所想后的心声。自古闺怨与弃妇诗中便多采用第一人称或对话方式,不论是《氓》还是《上山采蘼芜》抑或《孔雀东南飞》,无一例外,因此,《西洲曲》中以旁观者的角度与第一人称角度穿插结合的叙述方式可谓开其先河。
在后世的延续中,诗圣杜甫的《月夜》便模仿《西洲曲》的角度,同样按照第三人称的叙述角度来讲述其妻子在月夜对自己的思念。“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双照泪痕干”,作者用第三人称的叙述角度,想象妻子在家中思念自己的闺怨模样,感情真挚,惹人感叹。
3 结语
《西洲曲》不仅代表了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也是我国诗歌史上难得的精品。《西洲曲》中大量双关隐语的运用,顶针手法的衔接,及它哀伤的感情基调,鲜明的女性形象都是十分典型的南朝诗歌特征。与此同时,关于它的叙事视角问题至今尚未定论,这使得我们对《西洲曲》的讨论从未消退,还需不断学习、探讨。
[1] 南朝民歌—穿越时空的绚丽爱情.2008-10-20
[2]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汉魏六朝诗歌鉴赏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3] 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
[4] 王太阁,赵民杰.略论西洲曲的双层结构.[J]殷都学刊.1996年1期
高云飞(1992—),女,汉族,山东省济南市,硕士研究生,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
J648
A
1672-5832(2016)08-015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