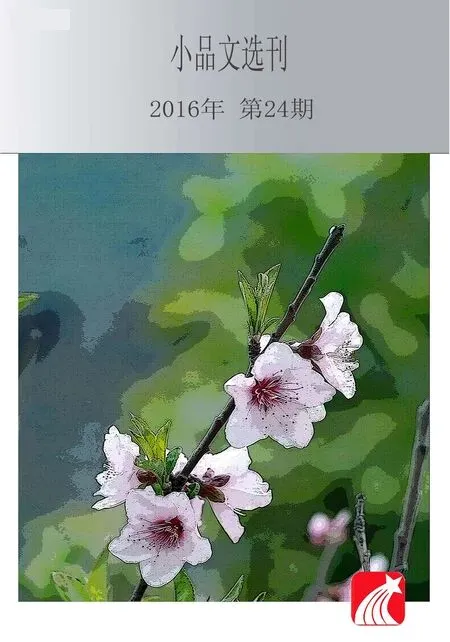对余华的《第七天》作品的解读
2016-11-26陈婷婷
陈婷婷
(湖北工程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北 孝感 432000)
对余华的《第七天》作品的解读
陈婷婷
(湖北工程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北 孝感 432000)
与余华以往小说的生存叙事一样,《第七天》也仍然以现实生存的艰难为主题,仍然弥散着死亡、荒诞和温情的元素。但小说通过亡灵视角的设置、温情乌托邦景象的营造和现实新闻的拼贴,对死亡图景进行了再置和重新叙述,对荒诞和温情进行了重新思考,对文艺与现实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处理。这些叙事上的新变,折射出中年过后的余华生命态度上的更为冷静平和,以及美学观念上向后现代主义的贴近和靠拢。
余华;《第七天》;荒诞;温情;后现代
余华是当代中国少数始终瞄准现实生存苦难,围绕“生存之艰难”主题进行不懈追索并取得重大成就的作家。从早期的先锋小说,到标志着其创作“转型”的作品,无论是创作态度还是艺术探索都显得更加成熟、理智与平实。《第七天》则蕴含着许多超越性的叙事新变。
1 死亡图景的再置与重新叙述
苦难是余华小说反复渲染的主题,他的人生经历使得苦难在他的心灵中留下了无法医治的创伤。而苦难的最高和最终形式,毫无疑问是死亡。也因此,在余华小说里,死亡就像一个反观现实生存苦难的支点。《第七天》同样如此,它以各种方式描写了十四个死亡事件和上百个人物的死亡。与以往不同的是死亡叙述的视角。小说开篇便写道:“浓雾弥漫之时,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孓而行。我要去的这个地方叫殡仪馆,这是它现在的名字,它过去的名字叫火葬场。我得到一个通知,让我早晨九点之前赶到殡仪馆,我的火化时间预约在九点半。”这个不无幽默怪诞意味的开头,清楚地说明这是一个亡灵的视角。
从死亡世界反观生,使得不管生死两个世界在篇幅上的比例如何,至少在心理和审美效果上,死亡世界会显得更为根本和终极。在中国,由于儒家“未知生焉知死”传统的影响,一般不大习惯从死亡角度来思考生命的意义。
2 荒诞的延伸与温情乌托邦的建构
2.1 荒诞色彩浓重
所谓荒诞,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手法和技巧,具有怪诞、不合常理、不可理喻、不可捉摸和悲观主义等多重意味。但怪诞不过是荒诞的表面。更深层的荒诞,是对不可理喻、不可捉摸之生存本质的悲剧性体认。
在一个荒诞的世界里,人性变得冷漠和乖张。公司同事向李青下跪求爱、鼠妹跳楼自杀两件事情,就几乎再现了鲁迅式的“看被看”的场景:“他第二天没来公司上班,所以公司里笑声朗朗,全是有关他下跪求爱的话题,男男女女都说他们来上班时充满好奇,电梯门打开时想看看他是否仍然跪在那里。他没有跪在那里让不少人感到惋惜,似乎生活一下子失去不少乐趣。”
一个生命即将在自己眼前逝去,人们却觉得于己无关。这种人性的冷漠,与卡夫卡《变形记》中“他人即地狱”式的隔膜与孤独异曲同工。
2.2 荒诞里不失温情
如果说人性的孤独与冷漠是西方现代主义和鲁迅小说的主要着力点,那余华的小说除了这种冷漠与孤独,更贯穿着对温情的呼唤与书写。
《第七天》不仅从事象学角度写了温情及其美好,也从结果论角度写了温情追求的不可能实现。首先,温情固然不是人物死亡的原因,但死亡却是这些寻找温情、充满温情之人的唯一结局。我在对父亲的寻找中死于非命,父亲则在对的怜爱中出走并客死他乡。鼠妹在对男友伍超的无限爱恋中跳楼自杀,伍超则在对鼠妹的愧疚中卖肾而死。温情追求者无一例外的死亡结局,无言地宣告了温情追求的虚无。
其次,它所建构的那个温情乌托邦的景象叫“死无葬身之地”。人只有在死后并且在死无葬身之地中,才会真正得到平等,收获温情。这无疑是关于现实荒诞性的更深层揭示,也是关于温情追求之艰难的更深刻体认。
3 更为贴近和靠向后现代的现实
3.1 荒诞里的现实色彩
《第七天》使余华遭遇了有史以来的最大质疑。质疑者认为,小说“照抄”了太多现实里的新闻,更未作出比新闻更高的主题概括,整个小说有“口感”却没有“营养”。
小说不能照抄现实尤其是现实里的新闻,必须有一个完整统一的结构,必须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其实是20世纪以前西方古典和现实主义文学所固守的观念。20世纪以后,一种现代主义的文学观念开始出现:文学的结构可以采取任何方式,它可以是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的,也可以是怪诞破碎甚或漏洞百出的。
发展到后现代主义,还出现了许多更为极端的美学观念和创作尝试,如非历史化和非深度化的故事,无规则甚或完全破碎化的叙述,无深度甚至无意义的主题设计等。就此而言,《第七天》里饱受诟病的“瑕疵”,便很可能是某种后现代美学的尝试。
3.2 荒诞时的美学体会
这种后现代式的“新闻串烧”,还提供了一种新的同样是后现代的美学体会。
一方面,小说的“新闻性”会不断地把我们引出文本的边界,引向对现实世界的记叙与回忆;而另一方面,小说的“小说性”又不断地突破现实的藩篱,把我们带回文本对现实的独特思考与观照之中。这样,小说和现实的边界就都被拆除了,并在文本和现实之间造成了一种双向互文的景观。而各种“边界”的拆除和互文景观的呈现,亦正是后现代主义美学的重要原则。
但《第七天》这样的小说,却不再是现实世界的完整的对体。它对现实的反映与参照,由整体变成了碎片。如果说以前的小说就像一块完整统一的平面镜,那《第七天》则是一块棱镜,每面都反射着现实的一部分,它们之间是破碎不连贯的,就如生活本身一样的散乱。这个棱镜般的“现实”表明,余华在走过现代主义为主的先锋、现实主义为主的后先锋之后,已不由自主地滑向后现代主义的美学阵营。
[1] 付建舟.余华《第七天》的创作意图与其叙事策略[J].小说评论,2013,05:95-100.
[2] 吴树桥.文学与当下中国的现实景观——评余华新作《第七天》[J].小说评论,2013,05:107-111.
[3] 周明全.以荒诞击穿荒诞——评余华新作《第七天》[J].当代作家评论,2013,06:120-125.
[4] 洪治纲.寻找,是为了见证——论余华的长篇小说《第七天》[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11:153-162.
[5] 刘霞云.超越苦难与生死的高尚书写——评余华新作《第七天》[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3,05:77-83+139.
陈婷婷(1993-),女,汉族,河南项城人,文学本科,湖北工程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I206
A
1672-5832(2016)12-006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