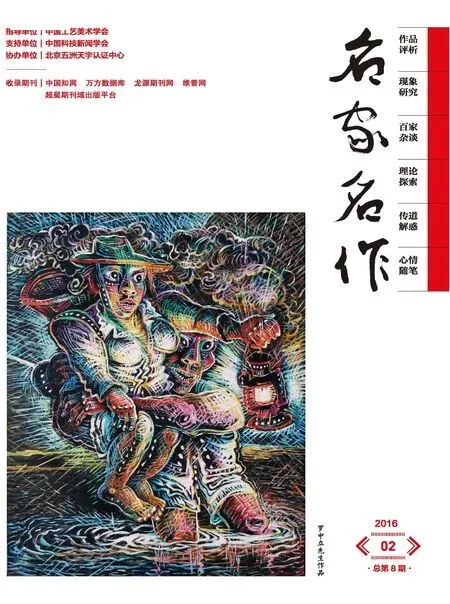一面追求,一面泪流
—谈鲁迅《药》的解读
2016-11-26杨万得
杨万得
(江苏省南通中等专业学校,江苏 南通 226011)
一面追求,一面泪流
—谈鲁迅《药》的解读
杨万得
(江苏省南通中等专业学校,江苏 南通 226011)
[摘 要]《药》中小说“三要素”环境描写沉郁悲凉,人物形象充满隐喻,故事情节双线交织。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是作者孤独、绝望的心境,而在这凄凉的绝望中又寄托着渺茫的希望的复杂情感,是谓“一面追求,一面泪流”。
[关 键 词]小说三要素;环境描写;人物形象;隐喻;自噬其身
小说的解析还是要立足“三要素”来分析,即它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及环境描写,越是经典的作品在“三要素”的体现上越是典型。鲁迅先生的《药》正是这种经典作品的代表作之一。
一、沉郁悲凉的环境描写
《药》选取了三个场景:刑场、茶馆和墓地。刑场是前奏,着笔于自然环境的描写,渲染悲凉绝望的冷色调;茶馆的戏份较大,相较于刑场的凄凉寂冷的默片效果,茶馆里却是热热闹闹的有声片:茶客们七嘴八舌,表情各异。墓地场景描写重归悲凉绝望的冷色调。小说的意蕴就从这三个场景展现出来:一剂没有药方的药。
1.墓地的场景
这一年的清明,分外寒冷;杨柳才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天明未久,华大妈已在右边的一坐新坟前面,排出四碟菜,一碗饭,哭了一场。化过纸,呆呆地坐在地上;仿佛等候什么似的,但自己也说不出等候什么。微风起来,吹动他短发,确乎比去年白得多了。
春寒料峭的清明,吐芽迎春的柳枝,风中的白发,这个画面从坟场灰色调中推进到特写的对象:一坐新坟,祭品(绍兴民俗,以祭品多寡来表明坟里人的身份,也为下文的夏母祭儿埋下伏笔),一头的白发。画面中的春意仍被“分外寒冷”的阴冷悲凉的气氛所笼罩,华大妈“呆呆”枯坐中空洞的眼神,衰老单薄的身体,风中凌乱的白发。寥寥几笔,老年丧子的母亲凄婉心境跃然纸上,由此而可推想带着些许羞耻心情上坟的夏母内心是何等的复杂。
……两面都已埋到层层叠叠,宛然阔人家里祝寿时的馒头。
微风早已停息;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
他们走不上二三十步远,忽听得背后“哑——”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悚然的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
乱坟岗、坟头、枯枝、枯草、乌鸦,整个画面充斥着坟场的味道:荒凉、沉郁、凄清、死寂……一派肃杀之气扑面而来。在这灰色调的画面中活动的,是两位白发苍苍的母亲。而她们面前隔着小路并列的新坟里头,是两家的儿子。白发人送黑发人,白发人祭黑发人,其景其情,思之断肠。
2.茶馆场景
人物描写与环境描写糅杂在一起,互为衬托,互为依撑。而仅有的“老栓走到家,店面早经收拾干净,一排一排的茶桌,滑溜溜的发光”。一句也只是为了衬托作为城市小业主的华家夫妻勤谨和茶馆的档次,这段我们到人物描写里再分析。
3.刑场写人状景
丰富的灰色系色彩:“乌蓝的天”“青白的光”“街上黑沉沉的”“一条灰白的路”“一个大白圆圈”“暗红的镶边”……画面中呈现的色彩中既有对社会环境的描写,又衬托了人物的心境。其对小说主题的氛围营造、人物心理的烘托的作用,自小说产生以来,分析颇多,见仁见智,在此不再赘述。
二、处处充满隐喻的人物形象
《药》中的人物,充满强烈的隐喻性。如主要人物两家的姓氏合为“华夏”暗指中华民族,题目《药》也就成了寻求疗治当时积弱成病的中国的药方的隐喻。
1.夏瑜形象的分析
小说中革命者夏瑜暗指革命烈士秋瑾。取季节名以夏对秋;瑾、瑜均是美玉,也指美德、贤才,语出屈原《楚辞·九章·怀沙》“怀瑾握瑜兮,穷不得所示”;司马迁《史记·屈子贾生列传》“怀瑾握瑜”。既有美德贤才之意,又有怀抱高洁之喻。文中的夏瑜,是清末知识分子的精英和思想启蒙的先锋,有着高远的志向和为民族未来负“匹夫之责”的担当。但被无声地杀害在秋日的凌晨,而华老栓此时正待在刑场旁边等着通过他的“人血馒头”来移植一个新的生命到自己家庭中“收获许多幸福”。作为夏家的儿子,为华夏的未来奋斗,但生前孤独、死后凄凉,令人叹惋。
2.华家夫妇形象的隐喻
华老栓夫妇是城市平民的代表,他们勤劳、善良、谨小慎微又奴性十足,是鲁迅先生笔下“庸人”的具体化形象。日子的琐碎、生意的艰难、寻常生活中的意外,儿子的痨病、康大叔、红眼睛阿义之类的敲诈……在种种困境中,他们施出浑身解数,像蝼蚁一样卑微地活着,奋力挣扎以延续生命和家族血脉。很多学者或研究者认为,他们是麻木愚昧,无知自私。
3.可疑的小栓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小栓在小说全文中除了不停地咳嗽之外,没有一句台词,没有任何对于他的肖像描写。只有一段着墨于他的话:
只有小栓坐在里排的桌前吃饭,大粒的汗,从额上滚下,夹袄也贴住了脊心,两块肩胛骨高高凸出,印成一个阳文的“八”字。
痨病、有些吓人的瘦弱身体、年龄未知、面目模糊,除了咳嗽就是睡觉。小栓是老栓夫妻的独子,是这个家庭的希望,他不加辨别地听从父母的安排,叫他吃他就吃,命他睡他就睡。用两个字来形容——驯顺:听话的孩子不一定懂事。
小栓是华家的未来和希望,他瘦弱而身患绝症,父母虽百般呵护,但最后竟也没保得住。华家的希望破灭。华家的小栓是肉体的死亡。无数的小栓在这种家教的氛围下是独立精神的丧失。
再有,中国传统社会中父子名字不能用同一个字,谓之“家讳”。先生肯定知道这个禁忌,而故意命名为老栓、小栓,隐含的是作为下一代的小栓,仍然承袭着父一辈的体格健全,思想麻木(不能叫保守,保守还是有一定的原则和主张,只是不肯应时而动,顺应潮流)。是谓之“栓”。
如同夏瑜坟上的花圈一样,小栓的失语和命名可能也是作者有意为之。这种隐喻中流露出来的就是鲁迅的心境。
三、自噬其身的绝望
历来将《药》作为鲁迅“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系列小说之一,认为它刻画了当时国民在封建势力重压之下麻木的精神状态。但作为能深刻体会这重压下国民的麻木,且被无力感深深包裹的鲁迅,在黑铁屋里独醒的呐喊,心境的苍凉与绝望却是其他小说中所没有的。从小栓的失语与命名的隐喻中,包含的是对当时社会思想僵化、民众麻木、新一代精神萎靡的深沉忧虑。所以从《药》的创作意图上来说,它不是揭出病苦以求疗救为目的小说。它应该与《孤独者》一样,属于“哀莫大于心死”的绝望。夏瑜坟上的花圈只能是作者聊以自慰的安排,更真实的现实是革命者生前寂寞,死后凄凉,正如小说的结尾一样:“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连一只乌鸦也不肯光顾摆满祭品的夏瑜的坟。
反观《阿Q正传》,虽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小说中作者的叙述以入木三分的心理描写略带戏谑的语气来观照主人公,潜伏在字里行间的是医者仁心的细细解剖。有对阿Q本身“国民劣根性”的典型化描写,又有对辛亥革命不彻底性——地主乡绅投机革命的细节及“城里人剪辫子,未庄人盘辫子”的形式化革命的批判。要说揭示病根,以求疗救。子孙不绝的负面阿Q精神才是需要引起重视并救治的。
而《药》中有的只是被悲观和无奈掩起来的鲁迅——“寂寞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华夏两家没有了未来,中华民族前途堪忧。这一切在少年时辗转于当铺药铺间,看尽世态炎凉;青年时求学异国,痛感祖国衰弱,国民麻木,转而弃医从文;继之以无爱的婚姻;兄弟反目,朋友远离的鲁迅看来,他的悲观主义与绝望心境完全加大了《药》的沉重,如他在《野草·墓碣文》中恐怖阴森的文字: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 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
1919年的鲁迅清楚地知道过去,活在沉重的当下,未来在哪里?他看不到。1919年的中国新旧思想阵营处处列阵,从阴影中努力走向光明的他以匹夫之心,负振国之任,甲胄重装,荷戟独行,有些彷徨……
脸上挂着泪滴。
参考文献:
钱理群.鲁迅:远行以后(1949-2001)(之四)[J].文艺争鸣,2002.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8854(2016)02-0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