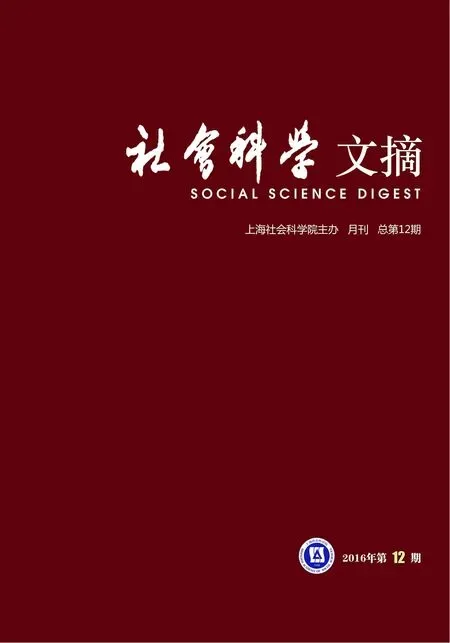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开创政治哲学的传统?
2016-11-26李佃来
文/李佃来
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开创政治哲学的传统?
文/李佃来
从理论传统的视角,全面揭示马克思政治哲学相对于西方主流政治哲学的异质性理论思路与超越性关系,不仅是一个关涉到如何准确把握思想史关系的一般学术性问题,更是一个关涉到如何准确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乃至全部哲学的思想实质,以及如何开显其当代性价值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性问题。
从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
我们虽然可将近代以来的西方主流政治哲学界分为功利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平等的自由主义以及共和主义等各不相同的学思传统与理论流派,但这些不同的学思传统和理论流派,大致又都是以权利和自由为价值基点开展政治哲学研究的,权利和自由在此意义上成为西方主流政治哲学的理论中轴。就发生学本源和生成基础而言,权利和自由并非像边沁所认定的那样,是由成文法所规定和给予的,情况毋宁是,这些在霍布斯、洛克以来的近现代政治哲学中凸显出来的价值原则和政治规范,深深植根于黑格尔所描绘的“作为劳动和需要的体系”的市民社会之中,故而市民社会才是权利和自由的发生学本源和生成基础。
由此观之,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绝不是在一种单纯的概念史和观念史的前后相接与渐次分化中向前推进的,而是基于市民社会的出场与经验性在场这一现代社会历史结构的重大变迁而建构起来并不断发展的。进一步说,霍布斯、洛克以降自上而下的政治哲学家不仅是在市民社会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下,而且也是以市民社会为根本立足点来从各自所属的传统和视界来予以推理的。
从现实层面来看,市民社会由于是一个以个体的经验性存在为基础的社会组合体,所以借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生活在这个组合体中的人无不“把本身利益作为自己的目的”,无不根据主体性或特殊性、为我主义或利己主义的精神性原则来安排自己的各项事务。照此来说,我们自然可以顺理成章地将经典自由主义传统中的洛克、斯密、穆勒及诺齐克等推认为以市民社会为立足点的政治哲学家,原因在于,他们几乎都从“个体自由”这个始源性的逻辑起点出发,遵从严格的“自我决定”原则来构建其各极其致的理论学说,这一做法不仅与市民社会的精神性原则相符合,而且还从理论上对这种原则作出了强有力的辩护。然而,卢梭、黑格尔及罗尔斯等对经典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提出反拨的政治哲学家,是否也应被一体划归在以市民社会为立足点的阵营当中?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因为问题在于:主体性或特殊性、为我主义或利己主义的精神性原则,使得市民社会从一开始就没有展现出洛克所勾绘的那种风平浪静、井然有序的理想性图景,而是使之成为了一个充满各种竞争性和博弈性的利益关系,将自由与平等、个体与群体、特殊性与普遍性等矛盾推向极致的一个领域。这样来看,卢梭、黑格尔、罗尔斯等人相继用“公意”“国家伦理”及“公共理性”来克服唯我独尊的主体性或特殊性原则,其旨趣并不在于构建一种根本超越于市民社会经验性存在的理性法则,而是在于用一个统合了自由与平等、个体与群体、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较完整理论框架,从一种较高的理论反思水平来审视和把握市民社会的经验性存在。这说明,他们并没有疏离市民社会的精神性原则,而只是以一种在他们看来更符合道德直觉的理性方式,来补充、修缮和提升这种原则。由此来说,自霍布斯、洛克直到罗尔斯、诺齐克,不管是哪种运思进路和学术传统中的政治哲学,其工作的最终目标,都在于竭力构建一套契合市民社会的精神性原则和商业社会运作模式的伦理规范和行为规则,进而以此来协调和安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社会关系。
对于马克思而言,其政治哲学的理论创制则体现出截然不同于西方主流政治哲学的情形。西方主流政治哲学家们之所以相沿成习地以市民社会为立足点来发展其理论学说,是因为他们始终相信,市民社会是既能满足自我需求、又能满足他人需求,从而实现人与人互利共赢的最佳社会组合模式。不能不说,探寻一个人与人互利共赢的社会组合模式,不仅是西方主流政治哲学各个理论流派的共同旨趣,也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一个重大课题。但在马克思看来,在市民社会的视域和框架内寻求一种人人互利的组合形式,只不过是一个天方夜谭、没有答案的迷梦,原因就在于,市民社会归根结底乃是一个由私人利益所织就、只能形成竞争性与对抗性而非协作性关系的领域,即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互相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由此来说,只有跳出市民社会的理论框架,并进入到人类社会的思想界面,才能够实质性地探索出解决个体价值与共同体价值、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之矛盾的方案,因而也才能够从根本上把握到何为人人互利的最佳社会组合模式及如何通达这一模式的问题,否则,这一问题将永远是无解的。在人类社会中之所以能够实现人与人的互利共赢,并非因为这个社会组合模式消解了个体价值而仅仅维护了共同体价值,而是因为个体价值与共同体价值在其中达到了真正的统一,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综合起来,如果将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这两个不同的政治哲学立足点视为前后相接的两个不同历史位阶,那么这两个历史位阶之间的关系,就如同黑格尔逻辑学中知性和理性的关系,后者并非构成对前者的全盘否定,而是以前者为坚实的踏脚石到达新位阶的。这种关系直接表明,人类社会既具有超越于市民社会的特质,也具有与市民社会相通的地方。从后一方面来看,马克思确立起来的是一种与西方主流政治哲学在论题上相重合,但在论证方式和理论内核上根本相异的现实性政治哲学话语;从前一方面来看,马克思确立起来的则是一种在西方主流政治哲学视野中完全缺失的超越性政治哲学理论叙事。这就涉及到马克思所开创的政治哲学传统的另外两个问题,一是从自然论证到社会论证,一是从此岸价值到彼岸价值。
从自然论证到社会论证
霍布斯、洛克以来的政治哲学家们之所以认为在市民社会这个组合模式中,能够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互利共赢,则是由于权利和自由在他们看来,不是专属这个人或那个人的,而是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普遍有效的。就此而言,“平等的权利”是全部近现代西方主流政治哲学的一个立论前提。问题在于,权利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并且常常会受到一些复杂多变的社会因素的影响,这使得人们在享有或行使权利上未必能够达及平等。为了在理论研究中绕开这个问题,从而使平等的权利成为一个可靠的立论前提,西方主流政治哲学家的通行做法就是将有差别的社会人还原为同质性的自然人,原因是大概只有从同质性的自然人的视点来看,平等的权利才可成为一个不加任何限制或背景性说明就能成立的立论前提。在如此这般的意义上,我们认为近代以来的西方主流政治哲学是通过自然论证的方式来建立其理论框架的。
然而,权利既然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那么只有从自然论证转向社会论证,在关涉具体社会历史问题的坐标系中研究权利以及自由、平等、公正,才有可能对它们予以通透彻底的理解与把握,否则,不仅无法对这些在现代社会中挺立起来的政治原则和政治价值作出具有历史规定性的解释和说明,而且也注定会使自然论证所蕴含的规范性基准蜕变为毫无效力甚至为相反的东西作隐性辩护的东西。
能否实现从自然论证到社会论证的革命性转换,从而使后者成为政治哲学的根本学术方法和主导理论思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哲学家们是如何理解市民社会问题的。以市民社会为立足点的西方主流政治哲学家们,由于并不注重对市民社会问题本身进行反思性探究(黑格尔是个例外),所以,他们只能把握到市民社会及其所表征的历史时代的外在表象,而无论如何都到达不了其内在本质的层面。他们之所以始终不能从自然论证的理论路数中抽脱出来,与其对市民社会滞留于表象的直观式研究不无相关,这是因为仅从外在表象来看,生活在市民社会中的人无非就是孤立的自然个人而非处在相互联系中的社会人,故而在市民社会的历史地平上所凸显出来的权利、自由、平等、公正等等,牵涉到的也无非就是自然人之间的关系而非真正的社会性政治关系。与西方主流政治哲学家判然有别,马克思则正是在对蕴藏于市民社会中的发达的社会关系及其所指示的内在本质的深刻考索与揭示中,将政治哲学的自然论证理论思路根本性地改换为了社会论证理论思路,并由此大尺度地改写了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学术传统。
马克思将政治哲学的自然论证思路改换为社会论证思路,其对蕴藏于市民社会中的发达社会关系及其所指示的内在本质的揭示只是一个笼统的理由。而如果仅仅局限于这个笼统的理由,我们还不足以将马克思与西方主流政治哲学家完全界分开来,原因是如果由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冲突所造成的竞争性与对抗性关系,乃是市民社会中发达的社会关系的根本表现形式,那么像霍布斯、卢梭、休谟、斯密及黑格尔这样的政治哲学家,实际也都看到了市民社会中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冲突及由此而来的竞争性与对抗性关系。所以,需要追问的更深刻的问题是:马克思与他之前的这些政治哲学家们,分别是如何来解读市民社会中的竞争性与对抗性关系的?马克思之前的这些站在市民社会立足点上的政治哲学家,无不将市民社会中的竞争性与对抗性关系解读和解释为人的利己本性的一个自然释放和必然表现形式。这种解读和解释虽然看似已接入到社会论证的理论思路中来,但实际与这种思路渐行渐远。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这种解读方式予以了激烈批评:“把竞争看成是摆脱了束缚的、仅仅受自身利益制约的个人之间的冲突,看成是自由的个人之间的相互排斥和吸引,从而看成是自由的个性在生产和交换领域内的绝对存在形式。再没有比这种看法更错误的了。”马克思的这个批评是要告诉人们,市民社会中的竞争性与对抗性关系的始作俑者,如果不是人的利己本性及因之而来的个体自由这个自然性因素,那么就一定是比这个自然性因素远为深刻的社会性因素。这个社会性因素就是在市民社会中起支配作用的资本。
如果说马克思与近代以来的西方主流政治哲学家一样,也对权利、自由、平等、公正等基本命题给予了积极关注和研究,那么他与后者的分野之处就在于,他并不是拘泥于这些政治哲学命题本身来关注和研究这些命题的,而是在政治经济学的视域中,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方法,借助于“资本批判”这一特定的话语形式来做这项工作的。前一研究方式和学术路数归根到底只是自然论证的一个表现形式,而后一研究方式和学术路数才是马克思确立社会论证理论思路的根本标志。
从此岸价值到彼岸价值
政治哲学不同于实证性科学,它追求的是“应然”的政治生活状态,因而在本质上它是一种由价值判断所证立起来的规范性理论。
在马克思与古典政治哲学之间存在着一种隐微的思想史关联,这一思想史关联启示我们,不能像一些当代政治哲学家那样,仅仅从现实性层面上、参照此岸价值来把握人类社会概念,而应当看到这一概念所实际蕴含着的深刻的超越性思想和彼岸价值。如果只是停留在前一思维阶段,我们将缺少把马克思与西方主流政治哲学家区隔开来的充足理由,而只有将思维推进到后一阶段,才有可能再次在“传统”的意义上,洞见到其政治哲学的独特理论见识和卓尔不群的思想气质。人类社会概念所蕴含的彼岸价值是什么?
阿伦特将这一彼岸价值主要解读为一种与亚里士多德所提的“闲暇”相类比的未来社会的“闲暇”。不过,这个“闲暇”并不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价值论范畴,它主要指涉一种生活样态,比之更具有概括性的应是与近代以来西方主流政治哲学中的权利和自由完全不同的“自由”。这一自由与古典政治哲学中的德性、智慧、卓越、崇高等虽然具有不同的链接对象,但它们在思想命意上却是基本相通的,都具有超越性的祈向和彼岸价值的共同特征。
自霍布斯、洛克到罗尔斯、诺齐克的政治哲学家们虽然普遍将基于平等权利的公正话语论定为政治哲学的最高知识形式,但与马克思通由终极性的自由这个价值而达到的理论反思水平相比,前者则还处在一个需要提升的较低学术层面。
当然,建立一个比近代以来经验性和操作性的政治哲学思维更高的思维界面,进而提升政治哲学的理论反思水平,不仅是马克思,而且也是康德以来德国古典哲学家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康德的物自体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解决这个课题。但由于康德在理论理性的界限内否定了物自体的可把握性,所以从这个概念几乎不能推出类似于马克思自由的高位价值。康德虽然在实践理性领域赋予了道德以一种高于经验原则的地位,但正如阿伦特所指出的,这个道德只是一种封闭的“驾驭和限制人类自身理性精神的力量”,所以也并不能真正为经验原则树立一个标尺,从而有效克服后者所可能具有的偏蔽与不足。黑格尔借助于辩证法推进了康德所提出的问题,由此把握到了与马克思的自由相通约的自由以及精神、上帝等无限世界的对象。但黑格尔将理论活动视为“黄昏到来才会起飞的密纳发的猫头鹰”,故此,其所讲的自由、精神与上帝等只是在认识论领域超越了经验性知识,在实践哲学领域我们则看不到这种超越。康德与黑格尔的范例说明,即便是德国古典哲学不无深刻的批判性和反思性理论进路,也并没有将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实质性地引向更高的思维水准,并由此独辟蹊径地进行政治哲学的理论创制。与康德和黑格尔相比,马克思的自由是针对人在世俗市民社会中的生存结构而提出来的一个高位价值,它既具有物自体超凡脱俗的精神性意义,也并非神秘莫测、不可把握的东西;它绝不仅仅是历史存在中供人们认知的理性法则,更是改造现实政治秩序和塑造未来理想政治生活的模板。从这个情况来看,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毋庸置疑只是到马克思这里才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写,由此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理论至高点上。
从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从自然论证到社会论证、从此岸价值到彼岸价值,这三个重大转换一体表明马克思在政治哲学史上开创了一种与西方主流政治哲学理论迥然有异的理论传统,并由此打开了政治哲学研究的全新学术空间。
(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摘自《江海学刊》2016年第6期;原题为《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开创了政治哲学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