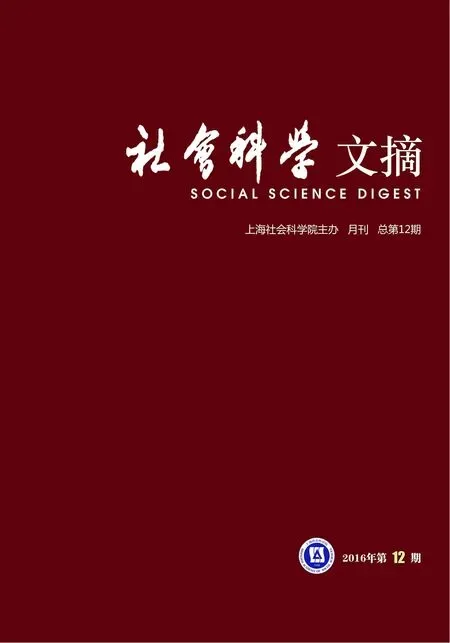地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之规范分析
——兼论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关系
2016-11-26王万华宋烁
文/王万华 宋烁
地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之规范分析
——兼论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关系
文/王万华 宋烁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在《国务院2016年立法工作计划》中属于“全面深化改革急需的项目”类别。地方现已出台大量关于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地方政府规章与行政规范性文件,地方立法先行虽得以为中央立法积累宝贵的立法经验与实证经验,但如何处理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关系本身亦成为中央立法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本文对收集到的326份规定就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展开规范层面的分析,并进而对如何定位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关系提出初步思考。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采用了国务院指导性文件与地方立法先行先试相结合的推进方式
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主要是一个实践话题,政府的自我推动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国务院通过一系列指导性文件提出并逐步完善了重大行政决策的制度框架:2004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下称《纲要》)将“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行政决策机制和制度基本形成”列为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目标的一项内容;2008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下称《市县依法行政决定》)进一步规定了完善重大行政决策听取意见制度等6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2010年《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下称《意见》)提出“要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依法治国决定》)中明确提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进一步就完善决策程序提出了6项具体要求。
立法对接层面,各级地方政府承担了先行先试的任务,并沿着两条路径展开重大行政程序立法的推进:一条路径以2008年《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为代表,在综合性行政程序规定中规定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另一条路径是制定专门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和行政规范性文件。此路径之下又分为两种做法,一种是制定综合性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对重大行政决策进行全面规范,如《浙江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另一种做法是制定关于重大行政决策单一程序机制的规定,如《大连市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办法》等。截至2016年5月1日,我们收集到地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共计326份。
地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的形式分析
1.区域分布。除西藏自治区外,我国大陆其他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关于重大行政决策的程序规定。其中,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了省级重大行政决策规定,约占我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域的67.74%。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在地方区域分布的广泛性为中央立法的实施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2.立法形式包括两种:一种是以《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为代表,在统一的行政程序规定中专章或者专节规定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326部规定中有15部为地方行政程序规定,约占全部规定的4.6%;另一种是制定专门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326部规定中,专门立法形式为311部,占95.4%。311部专门立法又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种是制定综合性重大行政决策规定,如《浙江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共计159部,占总数311份的51.1%;第二种是制定针对单一程序制度的规定,如《珠海市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办法》等。单一程序制度规定共计152份,占总数311份的48.9%。其中,听证制度(44份)、合法性审查制度(32份)、专家咨询论证制度(24份),分列前3位。
3.立法位阶。地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分为政府规章与行政规范性文件两类。其中,仅有36部地方政府规章,约占地方立法总数的11%;其他290部都为行政规范性文件,约占地方立法总数的89%。立法位阶分布显示在地方层面有关重大行政决策的规定位阶普遍较低。
4.制定主体。326部地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的制定主体全部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尚未有地方人大制定条例,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成为推动决策立法的力量。15部地方行政程序规定的制定机关均为地方人民政府,311份专门立法中有236份规定的制定机关是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占全部规定的3/4以上;74份规定由政府办公厅(室)制定;1份较为特殊的是广州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制定的《广州市重大行政决策论证专家库管理工作细则》。制定主体分布显示,政府自身成为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的推动者。
5.生效时间。15部地方行政程序规定中2008年出台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是第一部生效的统一程序规定。311份专门决策程序规定中,除《汕头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基本程序的规定》生效于2002年以外,其他310个重大行政决策均生效于2004年后。分析326份规定的生效时间可以看出,地方重大行政决策相关规定的出台,与国务院不同时期发布的指导性文件中关于完善重大行政决策机制的要求形成有效互动,以中央层面规范性文件确定的制度框架为基础展开的地方立法在程序制度上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共性,从而为中央层面的统一立法奠定了很好的地方先行先试基础。
地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之内容分析
地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的内容基本在国务院不同阶段指导性文件所确定的制度框架内展开,内容因而具有高度相似性。
(一)立法架构的两种思路
第一种,以决策过程为单一主线架构重大行政决策相关内容,事中程序制度并不凸显。此种方式的代表性规定有《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规则》等。采用此种架构方式的规定多发布在2006年至2009年间,主要依据2004年国务院《纲要》制定,是我国地方重大行政决策规定的初期样态,立法对决策程序制度的规定较为笼统、原则,缺乏可操作性。
第二种,以决策过程和决策程序制度为双主线架构立法内容,决策程序制度单独设章予以规定。采用双主线架构模式的有《四川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等。此种模式一方面按照事前、事中、事后的流程架构立法内容,同时以程序制度为主线架构立法,对五大程序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单独设章加以规定,细化了各项决策程序制度的规定,完善了决策的程序机制。采此种立法架构类型的规定多发布在2012年至2015年间,2015年数量最多,这与五大程序机制在《依法治国决定》中得以明确并细化其要求相对应。
(二)适用范围的4种规定模式
由于我国立法采用了先行规范重大行政决策,而非规范全部行政决策活动的策略,确定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范围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是目前困扰实践的最大难题。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确定的模糊性造成大量重大行政决策游离于立法之外,很多应当纳入法律调整范围的决策被政府以不属于重大行政决策为理由规避了立法的适用。地方立法也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做了一些探索,出现4种规定模式。
第一种,“仅正面列举”模式。此种模式不对重大行政决策作概括性规定,直接列举重大行政决策事项。
第二种,“概括+正面列举”模式。这种模式首先界定了重大行政决策的内涵,同时正面列举属于重大行政决策的典型事项。
第三种,“概括+正面列举+反面列举”模式。这种模式增加了反面列举,将部分事项排除在重大决策事项范围之外,有助于进一步明确重大行政决策的范围。
第四种,“目录机制模式”。此种模式放弃正面列举,代之以目录管理机制,同时使用“概括+反面列举”方式为行政机关制定重大行政决策目录提供依据。
(三)重大行政决策中的多元主体
以不特定人为行为对象的重大行政决策行为涉及的主体范围宽泛,不同主体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亦相对复杂:
1.行政机关,包括决策机关、决策承办部门、决策事项相关部门、决策批准机关、决策执行机关、决策监督机关、决策机关办公厅(室)、决策承办部门法制机构和决策机关法制机构等。不同类型行政机关之间形成横向与纵向两类关系。目前立法关于内部不同机关、不同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与衔接、机关之间的协力等内部法律关系的规定比较薄弱,这正是实践中重大行政决策综合决策不足、部门决策色彩过强的制度上的薄弱环节。
2.公众,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属于决策中的外部主体,与决策机关之间形成外部法律关系。
3.专家,属于决策中的外部主体,为决策提供技术理性支撑。
4.地方人大、政协、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如何在宪法、地方组织法的框架下,处理好决策机关与人大的关系,是中央层面立法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5.政府法律顾问、第三方专业机构等社会服务主体。
(四)五大决策程序制度在地方立法中得到普遍规定,成为法定必经程序
《纲要》《市县依法行政决定》《意见》《依法治国决定》《法治政府建设纲要(2015~2020年)》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要求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不同阶段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因而呈现出不同的制度特点。2010年之前出台的规定,多数较为笼统、简单地规定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条款;2010年以后出台的规定,形式上将五大程序制度单独设章加以规定,内容则更为具体、详细,五大决策程序机制内容逐渐丰富、完善,为中央立法打下很好基础。
在五大法定必经程序制度中,公众参与和专家论证属于外部程序制度,其中的公众参与是现行立法规定的重点内容,很多地方立法关于公共参与的规定都很具体,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则是制度构建中的重中之重。关于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专门规定多达44份,是单一制度专门立法中数量最多的。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属于内部程序制度,这3项制度的规定相对简单一些。风险评估机制是我国独具特色的决策程序制度,地方在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普遍要求进行决策风险评估,这与我国近年来各级政府信访压力过大有关。
(五)重大行政决策实施评估制度
决策领域长期存在“重制定、轻评估”的问题,而决策是面向未来的行为,决策实施后需要及时跟进开展实施效果评估。地方关于决策后评估的规定详略不一,广西仅用一个条文对决策后评估机制做出概括性规定,贵州设专章规定了决策后评估制度。决策实施评估制度宜由中央立法予以统一规定。
(六)重大行政决策的责任追究制度差异较大
自《纲要》始就将重大决策责任机制与重大决策程序机制的完善并提,各地均在规定中对法律责任进行了规定,但内容的详略程度有所不同。福建等地方仅用一个条文对法律责任进行规定,重庆等地方规定则以专章形式规定重大决策的法律责任,包括责任主体、追责情形、归责原则、责任形式等内容。
责任机制属实体法内容,且与行政问责机制、公务员纪律处分机制、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都有交集,不适合在地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中予以规定,应由中央立法予以统一规定。
“先地方、后中央”路径下的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关系
中央层面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有两条实现路径:一条路径为由全国人大制定《行政程序法》,设一章规定重大行政决策;另一条路径为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条例》。综合目前的各项立法进程,第二条路径即由国务院制定《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应为近期所能预期。基于地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之现状,“先地方、后中央”路径下的中央立法应当避免内容过于原则、概括,注重制度可操作性,使之成为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基本法,而不是地方立法的补充法。
第一,程序法应具有可操作性,条例作为规范重大行政决策活动的程序立法首先应当满足其法律属性,避免文本定位的政策属性。地方立法历经10余年探索已经发展至制度构建精细化阶段,中央立法如果仍然概括、原则,将成为又一份指导性文件,立法意义将受到很大削弱。条例属于行政法规,为法的一种形式,文本定位应当区别于各阶段指导性文件而凸显其法律属性,明确决策中各方主体的程序权利义务,厘清行政机关之间的职责分工。
第二,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是现阶段法治政府建设的中心任务,地方决策程序规定位阶过低,难以有效规范政府的重大行政决策活动,需要中央立法高度法典化,实质发挥规范作用,提升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活动的规范力度,进而实现将重大行政决策纳入法治化轨道的立法目的。我国依法行政初期选择以具体行政行为为对象展开,十八大之后,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活动的规范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的中心任务之一,对重大行政决策的程序规范为其基本规范进路。与中央在《依法治国决定》《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中关于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制度层面的高要求定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实践遭遇了相当大的现实困境,有的地方无决策程序法,有决策程序立法的地方多数得不到很好落实。很多信访事项暴露出重大行政决策在实践中面临多重问题:有的决策不进行充分科学论证和征求公众意见,有的决策绕开现有法律另辟蹊径违法决策,有的决策效能不足,有的决策部门决策色彩浓厚、综合决策不足。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遭遇的种种困境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地方立法位阶过低、难以形成对重大行政决策的有效规范则是其中原因之一。目前地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位阶普遍较低,难以对政府形成有效约束,此外,政府规章与行政规范性文件也不能作为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很难通过司法审查强化其约束力。
立法定位需要考量立法面临的任务与要达到的目的。当前重大行政决策中央立法面临的立法任务是一方面要回应国家对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在当前的功能定位,将《依法治国决定》和《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关于完善重大行政决策机制的具体要求转化为法律制度;另一方面要能够解决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在现实中遭遇的种种困境,解决现有立法位阶过低、法治动力不足的问题。中央立法需要对规范政府的重大行政决策活动实质发挥作用,一部高度法典化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中央立法才能够实现这一立法任务。
第三,程序规则具有统一性,地方决策程序立法内容呈现出相当程度的相似性,中央立法应吸收地方立法,建构重大行政决策基本程序制度,一方面避免地方不必要的重复立法,另一方面避免地方立法缺失之地出现法治空白。
(王万华系“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宋烁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生;摘自《行政法学研究》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