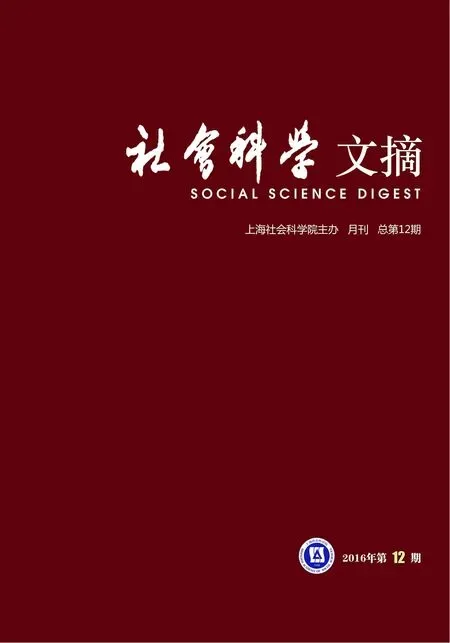征地拆迁背景下的村庄政治
2016-11-26贺雪峰
文/贺雪峰
征地拆迁背景下的村庄政治
文/贺雪峰
2015年暑假,笔者一行10多人到浙江L县城关街道作了20多天的调研。城关街道是L县的郊区,是城市新区的规划建设区,10年前开始征地拆迁,现在有些村已经征地拆迁完毕,还有些村正在拆迁过程中。调研期间获知,城关街道2015年有80多项县级重点建设项目要落地,另外还有之前立项未完成的跨年度到2015年的县级重点项目60多项。也就是说,一个街道,2015年一年竟然同时有140多项县级重点建设项目落地,而几乎每一个重点项目的落地都要涉及征地拆迁及与之相关的复杂的利益博弈,由此可以想见街道和行政村工作之繁重,及这个过程中机制和体制之重要。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城市建设更是日新月异,一天一变样,在这些日新月异背后的是巨大利益调查和激烈利益博弈。巨大利益调整是如何完成的?激烈利益博弈是怎么进行及怎样平息的?乡村治理是如何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来应对的?这些都是有趣的值得讨论的问题。理解了这些,多少就有助于理解中国奇迹为什么会发生的原因。
征地拆迁与村干部
地方政府要发展经济,要项目落地,要城市扩张,就必须征地拆迁,且征地拆迁必须在规划区内,在城市建设的扩展面上。遇到了钉子户,地方政府强拆,就可能引发激烈冲突,甚至出现自焚等恶性事件。中央为了防止出现此类恶性事件,要求地方政府不能行政强拆,问题是法院强拆也可能引发恶性事件,从而法院也不愿接手征地拆迁中的强征强拆。地方政府对付一个钉子户就感到棘手难办,若有一群钉子户呢?甚至整个村庄的村民都来当钉子户?若如此,地方政府的征地拆迁就进行不下去,项目就无法落地,经济就难以发展,城市也无法扩张了。
地方政府是如何在征地拆迁中解决钉子户的呢?地方政府必须依托强有力的村干部。村干部是村庄熟人社会的一员,是村庄集体利益的代表,是联结地方政府基层政权与农民的关键一环。如果村干部组织村民来借征地拆迁向地方政府要高价,地方政府的征地拆迁就陷入死结了。如果村干部协助地方政府来征地拆迁,如果村干部既缺少能力,又没有代表性,村干部也无法在征地拆迁中帮地方政府做有效的工作。只有当村干部有能力又有协助地方政府进行征地拆迁的意愿时,村干部才可能帮地方政府完成“天下第一难”的征地拆迁工作。
这就涉及与村干部有关的3个问题:第一,村干部凭什么有意愿协助地方政府完成征地拆迁工作;第二,什么样的村干部有能力协助地方政府完成征地拆迁工作;第三,村干部用什么办法来完成征地拆迁工作。
总体来讲,征地拆迁给农民的补偿是超出农民原有利益的,因此,农民是愿意征地拆迁的。只是既然征地拆迁是几辈子难得的一次为自己利益博弈的机会,只要敢博弈,就可能多获得数万甚至数十万元的补偿,那为什么不博弈一次?村干部对付这些人的办法就是软硬兼施了。找到这些人的所有社会关系,动员他们的社会关系来做工作,通过利益交换来满足一些人的利益要求,威胁不签字同意就拿不到按时征地拆迁的奖补,甚至拿出个人的面子来威胁钉子户,请黑社会出面威胁钉子户,等等。
最后还有几户坚决不签字同意拆迁,怎么办?虽然地方政府明确要求不能强拆,但村干部可能为了自己利益而与地方政府合谋,通过灰色手段来拆迁,比如“意外”失火将钉子户的房子烧掉了,挖机“失误”将房子推倒了。总之是通过各种办法造成拆迁的事实,然后再给补偿。因为“意外”“失误”导致房子倒掉,农户里面还有家具未能搬出而受损失,地方政府给予较高的补偿,名义上是补家里损失,事实上是将钉子户要的高价补了部分,钉子户达到了部分目的,房子也已经拆了,也就不好再闹下去了。其他村民也不好再与这种房子被“意外”烧掉村民拿了较多补偿来攀比。
征地时,地上附着物的补偿也是一个难题。地方政府很难真正搞清楚计划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情况,他们可以按一定基数将地上附着物补偿包干给村干部,村干部了解地上附着物的情况,也就有能力防止村民的无限要价。
那么,什么样的村干部有能力协助地方政府完成征地拆迁任务?显然,一般的老好人村干部是无法完成征地拆迁任务的,办厂经商致富的企业家也不会愿意来做这个得罪人的事情。有能力又有意愿来协助地方政府征地拆迁的,是可以从征地拆迁中获得个人利益、又在乎这个利益、及有能力获得这个利益的人。这种人比较狠,孔武有力,高大威猛,甚至与黑社会有不明不白的联系,他们能说好话,也敢得罪人,软的硬的白的黑的都能来。
如果地方政府可以让村干部借征地拆迁之机谋取一些利益,有能力完成征地拆迁任务的狠人就可能走到征地拆迁的第一线。当然,他们不是以黑社会的身份来完成征地拆迁的任务(也不能以此身份来完成),而是成为村干部后来完成的。
这样就需要在接下来讨论两个问题:第一,这些狠人如何可以在协助地方政府完成征迁任务时获得利益;第二,他们怎样才能当上村干部。
村干部竞选与获利空间
这些有背景的狠人之所以愿意当村干部并协助地方政府来完成征迁任务,不惜得罪本村村民甚至自己的亲戚朋友,其中关键是他们希望借机获得利益。地方政府当然也要创造出这样的获利机会,给他们留下这样的获利空间。
具体地讲,在征地拆迁中,狠人村干部可能在以下3个方面有获利空间。
第一,征地拆迁涉及巨大的利益分配与调整,借征地拆迁,村干部可以从中做手脚,损公肥私也好,偏袒自己人也好,既然有巨大的利益分配空间,如何分配、谁优先,村干部就有一定话语权,就有寻租空间。
第二,地方政府为了调动村干部完成征地拆迁中最难的一些事务,倾向通过包干责任制来将征迁任务与预期补偿包干到村,由村干部来具体实施,最典型的如前面已讲的,征地时地上附着物的补偿,地方政府按一定基数包干到村干部,村干部因为有了剩余索取权,他们就有很高积极性来“据实补偿”。因为村干部对村里情况十分了解,且村干部可以动员各种关系,使用各种微妙的权力技术来实施地上附着物的补偿,就可以防止钉子户的漫天要价,降低征地的交易费用。村干部因此能用远比地方政府所给基数(包干费)低的成本完成地上附作物补偿,从而留下一笔数额不菲的剩余资金,这部分资金就可能通过各种办法落入到村干部腰包,甚至有村干部直接将这笔钱分掉了。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村干部的获利空间,是他们承揽村庄中的建设工程。征地拆迁之后必有建设任务,最典型的建设项目有打围墙、三通一平等,这些建设都是简单的土方工程,工程量也不大,利润相对固定。
这样一来,狠人村干部就可能借征地拆迁所必然带来的项目落地的建设机会来承揽土方工程,来获得稳赚不赔的利益。一个村,几千亩的村域面积,征地拆迁往往要经历很多年,几乎会有无穷的建设机会,也就有无穷的赚钱机会。他们只要找一些人,搞一个工程队,就可以几乎是无限地但并非违法地来谋取利益:他们并没有偷或抢钱,而是老老实实保质保量地完成土方工程,获得工程利润,这些都是正当、合法的,当然不一定合理。
地方政府对此当然也是心知肚明,且正是因为村干部可以从以上方面获取利益,村干部才有积极性协助地方政府完成征迁任务。地方政府在上述所有方面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方政府与村干部具有默契。
问题是,村干部可以在征地拆迁后获取的这些好处并非必然的,这些好处也不同于按规定必须给村干部的报酬,而是要由村干部去“经营”,且要有能力去“经营”,才可以得到的。得到这些好处,村干部还是要承担风险的。既想获得征迁好处又有能力获得征迁好处的,只有一种人,就是村庄中与黑社会有染的包工头,他们既有动力也有能力来当征迁村庄的村干部。
因为当村干部利益巨大,村庄中希望通过当村干部来获取利益者就试图通过村委会选举成为村干部。显然不只是一个人想当村干部及有能力当村干部,这些有意角逐村干部职位者就通过竞争来分出胜负。
要当选村委会主任,必须要有多数村民的支持。为了获得中间票的支持,也为了感谢铁杆支持者,参加村委会主任竞选者花钱请客,花钱送东西,比如香烟等,甚至花钱买票,就很正常。为了争取中间票及稳住铁票,村委会候选人就必须组织起竞选团队,里面要分工,要研判形势,要一对一地做工作,要用各种传统的关系和现代的资源去动员。竞选团队的运转本身也是要花费的。也就是说,村委会竞选中,有无资金是很重要的,没有钱想选上村委会主任实在是很难的。
竞选双方的高度动员和势均力敌会进一步加剧选举中的动员程度。在仅仅是差一、两票就全败的情况下面,竞选所可以调动起来的经济资源、心理能量、情感投入以及组织手段,很快就会达到可以达到的极限状态,很多事情也就无所不用其极了。所有村民在这些无所不用其极的动员手段下面逃无可逃,每个人都被拉入到不同的派系,且在不同的派系中同情感、共悲欢,由此,选举的过程也成为了塑造强烈派系的仪式及动员过程。
最终,有一方通过竞选当上村委会主任,这个通过激烈竞选上来的村委会主任就必须带着竞选上来的强大气势来展开工作。
派性斗争与村级权力的规范
当选上来的村委会主任首先所要面对的就是经过深度动员所形成的村庄中的两派:自己的一派与对立的一派。自己当选村委会主任,就不能只是自己当村干部捞好处获利益,而且必须为支持自己的人获利。竞选失败一方也是经过深度动员的,有过强烈的情感共振的群体,这种深度动员和情感共振会积累下来强大的心理能量,就构成选举结束后失败一派对抗当选者的力量。通过激烈竞选当上来的村委会主任如果不能化解竞争失败一派的对立情绪和对抗行为,这个当选的村委会主任将在之后的村级治理中处处受制,任何工作都难以开展。一个聪明的当选村委会主任会用各种办法来化解这种对立与对抗。这个化解要用时间,所以当选的第一年时间是磨合抹平派系。若当选村委会主任化解对立不力,或竞选中产生情感伤害太深,选举结束之时也就是派性斗争开始之时。村庄中激烈冲突持续不断。
在征迁背景下面,激烈竞选所形成的派性政治主要不会表现在村庄权力结构内部,而是表现在当选的在任村干部为一派,以落选村委会主任候选人为首的在野一派的斗争与政治。
因此,激烈的村委会选举之后,一派当选进入体制,另外一派落选,成为在野派。为了完成征迁任务,地方政府无条件支持当选一派,当选村委会主任者,一方面尽可能抹平反对派,另一方面,他一定要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面施展手脚,大干一场。村庄治理就在对抗中开展下去。
如果村委会选举中一派大获全胜,另一派溃不成军,则当选村干部一派就可以赢得进行建设的宝贵机遇。这种情况不常见,但并非没有。其中一个办法就是通过资源输送,分化瓦解反对派精英,进行派系重构,甚至消解了派系与派性。而在相当多的时候,反对派继续反抗,钉子户层出不穷,当选村干部者抓紧时间捞回投入选举的资源,同时使用各种狠的手段来摆平钉子户,来对付反对派的反击。村庄内出现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引起了基层治理中的混乱。在最近10年,L县城关街道,一方面征地拆迁总体来讲在顺利进行中;另一方面,基层治理中也出现了很大大事,其中之一是村级治理中出现了很多恶性事件。
因此,对村级治理进行整顿规范就势所必然。
征迁带来的可供分享的利益以及对利益的博弈,构成了征迁背景下面的激烈竞选、撕裂、对立的运动,这也是派性政治的动力所在。一旦征迁完成,村庄所有未被分配的利益都已分配到人了,或已有明确的分配方案了,村庄派性斗争的动力也就不再存在,激烈的村委会选举也不大可能再如此发生。因为征迁而形成的巨大的外生利益的消失(或分配完毕),村级治理进入到常规阶段,村庄政治就可能走出派性斗争与相互撕裂的恶性循环。
征迁的完成也使地方政府不再需要通过默许村干部的特殊利益来调动他们协助地方政府工作的积极性。相反,对于村庄治理中的各种混乱,地方政府失去了忍耐力,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就更倾向通过制度来规范村级权力运作,就更不能容忍村干部的“胡作非为”,这也正是五议决策法和“村级权力清单”得以产生的条件。结果就是,自己花了很多钱来当上了村委会主任,在当村委会主任时,钱还没有捞回,而征迁已经结束,不仅捞取利益的空间没有了,地方政府之前的保护默契也突然没有了。
这样一来,在征迁地区,通过激烈竞选当上村委会主任的狠人,自当上村委会主任之日起,就拚尽全力左冲右突,到头来却发现自己成了一个难以自控的陀螺,除了高速自转以外,没有其他办法。他们的结局大多悲惨:结局好一点的是选举花的钱当上村委会主任后没有捞回来而已,坏一点的则是村委会主任还没有当完,就因为经济犯罪而被判刑。L县城关街道大多数村委会主任的下场都不够好,甚至可以说是下场很惨。很多人悔不当初,早知今日,何必来竞选这个村委会主任啊!
小结
通过地方政府(国家)—村干部—村民的三层,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村庄政治是如何在征迁背景下面生动展开,以及村庄政治又是如何完成征迁任务,从而顺利地调整利益,从而让中国经济发展城市扩张中项目落地的。
征迁背景下的村庄政治带有一定特殊性,不过,这个特殊性却是中国基层治理一般性逻辑在特殊场景下的展演。这个意义上讲,这个特殊同时也就更为生动具体地反映了中国基层政治乃至中国政治的一般特点。理解中国基层治理和中国政治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工作。
在地方政府(国家)—村干部—村民的三层分析框架中,国家显然是通过为村干部设置剩余索取权调动了村干部完成国家任务的积极性,这是征迁背景下面村级治理动力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家为村干部设置的剩余索取权大都是默许的,是潜规则,这个默许与潜规则就给了国家随时依据需要来进行调整甚至追究的可能。基层治理的灵活性也由此可见。
村干部之所以能顺利完成征迁任务,其前提则是,城郊农村的村民很清楚,征迁对他们是有利的,农民是愿意征迁的。如果征迁对农民不利,他们坚决反对,村干部就不可能做好天下第一难的征迁工作。本质上村干部所做征迁工作只是针对钉子户,而不是全体村民,及村干部是要协助地方政府将因为征迁所带来的利益调整到位。征迁这样的大事及征迁所涉及巨大利益调整,正是借具有积极性的村干部的工作而完成的。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感激这些完成了征迁任务、自己却未必有好下场的村干部。
(作者系教育部长江学者、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摘自《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