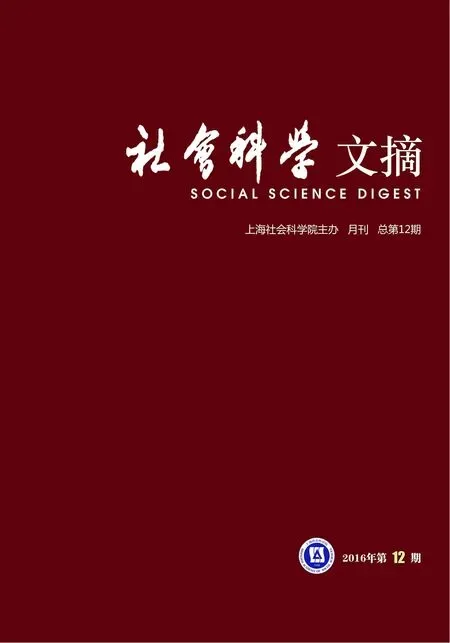办一个什么样的智库来支持国家改革开放
2016-11-26李灏
文/李灏
办一个什么样的智库来支持国家改革开放
文/李灏
一个开放的国家如何吸收全世界的智慧
1953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全国进入轰轰烈烈的建设阶段。我是这一年调到国家计委的。那时国家计委不归国务院管,非常独立,马洪同志是秘书长。我们听过他的报告,但还没有跟他单独接触过。1954年马洪同志被下放到基层。1956年6月,他又被调到新组建的国家经济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以负责人的名义从事调查研究和起草政策文件的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有许多机会与他接触,向他学习。
中国刚开始搞改革开放,非常需要跟外面的世界交流,开阔视野,吸收人家的思想和智慧。那段时间,我们对外的国际会议很多,一些有名气的专家学者都想来中国。1978年5月初,谷牧副总理就率领一个庞大的考察团赴西欧考察,我也是成员之一。在国外考察,发现有大量资金,都想到中国投资,却不得其门。我们就觉得确实要多请别人来讲学,听听外国的意见,学习先进的知识。当时交流的国家主要是日本和西德。谷牧同志曾经就我国经济怎么搞,向来访的日本朋友请教,提了许多有关经济发展的问题。日本的朋友说:“你提那么多问题,我回答不了,建议还是请这方面的专家来交流吧。”
后来日本就派来了大来佐武郎、夏河边淳和小林实三位学者来跟我们交流。同时我们又请了西德汉堡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古托夫斯基来讲学。我记得他来的时间不短,有十几天,主要在一个小范围里谈话,有关部委的十几个人参加了。他介绍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各国基本上都是社会民主党执政,社会主义思潮还比较热。西德有一段时间的供给不足,市场什么东西都缺乏,已经到了丢个马铃薯在地上都不知道有多少人去抢的地步。后来他们就做些研究:是把螺丝再拧紧一点,还是放开市场?最后决定走后面的路子,搞市场化了。此后西德就走向一个比较平稳的发展道路。他讲得很生动,对于我们加深市场经济的认识很有帮助,应该是最早为我们打开眼界的人。第二年,古托夫斯基又来了,但不像第一次那么提意见了。他说这样的交流没有形成机制,没有办法持续下去,不如搞一搞定期的中西交流会,请更多的经济学家来一起交流。
1981年,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提议,由谷牧同志和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大来佐武郎共同发起成立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这就形成了中日定期的对话交流机制。双方成员每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轮流在两国举办,重点讨论双方共同关心的宏观经济形势和中日经贸合作问题。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是一个小规模的内部交流研讨会,政府很难听到这种声音,如果第一次会议的时候能像古托夫斯基一样做报告,可能影响会更大一点。
中国刚搞改革开放,那个时候的政府机构没有国际视野,思想不太开放,仍然很保守,这就跟不上世界发展的潮流啊。国外的智库来跟你交流又面临许多障碍,没有一个很正规的机制,效果也都不太好。所以,我就想着我们确实迫切需要有一个思路开阔、有国际视野、有创新意识的研究机构,来为国家的改革开放服务。
办一个什么样的智库来支持国家改革开放
1985年12月份,我在深圳工作的时候,日本有一个很大的中青干部访问团,最后一站就来到深圳。中青干部访问团的领队不是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的成员,是某一个研究所的所长,他对我很信任,我每次到日本去,他都约我晚上出来喝个咖啡、聊聊天。他来到深圳见我,我们交谈后,他说:“你这个地方很重要,我回去要组织个机构来支持你。”1986年11月,在他的努力下,日本深圳协力会成立了。这个机构跟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不太一样,交流更加密切,日本组织的专家每年都来中国一次,我们有什么组织愿意到日本考察,就跟他们接洽,非常有诚意。日本深圳协力会操作了好多年,曾经把日本顶尖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组织到过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中日两国的经济交流合作。
除了日本深圳协力会,还有两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一个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一家智库给香港做了一个规划。还有一个是1987年3月8日下午,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林重庚先生来到了深圳,我组织了几个人跟他座谈。他建议我们要建立一个类似于其他新兴工业国家的发展研究机构,这个机构不一定隶属于某个部门,但可为各部门提供服务,成为政府的高级咨询机构。他的这个建议与我的想法是吻合的。因为,我总感觉到深圳是特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没有智库、没有研究机构是不行的,而且政府研究室是个写作班子,主要听一把手指挥,没有独立性。我觉得需要办一个研究机构,不能完全是官方的,不仅仅是为我们深圳特区的改革开放服务,还得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服务。
后来我就给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写信,建议在深圳设立研究机构。1987年11月12日,马洪同志致函给我,说这个建议,他们在中心党组会上作了一次酝酿,大家表示支持这个想法。1988年的4月28日,在马洪同志的部署下,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正式把报告提交给了中央。为什么这么顺利呢?因为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报告里把研究院的性质、定位、发展路径和治理模式这些关键的东西都说清楚了。比如说治理模式是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民办公助、市场化道路,明确提出以有偿的研究成果作为经费,自力更生、自我发展。这些在当时绝对是超前的一些意识和理念。9月3日,马洪同志和我联名写信,向中央报告了筹建有相当自主权和独立性、民办的新型研究机构的有关情况。10月,我们又向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口头汇报了筹建情况,得到充分的赞成和支持,并指示要把研究院办成一所真正民办的研究机构,首先要为深圳经济特区和各沿海省市服务,也要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示范建设服务,研究的范围可以从国内到国外,等等。
敢于这样提出,首先是深圳市当时有一定独立性,可以办一个不要靠政府拨款的智囊机构;其次是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对我们有参考意义。这个机构你说不是官方,他很多负责人基本都是政府下来的,但又好像不是全部靠政府拨款,而是以政府资助资金产生的利息作为机构的经费来源。
所以总的来说,我们综合开发研究院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办特区这么一个背景下展开的,没有改革开放我们要是成立这么一个机构的话,很难起作用,也就没有生存的必要。所以要有大环境,就像办特区一样,也是有很多曲折的,深圳现在还在突破,还要很好地发挥示范作用。其实我们正是因为既有官方背景,又是民间独立研究机构,才同这个时代比较合拍。不仅合拍,还要敢于突破自己,不断探索新的发展路子。研究院发展到现在,要感谢马洪、陈锦华、蒋一苇、高尚全、林凌等这些同志,没有他们的积极创办和示范,研究院也发展不起来。
研究院现在已经成为国家高端智库了,这是中央对我们的信任和鞭策,也是我们的荣耀和责任。我们要有一点前瞻性思维和战略眼光,突出自己的优势,聚焦国家发展急需的重大公共政策问题和舆论热点领域,开展前瞻性、对策性、储备性和实用性的政策研究,为党和国家战略决策服务。
为何所有制改革的研究很重要
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所有制改革,生产力水平大大提升。但是在我看来,城市才是要害,城市的生产关系如果不理顺的话,问题也会非常严重。所以智库研究城市经济问题,应当把所有制改革作为重中之重。
国有企业,国家所有,人人所有,却人人没有,没有人负责任,也没有人监管嘛!那时候,我们国家还没有专门研究国有企业股份制。我在国务院做副秘书长的时候,就曾思考过这个问题。1984年,国家财政部翻译了世界银行发布的国家经济年度报告,报告中说中国的国有企业没有董事会,也没有监事会,主张把像鞍钢这样的国有中央企业,在不触动公有制的前提下,可以考虑明晰股权,进行股权分割。这份报告很快送到国务院,我看得较早,启发也较大。于是打电话给体改委,问他们有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结果他们推荐了高尚全同志,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高尚全的。所以搞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我是有过一些思考的。1985年,我到深圳当市长,当时成立的4个机构里面我们就把政企分开,政府的公共财政是一个体系,企业是另外一个体系,我们搞一个投资管理公司来监管国有企业,同时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现在国有企业越来越放开了,当放开到一定的程度,公有制经济就慢慢地缩小,实际上,所有制结构也就更加开放了。我们要参加国际分工,参加国际竞争,需要我们的所有制问题放开,但不一定全部照搬欧美国家那套,而是在自己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改进。
所有制改革不仅涉及国有资产,我们也要让私有制经济合理合法。以前7~8个人以下就叫个体户、小业主,7~8个人以上就叫私人企业、资本家。经过快速发展,个体户几百人、上千人都有了,却没有合法身份,企业负责人都成了“资本家”。怎么办?他们就只能找个国有企业或者军队挂靠。我来了深圳以后,当时传来消息,说国家要把标准放宽一点,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没有了消息。我们就想另外的途径。1987年2月,我们深圳出台了《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哪怕你不是科技人员,沾一点边都可以,带点科技味道的,有技术含量的都算科技企业。我们不要求他到工商局去登记,直接到科技局来登记。这个红头文件一出,一两个月之内,一批全国各地来的科技人才创办了上百个民间科技企业。华为是怎么来的?就是那一批人在这个时候登记的。他们既不是大的私人企业,又不是个体户,我就理直气壮允许他们发展,我这也是搞科技嘛!在中国,如果戴着资本家这顶帽子,压力是很大的。现在华为的规模达到了17万人,成为全世界著名的民营科技企业。任正非现在还说,当年就是依靠那个红头文件发展起来的。因此从这方面来讲,所有制结构改革,实际上反映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这对于当时城市的经济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笔。
应该坚持以什么理论来指导自己
一个研究机构,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智库,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自己。现在社会上对于这个问题讲得少,讲得不够。比如90年代初我到全国人大的时候,搞改革、搞立法,有些同志就说搞那么复杂干嘛,一切恢复到50年代就什么都好了。但问题是,一个社会阶段过渡到另一个社会阶段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我记得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篇文章中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阶段”。从实际的历史情况来看,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没有阶级,没有生产工具,每个人都以打猎为生,谋生条件很差,只够养活自己。一个部落打赢了另一部落,就把俘虏吃掉,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生产力,不能生产更多的剩余,俘虏反而是个累赘。慢慢地,经过不断的发展,有了新的生产工具,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生产资料也有剩余了,社会就开始分化,出现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这才进入奴隶社会阶段。奴隶社会依次过渡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后才是共产主义社会阶段。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我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企图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革命阶段并作一步走,一举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不是很快就碰得头破血流吗?而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了当时的基本国情,认为中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还是重要的民主革命力量,我们既要把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制度推翻,也要积极利用资产阶级这一民主革命力量,领导并推动它的发展。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成功取得政权后,通过和平赎买、公私合营的方式对所有的官僚资产阶级的资本和民族私营资本进行改造,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但是我国仍然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阶段,因而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判断。同时党内还有一种思潮,有些同志认为可以加速经济建设的速度,提前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于是出现了盲目地不切实际地发展经济的问题,以致发生了沉痛的教训,这个教训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后期。90年代的时候,民营经济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资本家越来越多,资本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当时就有一些同志发牢骚说,这叫什么社会主义嘛!我觉得他们的思想还不是很开放,我们真地能够把民营经济消灭,全部回到公有制经济吗?
所以,我始终坚持,看待社会的发展阶段,最终还是要看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否相适应。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上来,掌握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这样才能更好地观察和解释中国社会各个阶段的各种现象,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趋势。
(作者系综合开发研究院名誉理事长;摘自《开放导报》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