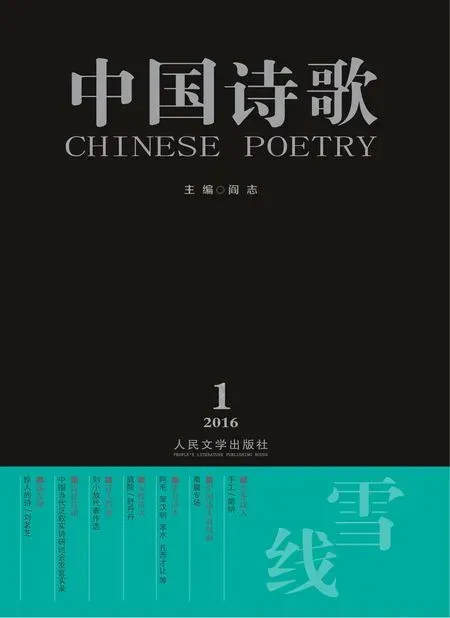自明的“还乡者”
——读《刘小放诗选》
2016-11-26陈超
陈 超
自明的“还乡者”
——读《刘小放诗选》
陈 超
由于对“现代性”在诗歌中的意指存在不充分的理解,吟述“大地”、展露“还乡者”情怀的现代诗经常受到“缺乏现代性”的指责。在当代汉语诗歌的语境当中,这种指责渐渐变为一种“透支”的创造力形态优势——似乎有那些处理现代都市、大工业、科技以及由此衍生的人文话语的诗歌,才有资格进入“现代诗”的畛域。这是对“现代性”的盲视。反观世界范围内的现代诗潮,其中有一条显豁的线索,即在一个高度机械化、商品化、科技图腾、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时代,诗人们倔强地捍卫着人与“大地”的亲缘,并以此间接地发出对异化生存境遇的反思和批判之声。弗罗斯特、叶芝、里尔克、佩斯、杰佛斯、帕斯捷尔纳克、叶赛宁、聂鲁达、艾青、苏金伞、昌耀、帕斯、埃利蒂斯、希尼、伯莱、斯奈德、狄兰·托马斯、蒙塔莱、特朗斯特罗姆、鲁勃佐夫、沃尔科特、海子、张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获具了其更内在的现代性。
在我看来,新乡土诗人刘小放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已自觉地使自己的诗歌语境摆脱了简单的地缘风情画和家族记忆“本事”,而置入了更开阔的人类文化乡愁——对家园意识的追寻和命名中。从诗学谱系上,他与上述诗人有着隐喻意义上的“家族相似性”。也只有从这个谱系看过去,我们才能对他的诗歌做出恰当而有效的衡估。《刘小放诗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是诗人八十年代中期至今诗歌创作的精选本,在此我们得以领略他创造的复归大地和生命本源的“还乡者”的道路,得以看到那些被都市化浪潮所忽略和贬低的细小的乡村事物重放光华。他将个人内心生活的激流和具体历史语境的真实性融合为一体,唱出了既“古老”又“现代”的自明的还乡之歌。海德格尔在论述荷尔德林诗歌中的“还乡”母题时尝言:“惟有这样的人方可还乡:他早已而且许久以来一直在他乡流浪,备尝漫游的艰辛,现在又归根返本。因为他在异地已经领悟到求索之物的本性,因而还乡时得以有足够的丰富体悟和阅历。”海德格尔的话意在陈明这样的意思:对于诗人和思者而言,真正有效的“还乡”,必以精神的广阔漫游为前提。如果没有在“异地”的噬心体验,没有对生存和生命的反思,你的“还乡”,不过是简单和独断的恋土情结所致。刘小放早期诗作,多是由自发的恋土情结所导致。它们聚焦于故乡生活的具体细节,以准确的观察和描述,表达诗人在回忆往事时的怅惘或惊喜。而进入八十年代中后期,诗人的创作由“自发”进入了“自觉”阶段,“土地”、“家园”、“故乡”在他的诗中已超越了其狭隘的具体性,而成为一种灵魂家园的象征,一种带有超验感的人类生命意志的图式。在它们之后,有一个受到质询的巨大的历史背景,即人类对大地的遗忘,对顽健的生命力的自我闭抑,对清苦、付出而纯洁的道义感的讥嘲。如果追求现代性带来的就是这些,那么诗人的质询就犀利地插入了我们心灵最晦涩、最无告的角隅,并要求一个答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小放的“还乡”背景才具有了更为深厚的吟述,也就于波澜不惊中体现了诗人对当代人精神和生命力下滑的忧思、批判。
且以《血酒》一辑为例。辑中收入了诗人近期创作的“大地块垒”系列。这里的“块垒”含有复义性。一方面它是对块垒峥嵘、葳蕤起伏的土地的歌赞,对大地之子们生命强力的命名另一方面,“块垒”又有心事郁结、时代忧患的含义。所谓借往昔之“血酒”,浇今日之块垒是也。在这里,我们听到诗人竟让一只粗瓷大碗发出了金击玉振的声音:“那是一副铁钳子似的粗手/不知在太阳地里经过多少次淬砺/手指节都磨成榆木疙瘩/两手空空/却缀满金黄的老茧的铜钱//这样的手/才能端起那大碗”。写碗是为了写人,粗粝的碗具上,浓缩着对人生命力的隐喻。为了与孱弱的享乐主义时代比照,诗人选择了这个与口腹相关的日常器物的意象,挖掘出它博大的内涵。清贫的年代,一碗红薯稀粥,一碗泥鳅梭鱼,一碗菜汤,一碗井拔凉水,滋养了多少苦难大地的孩子;而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境遇获得改变的时候,是否有一些珍贵的生命意志和品质,也随之离去了呢?诗人无意于歌颂清贫,他只是借此表达对当下生命意志阙如的关怀。犹如梵高从对一只破烂的“农鞋”的审美描绘中揭示了人类生存的“劬老功烈”一样,诗人也从乡村生活的“端大碗”、“赶大车”、“砸大夯”、“挖大河”、“开大荒”中,发现了人类肉体和灵魂的“脊梁”应有的载力和韧度。在世纪末“向前看”的诗歌语境中,刘小放诗歌文本的溯源甚至“怀旧”,反而使我们获得了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深度感。他不是以自诩的“精神家园守望者”的形象来启蒙或训诫众人,而是沉静地述说,平等地沟通和对话。他的音质是重浊的,但没有怨痛。他显然已预感到这种回溯的姿态有可能被某些盲视者判为“非现代话语”,但他更知道,不是艺术的题材而是诗人对题材的领悟力、穿透力,决定着作品是否具有现代性。因此,他始终对自己的艺术道路持有足够的信心,这个自明的“还乡者”从古老的题材里发现了人们未曾领教的现代性。
对土地和农耕文明的依恋,一直是乡土诗的重要特征。但是,如果深入细辨,我们就会发现乡土诗人之间巨大的差异性。我认为,新时期以来,现代乡土诗从文脉上可分为三类:其一是遣兴式的“田园乌托邦”歌者。这种诗人虚构了一种潇洒出尘的田园乌托邦,作为自己精神的静养之地,而对现实的生存和生命状态缺乏起码的介入和敏识。其二是经由对“土地——天空”维度的吟述,体现诗人高蹈的、升华的所谓“终极关怀”,以对抗现代工业霸权和物质放纵主义。这种诗人将超越的动力,建置在虚幻的生命玄学上,诗中频频出现的“圣词”告诉我们,他们缺乏起码的“世俗关怀”。这样,其“终极关怀”就是可疑的了。其三是面对具体生存语境的复杂性,以乡村生活为想象力原型,进而在表象的、细节的描述,和整体历史的、本质的象征之间达成深度平衡,使诗歌承纳揭示生存的力量。
我想说,刘小放的诗歌就属于第三类。长诗《大地之子》不但是诗人、也是汉语乡土诗的重要收获,被公刘先生赞誉为“生命之绝唱,乡土之离骚”。这首诗由十大部分组成,完整体现了诗人对生命意志、种族精神历史、大地的真义及幻象世界的综合命名能力。刘小放并没有在普遍意义上的“地母——感恩”主题中循行,他倾心的是人与土地彼此塑造,斗争,同时改变自身精神结构的过程。《蝗祸》、《酷夏》、《铁血的扁担》、《我不敢凝视那飞扬的芦花》、《地母呵》,以及短诗《马贼之死》、《大草洼》等,都将具体的情境描述最终猛然扩展在巨大的历史视屏中,仿佛诗中的细枝末节也都焕发出了诡异而尖利的生存光芒。这个“还乡者”,给我们带来的不是安恬,而是大地漩流着的元气、人在生死考验前迸涌出的活力。它在拷问并启示着我们:强大的生命力的欢乐,是敢于和生存的痛苦、灾难相抗衡的结果。生命的充实与其说是靠物质的富足,毋宁说更要依赖于活的血性、道义担待、求真意志的持续冲涌。这是在我们所有的“现代”经验中的一条被忽视乃至否弃已久的经验,诗人以审美的骄傲为之做了直指人心的命名。至此,诗人笔下的“还乡”,就成为对人原始生命力的唤起和回归,它是一切的“本原”、“基础”、“核心”,是不断更新顿起的恒久力量。
从这部诗选中,我们同时会看到这个自明的“还乡者”在语言意识和具体技术环节上的变化。如果说他前期的创作是依恃于单一的抒情性,那么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他已进入了复杂经验的聚合状态。这部诗选共分六辑,“血酒”,“地气”,“土窑”,“情根”,“圣焰”,“石魂”。这不仅仅是基于题材的划分,从情理逻辑上,它们更有着明显的意向递进性。在这里没有机巧的炫耀,没有心智的假象,诗人生命体验的独特“纹理”都嵌入到了明快、鲜润而又硬实的诗行中。我们在此看到了于烈火和坚冰中轮回的精神,也领略了现代乡土诗那“古老”而崭新的话语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