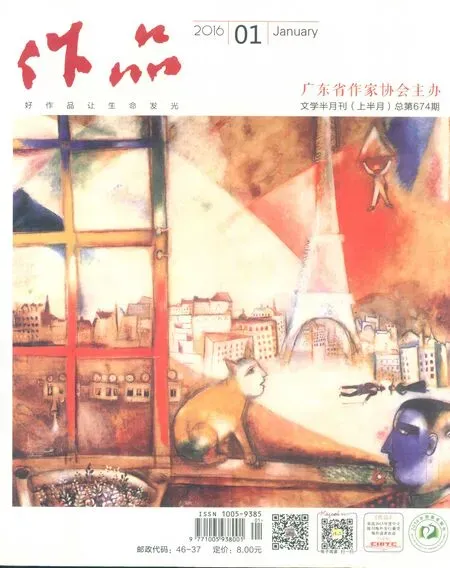鬼 火
2016-11-26范墩子
文/范墩子(男)
鬼 火
文/范墩子(男)
范墩子男,1992年7月2日生,陕西永寿人。中短篇小说见《山东文学》、《 延河》、《 满族文学》、《 辽河》、《 西部》、《 黄河文学》、《 青年作家》、《 北方文学》等期刊。现居杨凌。
院子里很安静,除了有风在吹打外,再无其它的声音。我很失望,各种难言的情绪汇聚一起然后从我的身体内部汩汩涌出来,我的眼睛一潮,眼泪便掉了下来。我已经找遍了所有的屋子,寻便了整个村子,也没有发现任何消息。我已尽了我最大的努力,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发现任何线索了。我的确有些悲观,但我没有办法从悲观的情绪中逃离出来。我搜遍了所有可以搜寻的东西,连厨房墙角里的老鼠洞我都挖进了三尺,可等待而来的全是徒劳的结果。我似乎陷入了某种追踪的过程,沉重的双腿被黑色的重压紧紧包裹着,我的脑子里漆黑一片,但我还是要向四处张望,生怕错过了某些重要的线索,然而我仅仅闻到了桐树叶子的臭味儿,仅仅听到了风吹的声响。那些紧张的、慌乱的情绪时时刻刻都有可能跳出来,它们在聚集着更大的能量,试图在某个特殊的时刻里全部爆发出来。
这是上个月的事情,是的,我的父亲丢了,我不想在此用失踪一词,对这个词,我既感到恐惧,又报以无限的唾弃。我相信我的父亲只是暂时走丢了,他一定会回来的,母亲还在家里,我也在,他的乖孙子也在,父亲有什么理由不回来呢?我跪在后院那块被父亲栽满了柴胡的土堆上,看着那些有点干黄的柴胡,我的心里再次难受了起来。这是父亲花了很多的时间才栽好的,那些天他每天都要去沟里挖药,专挖柴胡,他将它们挖回来后就栽在后院的土堆上,然后在每株柴胡跟前浇上一点水,他没事的时候就蹲坐在后院里,出去转悠的时间很少。有时候我想,父亲在土地里刨了一辈子,现在年龄大了终于不用做活了,他应该和那些和他年龄差不多的老人一样出去晒晒太阳呀,总之不应该干这么奇怪的事情。
可父亲一直这样,我始终不能够理解。父亲成了我们村里的怪人,那些和他年纪相仿的老人提到我的父亲时,总会嗤笑着说:嗨,真是个怪家伙。起初,父亲的怪行为在村子里到处被议论,仿佛这个话题没有尽头,比如有人正坐在门前无聊的抠脚指甲,而旁边有人突然提起了我父亲的怪异行为,这时他们可能会兴致勃勃地谈论一整个下午。我没有危言耸听,那段时间,的确是这个样子。可后来时间长了,有关父亲的话题可能被大家说得舌头上都生出了茧子,人们不再关心我父亲的一举一动,不再关心有关我父亲的任何事情,我也为此松了一口气,起码少掉了很多的尴尬。这种尴尬里既裹挟着一些失望情绪,又掺杂着无尽的羞耻之情。
每到这个时候,我总会通红着脸看着周围的每个人,然后转过身急速地走掉。我知道他们肯定在盯着我黑瘦的背影,如同看着一个怪物,就好像父亲的怪异行为也必然会发生在我身上一样,这一点是我早已发现了的。有关父亲为何喜欢挖柴胡回来栽在后院里的原因,我也一直在想,但我始终没有想明白,父亲这一举措颠覆了我的惯常思维,说明白点,你会觉得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小孩子的身上,大人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呢?何况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那些柴胡还活着,父亲不在家的这些天,我每天会给它们浇一点水,父亲在家时,我从没有干过。说真的,我想念父亲了,他在家时,一切都显得很正常,而他丢了的时候,我心中总会生出一种空落落的感觉。
我注视着这些长势旺盛的柴胡,它们那些细小的叶子紧紧贴在地皮上,风偶尔会吹动它们的影子,周围有几只蚂蚁跑了出来,顺着它们的足迹,我看到了那口隐藏在某片柴胡叶子下面的蚂蚁洞,我甚至生出了父亲会从那里爬出来的想法,这是多么滑稽可笑,我猛地将目光收了回来。我真想不出父亲如果此刻现身出来的样子,灰头土脸?或者穿一身破旧的衣服,头上沾满了荒草?我猜不出来。而就在我一直凝聚目光的过程中,某个瞬间里,我竟然真的看见了他,他的身影很小,脸色暗黄,鬓角上的头发已经变白了,他朝着柴胡叶子下面走了进去,我慌忙地伸出了一只手去拦他,他却已经消失了。我想,可能刚才我是出现了短暂的幻觉。
我还能想起以前的很多事情,那时候我只有四五岁,父亲经常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卖柿子,他装满一架子车柿子,凌晨两点多就出发了。有次,我非要跟着他一起去,父亲对我说,路太远,爸走长途呢,你咋跟得上?我见父亲一点没有带我要去的意思,哇哇大哭起来,边哭边说,我坐在架子车上,你拉我去。父亲皱皱眉头,看了看我母亲,母亲想了会儿对父亲说,他非要去那你带他去一回吧。父亲看着我,嘴角露出一丝笑容说,看你娘的面子上,就带你去一回。怎么说呢,那确实是一次很难忘的经历,我坐在架子车上,父亲拉着车子缓慢地走着,边走边和我说话,他大多说一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话,比如他说,柿子价钱也不好,种酸枣都比这强,娃多日子苦哇,二娃你睡着了没?我怎么可能睡着呢?这可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兴奋的情绪始终缠绕着我,我大声地说,没。
那时还没有修柏油路,土路上到处都是坑坑洼洼。路很远,要翻两条大沟,全是弯弯曲曲的S型路线,我最终还是被那无尽的困意给席卷,半道上,记得是在下沟的时候,因为我睡得太死,架子车在经过一个小坑时猛地晃了一下,把我从车子上摇了下来。父亲竟然没有发现,如果不是我哇哇大哭的声音,他也许不会觉察到我从车上掉了下来。父亲吓得脸色铁青,嘴唇都紫了,我还在大哭,鼻涕眼泪一起往下流。父亲大声说,二娃,二娃,你好着么?好着么?我只是哭,不说话。父亲将我抱在怀里,给我揉腿揉胳膊,拍了拍我衣服上的土,我隐隐看见他的嘴唇不住地在抖动着,他说,二娃,你走走,看能走不?我住了哭声,父亲将我放在地上,我走了几步,能走,也能跑。父亲突然笑了。他再次问我,身上疼不?我说,不疼,他长舒一口气,然后哈哈笑着说,真是个铁娃。
你猜后面怎么着?连我也没有想到,我的父亲是如此的生气,他把架子车拉到沟边,然后将后面的箱板卸下来,再抬起车杆,柿子们就像一个又一个欢快的娃儿从车箱里跑了出来,那些柿子最终都被我父亲倒在了沟里。我站在旁边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始终用迷茫的眼神盯着父亲的脸,他的脸起初是铁青色,后来慢慢舒展开来,而且微微有了些笑容。父亲倒完了柿子然后将我揽在怀里说,要是今天把我娃摔得怎么了,让俺咋活啊?父亲说到深情处,眼泪竟然掉了下来。我说,爸,那你把柿子倒了,咱回去咋给俺娘交代?父亲说,只要我娃好着就行。这的确是一次让我永生难忘的记忆,每次想到这里,我都会格外想念我父亲,可他已经丢了一月多了,我们还没有找到他的下落,我怎么能不着急呢?我的眼眶有些潮湿。我的耳际隐隐传来了父亲的声音,那声音接连响着,不绝于耳,我闭上眼睛的时候,那些声音会越来越大,如同一群发魔的黑色蚂蚁。
也不知道父亲是否还会记起那次卖柿子的经历,也许他早忘了他曾往沟里倒了满满一架子车的柿子。我走进父亲住过的屋子,他一直和母亲分开睡,具体是什么时候,我也记不清楚了。屋子里漆黑一片,四处散发着一股浓郁的怪味儿,我说不上这是一种什么味道,我记着我也曾在其他老人的屋子闻到过,难道这是老了的味道?我拉开了灯,灯泡瞬间散出阴暗的、黄色的光亮,它给整个空间涂抹上了一层梦幻的感觉,让我觉得这间屋子极为不真实。我凝视着父亲一直在使用着的木柜子,据说这是爷爷留下来的,我企图从这个柜子上得到某些和父亲的踪迹有关的启示,我走到柜子跟前,然后缓缓打开了柜子,里面除了一些衣服外再没有其他的东西,我摸着这扇散发着古朴气息的柜板,分明感受到了父亲的气息,感受到了他身上那浓郁的汗味。
我不清楚这种飘然而至的感觉来自哪里,它或许来自墙壁上的红砖里,是对我父亲的存在的另外一种诠释,我无法具体捕捉到它,但当我紧闭双目的时候,我就会感受到父亲的存在,父亲啊,你分明就在我跟前,可我为何不能看到你?从这层关系来看,似乎我们的关系总是有着些许牵连的,可能很细微,但隐隐存在记忆当中。当我坐在父亲睡过的炕上时,那些熟悉的气息就更加浓郁了,争抢着从另外一个空间里飘散出来,而时间呢,就这样紧固在了沉厚的空气里,如同无数个细小的虫子。我这样说或许有些深奥,但这种感觉是真实的,因为我抓住了某个瞬间,抓住了与父亲有关的各种物件,那是父亲留在我脑海里的记忆啊。我打量着那个蹲在地上的火炉,它还是老样子,没有一点儿变化,然而当我细看或者说一直盯着看的时候,我发现它还是有着些许细微的差别。
二娃,二娃。母亲的声音将我从过往的记忆中拉了回来。
妈,怎么了?我说。
你在这干啥哩?母亲问我。
没干啥,看看我爸。我说。
哦。
你爸找见了。母亲轻轻说。
什么?我连忙下了炕。
你爸找见了。母亲再次说道。
在哪里?我问。我的心脏狂跳了起来。
南沟。
南沟?
就是你爷的坟地那块。
谁见了?
麻牛。
啥时候见的?
上午,麻牛放羊见的。
哦。
我爸咋跑那去了?我说。
鬼知道。
我和母亲边说边往出走,我不时侧着头看母亲,她的表情有些冷,也可以说没有表情。我猜不透母亲现在在想些什么,按常理来说好些时间不见父亲了她应该有些着急才对,可我并没有从她身上发现一点儿紧张的、焦急的情绪。我突然意识到很长时间已没有跟母亲好好聊过了,上次坐在一起聊天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我想至少也有两三年了吧,平时也就偶尔说两句罢了,想起这些,心里真不是个滋味。记得我上学的那时,母亲每天都要早起为我熬粥煮鸡蛋,放假回来我总会和母亲一起坐在炕上聊东聊西,我给母亲讲述我在学校所见到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有时母亲会被我逗得咯咯笑起来。但毕竟过去那么久了。我再次微微斜着目光看母亲,母亲的头发已经花白了,腰也佝偻了起来,她微微喘息着,我们走得急,母亲似乎有些赶不上我的脚步。我说,妈,休息会吧。母亲回过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明显有责怪的意思,她说,你爸在山上呢,我还能走慢?我咯咯笑了出来。我笑是因为母亲原来也在心里挂记着父亲呢,我说,妈,你想我爸不?我有点后悔说出了这句话,毕竟在母亲跟前说出这样一句话,我还是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可没想到的是母亲很随意地说,死老头子就知道乱跑。
母亲心里在想什么我是没法猜透的。等我和母亲赶到南沟里的时候,已是下午两点了,沟里路陡,加上到处都是荒草,我和母亲便走得很慢。这些年很少有人下沟了,不像我小时候,我们那时候的孩子都是在沟里野大的,现在谁家的孩子还去沟里?都在幼儿园里呢,就是去了沟里回来也必得被父母揍一顿。因为人来得少,草就盛,到处都是虚土,稍没踩好,可能就会掉进沟里,我扶着母亲的胳膊小心翼翼地往下走,南沟就是这块了,但我爷爷的坟还在对面的沟坡上呢,也就是说我必须和母亲先下沟,然后接着上沟才能到,母亲老了,走起路来颤颤巍巍,我必须走得慢点,必须将母亲扶好,我说,妈,行不?母亲没抬头说,有啥不行的?年轻的时候我能从这跑下去。我笑了两声,母亲的手很粗糙,胳膊细得跟家里的火棍差不多了,哪里还有肉,净皮包骨头,我扶着母亲,心里起起伏伏的,母亲每次的晃悠,都会轻轻传进我的心里,然后引起巨大的阵痛。
上沟费了不少气力,母亲气喘吁吁地说,老啦老啦,走不动了哇。我说,妈,你年轻着呢。母亲笑笑,然后说,被你那鬼爸快气死了。我沉默,没有说话。坡上埋人那块柏树很多,老远看绿压压一片,跟用绿漆刷过一遍一样,还没走到我就大声喊,爸,爸。我母亲拽了一下我的胳膊说,喊那个死鬼干啥,他死不了。我觉得母亲这话里隐藏着某些锋利的东西,但我说不清,我想不通为啥母亲这么恨父亲呢,她难道一点也不担心父亲吗?我和母亲走到坟场跟前后,一群黑老鸹从柏树林里飞了出来,黑压压一大片,母亲吓得使劲往空中吐唾沫,我说你这是干啥?母亲说,辟邪哩,这东西可不吉利。我隐隐感觉此地有些恐怖,那些柏树粗壮得很,简直快插进了云霄,记得小时候父亲常给我讲世上是有鬼的,鬼都住在南沟的柏树林里。
现在有风吹起,柏树便摇晃起来,隐隐约约,影影绰绰,似有野狼穿过,我心里不禁暗暗紧张了起来,我看了看母亲,母亲却丝毫没有一点恐惧的样子,我便也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我可不想让母亲觉得我这么大的人了还害怕鬼呀啥的。我和母亲走了进去,两旁不时发出沙沙的响声。我和母亲都知道爷爷的坟的位置,我俩踩着那些厚厚的荒草朝里面走了进去。但我和母亲没有在爷爷坟的周围找到父亲,我对母亲说,麻牛不会哄咱吧?母亲犹豫了片刻说,不可能,麻牛说他看得清清的。母亲又在四周转了转,然后他喊我过来,我过去后,母亲指着一堆白酒瓶子对我说,这不是你那鬼爸喝的还是谁喝的?他肯定就在这儿呢。我同意母亲的说法,这些酒瓶子肯定都是父亲留下的,旁边还有烟头呢,而且那些烟头看起来都是新近留下的,不是父亲还能有谁来这个地方?
就在我这样推断的时候,母亲突然朝着爷爷坟跟前的柏树上大喊了一声,死东西,有本事你下来!
我朝着母亲喊的方向看了看,并没有看见父亲,但母亲怎么看见了呢?我说,妈,哪里有我爸呀?
母亲有些生气地说,死鬼拿树叶把他遮着呢。
我又看了看,经母亲这么一说,我确实发现树上那块有些奇怪,显然那儿叶子比周围稠密呢。我叫了声,爸!
没有人回答。
母亲说,有本事你出来,隐着藏着算啥本事?
爸,你出来吧。我说。
滚出来。母亲说。
妈,你,你这样吓着我爸了呢。我对母亲说。
吓着?他也知道吓着?母亲说得脖子上的青筋都暴了起来。
我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不知道母亲对父亲为什么这么尖锐,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吗?
父亲还是没有出来,看起来他也并未被母亲的话激怒。
爸,求你了,你下来这吧,你这样让我和妈真的很担心呢。我声音很小,几乎带着哭腔了。
树上还是没有动静。
你这样那个死鬼不会下来的。母亲忿忿地说。
老鬼,有本事你下来,蹲在树上你不怕被黑老鸹吃了哇?俺知道你没忘那事,俺知道你心里过不去,你在心里堵了几十年了,我也不会原谅你的,你个老鬼,但你这样蹲在树上让儿娃挂记呢知道不?要不是念在儿娃,我才管球你呢,你爱蹲在哪蹲在哪。母亲越说越激动,以至于嘴角上都沾满了白沫。
我看了一眼母亲,然后拉长着音说了声,妈!
母亲没有理我,继续说,老鬼啊,多少年了,你知道我心里有多恨你?你可知道?
我朝着树上看了一眼,除了风吹得树叶微微晃动外,并无其他的动静。
其实有时候我也不去想这些事了,毕竟时间过去了多少年了,儿娃都多大了,孙子都多大了哇,可你现在这样,老是跑出去不回来,算个啥子哇?
我听出了母亲的话里有话。我很想知道母亲不再去想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什么事情让他俩如此耿耿于怀,以至于到现在还无法忘记?
妈,你说的是啥事?我朝着母亲说。
你问那个死鬼!让他自己说。母亲愤怒地说。
我转头看树上,树叶还在微微摆动,偶尔有只老鸹从茂密的树丛里飞出来。我说,爸,究竟是啥事哇?
除了风吹树响的声音,一点儿动静都没有。
那个死鬼不敢说,他在肚子里憋着呢。母亲接着说。
啥呀?我有些着急了。
母亲佝偻着腰身,手里拿着一根柴棍子,不停地在草丛里拨拉着,他拨拉一会儿,又抬头看看树上的父亲。
妈。我说。
怎么了?母亲微微抬头看我。
我爸,我爸……他怎……么了?
老鬼还能咋?
你讲讲呗。我说。
忽地,四处升起一股股的烟雾,然后弥漫在四野,随着风的吹拂,它们愈加浓重厚实,似乎即将要将这块地方包围起来。旁边的塄坎下面,有野兔正在拼命地刨着窝儿,蛐蛐们狂乱地叫着,那些声音,汇聚在一起便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向着父亲藏身的这棵柏树上拥挤,柏树哗啦啦地摇响,树叶一片接一片掉了下来,地上的树叶显得更厚,整个坟地里便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气氛。我闭上了眼睛感受这种奇怪的力量,我感到我的背后站着一个黑色的幽灵。我缓缓睁开了眼睛,抬头看柏树,啊,柏树上的叶子竟然掉光了,全部落在了地上。树上并没有父亲,空荡荡的,只有树干突兀着,活似一截毫无生气的木乃伊。
妈,我,我爸他?我说。
母亲站在原地,目光四处游离。我看她的手背微微发颤,白色的头发在风中孤独地飘展着。
他走了。母亲说。
哦。我轻轻摇了摇头。
一颗浑浊的眼泪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四十年前他就走了。这句话母亲说得极轻,仿佛一直在空气中飘着,飘着。
是的,我没见过他。
你不会见的。
为什么?
……
妈。
啊……母亲突然扬起了头,看着那棵死沉沉的柏树。
怎么?
他斗死了我的父亲。母亲的声音极小,若不是刚才的那股风吹过来,我是不会听到母亲所说的话的。
谁?
你的外爷。
哦。
母亲回去了。剩下我一人站在爷爷的荒坟跟前,其实是我外爷的坟。我的爷爷埋在另外一个地方,具体是因为什么,我也不清楚。天很快就黑了,我在那棵掉光了树叶的柏树跟前坐了下来,我对着立在我对面的黑老鸹说,你是谁?是我爸变的吗?黑老鸹呱呱两声,好像明白了我所说的,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听明白,我一气之下,捡起一颗碎石头朝着它扔了过去,黑老鸹惊慌地飞走了,看着它远去的黑影子,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林子里风声紧,不时传出呜呜咽咽的声音,似鬼吹灯的声音。你知道鬼吹灯的声音吗?你应该不知道,其实我也不知道,正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才可以将其命为鬼吹灯的声音。它至少是隐蔽的,黑色的,一般人无法接近的暗色物质。我躺了下来,我想想父亲应该此刻睡着了吧,他正睡在大地深处,我隐隐地听到了他那既熟悉又陌生的呼噜声,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然而我认识他,我知道这并不矛盾。正如月亮,我并没有摸过它,但我却认识月亮。而这个时候,天空黑漆漆一片,四周静悄悄的,偶尔会传来野鸟野虫的叫声,它们或长或短,或大或小,一起钻进我的耳朵里,弄得我的耳根处痒酥酥的,我用手一摸,哎呀,竟有液体,我估计是我的耳朵化脓了,但它是什么时候破了的呢?
这时候,一团跳动着蓝光的火焰从旁边的坟头上面升了起来,周围的烟雾更加厚重,天空漆黑一片。它悬在坟头上面,微微闪光,像一颗剧烈跳动的心脏一样,时而膨胀,时而紧缩。我清楚这就是鬼火,传说中可以吓死人的鬼火,它慢慢在移动,然后像一只胆怯的耗子一样缓缓移动到了爷爷坟头上面,它跳动的频率愈来愈快了,好像谁掐住了它的喉咙,那棵高大的柏树的枝干插入云霄,空气向四周蔓延了起来,地皮微微颤动,那些藏身的老鼠呀臭虫呀野虫子呀都跑了出来朝着远处的方向逃走了,似乎此地即将要上演一场灾难。我的心脏一直悬在嗓子眼,说实话我也害怕。
过了不久,我便听到了呜呜咽咽的哭诉说,那些声音续续断断,起起伏伏,仿佛来自地面下面,又似乎来自空气的隐秘处,我循着它的源头,一点一点努力判断,最后我肯定那些奇怪的声音就隐在那团蓝色的跳动的鬼火里。所有的树木都开始哆嗦起来,所有的气流都凝固了,我大气不敢出一声,手里紧紧抓着一根桃木棍子。就这样大概一直持续到了后半夜,那些声音才渐渐弱了下来,直至渐渐消失在了空气尽头,当然,那团鬼火也返回了原地,消失在了旁边的坟头里。
后来,我还去南沟找过父亲,母亲也跟我去过几次,但每次她都早早地就回去了。而我呢,仍然如以往那般见证着那个怪异的场景,听着那些呜呜咽咽的怪吓人的声音,自然,听久了,也不怎么害怕了。我并没有找见父亲,他或许躺在爷爷坟头旁边的那个荒冢里,谁晓得呢。
(责编:郑小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