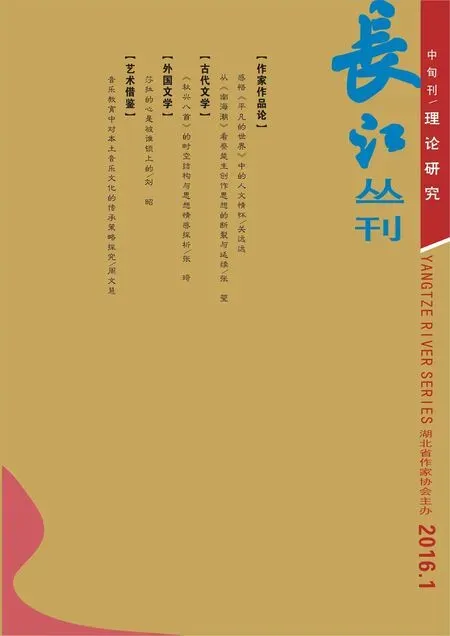家谱叙事话语的直义行为
——以河洛地区若干家谱为例
2016-11-26王忠田
王忠田
家谱叙事话语的直义行为
——以河洛地区若干家谱为例
王忠田
【摘 要】医疗过失是引起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主要因素,也是导致医患关系紧张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原因,因此有必要对医疗过失的认定进行研究,推进医疗行为的合理化、规范化,从根源上减少医疗过 失的形成。本文将采用运用比较法和归纳演绎法讨对医疗过失认定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其中包括医疗 过失的内涵、特点、类别、认定标准及影响因素。
【关键词】医疗过失 注意义务 认定标准
家谱作为国家历史的三大来源(正史、方志与家谱)之一,其研究涉及众多学科,已有成果基本是从社会学、档案学、文献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图书馆学等方面进行研究的,真正运用叙事学研究家谱的学术论文在中国学术期刊网上还没有发现,这里就从叙事学角度来简单论析家谱叙事话语的特点。修撰者在借助叙述者对话语进行精心建构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也无法回避其自身的主观性与倾向性。在面对文本与宗族史、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时,其本身既是对宗族生活与宗族事件的阐释,同时也是对本宗族文化内涵的呈现与描述,这样,文本必然是主客观统一体的话语实践,在话语大量直义之下,离不开转义的话语形态。在家谱中,从叙事学角度讲,直义最为基本的含义是直陈其事,转义最基本的含义是隐陈其事。论析家谱叙事话语的特征,主要从两个层面入手,一是话语表现具体叙事对象层面,这一层面用话语直接描写、叙述一个对象的行为,就是直义行为;而通过特殊的手法,如象征、拟人、隐喻、双关、暗示、反讽等等手法来叙述描写对象的行为,就是转义行为。因此,在用话语叙述对象这个层面,家谱的叙事应该主要是直义性为主,而转义性为辅的。二是通过宗族历史与人物的叙述表达特定宗族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层面,这一层面则主要是转义性的。因为,特定宗族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一般不会直接全面地表述在叙事这个层面,或者说形象这个层面。家谱要通过塑造宗族历史和人物这个形象世界来隐晦地表达特定宗族文化和意识形态观念,在这个层面上,两者的关系主要是一种转义关系。修撰者在编纂时,以自身的意识形态影响着叙事文本,赋予本宗族有关事件的思想以不同的情感价值,他们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指示的事物或事件,更重要的是要让本宗族成员回想起事物所指的形象或事件所隐含的意义,因此,家谱文本具有较多的叙事比喻性话语。论文试图从话语表现具体叙事对象层面与宗族历史与人物的叙述表达特定宗族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层面这两个层面入手,以此为纬,以宏观叙事体例、中观叙事体例与微观叙事体例为经,分析家谱中叙事体例的直义行为与转义行为。
家谱记载内容十分广泛,主要记述本宗族姓氏源流、播迁状况、世系图表、人物传记、宗族风俗、祠堂坟茔、族规家法、艺文杂志等。根据传统历史的编排,可将最基本的体例归类为史、表、图、志、传、文共六种叙事体例。其中史包括谱序、姓氏源流、宗族播迁等;表主要包括世系世传等;图包括祖先像、祠堂图、祭祀器物图、住宅图、播迁图、坟茔图、书院图等;志包括祠堂志、讲堂志、碑记等;传主要包括人物传记等;文包括诗文、像赞、族规、字辈排行等。为了叙事分析的需要,再大而化之,可将私修谱牒的叙事体例分为宏观叙事体例,中观叙事体例和微观叙事体例。其中宏观叙事体例主要是表;中观叙事体例主要是宗族史;微观叙事体例主要是图、传、志、文。
叙事话语是家谱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话语是在一个宗族中处于相互交流环境中的个别成员所发出的信息连续体。这是一种运动的话语传递过程,这种运动是辩证的,以话语作为分析目的是要深入探究家谱文本的主题,进一步解析文本叙述者希望该主题表现的个人意图。
一、叙事话语的本质
家谱的叙事话语是指在家谱叙事文本中以宗族社会背景为语境的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的语言沟通活动。修撰者在编纂谱牒叙述宗族史时,根据自己的意识将自己认为可以编纂成故事的宗族史材料按照自己所设想的模式组织起来,以供本宗族成员阅读,这里自己的意识往往由本宗族的文化传统与个人的生存境遇相互融合后而决定的。本宗族成员在阅读的时候会把文本中的故事与自己意识中故事模型进行比较,这里的关键是本宗族成员是否可以确立故事的新模型,不同的人阅读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这样也就形成了叙事话语的不同理解。罗兰·巴尔特认为:“如我们仅仅通过其结构就能看到的,在不诉诸其内容的本质的情况下,历史话语本质上是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阐释。或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想象的阐述,意思是说这是一种‘言语行为’,它在性质上是‘述行的’,通过这种言语行为,话语的说话者(一个纯粹的语言实体)‘填补’了说话主体(一个心理或意识形态主体)的位置。”[1]罗兰·巴尔特从文本的结构出发,认为叙事话语的本质是形式的意识形态阐释,若从文化叙事学的角度分析,叙事话语本质是阐释宗族文化内涵,意识形态是最主要的方面。
家谱的叙事话语至少有三层次意义,第一层是进入宗族史叙事中的宗族历史与人物的原生态资料,相当于俄国形式主义所说的“故事”。即未被特定叙事作品组织的事件的自然时空形态,又称之为“事序结构”。这些进入宗族史叙事中的宗族历史与人物的原生态资料主要存在于用话语表现具体叙事对象层面,主要是直义行为。第二层是这些原生态事件在具体作品中的存在形态,即叙事结构或情节。若是直陈其事属于直义,隐陈其事属于转义,这一层次是直义行为与转义行为的结合体。第三层是宗族史的整体的深层意蕴,这些只有通过对作品中“情节”进行还原性处理才可以知道,主要是转义行为。
二、叙事话语的直义行为
在家谱的叙事话语中存在直义行为,这里的直义行为是指存在于一种观念事物运动中的内在关联,在字面意义上只能产生一种意义,在具有相同母语的前提下,只能用一种语言表达,从叙事学角度讲,在用话语表现具体叙事对象这个层面,用话语直接描写、叙述一个对象的行为。
这里的直义行为与历史叙事中的直义行为,既有联系又有有区别,其联系是在话语与形象层面都存在大量的直义行为,区别是在某些地方家谱叙事中的直义行为比历史叙事的直义行为更直接,尤其在作者本身更为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修撰者与历史学家运用原始材料的不同,大多数修撰者对于比较久远的事件或世系等都会完全照搬转录,这在文本篇幅上占有半数之多,这也是家谱具有直义行为的最主要原因,而历史学家在运用原始材料的时候往往会移注自己的主观性,这样会改变原始资料的真实性,虽然也存在大量直义行为,但与家谱相比离客观性就较远一些了;二是历史家所编纂历史文本与家谱的修撰者所编纂的宗族史文本在叙事基本体例与叙事内容大不相同,家谱的叙事体例比历史的叙事体例繁杂的多,比如:族规、字辈排行、像赞、住宅面积、祭器尺寸、坟茔方位等这话语在历史叙事话语中基本看不到,这些叙事话语中大多具有直义行为,这也是家谱具有直义行为的重要原因。因此,直义行为仅对修撰者而言,在这一限制性下,修撰者的直义行为分为自纂直义行为与转纂直义行为两种类型,自纂直义行为是修撰者本人关于本宗族史的客观记载,如宗族世系、祠堂志等中的直义话语;转纂直义行为是修撰者在编纂时客观转载以往本宗族成员撰写的宗族史,如谱序、字辈排行、诗文等中的直义话语。在家谱的宏观叙事体例、中观叙事体例、微观叙事体例中均有直义性。
家谱中的直义是对话语而言,主要指直陈其事的话语;直义行为是对话语叙述对象这一行为而言,主要是指直陈其事的话语行为。直义主要存在于用话语表现具体叙事对象这一层面;直义行为就存在于直接叙述或描绘某一对象的行为中。
(一)宏观叙事体例中的直义行为
宏观叙事体例主要是宗族世系,宗族世系在家谱中占有篇幅最多,将近文本的四分之三。宗族世系的有序连续陈述式文本、有序间断陈述式文本、无序连续陈述式文本与无序间断陈述式文本皆有叙事话语的直义。再细而分析,宗族世系中除了存在世系外还有传记,直义行为是指的单纯的世系图中部分话语,即修撰者在编纂时对本宗族世系的客观记载,主要包括姓名、字号、生辰、婚配、子嗣、葬地。除此之外宗族世系中的传记、故事所运用的比喻、转喻、隐喻、对比等表现手法均属转义。如何得知修撰者没有将自己的主观意识谱录其中呢,在具有相同母语前提下,只有一种语言表达方式,这也不乏判断是否客观记载的一种方法。
宗族世系中的直义行为是自纂直义行为与转纂直义行为的结合体,在宗族世系的话语中,年代越久远的世序,修撰者转纂直义话语越多,年代越近或当代的世序,修撰者自纂直义话语越多。
世系图从宗族的一世祖开始谱载,依世次的延续传承到修撰者编纂谱牒时的世次而止,少则几十代,多则几百代,宋朝以前的世系图,一图几表无准确规范,有的九世一图,有的十世一图,时至范仲淹、苏轼、欧阳修、二程后,在总结前人谱法的基础之上,统一采用五世表为一图,简称五世图法。这一表达形式延续至今,经久不衰。这里的直义话语不包含这五世图法的隐含意义,因为五世图法有着更为深层的文化意蕴。在宗族世系中,世系通过叙事话语,连续性地叙述本宗族上下世代之间的继承关系,通过有序连续陈述式文本、有序间断陈述式文本、无序连续陈述式文本与无序间断陈述式文本以文字、图画、表等形式展现世代更替。在这些形式中,内容涉及姓名与传记,直义的叙事话语主要存在世系中那些只能用一种语言表达的形式。此四类叙事文本中,有序连续陈述式文本谱载的直义话语最多,其原因有二,其一是有序,世代次序明确,在整个世系图结构框架中,直系与旁系清晰明白,无混淆,有利于直义话语的表达客观性;其二是连续,世代之间连续无断代,这样在时间上是一个连续体,有利于对本宗族成员的查找与辨认,这样,直义话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有序间断陈述式文本的直义话语是对直系旁系客观记载,其中世代之间连续部分的直接叙述世系的话语行为属于直义行为,断代中的话语或断代再接话语若是直接陈述世系的话语就是直义,要是婉陈世系的话语就是转义,这是在话语形象层面而言,但是若是通过世系叙述表达特定宗族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就具有转义性了;无序连续陈述式文本中的直义话语是对世代之间的客观记载,直系旁系间清晰的框架记载属于直义行为,在直系旁系混淆或断系的记载中,若是对形象层面直接叙述世系对象这一形象的行为属于直义行为,若是对形象层面隐陈世系对象的这一行为属于转义行为,这些直义或转义背后的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呈示具有转义性;无序间断陈述式文本的直义话语主要存在于无序外有序部分与断代外连续部分的话语中,即便是这样,直义话语的分量也是相当强大,依然可以占据私修谱文本牒篇幅的四分之三。
在《洛宁张村白氏家族历代家谱》的宏观叙事体例宗族世系第一门第一支中记载“二十七代,白永顺,配夏氏,子四,长,生荣;次,生华;三,生富;四,生贵。”[2]这些话语便是直义呈现。直义话语在具体叙述白永顺生命信息的行为便是直义行为,在直义话语中,本宗族成员的姓名、婚配、嫁娶、子嗣、坟茔是世系要点集结处。在《孙氏族谱》宗族世系图中,载有:“第十世,世贵,可久公长子,配王氏,生子二,长,承芳;次,启芳,公卒葬于村东南柏坡坟,西与可观坟为邻。”[3]如此直义话语在宗族世系图中随处可见。
宏观体例宗族世系的直义话语,不但是宗族世系最为主要的构成部分,也是家谱的最为显著且分量最重的部分,也是与历史叙事体例最为不同的呈现。
(二)中观叙事体例中的直义行为
宗族史是家谱的中观叙事体例,在宗族史中,谱序的分量最重,是宗族史最主要的来源,谱序的叙事话语是直义与转义的结合,其中直义话语主要存在于用话语表现谱序中具体叙事对象这一层面,叙事对象主要包括始祖、始迁祖、姓氏源流、住宅、坟茔、祠堂等,这一层面主要就是对这些叙事对象进行直接具体的叙述描绘,同时,对这些具体对象直接叙述描绘的行为属于直义行为。
在谱序中,大多数修撰者或撰写谱序者直接叙述宗族史,直义较多,转义较少,如在《河南程氏正宗世谱》中的《重录河南程氏正宗世谱序》载有:“余族自先夫子讲学鸣皋,卜宅陆浑而后世居樊水之阳。宋建炎初,随高宗南渡,至明洪武初先人讳德用祖者来归陆浑,世守先祠。明景泰六年,昭录两程后裔,授翰林院五经博士,世其官,盖自克仁祖始也。明弘治十三年,先博士继祖奏请数事于朝,遂给田修理、免役、改民籍为贤籍、豁除丁徭。”[4]该谱序作者为程氏伊川二十四世代程延祀重纂,这里直接叙述先祖概况,定居陆浑,而后播迁,后又回归陆浑守祠事迹,这里采用直接叙述的形式对宗族史进行叙述,这一行为属于直义行为。
(三)微观叙事体例中的直义行为
家谱的微观叙事体例主要由图、传、志、文三部分组成,其中叙述对象的话语多为直义话语,其叙述对象的行为也蕴含较多的直义行。
1、谱图中的直义话语
谱图主要由祖先像、祠堂图、祭器图、住宅图、播迁图、坟茔图、书院图、人事图组成,在这些谱图中,直义话语最为突出的是祭器图、住宅图、坟茔图的文字阐释。这里是直接对其进行叙述或描绘。祭器图文字中的直义话语表达主要涉及祭祀器物的大小、尺寸、容貌的叙述。河洛地区的家谱祭祀器物图以《河南程氏正宗世谱》谱载最多,直义话语的文字记载甚为详实,其中载有簋这种祭器,簋是古代青铜或陶制盛食物的容器,圆口,双耳或四耳,簋的祭器图文字记载:“通足重九斤,高六寸七分,深二寸八分,阔五寸,腹径长七寸九分。”[5]
此外,还有象尊(古代的一种酒器,其形如象。)、拟象、台烛、巾悦、盘盥、祝版、鼎、洗、罍(古代一种盛酒的容器或盥洗用的器皿。小口,广肩,深腹,圈足,有盖,多用青铜或陶制成。)、坫、爵(古代饮酒的器皿,三足,以不同的形状显示使用者的身份。)、笾(古代祭祀和宴会时盛果品等的竹器)、龙勺、登、豆(古代祭祀时放祭品的器物)、尊雷云、尊幕、架盘盥、钏、篚(古代盛物的竹器)、俎(古代祭祀时放祭品的器物)、幕龙、巾笾等祭器图皆附有直义话语。有的还用文字记载该祭器材料、外貌、用途、使用方法等,如“坫:置爵承尊皆用之,重二斤九两,纵广九寸二分,措诸地而平正。”[5]“尊雷云:盛酒器也,范金为之,纽以螭首,书云雷于腹,雷取其奋豫;云取其需泽,用贮初献酒。”[5]修撰者不动声色的按照祭器客观的记载了它们的材料、规格、容貌、形状、用途等,这些都是直义话语的载体,直义现实了事物的客观性与持久性。
住宅图文字中的直义话语表达主要涉及住宅的方位、地点、面积、事物名称的叙述。《白居易家谱》载有住宅图并附有文字《履道里第宅记》:“宅在西北隅闬北垣第一邸也。坐向南方,于东五亩为宅,其宅西十二亩为园,方正共十七亩。”[6]这些直义话语的客观记载了住宅地。
坟茔图文字中的直义话语表达主要涉及与坟茔有关事物的名称、位置、面积、墓碑等的叙述。河洛地区家谱中,半数之多的修撰者都有关于坟茔客观记载,在《范氏家谱》中,坟茔图部分载有天平山坟茔图、山东淄博长白山图、河南洛阳伊川万安山图等。在万安山图中文字记载,西邻伊川彭婆镇路,路北通龙门,南抵彭婆镇;北靠万安山;南朝嵩州地面樊店;东接登封县地面。这一区域内载有范氏坟茔,包括范仲淹墓、守墓子孙居地、十三安人、十四安人、六县君、七县君等。在《洛宁张村白氏家族历代家谱》载有坟茔图,文字记载:“我白氏家族自巩县(巩义市)石关迁至洛宁王范,择茔香泉寺南少许,殡葬五世……后又迁入张村,择茔村西现张村电站西南,分上下两茔,上茔葬六世;下茔葬七世。”[7]这些话语都是直义行为的呈现,对坟茔客观记载。又如《邵氏家谱》谱载“康节先生坟茔,先生葬嵩县莘店镇紫荆山之阳,离洛城七十里许,茔内建享堂五间,东西厢房六间,大门三间,外竖石房一座,题曰:康节佳城。墓碣题曰:宋新安伯邵康节墓。周围设立祭田五顷,仍设看坟人役二名,工食本县支给额,设奉祀生员四名,茔域焚修世代相继永为故典。”[5]这些都为直义话语。
2、志中的直义话语
在志中,直义主要存在于祠堂志、房宅志中叙述话语中,这些直义话语直接叙述或描绘其面积、方位、建材等。《程氏宗谱》载有《河南两程子故宅序》云:“隋于天津桥南开大道,封瑞门,名曰天门,街阔一百步,道旁植樱桃、石榴两行,自瑞门至建国门,南北九里,四望成行,中为御道,通泉流渠,映带其间,直南二十里正当龙门。”[8]从中可以看出直义话语点明了程子故宅的方位、建筑、道路、道旁植被等。《范氏家谱》载有《广玉田记》云:“广玉田记万安山,先贤范文正公埋玉地也……洛阳万安山第一域也……义田十二顷……忠宣诸公胥附葬于茔之西北第二域……共义田十五顷三十亩。”[9]诸如此类直义话语,在志中比比皆是,在家谱中,凡有志者,均有直义话语。志中的直义话语是自纂直义话语与转纂直义话语的结合体。志中修撰者自己编纂的直义话语为自纂直义话语,转录本宗族其他成员文字的为转纂直义话语。
3、文中的直义话语
在文中,直义话语比较普遍,诗文、像赞、字辈排行均有直义行为,像赞、诗文与字辈排行中的直义行是指修撰者在把本宗族成员的诗文、像赞或字辈排行转录家谱的过程中没有改变原始文稿,只是照搬过来诗文、像赞和字辈排行这一行为是直义现象。像赞内容多涉及像者容貌与功业,其中的直义话语主要涉及画像者的姓名与容貌叙述。有名望的宗族对字辈排行很是慎重,修撰者只是实录已经存在的字辈排行,如《程氏宗谱》载有最后由程占文编续的程氏字辈排行:“子彦思克,继世心宗,佳接起延,倓洛璋铭,毓秀广远,相传大千,源推其业,长流万年,恪守秉正,修齐治平,道衍仲舆,志笃永恒。”[8]文中的直义话语并非修撰者自己编纂上去的,而是客观转录本宗族成员的文字,所以均属于转纂直义行为。
总之,话语是比句子大得多的语言单位,对于家谱的修撰者而言,直义话语的主要功能是直接地描述或转述作为客体的经验内容:只停留在修撰者对客观表达层面,以直陈其事的形式展现整个宗族的历史。从性质上说,其作用是客观表现的,强调事物的单一性、外在性与真实性。如果没有直义话语,对于修撰者而言,编纂家谱也就失去了其根本意义,与虚构滑入同一条轨道,家谱也就不再是宗族判断宗亲的可靠依据了。
参考文献:
[1](美)海登·怀特著,陈永国,张万娟,译.后现代历史叙事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7.
[2]不题撰人.洛宁张村白氏家族历代家谱(第一门篇)[M].洛阳:洛阳理工学院图书馆馆藏,2014.
[3]不题撰人.孙氏族谱(第一分卷)可久裔篇[M].洛阳:洛阳理工学院图书馆馆藏,2014.
[4]不题撰人.河南程氏正宗世谱[M].洛阳:洛阳理工学院图书馆馆藏,2014.
[5]不题撰人.河南程氏正宗世谱(祭器篇)[M].洛阳:洛阳理工学院图书馆馆藏,2014.
[6]洛阳市郊区委员会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白居易家谱[M].洛阳:洛阳理工学院图书馆馆藏,1990.
[7]不题撰人.洛宁张村白氏家族历代家谱[M].洛阳:洛阳理工学院图书馆馆藏,2014.
[8]不题撰人.程氏宗谱[M].洛阳:洛阳理工学院图书馆馆藏,2014.
[9]不题撰人.范氏家谱[M].洛阳:洛阳理工学院图书馆馆藏,2014.
作者简介:王忠田(1983-),黑龙江黑河人,硕士,郑州成功财经学院科研处,研究方向:文艺学、民俗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度河南省社科联、河南省经团联调研课题《中原传统家族文化的现代功用》(项目编号:SKL-2015-936)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系河南省教育厅2016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私修谱牒的叙事性研究——以河洛地区236套家谱文本为例》(编号:2016-qn-091)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