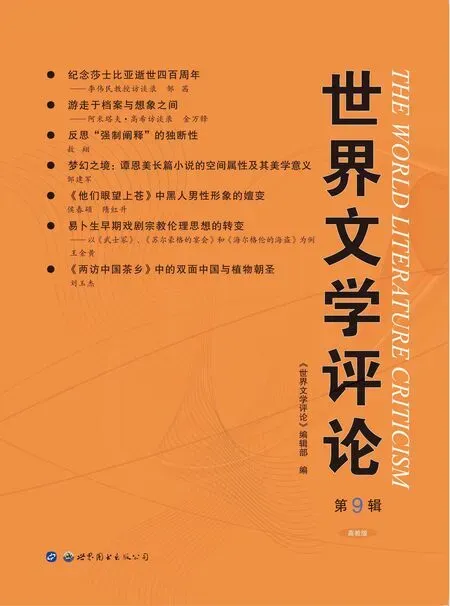反思“强制阐释”的独断性
2016-11-25敖翔
敖 翔
反思“强制阐释”的独断性
敖 翔
张江在其论文《强制阐释论》中重点反思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强制阐释问题。强制阐释的症结在于文学阐释的“独断性”,即完全不尊重作者原有意图,不考虑文学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排斥其他批评家的不同解释,甚至忽略文学文本本身,最终沦为了批评家的自说自话。为避免强制阐释,文学阐释应趋向多元化。同时,强制阐释问题也启示我们重新认识“文学本质”,即应尊重“文学”概念的多元性,以发展眼光和开放心态看待“文学”概念,而不宜急于对之下定论。
强制阐释 独断性 文学本质
“强制阐释”是张江教授在《强制阐释论》中重点批判的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根本缺陷。该文发表于《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张江将“强制阐释”定义为“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称,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1]他继而归纳了“强制阐释”的四大特征,即“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和“混乱的认识路径”。两年后,张江又在《文艺研究》2016年第8期上发表《强制阐释的独断论特征》一文,指出“独断论”正是“强制阐释”产生的基础,同时两者彼此依托、互为因果:“独断论与强制阐释的关系是,以独断论为基础的强制阐释,在阐释学谱系上可以是一种理论;以强制阐释为展开的独断论,在阐释过程中可以是一种方法。两者互为依托和因果:独断论的立场,需要和运用强制阐释的方法;强制阐释的方法,巩固和实现独断论的立场和目的。”[2]独断论是强制阐释的基础和方法,而“强制阐释”的根本特征与根本缺陷大概可由此归纳为“独断性”,正是“独断性”使得“阐释”沦为“强制阐释”。“强制阐释”的“独断性”恐怕正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之处。笔者的反思具体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独断性:“强制阐释”的症结所在;其二,为避免“强制阐释”及其“独断性”,我们应如何阐释文学;其三,对“文学本质”的反思。
一、独断性:“强制阐释”的症结所在
首先,应充分认识“强制阐释”的症结所在,即其“独断性”。以“独断论”为基础的强制话语,并非一种开放性的阐释话语,而是一种排他、封闭的独断性话语,这种“独断性”正是“强制阐释”的问题所在。文学批评家进行文学文本阐释,本应是与文本、作家乃至整个社会语境所进行的一场平等对话,但在“强制阐释”那里,这场本应开放的平等对话,却沦为了批评家的自言自语,而不容任何其他话语。这种“独断性”最终也会导致强制阐释的“无效性”——阐释原本是为了与作者、文本对话,强制阐释却无视作者和文本本身,自说自话,失去了阐释应有的意义。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将梵高写实性油画《鞋》衍化为一个抽象的哲学转喻。张江认为海德格尔的这种解释是一种“强制阐释”,因为“他(海德格尔)的‘决定’是思想家个体的决定,而无任何对话和商榷”[3]。因此,“强制阐释”不同于创造性误读,其问题不在于阐释者提出了异于作者原意或文本客观呈现的见解,而在于阐释者根本无视作者原意和文本本身,仅将个人意图强加于文本,甚至强加于原作者。这种“强制阐释”缺乏与作者和文本的平等对话,而陷于一种封闭的“自说自话”中。此外,张江还指出,“强制阐释”排斥其他不同角度的阐释,而将自己的阐释奉为圭臬,奉为“唯一解释”,最终导致各学派和各理论流派之间的相互否定、相互排斥和相互隔绝。如弗洛伊德以“恋母情结”解释《俄狄浦斯王》,本不失为一种有趣解读,但他否定了将该剧作为“命运悲剧”(命运与人类意志之间的冲突)的阐释,将“恋母情结”作为唯一解释:“如果说伊谛普斯(又译‘俄狄浦斯’)王这一悲剧感动现代观众的力量不亚于它感动当时的希腊人,其唯一可能的解释只能是,这种效果并不出于命运与人类意志之间的冲突,而是在于其所举出的冲突情节中的某种特殊天性。”[4]这便沦为了独断的“强制阐释”。实际上,对《俄狄浦斯王》的不同阐释,如“命运悲剧”、“恋母情结”、“新旧伦理冲突”(文学伦理学对《俄狄浦斯王》的又一阐释,认为该悲剧反映了父权社会建立初期,原始母系社会伦理与父系社会伦理的冲突)等,可以同时并存,而不应互相否定、互相排斥。张江也并未否认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卓越贡献,但他同时又指出了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各类流派共同存在的“独断性”问题,即“相互否定和隔绝”,消解了一个旧有中心,却又迫不及待地建立了一种新中心。因此,形式主义和新批评一方面排除了庸俗社会学的干扰,让文学研究聚焦于文本,却又过分强调文本,排斥了文学文本本来可能蕴含的社会历史内涵及思想文化内涵。解构主义打破了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但又开始以“解构”本身为中心。再如接受美学指出了读者对文学文本的建构意义,却偏执地以读者为唯一中心,排斥了作者等其他因素。
“强制阐释”论所讨论的对象主要是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但他真正的批判对象大概并非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本身,而只是当代西方文学批评中所存在的“独断性”弊病。因此,“强制阐释论”大概并没有否定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有益成果,也没有反对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来阐释文学,而仅仅在反思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普遍存在的“独断性”问题。此外,我们也应反思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所存在的“独断性”问题。尽管,张江的“强制阐释论”以反思西方当代文学批评为开始,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就不存在类似问题。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中谈论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第一讲和第二讲)时指出,张惠言认为词“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因此他用《离骚》的“香草美人”比兴传统来解释《菩萨蛮》(词句有“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被认为类似屈原《离骚》中的“众女嫉余之蛾眉兮”)。针对这一观点,刘熙载、王国维和李冰若都坚决反对。他们不约而同认为,张惠言在“过度阐释”,忽视了温庭筠词的审美特征(如刘熙载认为温庭筠的词作“不出绮怨”,缺乏比兴寄托),也忽视了作者温庭筠的性格特征(如李冰若认为,温庭筠风流浪荡,个性迥异于忠君忧国的屈原)。①刘熙载等人的批评的确有一定道理,再结合晚唐词“词为艳科”的文体特征(大概北宋苏轼“以诗为词”后,词中的比兴手法才开始普及),以“香草美人”解释温庭筠的《菩萨蛮》确实有些牵强,甚至有“强制阐释”之嫌:忽视作品的创作语境(如晚唐时期词的审美特征、作者创作风格及其人格特征等),而以“香草美人”解释强加于《菩萨蛮》。这大概正是一种“主观预设”,最终是为了证明“香草美人”这一理论,而非为了阐释作品本身。然而,刘熙载等人依据《菩萨蛮》的创作语境,完全否认张惠言的解释,似乎又沦为另一种武断。尤其是李冰若以温庭筠风流浪荡的性格侧面来否定《菩萨蛮》可能隐藏的比兴内涵,既混淆了作者人格和作品风格的区别,也忽视了人性的复杂性。叶嘉莹则给出了两种解释。其一认为温庭筠创作“艳词”时,受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因此使用了“蛾眉”这一具有特殊文化内涵的词语。其二则结合温庭筠生平指出,“甘露事变”后,温庭筠可能因同情宰相王涯和庄恪太子李永致使自己仕途不畅,内心亦有忧愤,因此或许在写作“艳词”时,无意流露出了潜意识中的忧愤之情,尽管没有刻意使用“香草美人”比兴手法,但或许因潜意识隐约显现了类似《离骚》的忧愤心境。(53—57)
二、多元阐释:一种更为开放的阐释方式
叶嘉莹对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的阐释,较之张惠言和刘熙载等人的解读,更为开放,也更为谨慎,没有轻易否认任何一种说法,也没有武断标榜自己的解释为唯一合理解释。这种文学批评态度,大概才真正可取。这也是我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即为避免“强制阐释”,如何阐释文学的问题。即应采用开放性话语,在创造性阐释文学文本时,充分尊重作者原意、创作背景和文本本身,也应包容其他不同阐释。在文学的“四要素”(世界、作者、作品和读者)中,不应以任何一要素为绝对中心,而应尽可能关注到每一要素。正如张江所言:“一个成熟学科的理论必须是系统发育的。这个系统发育体现在两个方面。从历时性上说,它应该吸取历史上一切有益成果,并将它们贯注于理论构成的全过程;从共时性上说,它应该吸纳多元进步因素,并将他们融为一体,铸造新的系统构成。”[5]
张江与哈派姆关于文艺理论的对话《多元阐释须以文本“自在性”为依据》中,张江反复强调作者原意的重要性:“对文本的阐释有两种立场、两种态度、两种方法。一种是您这种,认为有多重含义、多重解释,我赞成。您也应该同意,作家的意思在文本里,无论我们找到不找到它,它是在的。”[6]张江对作者的强调无疑是文学阐释应有的回归。文学文本为作者所创作出来,即使作者去世,也应该尊重作者的原意。罗兰·巴特的“作者已死”理论,尽管在肯定读者主观能动性方面颇有贡献,但恐怕又陷入了忽视作者的极端。同样,如今反思“作者能不能死”,也大概不可重复这类怪圈,即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的独断性循环。单纯强调作者,或单纯强调文本,或单纯强调读者,都仅强调了单一因素,都是一种独断性的阐释。文学作品本是四要素(世界、作者、作品和读者)的综合,它由作者创作,属于作者,但不独属于作者;它再现或表现世界,本身也虚构了一个世界,并与现实世界形成一种对话,但又不能与现实世界相混淆;它的文本本身具有独立性,但又应具有开放性,而不应封闭;它由读者阅读和阐释,也属于读者,但同样不独属于读者。因此,文学批评又是四要素之间的对话,作为阐释者,应该同时尊重作者原意和文本本身,也应该尊重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同时也不必做作者、文本或时代的代言人,不妨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总之,如果充分尊重作者原意、文本本身、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其他读者对文本的不同解读,文学阐释就容易成为建设性的创造性误读;反之,如果毫不尊重作者原意,完全不顾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排斥其他读者和批评家对文本的不同解读,甚至脱离文本本身,文学阐释就会沦为一种独断性的“强制阐释”。此外,我们大概需要认识到,文学批评仍有别于科学,尤其有别于自然科学,它本身似乎也具有一定“虚构性”。总之,文学批评抑或文学阐释不可能有“标准答案”。或许,批评家的职责不过是依据文学四要素,尽可能提出不同假设。大概只要有所依据,假设越多元(甚至不同假设间看似彼此矛盾),文学批评就越有价值。
三、“强制阐释论”对反思“文学本质”的启示
“强制阐释论”对于我们反思“文学本质”这一问题,亦有启示。笔者比较欣赏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的态度,在其著作《文学理论入门》中,他没有给“文学本质”下最终定义,而是介绍了五种有关文学本质的不同解释(“语言的‘突出’”,“语言的综合”,“虚构”,“审美对象”,“互文性的或者自反性的建构”),并认为:“对每一点论述,你都可以从一种视角开始,但最终还要为另一种视角留出余地。”[7]这一态度大概不同于“强制阐释”,是一种开放性论调。因此,我们不妨以开放心态来谈论这一问题,而大概不必急于给“文学本质”下一个最终定论。就“文学”这一词语而言,无论是汉语的“文学”,还是英文“literature”,最初所指都是“文献”,涵盖文史哲各个方面。如“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中的“文学”,即指涵盖文史哲的文献。即使“文学”开始强调艺术性后,文学大概也从未和历史、哲学、宗教、心理学等完全撇清关系。如杜甫被称作“诗史”,巴尔扎克被称作“书记员”,他们的一些重要作品往往再现了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又如王维被称作“诗佛”,其诗作禅学色彩浓厚,但丁《神曲》具有深刻的天主教内涵,萨特、加缪的文学作品则具有明显的存在主义哲学意味。以上都可以窥探出文学的“文化性”,即往往蕴含深广的思想文化内涵。除“文化性”外,文学还具有“艺术性”或“审美性”。最初,“诗乐舞一体”,诗歌的一大重要功用便是审美和抒情。唐诗宋词中的名篇也往往因其绚烂的艺术性而动人。但无论“文化性”还是“艺术性”,恐怕都不能单一地作为“文学本质”,而应综合看待,二者都是文学的重要性质,只是不同文学作品侧重不同。如同为杜甫的作品,其“三吏三别”等古体诗,“文化性”更明显,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其《秋兴八首》等七律,“艺术性”更明显,具有非凡的艺术审美价值。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也均是优秀的文学杰作。再如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创作,以往读者更关注这些作品的独特文体特征和审美价值,现在学界又开始挖掘其作品对女性问题的深入反思。但如果单以“艺术性”论文学,或单以“文化性”论文学,恐怕都是一种独断性的“强制阐释”。除“艺术性”和“文化性”外,文学大概还具备其他性质,这些性质都应得到关注,而不应单独强调某一性质。总之,我们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应该多元化,而不宜单一化。或许,“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它没有明确固有的“本质”,因此,唯有不急于给“文学本质”下定论才最接近“文学本质”。换言之,大概不必纠结于“文学本质”问题,而应以开放心态看待文学,“文学”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
综上所述,“强制阐释”的最大症结在于其阐释话语的“独断性”,即排斥其他阐释话语,将自己的阐释话语奉为唯一合法的阐释,并忽略作者原意、作品文本本身及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为解决“强制阐释”,文学阐释应注重多元化,一方面应同时尊重文学四大要素(世界、作者、作品和读者),另一方面又应尊重其他批评者对文本的不同解读。此外,对“强制阐释”的反思也启示我们重新认识“文学本质”问题,即不必急于给“文学本质”下定论,而应以开放心态和发展眼光看待“文学”概念,不应仅仅关注文学的“审美性”。
注解【Notes】
①参见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47页。以下只在文中注明页码,不再一一做注。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张江:《强制阐释论》,载《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第5页。
[2]张江:《强制阐释的独断论特征》,载《文艺研究》2016年第8期,第12页。
[3]张江:《强制阐释的独断论特征》,载《文艺研究》2016年第8期,第7页。
[4][奥]弗洛伊德:《释梦》,孙名之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61、262页。
[5]张江:《强制阐释论》,载《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第17页。
[6]张江、哈派姆:载《多元阐释须以文本“自在性”为依据》,《文艺争鸣》2016年第2期,第116页。
[7][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30页。
Title: Ref ections on the Arbitrariness of "Imposed Interpretations"
Author: Ao Xiang is from the Faculty of Arts i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The issue of "imposed interpretations",arising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was stressed by Zhang Jiang in his paper A Discussion on Imposed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ations. The crux of "imposed interpretationinterpretations"lie in the "arbitrariness" of its literary interpretations, namely disrespecting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author, ignoring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literary creation, rejecting other interpretations from other critics and even disregarding the text of literary works. To avoid" imposed interpretations", literary interpretations should tend towards diversif cation. Furthermore, the issue of "imposed interpretations" also enlightens us to rethink "literary essence". Put it another way, we need to respect the diversity of the concept of "literature" and treat this concept with developing sight and opening mind.
Imposed-Interpretations Arbitrariness Literary Essence
敖翔,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西方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