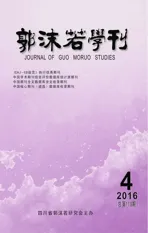郭沫若怎样应对沈从文的“挑战”
2016-11-25王锦厚
王锦厚
(四川大学 出版社,四川 成都 610041)
郭沫若怎样应对沈从文的“挑战”
王锦厚
(四川大学出版社,四川成都610041)
中国现代作家中郭沫若与沈从文的复杂而又特殊的关系是研究者乐于谈论的问题。汪尊棋声言是郭沫若撰写的《斥反动文艺》“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汪尊棋:《沈从文的转业之谜》《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沈从文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外文出版社1994年)家人及某些研究者为之附和,肯定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改变了沈从文的命运。《沈从文家事》作者刘红庆说得更加露骨,他说:“就是这个郭沫若以一篇《斥反动文艺》,葬送了沈从文的文学前程,换来了一本巨著《中国现代服装研究》。”(刘红庆:《沈从文家事》,新星出版社1912年6月)因此,人们往往把郭沈的矛盾、斗争归结为个人“恩怨”。
事情真如此吗?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有这样大的“威力”吗?我们不妨还是先读一读《沈从文批评文集》编者与沈从文夫人张兆和谈沈从文吧:
□系统看了沈从文的批评文章后,我最强烈的印象,是他的“不识时务”和倔强。他的批评文章,在文坛引起过不少风波,他敢直言不讳地批评权威,他只认真理。
○是的,他写文章从来不考虑利害关系,没有门派观念,他无所谓。上海时期,他给南京有政府背景的杂志报纸写稿;云南时期,在《战国策》上发文章,他与陈铨关系不错,但又和他论争。他从来不站在什么派一边,对什么看不惯就批评,他太固执,他有他的看法,这是湘西人的性格,没办法。
□在二十年代中期,他就写文章《扪虱》,自称要在文坛捉虱子,把名人的粗劣文章捉出来“示众”。他与废名同是京派成员,并且他还受过废名的影响,但他还直言不讳地说,废名后期的文字与海派作家穆时英一样,近于“邪僻”。
○他得罪了许多人。
□是这样,但他说的是真话,是行家说的话,他有他自己的标准,他的艺术感受力非常强,他敢去碰鲁迅、郭沫若。
○人家捧的,他要去碰,非要去碰一碰不可。其实他很佩服他们。我们过去对郭沫若非常崇拜,上中学时,崇拜得不得了,那时我们演戏尽演郭沫若的。
(《与张兆和谈沈从文》,1998年12月9日《文汇报》)
这个对话非常有趣。沈夫人回答得也很巧妙,既赞扬了沈从文“从来不考虑利害关系,没有门阀观念”,“说的是真话,行家的话”;又为沈从文作了辩护,“其实他很佩服他们”,“我们过去对郭沫若非常崇拜”。文中所说“我们”,应该不包括沈从文吧?!。沈从文真的“佩服”“崇拜”鲁迅、郭沫若吗?读一读他的这两段话吧:
至于自封的“专家权威”,以吃鲁迅作了文化官的批评家,虽已看出他那种唬人的“权威”,过去还起欺骗作用,对新的一代已失去“只此一家”的骗人效果,不免要改改过去的提法,却想出新点子,以为“鲁迅称赞过我”。我只觉得十分可笑。事实上我那会以受鲁迅称赞而自得?他生前称赞了不少人,也乱骂过不少人,一切以自己私人爱憎为中心。我倒觉得最幸运处,是一生从不曾和他发生关系,极好。却丝毫不曾感觉到得到他的称赞为荣!(沈从文:《致沈岳锟》1983年2月《沈从文全集》二十六卷)
……丁玲给鲁迅写了一封信,有人说是我写的,鲁迅就不高兴了。这个人后来被枪毙了,是国民党派到他身边的,是莽原社的,叫金水林。当时鲁迅先生很紧的,也没有什么原因,以后我就不见他了。(王亚蓉编:《沈从文晚年口述·社会变化太快了,我就落后了——与美国学者金介甫对话》,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二次印刷)
从这两段文字(还有其他文字),怎么也看不出沈从文对鲁迅的“佩服”“崇拜”啊!相反,是另一种不可言传的恨。“口述”中提到的“金水林”,不对!事实也很有出入,应予纠正。此人叫“荆有麟”(1903—1951),又作有林、识芳,山西猗化人。综合《鲁迅全集》中关于此人的注释,应该是:1924年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读书时,因向鲁迅请教写作,翻译问题开始来往。1925年春世界语专门学校停办后,经鲁迅介绍任《京报》馆校对,参加《莽原》周刊的出版工作。在此前后,编过《民众文艺》周刊和《每日评论》。1927年5月开始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先在南京办《市民日报》,后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部干事。1928年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二师独立师秘书长。1930年至1931年先后在河北怀远及江苏萧县任教员。1936年时为国民党中央考选委员会科员。1939年加入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组织,混迹于进步文艺界,进行反革命活动,解放后,镇反运动中,在南京被枪决。
至于郭沫若,沈从文更是没放在眼里,1930年他撰写的《论郭沫若》《论中国现代小说》中就反复贬斥郭沫若。在友人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说:
依我看,是郭沫若郁达夫都不行的,鲁迅则近来不写,冰心则永远写不出家庭亲子爱以外。(沈从文:《复王际真》1930年1月12日《沈从文全集》18卷,第39页)
于是乎,沈从文要去“碰”鲁迅、郭沫若。所谓“碰”,实际就是挑战,挑衅。关于碰“鲁迅”,由于鲁迅过早离开这个世界,未能给沈从文以应有的回应。
对郭沫若的“挑战”,大致可以分三个阶段:
一阶段(1930—1936年)
文章有:《论郭沫若》(1930年《日出》月刊第一期)《论中国创作小说》(1931年《文艺月刊》4-6期),文章几乎一笔抹煞了郭沫若的小说创作,说“郭沫若不适宜写小说”,“太直”,“不曲”,“创作(小说)是失败了”……
此时,郭沫若“流亡”在日本,读了,但未立即回应,直到1932年写作《创造十年》,回答鲁迅先生的《上海文艺之一瞥》时,才顺便回应了一下,他是这样回应的:
总之,我应该感谢鲁迅先生,我读了他那篇《一瞥》,才决心来写这部《十年》。但我在这儿还要附带着声明一笔,我这《十年》倒并不是小说——记得国内另一位大小说家宣言过:我是没有做小说家的资格的,因为我的笔太直,不曲,没有象鲁迅先生的那样曲。是的,这层我自己是很承认的,假使要曲才配做小说,那我实在是不配做小说家。据说小说是“寒带”,那吗只适宜于Eskimo(作者原注:爱斯基摩人,居住于北美洲北部寒带)那样的小人去住,我也就敬谢不做。(郭沫若:《创造十年、发端》1932年9月20日上海现代书局初版发行,后收入《沫若文集》第7卷,现收入《郭沫若全集》12卷,均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如果说,这个“回应”带有“恩怨”之嫌,那么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沈从文对郭沫若的种种“挑战”及郭沫若的回应,则完全应当另当别论了。按“挑战”性质,算是第二阶段了。
二阶段(1936—1945年)
沈从文的“挑战”文章有:
《作家间需要一种新的运动》1936年10月25日天津《大公报·文艺》收入《沈从文全集》17卷。(曾在文坛引起一场大论争)
《再谈差不多》1937年8月1日《文学杂志》第1卷第4期,收入《沈从文全集》17卷。
《一般或特殊》1939年1月22日《今日评论》1卷4期,收入《沈从文全集》17卷。
《一种态度》1939年6月25日《今日评论》2卷1期,收入《沈从文全集》14卷。
《对作家和文坛的一点感想》1942年2月11日重庆《大公报·战国策》收入《沈从文全集》17卷。
《文艺运动的重造》1942年10月25日重庆《文艺先锋》1卷2期,收入《沈从文全集》17卷,立即遭到批判。(如杨华的《文学的商业性和政治性》1943年2月17日重庆《新华日报》)
《“文艺政策”的检讨》1943年1月20日重庆《文艺先锋》2卷1期,收入《沈从文全集》17卷
……这些挑战,隐藏在他心灵深处的秘密是话语权,领导权。
过去,时人及研究者总是认定“与抗战无关论”是梁实秋的专利,其实不然,始作俑者,应该归功于沈从文。早在1936年,他在《作家间需要一种新的运动》文中就号召开展一个“反差不多”运动,其实就是要作者写与抗战无关的题材;此论遭到文艺界的一致反对,接着又在《一般或特殊》《一种态度》中转弯抹角地提出并倡导、鼓吹“与抗战无关”。他说:
大家应当就见得到想得起的事情从小处努力,尽可能来谋求改善。假若拿笔的朋友还相信文学艺术在社会上有一点力量,新的文学艺术便可从这方面下手,表现出一个综合的新的理想,新的生存态度。这种文学艺术,即或无关于当前抗战,然而大有助于明日“建国”。有心人应当承认用这种态度来写作,似迂腐,实健康。虽易触恼当前男的女的村的俏的少数读书人,对另外多数将来读书人,或者还有点好处。(沈从文:《一种态度》1939年6月25日《今日评论》第2卷第1期,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128页)
这不是明明地在提倡鼓吹写“与抗战无关”的题材么!
《看虹摘星录后记》1944年5月21日桂林《文公报·文艺》,同日重庆《大公报》;1945年12月8日、10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刊发。
这些文章的中心内容:鼓吹“与抗战无关”;“反对作家从政”;辱骂作抗日宣传工作的文化人;
倡导写男女身体接触……并以《看虹摘星录》示范。
这些口号,这些理论,有专门针对郭沫若的,更多的是针对整个文运、文艺运动,关系抗战建国,因此遭到左翼文艺工作者的批判,理所当然。郭沫若肩负领导抗日进步文化运动,能够不说话吗?其实,郭沫若公开批判这些谬论,也并非完全针对沈从文,而是针对文坛,作为一种倾向看待的。在纪念文协成立五周年的时候,才先后指出:
自然,在这种洪涛激浪的澎湃当中,总也不免有些并不微弱的逆流。起先我们是听见“与抗战无关”的主张,继后又听见“反对作家从政”的高论,再后则是“文艺的贫困”的呼声——叫嚣着自抗战以来只有些田间式的诗歌与文明戏式的话剧。这种种声息,无论出于有意识或者无意识,都以说教的姿态出现,而且发出这些声息的人又都是不屑和大众生活打成一片的人。民族已经膺受着空前的浩劫,而一二文学教员们却要高喊着“与抗战无关”。究竟是何用意,真正令人难解。这声音由于不合时宜,早已低弱下去了,然而也并未消灭,或则一改调门变而为“要直接与抗战有关”,或则缩小范围变而为“反对作家从政”。
“作家从政”,我们也可能反对,但要看是怎样在“从”,而所“从”的又是怎样的“政”。假使是在军阀统治时代,一个作家要以蝇营狗苟的态度,运动做官,运动当议员,那当然是值得反对的事。旧时代的“八不主义”里面,早有“不做官”一条,在当时真正做到的人倒不失为清高。然而在抗战期间,作家以他的文笔活动来动员大众,努力实际工作,而竟目之为“从政”,不惜鸣鼓而攻,这倒不仅是一种曲解,简直是一种诬蔑!发出这种议论的先生,既有高才,又有闲暇,与其写文骂人,何不便把满腔的抱负或抑郁,凝结而为美妙的结晶品呢?(郭沫若:《新文艺的使命——纪念文协五周年》,刊于1943年3月27日重庆《新华日报》,现收入《郭沫若全集》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北京1版)
国家临到争生死存亡的关头,民族受着了空前未有的浩劫,一切都应该为了前线。作家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多数是动员起来了。虽然在初期也有少数人倡导“与抗战无关”论,但为大势所迫,不久也就消声匿迹。近来如沈从文又有“反对作家从政”的见解,这在平时可以不成问题的议论,但在战时却可大成问题,而且把作家努力参加动员工作认为“从政”,那更是超过了误解范围的诬蔑。(郭沫若:《抗战以来的文艺思潮——纪念文协成立五周年》1943年3月27日重庆《抗战文艺·“文协”成立五周年纪念特刊》,《郭沫若全集》19卷,第385-386页)
这都是从时代大局,民族利益入手进行的批判,哪有一点“个人恩怨”色彩呢?!
三阶段(1945—1949年)
这一阶段,沈从文从昆明复员到北平,格外活跃,不但大抓报纸副刊,先后主编或同时主编昆明的《观察报·生活风》,天津北平的《大公报·星期文艺》《平民日报·文艺》《益世报·文艺周刊》《益世报·诗与文》等副刊,把这些副刊作“为一个具有自由竞争表现新作的据点”,同时,还不时接受记者采访,发表大量煽动性的言论,引人注目的有:
《读书人对政治的态度》1945年5月15日《观察报·生活风》(该文立刻遭孟南批判:《沈从文的“政治观”》1945年5月24、25日《扫荡报》)
《人的重造——最后一个浪漫派的理想重申》1946年3月8日《世界日报》(该文立即遭袁微批判:《读“沈从文人的重造”》1946年1卷5期《中坚》)
姚卿详《学者在北平:沈从文》(1946年10月中旬)采访记中写道:称赞巴金、茅盾以及卞之琳、萧乾默默地坚持工作,而对原来静静地写文章的人现在“出风头”、闹运动,“显然有些爱莫能同意”,对郭沫若“飞莫斯科”,风子“跑到苏联大使馆去朗诵诗”以及丁玲“到铁矿上去体验工人生活,写文章还要请工人纠正”也不以为然。提到何其芳等去了延安的作家时,沈从文认为是“他们是随政治跑的”,对文学不会有好影响。并认为:“文学是可以帮助政治的,但用政治干涉文学,那就糟了。(姚卿详:《学者在北平:沈从文》,《学者在北大》1946年10月23日《益世报》)
《新书业与作家》1947年1月《大公报?图书评论》
以上几篇文章,均未收入《沈从文全集》,也未收入沈从文的其他选集或文集,算是佚文吧!
《一种新的文学观》(1946年9月1日《文潮》月刊第1卷第5期)现收《沈从文全集》17卷(立刻遭到批判。高克奇写了《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重造论”——读沈从文“一种新的文学观”后》1947年《唯民周刊》3卷14期)
《从现实学习》(1946年11月3日,10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立刻遭到史靖批判:《沈从文批判——这叫做从现实学习吗?》1946年12月21—25日上海《文汇报》杨华的《论沈从文的“从现实学习”》1947年1月1日《文萃》周刊第二年12、13专刊)
《我们需要第四党》(未能公开发表)如他后来在文章中所说的:“例如在一篇没有刊出的论党派的文章中,一面说国民党前途无希望,另一面却认为共产党也没什么了不起。……因此做八股似的,提出一个荒唐到家的结论说,明日真正能够担当天下大事,又能折衷于世界两大阵营的,只有一个折衷于国内实力派,又能折衷于世界两大阵营的“第四党”。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集团,能够有办法!我虽没有天下舍我其谁作帝王师幻想,但在写作意识上,却不免以在云端里诸葛亮自居。”(沈从文:《一个知识分子的发展》《沈从文全集》27卷第365页)
《一种新希望》1947年10月上海《益世报》,11月20日北平《益世报》现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4卷(遭到荃麟的批判:《二丑与小丑之间——看沈从文的“新希望”》1948年2月2日《华商报》)
《中国往何处去》1948年9月1日《论语》半月刊160期,9月13日上海《大公报?文艺》现收入《沈从文全集》13卷
……
这些文章,大肆鼓吹“关系重造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重造;文运重造;文艺运动重造;社会重造;国家重造;人重造);诬蔑从事民主运动的领导人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领袖欲”;不遗余力地提倡专家治国,……从而在“多数人情感观念中”“消毒”“免疫”,“不至于还接受现代政治简单化人头脑的催眠,迷信空空洞洞的‘政治’二字能治国平天下”,“而解决一切困难与矛盾。却明白一个国家真正的进步是奠基于吃政治饭的越来越少,而知识和理性的完全抬头”。……就这样再三再四公开向“读书人”(即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喊话:需要第四党,走第三条道路。
面对沈从文的种种严重的“挑战”,“挑衅”,进步文艺界人士纷纷撰文予以批判、回击。作为文化运动领袖的郭沫若理所当然,义不容辞要回击,1947年1月,也撰写了罗斯福体式的《路边谈话》,对文艺界的逆流进行批判,并非专门针对沈从文,当然其中也点名未点名的批判了沈从文:
八超级海派
在平剧界旧时有京派与海派之分,文艺界近来也有人兢兢于作此区别。有人自标为京派以榜其清高,而斥人为海派以责其庸俗。
其实旧时的所谓京派与海派只是封建地主式与近代买办式之分;而今天的新京派则是超级海派,他们是把地主式与买办式合而为一了。
不信你请试试看,你看今天自命京派的人谁有胆量敢说美国人的屁不是香的?
九黄豆咖啡
周作人曾自标为京派,而名其斋曰“苦茶”。其所为文确有苦干茶味,虽然并不甚苦。
今之自标京派者流,其为味也有如黄豆咖啡。
十一 嘴上有血
既有口谈民主而心想做官者。
扩而充之:凡谈民主者皆想做官者也。
更扩而充之:凡不谈民主者不想做官者也。
更更扩而充之:凡反对民主者反对做官者也。
我虽然是在做官而却反对做官,故我最清高,最杰出,最不同乎流俗。
这是新京派教授(作者原注:此人指沈从文。)的又一逻辑。
原〔附注〕大学教授亦朝廷命官也,不要忘记。
(郭沫若:《路边谈话》初载1947年1月16日重庆《新华日报》,现收《郭沫若全集》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北京1版)
沈从文将书业不景气的罪状加在出版家的头上,胡说创造社“终因经济方面转手不及,不易维持”而倒闭,歪曲创造社的历史,把“政治”的责任推开,替国民党对文化事业,对创造社的迫害开脱,特别撰写了《新书业与作家》一文。对此,郭沫若非常气愤便写了《拙劣的犯罪》,以自己办创造社出版部的亲身经历,揭露沈从文《新书业与作家》(此文未收入《沈从文全集》)冒充文坛长老捏造事实、蒙蔽真相的面目。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就是创造社出版部的简略的经过。它的结束,我要明明白白地告诉沈从文,并不是什么“终因经济方面转手不及,不易维持”的。
这种不顾事实,自我作故的态度,就是沈从文的态度。
达夫虽然死了,成仿吾和我还没有死,田寿昌、郑伯奇、阳翰笙、李一氓、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及不少的“小伙计”和股东们都还没有死,冒充一个文坛长老而捏造事实,蒙蔽真相,那明明是一种犯罪,而且是拙劣的犯罪。(郭沫若:《拙劣的犯罪》初刊1947年1月27日上海《文汇报》现收入《郭沫若全集》16卷)
1947年1月25日
这是对冒充文坛长老的沈从文的讨伐。
不久,又在《新缪司九神礼赞》文中对沈从文的记者谈话和《从现实学习》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说:
还有一位“自由主义”的教授,听说一提到我便摇头,因为我去年曾经“飞莫斯科”,更成为了他的摇头材料。我看到好些朋友为这事在替我不平,其实是大可以不必的。我要更坦白地说一句,我对于我自己也时常在摇头,而且一定比任何教授摇得厉害。不说一年来毫无成就,就是我一辈子到底又成就了什么,真是可怜得很!幸好我还不敢坐井观天,因为我也到海里去游泳过一下。我知道井外的天地还宽广得多,而在那宽大的天地里面无数的大星小星实在光辉夺目。“飞莫斯科”在我倒也同样是一件遗憾,因为自己的本领太低,没有好好利用这个机会更学进步一点,写些可以见人的东西出来。
我倒也并不想故意自谦,借这个我们东方人所特别夸耀的“谦虚”美德以掩盖自己的怠惰和空虚。确实地有真才实学的人,他是不屑于自我宣传,但也无须乎自我贬责的。我的努力不够,我得承认,但我也不想宽大到让时代和环境的罪过也要由我来担负。“胜利前后到现在”的这一两年到底是什么时代呢?而我们所处的又是怎样的环境呢?费巩教授的下落至今都还不明,李公朴、闻一多的血还没有干,三千万的饥民应该还没有饿死完,蔓延了十九省的内战每天每月不知道要死几千几万同胞,……只要不是白痴,是谁也认识得清楚!
……
我依然要在这冰天雪地中挣扎,我要扎根,我要迸芽,我要开花结果。这儿是我的现实。我可能也还要为红白喜事奔走,只要是和人民大众有关的红白喜事也就是我的现实。我听见有声音自温室中来:“从现实学习”吧。这是很中听的声音。虽然温室中的“现实”不是我的现实,而温室中的“学习”不是我的学习,但我还是喜欢那个中听的声音。谁个又能够否认,那温室中的花草们毕竟是可怜的呢?他们也有他们的“岗位”,让他们去独自欣赏,或为所憧憬的对象们所欣赏吧。从石榴裙下的现实去学习拜倒,从被窝中的现实去学习自渎,那是不同乎流俗者的自由。至少在这一方面我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我是不愿意干犯别人的自由的。然而我敢于自信,我以前虽然毫无成就,主要的原因大约也就是由于我的“有所不为”,而我今后却是要“有所为”了。严寒的冬季也不会那么太久的。有我们的新宙司大神在上,有我们的新缪司九神在旁,谁能量定我就得不到他们的加庇,使我也可以得到不断的新的“灵感”?(郭沫若:《新缪司九神礼赞》1947年1月上海《文萃》周刊第二年十四期《郭沫若全集》第20卷第213页、222页)
“万般皆下品,唯有人民高”。人民是社会的主人,是文化生活的创造者。本质的文艺本来就是人民文艺,这在任何民族都是文艺的本流,而且站着极高的地位。脱离了人民本位的文艺,虽然借政治的力量可以博得一时性的月桂冠,但其实那是堕落。旧式的《剧秦美新》是堕落,新式的《看云》、《摘星》(作者原注:《剧秦美新》是扬雄歌颂王莽的文章,《看云录》(应是《云南看云集》——注释者)和《摘星录》是沈从文的文集。)是更悲惨的堕落。那样的作品虽然冒充过、或冒充着“纯文艺”的佳名,其实那是最混杂的排泄,不必说到纯不纯,根本就不是文艺。
“纯文艺”的真正的意义,我们要作这样的认识:凡是人民意识最纯,丝毫没有夹杂着对于反人民的权势者的阿谀,对于不劳而获的垄断者的赞颂,或钻进玻璃室里作自渎式的献媚,丝毫没有夹杂着这些成分,而只纯真地歌颂人民的辛劳,合作,创造,而毫不容情地吐露对于反人民者一切丑恶、暴戾、破坏的如火如荼的憎恨。这样的作品,我们便认为是今天的“纯文艺”——纯人民意识的文艺。(郭沫若:《人民至上主义文艺》初发表于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上海《文汇报》,系该报副刊《新文艺》发刊词。现收入《郭沫若全集》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北京1版)
团结抗战是文协最大的成就,也可说就是文协的生命。文协的每一个分子当然应该保护这个生命,加强这个生命,发展这个生命。
尽管有少数人在中伤诽谤,离间挑拨,然而我们总不好因为那些人便把这个宝贵的生命抛弃。
有人说,搞文协就是干政治活动,搞文协的人为的是要满足领袖欲。这种人无疑地是一种恶性的诽谤者。他其实也正是领袖欲过剩,而在替某种政治效忠。
有人说,文学是有超越性的,以永远普遍的人性为对象,文协标榜“抗战”,根本就违背文学的本质。这种人更不啻是在替敌人说话了。
自命清高而又不甘寂寞者流的病态戚察,无疑地是退化的象征,那要叫多细胞体退回到单细胞的状态。但是可能吗?是应该吗?(郭沫若:《沿着进化的路向前进——纪念文协五周年》1947年12月上海大孚出版公司《沸羹集》《郭沫若全集》19卷第390-391页)
1948年1月3日,一群已离校的中大师生在海边一座洋房的四楼举行新年团拜会:郭沫若应邀参加,并在热烈掌声中发表了《一年来中国文艺运动及其发展趋势》的讲演。其中讲到“反人民的文艺”时说:
郭先生说:文艺方面像政治一样,一方面有为人民的文艺。一方面有反人民的文艺。
反人民的文艺有四种,第一种是茶色文艺。搞这种文艺的一群中,有肖乾,沈从文,易君左,徐仲年等。肖乾比易君左还坏。他们有钱有地盘,更有厚的脸皮。硬是要打击他们才行。
(邓初民先生插嘴说:硬是要消灭他们才行。在座的都笑起来表示赞成)
第二种是黄色文艺。这是反民主阵营的别动队。要消灭他们,不光是文艺方面的问题,还得靠政治上的努力。
第三种是无所谓的文艺,这是文艺上的所谓中间路线。政治上的中间路线已被打倒,但文艺上的中间路线还没有人去清算。这是客气过份。另一部分人是思想不搞通,自以为既非共,也非国,很清高,其实所写的东西是反人民的。对于这些人,可能时应开导,争取,否则即予以揭穿。
第四种是通红的文艺,托派的文艺。他们骂《李有才板话》。他们骂陈白尘的《升官图》。对于这种文艺,也应如初老所说,应予消灭。
可见“打击反人民的文艺”是大家的共识。为了打击“反人民的文艺”,香港进步文艺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创办了《大众文艺丛刊》(双月刊),第一辑确定了《文艺的新方向》,发表了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郭沫若应约,分工撰写了《斥反动文艺》,文章是对形形色色的反人民文艺进行揭露和批判。沈从文不过是其中的一种。文章里这样说的:
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衡定是非善恶的标准非常鲜明。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是,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我们今天来衡论文艺也就是立在这个标准上的,所谓反动文艺,就是不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那种作品、倾向、提倡。大别地说,是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封建性的,另一种是买办性的。今天的反动势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集封建与买办之大成,他们是全面武装,武装到了牙齿了。文艺是宣传的利器,在这一方面不用说也早已全面动员“戡乱”了(《全集》注释: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政府颁布《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从政治上对人民实行血腥镇压,在文艺方面也加强其法西斯统治。)。因此,在反动文艺这一个大网篮里面,倒真真是五花八门,红黄蓝白黑,色色俱全的。
什么是红?我在这儿只想说桃红色的红。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如沈从文的《摘星录》、《看云录》,及某些“作家”自鸣得意的新式《金瓶梅》,尽管他们有着怎样的借口,说屈原的《离骚》咏美人香草,索罗门的《雅歌》也作女体的颂扬,但他们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正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里再生的时候,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之为“民族自杀悲剧”,把全中国的爱国青年学生斥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而企图在“报纸副刊”上进行其和革命“游离”的新第三方面,所谓“第四组织”。(这些话见所作《一种新希望》,登在去年十月二十一日的《益世报》。)这位“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你看他的抱负多大,他不是存心要做一个摩登文素臣吗?(郭沫若:《斥反动文艺》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八年五月香港生活书店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双月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现收入《郭沫若全集》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北京1版)
这里,郭沫若所揭露的难道不是事实吗?铁的事实,白纸墨字。在两个命运、两种前途决战的斗争中,沈从文为代表的反人民的文艺正是麻醉人们的毒药,阻碍人民解放战争的石头,给予揭露、给予打击是完全必要的,是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作者都应该做的,何况郭沫若负有领导人民文艺运动的神圣职责,他和其他进步文艺工作者一道,对沈从文的错误言行进行揭露、批评、甚至打击,有什么不对呢?沈从文的自杀,沈从文的转业,能归咎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一文吗?鲁迅说得好!“世间有所谓‘就是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鲁迅:《“题未定草”(七)》《鲁迅全集》第6卷)
2016年10月于蓉城川大花园寓所
(责任编辑:陈俐)
2016-11-16
王锦厚,男,四川大学出版社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