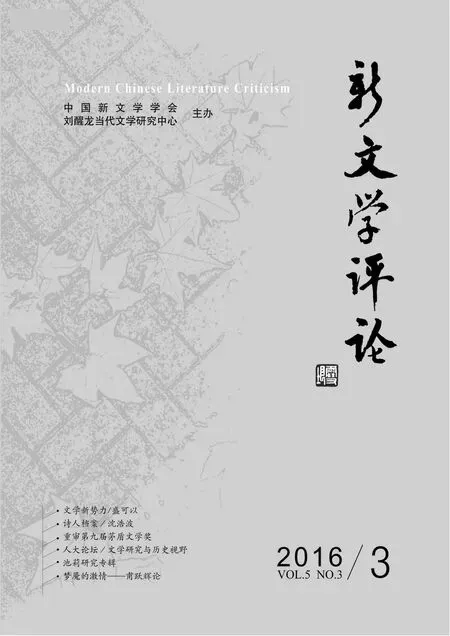时代回声与生命感悟池莉小说创作论
2016-11-25◆阳燕
◆ 阳 燕
时代回声与生命感悟池莉小说创作论
◆ 阳 燕
从1978年发表第一首诗歌算起,池莉的文学创作迄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而这个时间表恰好对应着中国改革开放,由传统的政治主导型社会向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信息化、传媒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作为一位对时代变革与生活变化有着敏锐触觉的写作者,池莉将其对于社会、历史、文化、生活的观察与思考诉诸文字,描摹了时代变化投射于日常生活的丰富侧影,同时,与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也保持了高度的契合。“现在的城市生活无时无刻不发生着急骤的变化,荣与辱、富与穷、相聚和别离、爱情和仇恨等等,皆可以在瞬间转换,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历史阶段。希望与困惑并存,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撞击起了比物质世界更大的波澜。我的小说,便在这波澜中载沉载浮。”①池莉将时代的印辙与个体的生命感悟融汇一起,转化成以市民为本位的文学书写,以平民化的立场、仿真性的叙述、地域性的色调凝聚成极富世俗性与亲和力的艺术个性,跻身1980年代末新写实文学潮流的前列,并一直延续了强劲的创作势头,成为中国当代文坛颇具影响力与代表性的作家之一。追踪时代步履且以普通市民生活为契入点的创作,既为池莉赢得了读者的广泛欢迎,获得了市场的巨大成功,也因此备受质疑与争议,使池莉小说及池莉现象拥有了更丰富多元的观察角度与言说空间。
一
池莉的小说创作始于1980年代初期,《妙龄时光》、《鸽子》、《有土地,就会有足迹》、《月儿好》、《雨中的太阳》、《细腰》是她最早的一批“试笔之作”,表达对纯真自由的爱情的渴望、对崇高理想与事业的追求、对真善美品质的守护,情感细腻、文笔雅致、风格清新。《月儿好》是池莉“第一篇引起国内注目的小说”②,描述了明月好经历恋人悔婚、丈夫病亡、生活沧桑后依然保持人格尊严和精神高洁,并凭借其乐观、坚韧、勤劳重新开拓生活之路的故事,使一个传统的道德化的“弃妇”母题焕发了别致的新意。作者赋予主人公“被无情的岁月和故乡的自然山水雕得如此美丽”的形象,用散文化的笔触抒写人物内心深处婉转的情愫,用优美隽永的语言描绘襄河边的风物人情,景物的明月和人物的明月相互映衬,营造出一种诗情画意的审美意境。池莉早期的小说大多是一种“模仿性”的写作,依据“前人的目光”看取生活,仿造“文学名著的创作成规、言说模式”进行写作,情节简单、人物纯粹、主题明朗、富有理想化色彩与抒情性意味。初涉文坛的池莉难免单纯轻浅,但她执着探索人生意义,侧重发掘生活之美与人性之善,彰显女性作者特有的敏感与细腻,为之后的文学之旅奠定了良好的开端。
行医八年,池莉经历了“赤裸裸的生与死,赤裸裸的人生痛苦”,其注意力日渐转向“注重真实的人生过程本身”③。1987年,几经退稿的《烦恼人生》在《上海文学》刊出,标志着池莉开始了“撕裂”过去、找到“自己”的创作新起点——作者从崇高、优美、诗意的文学惯例中走了出来,将视线转向卑微平凡的小人物及其平淡琐屑的世俗生活。《烦恼人生》以近乎摄像的方式“跟踪”了普通产业工人印家厚24小时的行程,循着时间的变化和地点的转换依次铺叙了他一天中工作、生活及情感的流水账,巨细无遗、单调琐屑、烦冗沉重。这种极尽逼真的描述试图还原生活的本来面目,展示其“毛茸茸”的质感,表现得富有弹性和张力,主人公的生存样貌与心理状态也把握得比较准确。作者将印家厚塑造为一个在理想与世俗、物质与精神之间摇摆游走的形象,他对工作与事业富有责任心、自豪感,对美好的情感也不乏憧憬和向往,但现实而具体的日常生活却令其深陷其中,难以升华,无可逃避。如果说,《烦恼人生》涉及了面对理想失落时的些微挣扎,之后的《不谈爱情》和《太阳出世》则将世俗性的日常生活完全书写为普通市民生活的全部重心:前者从婚姻角度细致描述了知识分子庄建非和平民女子吉玲从恋爱到进入婚姻的种种纠葛,后者则逼真地记录了赵胜天和李小兰结婚、怀孕、生产、养育孩子的冗长琐碎过程。池莉的“人生”三部曲为我们真实再现了一幅幅武汉市民凡庸平实的生活图景:上班下班、挤车子、跑月票、工资奖金、柴米油盐、住房紧张、气候冷暖、鸡毛蒜皮……“她不拔高、不放大、不矫饰,充分深入现实人生、日常生活及婚姻关系中的琐屑、辛酸和艰辛。”④印家厚们的人生烦恼来源于物质困窘主导的日常生存的挤压,其庸常困顿、沉重黯淡、毫无诗意的生活折射出了处身时代变迁漩涡中普通人群的敏感、不安与焦虑,成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折点上“城与人”的一个缩影。
与“人生”三部曲类似的创作还有《一冬无雪》、《你是一条河》、《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绿水长流》,这些小说以普通人物为主角,以世俗生活为内容,采用生活流式的仿真叙事,语言质朴细致,以行文平实细琐,契合了80年代末期新写实主义的创作潮流。此外,池莉还以平民化的视角、世俗化的立场观照历史人物的命运起落,《预谋杀人》、《滴血晚霞》、《凝眸》追溯了历史辙印中个人的生命遭际和心灵轨迹,揭示了历史进程与个人生存之间的歧离与悖反。池莉将普通凡人的世俗人生推向前台,重新确认了被传统的宏大叙事忽视或遮蔽的个体存在,纠正了主流文学长久以来的高调话语、空疏风气,这无疑具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但同时,池莉对世俗生活的张扬又建立于颠覆、摒弃精神性价值体系的基础之上,消解爱情的浪漫与诗意,拆穿理想主义的神圣和崇高,使其创作质朴有余、超越不足。
90年代中期之后,市场经济全面铺开,消费社会迅速形成,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出现了巨大变化,池莉的创作也发生了“战略性转移,正在由静态人生素描转为动态人生速写。由社会结构内部关系的社会静力学研究,转为历史过程、社会变迁等社会动力学研究”⑤。在此期间,池莉固然关注到了时代转型中被动者、落伍者的犹疑、愤懑与抱怨,也描摹了金钱与实利的环境下坚持理想者的操守与寂寞,但她笔下的主人公已从活命顺世的芸芸众生转向了不乏传奇色彩的市井强者与时代弄潮儿。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孤苦伶仃的小丁从孤儿变成了百万富翁(《化蛹为蝶》),本分勤谨颇有前途的机关职员王建国在外界的诱惑和刺激下终于下海经商(《午夜起舞》),陆武桥从一个当年的车间主任变身为餐馆小老板(《你以为你是谁》),康伟业由一个肉联厂工人成了叱咤商海的风云人物(《来来往往》),失业的来双扬则一路打拼成了吉庆街上个体户生意人的样板与偶像(《生活秀》)。在经济转轨与市场竞争的新形势下,陆武桥、康伟业、来双扬,以及《口红》中的赵耀根、《小姐你早》中的王自力、《水与火的缠绵》中的高勇、邝园等,皆或被动或主动地离开了传统体制,放弃固有的生活模式,他们不再延继印家厚式的循规蹈矩、知足能忍、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而是不满现状,拼搏进取,凭自己的远见、胆识和能力开拓事业,以种种合法或不那么合法的手段致富。停薪留职、下海经商、个体户、企业家、白领、商人、酒吧、饭店、歌厅成为池莉90年代小说中频繁出现的新词汇,在这些新词汇构筑的新场景里,摆脱了生活重负与情感压抑的“金钱英雄”康伟业们与宜欣、林珠、时雨蓬等更年轻、前卫的新人类一道,完成了池莉对于市场经济时代金钱神话的书写。同时,这些被称为“都市传奇”的小说的戏剧化故事模式、大众化叙事风格、时尚化审美方式,也极大地契合了普通大众的阅读趣味,将池莉及其创作推向了畅销书、影视改编等新的生产方式。
“体制与经济的复杂变化,中国大陆男人这一群体经历着大起大落,大悲大喜,他们腐败着,消亡着,或者成长着,成熟着。”⑥作如是观察的池莉叙述了康伟业、赵耀根等人在商业竞争中不择手段聚敛财富、在情感上抛弃妻子另结新欢的故事,既铺排了金钱为之带来的物欲膨胀和奢侈挥霍,也对其不负责、过分膨胀的欲望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讽刺和批判。尽管池莉力图在“升腾与坠落之间”进行一种理性的折中的表达⑦,但总体而言,其创作更多的还是以不无欣赏的态度肯定物欲时代的世俗生活,赋予追逐金钱物欲者的行动无可辩驳的现实合理性。池莉以小说叙事进行着时代变迁中市民生活的现象式描述,但对变化所导致的精神应对、心灵反省却涉及甚少,不乏仓促急就、流于表面的遗憾。
二
从初涉文坛的清新诗意,到新写实时期的现实仿真,再到90年代中后期的“都市传奇”,池莉敏锐捕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日新月异,并用独特的视角反映变化中人们的现实生活,其创作呈现出了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⑧。从历时角度观察,池莉的小说创作的确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甚至转向,但池莉对个人创作一以贯之的东西尤其看重,她一再提醒读者:“从我的主观意识来说,我的文学立场和写作视点,从八十年代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变化,只是进一步地在向纵深探索和发展……读者感到的变化只是小说的取材、结构、语言之类的变化,都是技术变化,不是内核的改变。”⑨从池莉小说创作的整体来看,其所谓没有改变的内核即是以市民形象和世俗生活为主导的写作视点,以平民立场和世俗情怀为作品的普遍底色。
从“烦恼人生”三部曲开始,池莉即执着表现普通市民的生存状态、命运浮沉、喜怒哀乐,从衣食住行、七情六欲、婚丧嫁娶、家长里短等普通人最日常而世俗的生活现象、生存状态入手,观照社会与生活的变化,并以此彰显生活之真、人性之常。从印家厚、吉玲、李小兰、赵胜天,到陆武桥、康伟业、赵耀根、来双扬,这一系列人物及其故事构成了社会转型背景下城市生活的演变与发展,彰显了一个市民阶层从萌芽、崛起到不断壮大的过程。池莉笔下的人物形象尽管具有产业工人、公司职员、商人、小贩、知识分子等不同的身份标识,但池莉大多从普通市民的角度去理解他们、诠释他们,并让他们带着“市民”的文化与情感认同成为生活的主体、文学的主角,为市民文化争取表征自身的话语权力。对于小市民这个概念及其指称的特定群落与文化内涵,池莉自有一番客观而清醒的认识:“自从封建社会消亡之后,中国便不再有贵族。贵族必须具备两方面的条件:物质的和精神的。光是精神或者光是物质都不是真正的贵族。所以‘印家厚’是小市民,知识分子‘庄建非’也是小市民,我也是小市民。在如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家全是普通劳动者。我自称为小市民,丝毫没有自嘲的意思,更没有自贬的意思。”⑩对市民具有高度情感认同的池莉非常认可世俗之于文艺的内在生命力,追求一种“大俗即大雅”的审美之境。因此,池莉宣言:“我希望我具备世俗的感受能力和世俗的眼光,还有世俗的语言,以便我与人们进行毫无障碍的交流,以便我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观察生命的视点。我尊重、喜欢和敬畏在人们身上正在发生的一切和正存在的一切。这一切皆是生命的挣扎与奋斗,它们看来是我熟悉的日常生活,是生老病死,但是它们的本质惊心动魄,引人共鸣和令人感动。”
池莉式的市民小说的出现,既是社会转型期“放弃理想、疏离政治、肯定现世”的时代风潮影响的结果,也与池莉本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际遇的变化相关,同时还与地域性的文化环境有密切关联。对于武汉这座城市及生活于斯的市民,池莉怀有深厚的情感,正是透过武汉这个窗口,池莉观察、探索并书写下了时代变化及社会发展的脉动节律。池莉的创作多以武汉市民为人物原型,以武汉的世俗生活为书写对象,以武汉的民俗风情为环境营造,建构起了一整套关于汉味文化的象征性符码,成为湖北汉味文学的典范与代表。植根于武汉这片熟悉的土壤,池莉的小说涵盖了数量丰富、元气淋漓的汉味元素,包括武汉的地理风景(如长江大桥、水陆码头、吉庆街、汉正街、花楼街),美食特产(如凉面、热干面、豆皮、糊米酒、鸭脖子、家常小菜),乡情俗貌(如过江的轮渡、消夏的竹床阵),以及大量原汁原味、地道纯正的方言俗俚,使小说真切细致、鲜活自然,富含生活的质感并充满了浓郁的汉味气息。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武汉是一个世俗化程度极高的城市,暴冷暴热的气候、艰窘恶劣的生存环境以及码头文化、商业文化的底蕴,共同滋养了武汉及其市民特有的民风脾性,展现为热闹喧嚣、粗放世俗的文化氛围,务实市侩、机智练达的处世准则,坚韧顽强、隐忍顺应的人生哲学。池莉生动地刻画了印家厚、陆武桥、吉玲、辣辣、来双扬等市民能屈能伸、世故精明、泼辣幽默的性格特点,对武汉人将一切(包括爱情、婚姻)都看作“生意”的实用主义心态,及其蕴藏于内的粗野顽强的生命能量,都表现得十分到位。池莉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是汉味文学中堪称标本式的作品,作者用极简的笔墨、极短的篇幅镌刻了一桢灵动鲜活且略带喜剧色彩的武汉消夏图,从酷热无比的天气到俏皮无聊的闲话,从家常的饮食起居到心理的弯弯绕绕,再点染以浓郁特色的方言俗语、民俗风情,举重若轻地展现了武汉人充满生之趣味的生存形式,刻画了武汉市民乐感自在、充实坦然的文化性格。主人公燕华是一个典型的武汉姑娘,泼辣率真而又善良体贴,小说以其驾驶早班公汽“轻轻在竹床的走廊里穿行”作结,“她尽量不踩油门,让车像人一样悄悄走路”这个细节无疑是作者世俗情怀的外显,为作品涂抹了一笔温情脉脉的暖色调。
对池莉而言,市民小说既是题材意义上的概念,也关涉其特定的创作立场、价值趋向和审美趣味。在鲜明的平民立场和强烈的世俗情怀的驱动下,池莉拒绝提升、努力沉潜,对庸常困顿、毫无诗意的世俗生活报以认同、顺应甚至赞美的态度,以一种平和温馨的叙事口吻书写日常现实,以温情的目光检视凡俗人生,以不无欣赏的态度肯定市民的道德人格,营构“活着就好”的“过日子”的生存哲学与达观质朴的价值观念。为了强化市民形象及其世俗化生活的真、美、善,池莉有意忽视对形而上精神层面的追寻与书写,坚持以实用主义的市民价值观念衡量世事人情,不惜用夸饰嘲讽的笔墨刻画笔下并不太多的知识分子形象,如《你以为你是谁》中的李老师、《一去永不回》中的温达功夫妇、《一夜盛开如玫魂》中的苏素怀、《小姐你早》中的戚润物等,皆自私软弱、虚伪庸俗、冷漠固执、不近人情,与圆熟通透、怡然自若的市民形象构成鲜明对比。相反,《生活秀》中的来双扬则呈现了另一番景象,虽然出身贫寒之家,却在吉庆街上将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凭借其世俗生存中练就的本领智慧解决一个又一个的生活难题:放弃了背叛婚姻的丈夫,落实了来家老房子的产权归属,处理好了与父母和后母的关系,以务实态度对待与卓雄洲的爱情,交清了妹妹拖欠原单位的劳务费,照顾吸毒的弟弟与被父母忽略的侄子,将市井强者的人生传奇推向极致。在池莉满怀激情的笔墨浸润下,来双扬坚强自信、有情有义、光艳美丽、泼辣能干、游刃有余,堪称市民生存哲学的完美典范,而对其性格行为中暴露出来的缺点与弱点,作者则多以“做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堂皇借口给予宽容和谅解。显然,过于强烈的世俗情怀与趣味影响了作者应有的理性判断,对市民大众的价值观不加辨析地接受,对藏污纳垢的市民生活情态缺乏必要距离的审视,难免淹没了作者并不深入的思考,使池莉小说的内蕴变得单薄平浅。
三
以现实人生关怀为主调的湖北女性作家缺乏强烈、自觉的女性意识,她们的创作极少挑战男权中心文化、解构男性中心话语,也极少专注女性的身体感受、内心欲望等隐秘体验,而将女性的丰富性和微妙性融汇于社会生活之中。因此,笔者曾将湖北女性作家的创作称为“准女性主义”的创作。作为湖北女性作家群中不可或缺的代表,池莉的小说尤其契合“准女性主义”的内涵。
创作伊始,池莉即对女性形象、女性故事、女性命运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妙龄时光》、《月儿好》、《细腰》、《青奴》等小说基本上都可归结为“女人的故事”,主人公形象的刻画也大都以温柔、贤惠、善良、宽容等传统美德为依归。在《烦恼人生》等新写实小说中,池莉同样塑造了诸多女性形象,但“我们看到的却是芸芸众生中男人和女人共有的生存烦恼与艰辛,它并没有因为性别的不同有什么本质的差别”。显然,到1980年代末期,池莉以世俗人生为主旨的小说尚未触及真正意义上的“性别”思考,她“关注的是普泛意义上的人而不是一种性别意义上的女人,她笔下的女性人物不是性别秩序的质疑者与挑战者,仅仅是一种性别身份,而不具备价值判断的意义”。即便如此,在有关现实人生、日常生活的观察与书写中,池莉已凭借其自身的善感、细腻、敏锐把握到了女性世界的两个基本问题:其一是对爱情和婚姻的疑虑,其二是对女性独立意识的崇扬,在池莉笔下,婚恋与女性这两个关键词更是非常深入地缠绕在一起。
《锦绣沙滩》可以视为池莉自觉将女性意识融入婚恋叙事的开端之作。主人公立雪有着敏感而纤细的内心,对爱情婚姻始终抱有浪漫的情怀与想象,而现实的婚姻生活却令其深陷丈夫的隔膜与婆婆的非难之中,因而深刻体验到“她的尊严她的价值在这个家里被粗俗地践踏了”,女性的自我意识也由此萌生。冷漠的丈夫固然不可依靠,而原以为能够寄托情感的赵如岳后来也暴露出了伪君子的真面目,在小说中,作者给立雪安排了一条“回归”之路,以“孤军奋战”的方式去面对未来的人生长途。或者可以说,池莉的女性意识的觉醒是伴随着小说人物对婚姻生活的体认得以逐渐完成的。《锦绣沙滩》之后,池莉笔下的女性形象越来越趋向成熟、理智、世故,她们开始自觉自愿地规避“无用”的爱情或“危险”的爱情,如《你是一条河》中的辣辣为严酷生活所迫不断调整自己的性爱角色,却始终拒斥无用书生小叔子的浪漫求爱;《绿水长流》中的女作家与邂逅的异性两情相悦,甚至还有共处一室的偶然机缘,却“宁愿留下一片美丽的缺憾”。池莉笔下对爱情持怀疑、拒绝、否定态度的女人们,已经不再将爱情婚姻视为自己毕生的“全部事业”,无论因讲求生活实际而“不谈爱情”,抑或因洞穿爱情的虚妄而“不谈爱情”,这些主动放弃爱情的行动中已隐含了某种属于女性主体的因子。
90年代中后期,随着都市新传奇的出现,池莉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更为丰满细腻。开放的环境为女性发展提供了更阔大的平台、宽广的视野、多元的选择,也为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保持人格与精神上的独立自尊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来来往往》中的林珠一改池莉之前作品中常见的灰扑扑、粗拉拉的女性形象,而是一个明艳动人、聪明能干的白领丽人,她的出现使康伟业与段莉娜之间带着计划经济时代印记的婚姻濒临危机,但池莉并没有对第三者林珠作简单化的道德审判,而以不无欣赏的笔墨刻画了林珠投入爱时的真诚痴情与放弃爱时的果断潇洒,呈现了一个更有主见、更富理智、更能处变不惊游刃有余的女性形象。《云破处》和《小姐你早》是池莉女权色彩最浓郁的两部作品,前者的最强音是曾美善以柔弱之躯愤怒杀夫的酷烈描述,后者的重心则是戚润物与其他女性结成姐妹同盟惩罚背叛情感的丈夫的情节设计,小说尖锐呈现了“男性绝望”和“两性对峙”的主题,主人公的女性意识也以强烈的夸张之姿和非理性的报复手段得到彰显。
但《云破处》和《小姐你早》只是池莉女性意识觉醒的一次偶而为之的突进,池莉的大部分作品并不刻意将男女双方置于强烈的性别对抗之中。事实上,池莉塑造的女性形象大都以温和、圆润、世故为底色,她们对自身性别意识的体认和表达并不偏执焦躁、撕裂冲撞,反而显得沉静自如、淡定从容,彰显出一种母性的成熟气度。正是凭借着这份生活历练而就的成熟,梅莹、辣辣、易明莉等母亲或来双扬等深具母性意识的女性才能看穿男性坚硬盔甲之下的软弱,占据居高临下的心理优势,以沉默和距离来抗拒男性社会所主导的大众情理与公共原则,以迂回和包容来抵御源自男性世界的围困和侵蚀,既不自我否认,也不自我压抑,祛除任何形式的依附以使自身获得超越和自由。
池莉无意以孤立、悬空的方式描述女性,总是将女性生活融入更广阔的社会发展与时代环境,描摹女性与社会、时代、历史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水与火的缠绵》和《所以》这两部长篇小说中,作者以改革开放后中国近40年的历史变迁为背景展现女性主人公的成长历程及人生追求,曾芒芒和叶紫终于蜕变成长为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成熟女性,她们的对立物固然是一个个的男性、一段段的爱情与婚姻,但父母、兄妹、家庭以及整个的政治、社会环境都是她们大容量的人生舞台,在池莉笔下,女性命运和社会历史达到了比较深入的交融。池莉近作《她的城》虽然只是一个中篇,却承载了作者非凡的野心,即如小说标题所提示的,池莉希望借此完成一部关于女性与城市、女性与时代、女性与生活、女性与女性之“真相”的书写。小说以汉口最繁华的中山大道水塔街片区的一间擦鞋店为背景,塑造了店老板蜜姐、蜜姐的婆婆、擦鞋工逢春三个不同年龄、身份、性格的女性形象,既描述了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与酸甜苦辣,也叙写了武汉这个城市的历史渊源、前世今生及其气质底蕴。小说以“敞的”这经典方言词汇概括武汉的城市性格,三个女性主人公的性格气质则与武汉这座城市相容相映、相互诠释,即如蜜姐婆婆的宽容通透、蜜姐的精明洒脱、逢春的明亮快意。另一方面,小说将三个带着各自历史、经历、命运、创伤的女性聚集一处,充分渲染了女性之间惺惺相惜、相濡以沫、温暖默契的亲情与友情。与《小姐你早》不同的是,《她的城》中的“姐妹情谊”并不以对抗男性权利为旨归,而是遭遇生活劫难的女人们共同分担精神痛苦、缓解心灵孤独的庇护所,对男性不乏同情与理解,但女性之间却获得了更深层次的相互信赖与支持。
四
从新写实到新传奇,透过世俗生活、市民心态、城市形象、女性意识等不同角度的观察与刻写,池莉以小说的形式为1980年代以来这不断变化的时代留下了鲜活的记忆,提供了某些证言。尽管得到的回应褒贬不一、毁誉参半,池莉的文学思考与艺术探索却从未停止,在那些不乏商业气息与市场印痕的小说里,已隐含了这样的提问——当物质生活满足后,精神困扰将以怎样的方式呈现?伴随着这样的思索,进入新世纪之后,池莉的创作逐渐由都市的金钱传奇回返到普通市民的生存,但此“回返”并非退回“人生”三部曲的原地,而是试图超越物质挤压下人生的黯淡与沉重,在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重新建构对日常生活的审美观照和精神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将池莉2003年的《有了快感你就喊》看作其1987年《烦恼人生》的新篇章,但卞容大较之印家厚,已有了更丰富的性格内涵与不一样的人生选择。在《有了快感你就喊》这部小说中,池莉有意识地赋予主人公(卞容大)及其出生地(集贤巷)特别的文化意味,指示着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濡染之人、之地在市场化时代的变化。卞容大孤独压抑、内向敏感,同时也善良诚实、勤奋上进、富有责任感与事业心,以“积极的沉默”作为自己的生存之道与立身之本,但在父权桎梏、婚姻乏味、事业受挫等多重困境之下,普通职员卞容大早已丧失了阳刚之气和生命活力。集贤巷中流行着钱财、器物、麻将、新衣,物化现象已经渗入了所有的血缘亲情、人际关系之中,徒剩冷漠、猜忌和不信任,让卞容大感觉自己“没有亲人”。然而,在生活中饱受辛酸挣扎之苦的卞容大并没有就此沉沦,无论对势利的父亲还是难以沟通的妻子,卞容大都恪尽职责、忍让宽谅,“男人”对卞容大而言不仅仅是性别意义上的概念,更是文化上、道德上的自我塑形。当卞容大因正义之举遭受报复而下岗之后,他经历了更痛苦的人生挣扎和更猛烈的心理冲撞,终于在一次应聘中决定“离开”和“远行”。对于已经中年的卞容大来说,去西藏与其说是为优厚的工资待遇,不如说是“离开”和“远行”所赋予的自我拯救的意义,卞容大终于为自己的人生打开了一扇窗,让自己的人生有了些许诗意的光彩,真正体会到了“有了快感你就喊”的阳刚之意。在小说中,池莉直抒胸臆:“他是一个备受压抑的窝囊的阳刚男人。可是他一直在坚持着什么, 一直在追求着什么,终于,他被迫开始了以逃离为形式的自我坚守与自我救赎。中国男人尤其需要这种精神,人性的、自由的、坚定的、革命的、悲壮的。”在各种访谈与自述中,池莉反复强调“有了快感你就喊”是一句充满阳刚之气的军中格言,刊印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兵行囊里的火柴盒封面,这或许暗示着,在卞容大的故事里,作者试图以西方的自由人性去修正完善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原则与道德规范的企图。
《托尔斯泰围巾》则另辟蹊径,崇扬了中国传统儒道文化对庸常人生的诗意提升与发现。小说中,老扁担和张华是两个生活穷困、地位卑微的底层人,前者是进城的民工,后者是小区车棚的看守人,一个木讷寡言,一个爽朗乐天,池莉以这两个形象诠释了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老扁担用七年如一日的坚持在小区收破烂,依靠自己的忍耐、敦厚、知好歹、懂感恩等“好品相”赢得了信任和脸面;张华中年丧夫、女儿痴肥、生活艰窘,但她从不自怨自艾,反倒古道热肠,她精心照顾自己的女儿,也体恤他人、同情弱者、排解矛盾、主持公道,用善意、仁心和骨气活得“自然、敞亮”。小说通过一个作家“我”来观察、叙述老扁担和张华的生活态度,“我”由此也得到精神净化,感悟到“即便命运让人穷困到某一田地,也可以做到孔子赞赏的境界: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
池莉的平民立场和世俗情怀让她对知识分子抱有较深的怀疑和轻蔑,在其小说中,知识分子常是被贬抑的对象,精神生活和形而上的追求也常被作者给予漫画式的夸张甚至无情嘲弄。池莉对知识分子不加分析地肆意讽刺也是导致其创作格局狭窄的原因之一,遭到了评论界诸多非议。然而,池莉的《看麦娘》是一个例外,或也是一个改变。《看麦娘》的叙述者“我”(即主人公易明莉)是国家一级药剂师,拥有优越的社会地位、顺遂的个人事业、闲适的生活环境,丈夫也积极进取、名利双收。小说中,易明莉虽然并未遭遇普通市民日常的生活烦恼或底层市民难免的衣食之忧,却被越来越强烈的焦虑感所笼罩,而焦虑根源于对人之生存意义的困惑与迷失。养女容容的突然失踪使易明莉的焦虑更加放大,寻找容容的过程既是她感受现实环境欲望横流、疯狂混乱的过程,也是其逐渐清理生命内核、寻找生命真义和灵魂方向的过程。在易明莉的世界,无论是功利主义的丈夫于世杰,还是实用主义的养女容容,抑或母亲、兄弟、上司、同事,都与其错位疏离、相距遥远,惟有看麦娘这种植物带给她心灵安慰。看麦娘连接着易明莉记忆中相濡以沫的父女之情,记载着与上官瑞芳真挚恒久的友情,它指向澄澈、自由、明净的精神境界,成为主人公超越困境、抵抗孤独的心灵支柱。当质朴柔韧的植物看麦娘成为单纯而充实的生存方式的总体象征时,小说对世俗生活的质疑批判已经让位于对精神、价值、灵魂的寻找与求证,对池莉而言,这无疑是一次非常有价值的探索,让我们看到了她立足世俗而又超越世俗的可能。
第四届“大家·红河文学奖”授予了池莉的《看麦娘》,认为“《看麦娘》虽属写实类作品,但池莉却能写出意外之境、意外之意来。表明作家从‘新’写实走向了‘心’写实。她不再只是世俗生活的记录者和认同者,《看麦娘》是她创作的一次涅槃,也是小说精神的一次升腾”。对生命价值与存在意义的重新张扬,对诗意之美与艺术之真的重新开掘,使池莉的文学创作经过一个回环后进入了又一个新的通道,显然,这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让人期待作者下一部更完美的升腾之作。
注释:
①池莉:《说与读者》,《池莉文集1》,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②杨书案:《清水出芙蓉——我所认识的池莉》,《时代文学》1999年第2期。
③池莉:《创作,从生命中来》,《小说评论》2003年第1期。
④戴锦华:《池莉:神圣的烦恼人生》,《文学评论》1995年第6期。
⑤朱青:《生活的动感——池莉近作扫描》,《小说评论》1999年第4期。
⑥池莉:《读我文章若受兰仪》,《成为最接近天使的物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73~274页。
⑦於可训:《在升腾与坠落之间——漫论池莉近作的人生模式》,《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1期。
⑧刘川鄂:《小市民 名作家:池莉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5页。
⑨池莉:《〈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访谈录》,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7页。
⑩池莉:《我坦率说》,《池莉文集4》,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年版,第 223 页。
湖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