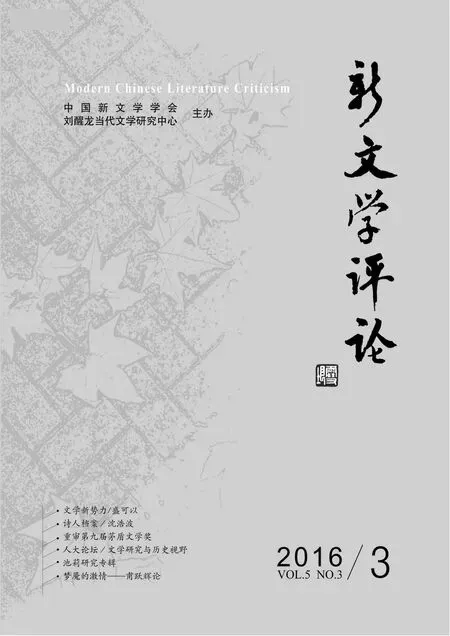孙犁在革命文学中的复杂性
2016-11-25◆李屹
◆ 李 屹
孙犁在革命文学中的复杂性
◆ 李 屹
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1953年版)里为孙犁在文学史上安置了一个不低的位置,这位根正苗红的解放区作家被放进了“进步”的文学潮流里——按照《中国新文学史稿》的体例,孙犁是“新型小说”这一章的代表作家之一,其写作一定是要符合“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反映解放区面貌”的,更深一步说,是要符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中对新中国文艺方向的定义。的确,孙犁在解放区发表的作品从大主题上可以归入“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其作品的确让“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①。但孙犁的这一进步性并不是完美的,其作品中对男女爱情的细致情绪写得“太过生动”②,必然与上述“大主题”生出龃龉感。批评意见也多集中于此,特别是因为1950年代后思想界和文化界“左”倾,孙犁在人物描写与主题刻画之间的矛盾被提高到政治正确与否的层面,曾被人夸赞的对女性的描写和对生活细节的生动刻画彼时成了小资产阶级趣味,孙犁其人其文也被定下了“花鸟虫鱼、风花雪月”的断语。近年来重评孙犁是文学界乃至文化界的一个热点,“晚年孙犁”研究的兴起与对其国学造诣的评判,已经在当代把孙犁从“解放区作家”拉到了“现代文人”或“最好的读书人”③的行列中。然而,无论孙犁是根正苗红的解放区作家,还是闭关读书的现代文人(更何况这两者本属于一个主体,是不能因此废彼的),他与左翼革命的关系是不能回避的问题。更加重要的是,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在文学史上应该如何描述孙犁,更关系到当代文学如何处理左翼革命与“左”倾错误对知识分子的影响这一重要命题。
近年来“晚年孙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断在媒体上曝光,这既与天津地区文化宣传工作有关,同时也是当代文学场向着某种形象化的“晚年孙犁”倾斜。为什么晚年孙犁的形象被作为某种需要尊敬、怀念的对象不断提起,而革命时代的孙犁却需要依靠“晚年孙犁”才能得到重视呢?从很多研究文章上可以看到,“文革”后孙犁出版的文集成为人们研究他的革命观和人生观的重要路径——很大程度上,“晚年孙犁”指的是1979年以来一年一本或两年一本出版的孙犁散文或杂文所构建起来的形象,是自《晚华集》(1979年)至《曲终集》(1995年)以及《芸斋书简》(1998年)、《书衣文录》(1998年)所构建起的“作者形象”。而在1990出版的《孙犁评传》(周申明、杨振喜著)中,“晚年孙犁”更接近于当代作家学者化的先行者:“他不仅学识渊博,论述广泛,指陈得失,明辨是非,颇具学者风范。而更为重要的,是他十分强调作家的‘人格’修养,强调‘人品与文品’的一致,强调作家的‘立命修身之道’。一句话,他期望包括自己在内的作家们,要使自己的学问、识见、追求、责任、使命,符合‘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荣身份。”④“晚年孙犁”形象中士大夫的传统美德与儒道精神成为读者与研究者的关注点⑤,但这同时也非常容易让革命时代的孙犁显出与大环境格格不入的边缘状态。“晚年孙犁”研究的确让我们看到了孙犁品格的丰富性,但这也有忽略或压抑孙犁的革命理想和信仰的嫌疑。
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孙犁本人的论述中思考他到底怎样看待革命文学,又是怎样的内在或外在的原因使他晚年选择了内倾式的写作。这些问题,将直接回应孙犁与左翼革命的关系到底应该用怎样的方式来描述。随着新材料的披露,孙犁与左翼革命的关系在一些个人性的事件中可以有不同角度的阐释。这些阐释都有着各自敏锐的洞见,但也会存在盲点。尤其是在孙犁与革命的关系到底疏远与否,孙犁究竟是否一直坚持共产主义信仰等问题上,采取非此即彼的论述方式会使孙犁被扁平化、标签化,从而失掉其作为文学创作者敏感、内敛而又感情丰富的一面。因此,与其追问孙犁究竟与革命、与革命文学处于怎样的关系中(对某种秩序、位置和情感偏向的描述),不如探讨用怎样的方式来描述他们的关系,会让孙犁作为一个人和一个文学创作者的丰富性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⑥。
孙犁对自己是如何走上创作的,有过这样的说法:“我的创作,从抗日战争开始,是我个人对这一伟大时代、神圣战争,所作的真实记录。其中也反映了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前进脚步,我的悲欢离合。反映这一时代人民精神风貌的作品,在我的创作中,占绝大部分。其次是反映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的作品,还有根据地生产运动的作品。”⑦按照孙犁的革命经历,他虽然因种种历史巧合没有受整风运动等影响,但他应对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非常熟悉,这一段话实际上是对自己的写作动因做了非常明确的排序:首先反映人民的精神风貌,其次反映特定历史。孙犁能够理解特殊时期文艺工作的需要,也清楚地认识到革命文学所承担的政治功能和时代任务,这一点,能让他很明确地站在为革命写作的立场。1988年孙犁与郭志刚谈话时感叹:“现在我总感觉到,有人极力地否定解放区的文学。解放区文学有它的一些缺点和所谓的局限性。但是,必须和时代联系起来,把那个时代抛开,只从作品上拿今天的眼光来看,当然就发现它有很多不合时宜的地方。……作家总是带有时代的烙印,作品总是带有时代的特征。另外,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我过去总提离政治远一点,老给人家抓小辫儿。所谓远一点,就是不要图解,不要政治口号化。……当时为政治服务,也不是有人强迫,都是出自本心。参加抗日战争,那是谁逼迫的?”⑧
有趣的是,1992年的孙犁在《庸庐闲话》中将自己的写作起步区分为大的环境和个人生活的原因。关于大环境,孙犁将自己“为人生”的起点归结于初学写作时对母亲和妻子劳动的感怀,在此时“人生”与“衣食”直接相关,是一种“民以食为天”的朴素的人生观,“求生不易”,怎样“养家糊口”呢?孙犁十分坦诚:“我的文学的开始,是为人生的,也是为生活的。”⑨这一观点,早在1981年的一首《生辰自述》的古体诗中就已显露:“初学为文,意在人生,语言抒发,少年真情,同情苦弱,心忿不平。”“战争年代,厕身行伍,并非先觉,大势所趋。”⑩但孙犁之后对此做了进一步解释:“并不像现代人,把创作看得那么神圣,那么清高。因此,也写不出出尘超凡,无人间烟火气味的文字。”起承转合之间,孙犁用散文笔法把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大旗又竖了起来,在诸多创作谈、文艺论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孙犁对鲁迅以来的现实主义道路的继承从未断绝。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孙犁的“为人生”,一开始与“为生活”有很大重叠,生活不好、时局恶劣,孙犁才开始认识到革命的重要性。
诚然,现实主义是孙犁以创作参加革命的基本道路,但道路是明确的,怎么走却是自己的事,在革命现实主义传统之中加入易被批判为小布尔乔亚情调的人道主义,正是孙犁走这条路时的个人选择。郜元宝总结出孙犁写作的“三不”原则,将孙犁独特的现实主义道路的特征总结为有“柔顺美”的革命文学道德,认为孙犁的创作显示出革命文学长期被忽视的另一种传统:在启蒙与救亡之外,以孙犁为代表的创作还显示出革命文学可以发扬对人性美好的歌颂和“顺服于革命需要的‘政治觉悟’的综合”。但孙犁本人是否有过这个意图?我们不得而知。从孙犁本人的论述来看,他非常清楚自己写作的目的性,也对革命文学的宣传功能了然于心,无论是正面描述农村人民积极抗战的觉悟,还是侧面书写他们在风云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好,孙犁始终为自己留有一块抒情的园地。仅通过作家没有真实地经历过血战这一点推断孙犁无力直接描写战争的残酷性是不合理的,孙犁的切身经历加上想象力足以写出一场遭遇战,然而他的视点往往还是在表达农民战士的生命活力上,早期作品《荷花淀》的战斗模式既可以被视为游击战略的典型,也可以被视为孙犁对革命的乐观和信心。不论如何,《荷花淀》、《芦花荡》等作品中明朗的气息和乐观的精神是不可忽视的,不能以历经沧桑后的“晚年孙犁”来否定这一时期他对革命的真实态度。1980年,孙犁在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写《铁木后传》时说了下面这番话:“在中国,写小说常常是青年时代的事。人在青年,对待生活,充满热情、憧憬、幻想,他们所苦苦追求的,是没有实现的事。就像男女初恋时一样,是执着的,是如胶似漆的,赴汤蹈火的。待到晚年,艰辛历尽,风尘压身,回头一望,则常常对自己有云散雪消,花残月落之感。我说得可能低沉了一些,缺乏热情,缺乏献身的追求精神,就写不成小说了。”使用这段材料时应当小心,断章取义的话很容易看成孙犁对革命事业的看法,细读上面这番话,孙犁对续写小说的意兴阑珊,实际上是因为此身所在的时代已经不是革命年代,孙犁走上革命与创作道路时的“大环境”与诸动力也已沧海桑田,孙犁晚年这回首一望中,包含了多少往事?孙犁话中的复杂情绪,如果没有曾经真挚地爱过、参与过、奋斗过、奉献过,恐怕也不会读来如此令人感叹了。
的确,我们应该注意到孙犁写作小说的历史背景,应该正视这些复杂情感中不那么明朗、乐观的一面。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小说的写作和发表时间,就会很明显地感到孙犁这些创作存在被批评甚至批斗的危险(这些事也的确发生过):1944年,孙犁在延安写下《游击区生活一星期》,开篇第一章就是“平原景色”——对比同期在延安的其他作家,孙犁这一起笔就游离在延安整体的气氛之外,“县委同志大概给我介绍了一下游击区的情形,我觉得重要的是一些风俗人情方面的事”,到了游击区,孙犁首先用诗一样的语言描述“好风景”,让人完全感觉不到这里发生过的事情。这篇小说里的种种风景描写和对历史的叙述,都给人一种时隔多年回忆旧事的错觉。依此,可以有种种不同的阐释方法,是孙犁刻意忽略战争的残酷性呢,还是他有意以开阔的风景化解革命内部的紧张感呢?我们需要了解更多的历史背景,才能看到其中隐藏着的难言之情——这大量风景描写既不是延安气氛,也不是当时抗日与革命的气氛,更像是孙犁为了舒缓某种情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根据李展对《琴和箫》发表历程和编选情况的研究,孙犁在解放区被压抑的一部分与上述明朗、乐观的一部分,构成了孙犁此时期文学创作中复杂的存在,这既是“孙犁的文学创作潜力与主流话语规约之间具有巨大的张力”,又是孙犁在“革命与人道之间寻得的一块二者兼容的‘中间地带’”。实际上,与其把孙犁这一时期的创作视为他尝试包容革命与人道的“中间地带”,不如将其视为孙犁既表达真实情感又在特殊的革命年代坚持现实主义道路的折中选择,巨大张力存在之所也是孙犁缓冲其内心紧张、忧虑的地方。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孙犁在《琴和箫》(1945年)中对“肃托”事件的怀疑与恐惧是不能被忽视的,孙犁1986年回忆道:“我那时不是党员,没有参加过政治活动,这些问题,无论如何牵涉不到我的身上。但我过路之后,心情并不是很好。……见到两个同学的这般遭遇,又不能向别人去问究竟,心里实在纳闷。抗日是神圣的事业,我还是努力工作着。我感情脆弱,没有受过任何锻炼。出来抗日,是锻炼的开始。不久,我写了一篇内容有些伤感的抗日小说,抒发了一下这种心情。”这部分情感,是孙犁这个革命者,这个解放区作家真真切切的感觉,如果说孙犁晚年有着生命的闪光点,那就是在创作继续保有现实主义精神,不回避自己彼时复杂的情感,不否定革命的伟大意义。目前关于晚年孙犁的研究,其难点就在于怎么描述晚年孙犁的作为才能不割裂上述复杂的心理现象。
1980年,孙犁接受《文艺报》记者采访,说出了下面这段话:“我们的生活,所谓人生,很复杂。充满了矛盾和斗争。现在我们经常说真善美和假的、邪恶的东西的斗争。我们搞创作,应该从生活里面看到这种斗争,体会到这种斗争。”但是,“看到真善美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恶的极致,我不愿意写。这些东西,我体验很深,可以说是镂心刻骨的。可是我不愿意去写那些东西,我也不愿意回忆它”。需要说明的是,这段话中所谓的“邪恶的极致”特指十年动乱期间孙犁看到的人与事,但他对邪恶的态度,似乎是一以贯之的——不愿直接提起。卫建民说:“在孙犁一生的冲突中,除了个人情感生活,就是理想与现实的背离,丑恶与美好的纠结,真实与虚假的并生并育。”这的确是对孙犁复杂境遇的“简笔画”。在1985年写作的“准自传”《〈善暗室纪年〉摘抄》(1913年至1949年部分)中记录他经过至少七次逃难、逃亡或紧急转移,有过狼狈(与陈肇紧急疏散),见过枪毙(本村孙山源),在石家庄遭遇敌机轰炸,长子也在敌人大扫荡期间因病无医早夭,这一切都深深地刻在了孙犁的心里,但并未大篇幅地直接呈现在他早期小说中。“在四十年代初期,我见到、听到有一些人,因为写文章或者说话受到批判,搞得很惨。其中有我的熟人。从那个时期起。我就警惕自己,不要在写文章上犯错误。我在文字上是很敏感的,推敲自己的作品,不要它犯错误。”孙犁在早期小说中对这些事情的隐晦书写,其原因不只是郜元宝乐观的分析——“三不主义”的美学,还有着孙犁敏感的对人对事的处理方式。
其实,孙犁何止在文字上敏感,他对世态与人事的敏感洞察可能就是他小说中各种情感此起彼伏、互相缠绕的重要原因。杨联芬认为,“文革”后孙犁对时局的认定有着“体认正统的传统儒者心理”,“在语言上体现出儒家的正统忠诚”,“三四跳梁,凯觑神器,国家板荡,群效狂愚”。在孙犁同时期的回忆和言论中,让国家和人民深受磨难的,似乎不存在体制的问题,而是以“三四跳梁”和效狂愚的“群氓”形象将错误原因分派了下去。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孙犁一生最痛恨也厌烦的,还真的可能就是这些“小人”。《庸庐闲话》里专门写了“我的戒条”,大量谈论的就是怎样处理人际关系,其核心正是亲君子、远小人。“不要涉及人事方面的重大问题,或犯忌讳的事。此等事,耳闻固不可写,即亲见亦不可写。”“不写小人……在生活中,对待小人的最好办法,是不与计较,而远避之。写文章,亦应如此。”“我少年时,追慕善良,信奉道义。只知有恶社会,不知有恶人。古人善恶之说,君子小人之别,以为是庸俗之见。及至晚年,乃于实际生活中,体会到:小人之卑鄙心怀,常常出于平常人的意想。因此,惧闻恶声,远离小人。”当然,这些话在他的工作心得和学习手记里不可能出现,但按照孙犁“我的作品单薄,自传的成分多”的说法,其作品中消极、纠结的一面未必是空穴来风。尤其是四十年代写作的那些作品中,孙犁在内容上避开直接描写解放区内部的紧张气氛,但还是没忍住写农村底层人民并不那么革命的一面。如小说《钟》中尼姑怀孕,村人的恶意和老尼姑的狠毒都暗藏于革命义举的波涛之下,这些活生生的案例,似乎正是《善暗室纪年》中描写农村人际关系时出现的断裂——1946年孙犁住蠡县,记载村中人际关系,前文刚说完“那些年在乡下的群众关系,远非目前可比”,后文即述“妇救会主任,住在对门,似非正经”。
其实,正如胡河清所洞见的,“孙犁写文章时其实非常照顾各方面的关系”。“他的文字背后深藏着一种对人际关系的病态的敏感。”“在处理公共关系时,就导致了过分的范防意识。”孙犁在革命文学中复杂的表现是可以从这方面寻找到合理的解释的。孙犁虽然是个“老革命”,但依然深受阶级出身论之苦,“当时弄得那么严重,主要是因为我的家庭成分,赶上了时候,并非文字之过”。但孙犁自己也清楚,出身问题乃是历史特殊条件的矛盾彰显,然而人心叵测,多的是自己无法把握甚至避之不及的事。“客里空”事件、为父亲立碑的请求以及土改期间被“搬石头”,这些都让孙犁在小说中面对革命的土地改革、清除阶级敌人等问题慎之又慎,投射出极为复杂的情感。
1986年至1987年,孙犁陆续写作了一些关于旧事的小说,这些小说明显带着对现实人际关系的暗影,这些芸斋小说里孙犁坦诚面对昨日心事,小说中对官员等级制、解放区“肃托”、斗地主、“文化大革命”等事情的直接描写,实际上是在1992年他写的“我的戒条”之外的。“正因为他对早年美好经历有铭心刻骨的记忆,才无法对现实丑恶保持沉默……才不得不违反个性地去创作那些揭露‘邪恶的极致’的《芸斋小说》。”“戒条”之存在,既是给自己和后辈提醒,是对政党文化和极端“左”倾的心有余悸,同时也是以戒条这一否定的语法宣告一段无法言说的历史的存在。孙犁耿耿于怀的东西,在人际关系上被他称为“小人”,在道德价值上被他称为“狂愚”。曾经的朋友冯前热衷于批判,对孙犁说:“运动期间,大家像掉在水里。你按我一下,我按你一下,是免不掉的。”孙犁对“小人”、“大风派”的深恶痛绝,是一根绷得紧紧的弦,这是一种不主动抗击、明确表示强烈反对,但又时刻警觉、极难融入异质的“防卫状态”。从早期参加革命到晚年闭门著书,这根弦的存在让他很难借着革命的激情和对革命理想的信仰跨进那个常常会出现“大风”的政党文化里。杨联芬之语——孙犁对主流意识形态“‘信’却又而不爱”,郭国昌之语——“公家”体系里的“疏离者”,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衍生的阐释。“文革”时期,王林交代与孙犁的交往情况时说:“他对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一向看得十分神圣的,可是自己讨厌严格的组织生活和严肃的党内思想斗争,而宁愿当‘非党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是想当超阶级的‘同路人’。”这些话,也不无道理。
孙犁小说的艺术困境,多少都与此相关。卫建民与孙犁在晚年有一些交流:“老人家在世时,我曾当面说他是个主观的作家,他同意我的认知。尽管他写过长篇,写过社会的动乱,身心受过摧残,但他仍缺乏广阔的视野,不会结构工程浩大的巨制。他的修行路径,是内省自悟,不是空间的扩展。”孙犁在小说中与彼时俄国“同路人”文学的特征相似,“同路人者,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然而,孙犁在革命文学中呈现出来的复杂性,孙犁与百年中国左翼革命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已经超出该语境下“同路人”原有的内涵了。但孙犁没有站在高处鸟瞰革命全局,小说中有斗争却少战争,其小说的局限性的确符合其精神导师鲁迅给俄国“同路人”作家雅各武莱夫下的断语:“然而,那用了加入白军和终于彷徨着的青年(伊凡及华西理)的主观,来述十月革命的巷战情形之处,是显示着电影式的结构和描写法的清新的,虽然临末的几句光明之辞,并不足以掩盖通篇的阴郁的绝望底氛围气。然而革命之时,情形复杂,作者本书所属的阶级和思想感情,固然使他不能写出更进于此的东西,而或时或处的革命,大约也不能说绝无这样的情形。”
日本学者木山英雄认为,晚年的周作人闭门读书,并非简单的遁世,“(周作人)处于中间的摇摆不定的局面,他反复设法对自己及自己的对象做出种种规定。规定的结果,其对象之所谓野蛮的制度遗留或现实进行中的过去的亡灵为主,其基准落实到‘人情物理’,手段则是‘闭门读书’。这样暂且确保了深切关怀历史与民俗的道德家式的观察和批评家的地位,引导他走到这一步的因素看似讨厌政治的心情,实际上其背后有着天生的反浪漫倾向在思想上的重新抉择”。孙犁晚年闭门著书,一方面是以淡如水的君子之交隔阻太过功利的人际交往,另一方面,也可从木山英雄上述论断中予以解读。只不过,孙犁背后可不是“天生的反浪漫倾向”,而是那绷紧的弦,是某种担忧与警觉。从晚年孙犁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分析来看,他很敏感地避开了到现在都无法论断的历史问题,闭门读书,以古典和传统的知识继续入世作文、参与新的历史进程。这些行为,继承了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也延续了他对左翼革命的复杂情感,左翼文化和革命文学内部的复杂性可以以孙犁的一生做一个参照。由孙犁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来窥探他处理与左翼革命的关系,可以知道孙犁心中并无彻底的疏离,也无彻底的投入,而这背后复杂的原因,又不是仅从“人际关系”、“历史选择”这些方面可以完全了解的。
鲁迅还原到当时的场景中,站在革命的立场上为“同路人”做了一番较为公正的判断。孙犁似乎没有这么幸运,在以往的研究中,孙犁和革命文学的复杂性都极容易被简化为一种价值判断式的叙述。实际上,不加说明地使用“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工农兵文学”或“解放区文学”等概念,并将孙犁与之并置,总有些以大概念规定具体事例的意思,不符合这些概念的部分被作为异质的、特殊的东西拎出来单独审视,由此在多大程度上能窥得一个“整体”的孙犁?洪子诚曾提出,这些概念在某些情况下应该保有自身的“含混性”,这也是孙郁所强调的“丰富性”。“当人们把‘非左翼’的东西添加在研究对象身上的时候,后者身上原有的‘左翼元素’不仅没有被剪除,反而因为剪除手段的过于简单化而显示了它的‘在场性’,我认为他们在用‘新孙犁’来压‘老孙犁’的时候,新的‘文学大师’所代表的新的‘当代文学’不仅没有露面,反而将原来的那个当代文学弄得面目全非、更加的不堪。”其实,在孙犁研究中,左翼革命的丰富性与孙犁的丰富性这二者是共生的。孙犁在革命文学中呈现出来的复杂性,远不仅只是他个人所有。由此看来,与其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最好的读书人”、“当代儒家”等名词来概括孙犁的形象,不如改变叙述方式,认真思考怎样描述孙犁与左翼革命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使这二者都保持其自身的丰富性与历史价值。
注释:
①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载《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第71页。②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第320页。
③张莉:《晚年孙犁:追步“最好的读书人”》,《南方文坛》2013年第3期。
④周申明、杨振喜:《孙犁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页。
⑤这方面的代表研究有:杨联芬:《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阎庆生:《孙犁与中国传统美学关系之整体观——兼论孙犁晚年文学创作的现代转型》,《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滕芳:《狷介:魏晋气质与晚年孙犁创作》,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等等。⑥孙郁在评论《潮起潮落——新中国文坛沉思录》(严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时曾提出这样的观点:“严平写的大量故事里,能够感受到从1917年,一直到‘文革’,一直到80年代,文艺家们、批评家们焦灼的一个最根本点,在这个体制下,我们的艺术有没有另外的空间,有没有其它的可能性,有没有可能不是列宁主义的思路,我们有另外的文艺,能不能让它出现?这是我们左翼发展过程当中,一个宿命的东西,直到今天还是一个很严峻的话题。”(孙郁:《左翼有它自己的丰富性》,腾讯新闻,http://view.inews.qq.com/a/CUL2016022602522409?refer=share_relatednews,2016年2月26日。)如果不从这一角度来讨论孙犁与左翼革命、与革命文学的关系,恐怕会重新落入孙郁所警示的单一的思考方式中。
⑦孙犁:《自序》,《孙犁文集·第一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⑧孙犁:《和郭志刚的一次谈话》,《孙犁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1~92页。
⑨孙犁:《庸庐闲话》,《孙犁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4页。
⑩孙犁:《生辰自述》,《孙犁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7~198页。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