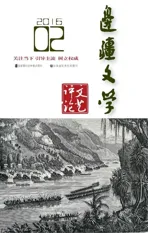狂欢的诗意
——论夏天敏小说中的传奇叙事与诗性张力
2016-11-25◎张伟
◎张 伟
狂欢的诗意
——论夏天敏小说中的传奇叙事与诗性张力
◎张 伟
昭通作家群中,夏天敏无疑是最出色的作家之一。如果要问夏天敏小说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好看。阅读夏天敏的小说,犹如参加了一场“底层农民弱势群体”的聚会,其特殊性就在于,在尘世的热闹中,扑面而来的是沉重和压抑,而感动读者的则是一份对生命的悲悯以及对苦难超越的情怀。但这份悲悯如果离开了昭通底层农民的人生景观便无从着落。所以对夏天敏作品的品评还应回到传奇这类游戏文本的文化功能的理解上来。从对文本的阐释中,梳理出那份充满传奇色彩的“狂欢精神”。我们不能因“狂欢”这个概念的西化背景,以及中国民族心理长期以来形成的不苟言笑的特点,便轻易否定“狂欢精神”的文化意义,无视夏天敏小说与“狂欢诗学”的内在关联。
一、传奇叙事与游戏笔墨
走进夏天敏的小说世界,雅俗共赏的“热闹”无疑是存在的,而这份热闹又显然得益于小说所依仗的昭通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离不开各式各样的传奇故事。这就意味着要真正深入夏天敏艺术创造的“门道”,不能遗忘这些作品的“传奇”叙事。这也恰是评价夏天敏小说的一个难点所在。在他的《好大一对羊》《四爷收徒》《皇木滑竿》《土里的鱼》《乡场上的皮匠》等小说中,的确包含着现实和传奇之间一种貌似相悖的冲动:既以一种清醒的姿态面对世界又以“游戏笔墨”超越日常生活。小说的独特性就来自于这两种冲动所构成的一种张力,处于这个“张力场”的中心的既是对现实世界苦难的仿造又是对昭通地方民风民俗“可能生活”的书写,使得夏天敏的所有小说都有一方面看上去像传奇。这类传奇故事既能让读者获得一种消遣性的满足又始终如一的坚守着民间文化之根,总是显现出超越日常事态人生的虚幻,同时又具有一种内在的游戏品格。如在他荣获鲁迅文学奖的作品《好大一对羊》中,德山老汉越来越贫穷,因为他养了一对“外国羊”,当羊的身价高贵于人的时候,人成为了奴役的工具;再加上乡长们的层层施压,使得这一对羊的生命价值、种的繁衍远远高于德山一家的生命价值,“羊”在此象征着难以抗拒的无形束缚的力量,不仅是权力的传递,更是德山老汉那愚钝麻木的灵魂深处的痛。看似荒诞的情节却隐透出一种残忍,“黑色幽默”的笔法成功的构建了现实世界的荒诞,匠心独具的构思创造了一个亦真亦幻的羊的世界,人被置于无望的怪圈而无力自救,虚构与真实的巧妙的结合,使传奇书写在 “游戏语境”中大显身手。
在《接吻长安街》中农民工“我”最大的愿望不是改善自己的工作环境或者工资待遇,而是要和女友在长安街上当众接一次吻,所有的一切都围绕“主体愿望的满足”这一主旨而存在,这也正是这篇小说的传奇性所在,既揭露了喧嚣世界背后小人物的种种梦幻,又使我们从中发现游戏的内在意义——生命为其无任何的自然束缚也无社会负担的单纯的存在感而感到由衷喜悦。这篇小说应当是对昭通人的文化精神的一次大胆探索,具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它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小说中的主角以生命尽兴的方式来实现自我解放;而那种对日常生活模式和僵化文明仪式的解构为内涵的怪诞形象和粗鄙化行为,构成了狂欢文化的核心意识;体现了平等自在的生命乐趣和诙谐,彰显的是作家和读者的良知和道义,具有一种雅俗共享、艺术与生活相融的既奇异又现实的特点,令人解颐之余,又充满了对人生的感悟。
其实,文学创作的出发点一般有两种:一种为俗世而写作,它追求的是“利”,即追求写作者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一种是为精神而写作,它追求的是“义”,即追求对人生的本质的探索和对人类精神的抚慰。毫无疑问这部作品是为“义”而作。小说通过想象力的空前活跃使底层人民的自由意志得以尽情释放,使得艺术活动的终极目标得以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创造出一个既来自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历史风景。
又如在他写的为数不多的长篇小说《极地边城》中,夏天敏成功地塑造了云霓小姐这样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女性形象,虽是大家闺秀却使得一身好拳脚;虽出生在偏僻落后的滇东北,却从小养尊处优没有经历过生活的磨难;更为传奇的是,她并没有身在政坛,却为了百姓的利益铤而走险。但这样一位集百宠于一身的云霓小姐,却未能逃脱自己的宿命,在出嫁当晚就沦为了寡妇;就在她守寡多年并最终决定追求自己幸福的时候,她的儿子却成为她的俄狄浦斯。这篇小说成功的奥秘就在于她比别的同行具有更到位、更自觉的“游戏意识”、更善于举重若轻,更彻底的解构了负载于生命之上一本正经,让具有传奇叙事的文本回归其民间文化之根。语言继承和发展了地道的民间话语的特色,既有高原人的“口气”特色,又有泼辣的乡村口语,既有诗化的情趣描写,又有对饱蘸人生世态的嘲讽,形象与心灵、结构与节奏融合无间,营造出了一个强大的艺术磁场。正如小说所描写的那样:“她哀叹自己显赫的身世、哀叹自己身上的光环,这些光怀实际是一条条锁链,别人走不进来,她也走不出去。”曼杰利塔姆说“一想到我们的生活不是一个有情节,有英雄的故事,而是一个由忧伤、由玻璃纸品,由不停息的到处蔓延的狂热的嘈杂声、以及由彼得堡流感引发的谵妄呓语所构成的传说,就让人毛骨悚然。”曼杰利塔姆描绘的其实就是人性的荒诞,因无力而生发的恐惧和恼怒。这种“真实”嘲笑了虚幻的美,消解了优雅与空灵,裹挟着生活中的苦闷气息,抗拒着智慧与玄思的过分炫耀。但归根到底,这既是狂欢区别于一般游戏的根本品质,也是它能够贯通传奇与小说的最宝贵的诗性内涵。
在本土化的文学创作过程中,夏天敏小说的故事类型有着较一般生活化小说更多的限定,更像是一种“带着镣铐的舞者”,但显然,只有不会跳舞的人才会怪脚镣碍事。他的小说,并未因这种本土化的先天限定而影响其艺术的表现力,反而在作品中,以有限的人物性格演绎出了让人别开生面、无与伦比的传奇故事。这类传奇叙事通过生动的情节大大强化了文字游戏的乐趣,使得小说文本拥有了一种本土韵味的狂欢精神,在伦理上具有双重指向的叛逆性,即不仅挑战现有的道德礼仪规范,而且还对最高的人道法则生命解放、追求幸福做出了一种肯定。
狂欢,虽然是西方诗学的概念,却可以用来说明夏天敏小说叙事的艺术奥妙,所有的传奇都具有游戏性,尽管并非所有的游戏都具有狂欢节的特征,但如果我们把游戏认可为生命的一种自律的自我确证,因而承认“游戏的基调是狂喜与热情”,那么狂欢便是真正的游戏活动的最后归宿和最高境界,也是游戏精神的本质的一种体现。夏天敏的作品并非完全体现在对貌似威严,不可侵犯的权威与规范的反叛和亵渎,更多的是体现在对平等自在生命乐趣的诙谐,体现在贯穿整个文本的传奇化的叙事氛围;由于这一切都是在一种诙谐的氛围下进行的,所以属于真正的狂欢形态,具有了一种形而上的意义,小说也因此化玩笑为创造,使得那一个个貌似荒诞不经的粗俗故事,拥有了一种不可多得的诗性内涵。
二、诙谐中的诗性张力
让我们再来谈谈《两个女人的古镇》,这也是一部充满谐趣的小说,以盐津豆沙镇为人文背景,以日本的长驱直入为历史背景,以历史文物为底色,以自然风景为衬托,以古镇上玉碗、蒋嫂两个传奇女人的爱恨情仇为线索,真实的展现了豆沙古镇的繁华热闹和淳朴民风,再现了五尺道上的俗世奇人,把千年古镇演绎得淋漓尽致,对人性的把握准确到位、对人生的体悟含蓄深刻,最后所有的爱恨情仇在“至善”中呈现“大美”。这样的结局固然匪夷所思,却渗透出了一种真情与和谐。这无疑是一个叙述圈套,因而读罢小说你会有一种中了作者的“埋伏”的感觉。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在狂欢节的自由自在、不拘形迹的气氛中,甚至连放荡的举止也获得一席之地”。而读者之所以不以为怪,是由于小说饱含真诚的乡土书写,节制而富文采的语言风格,对人性与社会的复杂性让人产生一种忍俊不禁的诙谐。又如《乡场上的皮匠》一文,讲述了一位世世代代居住在滇东某乡镇并世世代代以修鞋为生的皮匠牛顺德与一位外来皮匠之间的故事。牛顺德的手艺是祖上传下来的,早已得到乡亲们的认可。但由于没有竞争,所以他嗜酒成性,常常忘记了干活。可是,一位外地皮匠打破了乡场上秩序。外地皮匠手艺好、设备先进,还十分讲信用。这就不可避免地夺去了牛顺德的生意。最终,牛顺德经过一番痛苦挣扎后,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自己的祖传手艺,改行当擀毡匠了。在这部小说中作者用诙谐的本土语言为我们描写出了一个善良、和谐的小社会。毫无疑问,在夏天敏的文学世界里这两部小说的艺术分量并不算重,但它特殊的价值在于以“反苦难”的方式来建构新的艺术天地,使“狂欢精神”成为小说中的一种主旋律,再经过诙谐化的处理,不仅使作为“苦难”主干的人性失去了沉重性和嗜血性,也使得小说充满了人间的温情,对最高的人道法则做出了一种肯定,使小说拥有了一种不可多得的诗性品质。
其实,在夏天敏的小说中,诙谐的场面描写比比皆是,如《土里的鱼》中狗剩老汉临死前的遗言不是入土为安,也不是如何将遗产分给儿子们,而是要将自己“厝”起来,并相信这样能给子孙后代带来幸福;《皇木滑竿》讲述的是陈滑竿和谢长脚这两位靠抬滑竿为生的底层民众对陈滑竿家那副祖传的皇木滑竿的深情。他们对皇木滑竿有着如此深情——即使在不许抬滑竿的特殊时期,他们也要在院子里“过回干瘾”;《四爷收徒》一开篇就扑面而来地呈现出了一种“异域文化”“评猪”,这对于非滇东乌蒙山区的读者来说,想必是陌生的,而四爷就是这个行业德高望重的高手。这一系列奇人奇事的故事,道出了一种生命的大境界,一种建立于生命之间的互相沟通的人类之爱,使得这类小说较一般的苦难主题更多了一份美感。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说得好:“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确,我们之所以将“狂欢”视作夏天敏小说的艺术审美的一个核心,并不是说夏天敏先生在创作时接受了巴赫金的指令,使其小说自觉地运用了狂欢诗学的理论。我的意思是指,借鉴这个“狂欢诗学”的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夏天敏小说的艺术奥秘。
夏天敏的小说沉重而又不乏幽默,作为狂欢文化风格所体现出来的诙谐,包含着一种严肃性,即对苦难生命的解放与再生,在笑声中恢复人的尊严,让精神高扬,所以这种狂欢的诙谐同一般狂欢搞笑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与肤浅的区别、文雅与粗俗的差异,也就是在那些看似随心所欲、无遮无拦的叙述中,蕴含着对许多世态人生的深刻洞悉。
(作者系昭通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程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