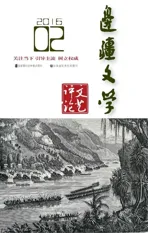对少数民族文学不能因“无知”而去“无视”
2016-11-25刘大先周明全
◎刘大先 周明全
对少数民族文学不能因“无知”而去“无视”
◎刘大先 周明全
“在暗夜里慢慢趟出自己的道路”
周明全:大先兄现在在批评界大名鼎鼎,但对你的求学经历,似乎还有很多人不知,兄能否简单介绍一下?
刘大先:明全兄过奖,我也才算起步,还没有写出让自己真正满意的著作。我是1996年考入安徽师范大学,高考志愿填的其实是英语系,服从调配到了文学院,可能因为我当时语文还不错吧,单科成绩是当年市的第一名,当然更多可能是我的分不够上英语系,哈哈。那时对文学并无特别爱好,倒是喜欢健身,做了四年体育委员和业余长跑运动员。本科毕业那会儿原准备报考复旦新闻系黄旦教授的传播学研究生,但是本校给我免试保研了,我也就懒得考了,上的是文艺学。因为本校的朱良志教授做中国古典美学还是很厉害的,我那时候读了些孔孟与王阳明,想着跟他做古代文论也不错,结果他那年调到北大美学系了,我就跟陈文忠先生读西方文论了。2003年硕士毕业本来考到安徽省财政厅做公务员,正好那年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的关纪新主编到安师大开会,提到要招个编辑,学院原先推荐的那位同学要到人民大学读博士,我那时从来没有去过北京,就“替补”进了社科院的民族文学研究所,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两年后,单位允许在职读博,我当时考了社科院文学所的美学专业和北京师范大学的现代文学专业,两个都录取了,但是后来想想可能在现在的单位无法纯粹做西方美学研究,就上了北师大。2008年毕业后有个出国的机会,我申请到了当时由斯皮瓦克主持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比较文学与社会学研究中心,2009年去,2011年回国。
这个求学经历中间充满了各种阴差阳错、随波逐流,是个缺乏规划的过程,就像是在暗夜里摸黑走路,磕磕绊绊地行走,慢慢趟出自己的道路。这样当然会走许多弯路,白费了许多精力和工夫。但好处是转益多师,文学的各个学科都接触到了,不至于陷在某个偏狭的学科门径中固步自封。我觉得一个人文学科的从业者,可能还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比较好,一开始就目标明确地步步为营、精心算计,就带有了商人和谋士的刻意了。
周明全:之前和徐刚、李德南两位“80后”批评家谈过,他们当初走上文学批评这条路也和大先兄一样充满了偶然,从你们三位身上可看出,也许不刻意为之,反而能做好一件事。现如今不少年轻批评家见人介绍,总不免说:“我是某某人的学生”之类,感觉很滑稽,难道自己的导师有大名自己就有大名了?和大先兄相识这么久,从来没听说你这么自炫过,所以,今天想请你谈谈你硕士、博士时的导师对你的影响?另外,从事文学研究,还受到了哪些师友的影响?
刘大先:你说的对,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尤其对于学术研究来说,老师只是指路之人,更多还要靠个体的自我砥砺。我的老师们都比较低调,不是什么名人大腕,我自己也不愿意扯大旗拉虎皮的攀鸿附骥。硕导陈文忠先生对学生的基本功要求很严格,他一开始给我开的书目就是按照朱光潜《西方美学史》最后提到的四位: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和康德,我最早写的论文就是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这些阅读让我受益终身,因为他们构成了一条经典的线索,此后返本开新,无论是继承发展还是对话批评,都离不开初始的影响。邹红老师是我的博导,她是专门做现代戏剧的,尤其是焦菊隐和“人艺”,我的同门几乎全部是做戏剧相关研究的,不过我因为已经工作了,也逐渐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所以选的题目是“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博士论文就是后来出版了的同名著作。我很感激邹老师和在清华大学任职的师公张海明教授给予我的支持和鼓励,没有他们的包容,我这个题目肯定无法毕业的。别的给我影响最大的学者就是关纪新、刘禾与李陀了。关老师是满学大家,早年致力于老舍研究,后来扩展到满族史,我受他启发也做了一些关于满族与清史方面的研究,不过成果还没有出版。刘禾是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时候的导师,她的《跨语际实践》《语际书写》《帝国的话语政治》还有那本The Freudian Robot在国际上享誉甚广,就不用我多介绍了。她的课常常会有阿君·阿帕杜莱、阿里夫·德里克、朱迪丝·巴特勒这样各种学科的名家来做客和交流,跨学科的方法与思想冲击非常巨大。最后一学期,我给她一门“鲁迅与现代中国”的课做助教,由鲁迅为基点关联起政治、历史、宗教、民俗、民族、性别诸多议题,是个系统而完整的学术训练。李陀则改变了我的思想取向,有一年多时间,几乎每个周日下午我都会去哈德逊河边他家聊天。他属于述而少作那种批评家,思路敏锐、视野开阔,逻辑严谨明晰,跟他对谈往往让人忘记时间,有时候甚至到深夜。他们家中有时沙龙会来冯象、商伟、卡尔·瑞贝卡、高彦颐、于晓丹、林鹤等学者作家,吉光片羽的言词之中,也受益匪浅。这二位等于让我重新读了个博士。
周明全:你身边大师云集,这和你文章视野开阔是有关联的。那么,当初你是受谁的影响或者说受哪些书的影响走上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之路的?
刘大先:如同前面所说,我走上文学研究的道路充满了偶然性,但是有一些启示般的瞬间确实是某些人与书籍所带来的。比如我研一的时候在图书馆乱翻书,偶然读到萨义德的《东方学》,就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由萨义德回溯到福柯,再到法农和尼采,让我对知识与权力、认知范式与现代学科都有了反省式的认识。到北京后也是机缘巧合,去清华听过葛兆光和汪晖的课,他们都是偏向思想史的,这些可能当初并非有心的吸纳,在后来无意中都会成为批评的滋养。我现在读的最多的还是关于批判思想和历史学方面的著作,像詹姆逊、安德森、伊格尔顿、齐泽克、阿兰·巴迪欧、孔飞力、沟口雄三、柄谷行人这一类的,他们的著作也是国内文学批评学者的案头书。我在2013年之前虽然已经写了很多电影方面的评论,但那些都是本能式的写作,真正开始当代文学批评,其实还是要得益于中国作协和现代文学馆提供的客座研究员的机会,让我进入到一个堪称全新的领域,结识了一批前辈与同仁,否则可能就会完全是所谓“学院派”的道路了。
应给少数民族文学一席之地
周明全:相对于主流的文学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很滞后,你开始研究少数民族文学是和你到民族研究所的工作有关,还是自己的兴趣所在?
刘大先:这个确实是因为到民族文学研究所工作才开始的。你们云南还是多民族文化繁荣地区,而我之前的生活环境和教育背景中没有这一维度,简直称得上全然无知。不过随着接触的时日愈久,倒是发现少数民族文学确实是个有着广阔学术生长点的领域。2006年中国作协的《民族文学》改版,叶梅主编敦促我每年做一个创作综述,这才开始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阅读和评论,此前我都是在做文学理论。
周明全:面对当下大力提倡的政治文化多元一体化与主流文学之间相互影响,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和方式去面对少数民族文学?
刘大先:我觉得最根本的是要葆有一颗同情与理解的心灵,而不是因为对它们的“无知”就去“无视”,这种傲慢与偏见由来已久,也是许多现实的文化冲突与民族问题的根源。我们需要正视本土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在“大传统”之外的各种“小传统”,它们也许在现代发展路途中是弱势,但却不能因此同质化了,这也正是“多元一体”的本义所在。
周明全:不能因“无知”就去“无视”,这个观点极好,我们现在大多数情况就是对少数民族文学缺乏必要的了解,而导致了对其呈现出的多样性的忽视。在你看来,少数民族作家应该如何在当下的汉文化语境中,保持自己独特的民族性呢?
刘大先:我一直以来的观点就是没有什么静止不变的“民族性”,它总是如同奔涌不息的流水一样,不断革故鼎新。因为历史不会终结,少数民族作家同时也是中国作家,也是世界上的某个作家,在目前所面临的并不是某种片面的“汉文化语境”,而是现代性、消费主义、阶层固化、信息与科技爆炸等一系列与汉族和其他国外族群共同的语境。如果我们承认大家都是同时代的人,那么族别的区分就没有那么重要,尽管少数民族作家可能有其独特的关注,比如母语的衰落、传统的式微、认同的转变等,但这一切都应该超越于某种怀旧主义的感伤与族裔民族主义的愤怒,而进入到更为广阔的议程之中。作为历史中人,少数民族作家在哪里,他的“民族性”就在哪里,这个民族性显然不是某种符号化的印象,而是内化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之中,如果改变必然来临,那也是历史理性自然的选择。
周明全:现在的文学教育,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关注依然不够,你认为,有必要在现当代文学上加重少数民族文学的比重吗?
刘大先:很有必要。明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的文学教育太多是主流文学史叙述的那种一以贯之的民族-国家范式倒溯式的知识,它们由少数文人化的精英人物与作品组成,平民大众的内容尤其是边缘、边地、边远地区的族群文学几乎是空洞的,如果有也只是插花式的点缀。在这种文学教育里,中国文学的整体传统其实是被中原、汉文字书写、精英文士所主导的。在现当代文学中,这种情形尤为明显,由于殖民文化的附加值,我们的作家、批评家特别热衷于外国文学尤其是西欧与北美的文学的传播与颂扬,对于弱小民族国家比如非洲就所知甚少,他们难道是一片空白?本土的少数民族文学处境也是如此,很少出现在文学教育议程之中,而历史与考古都一再证明,中华文化是“满天星斗”遍地开花,而不是由某个中心辐射出去全面影响了周边地区,那些处于无声状态的文学也应该有其一席之地。当然,这种文学态势的形成有着现代文学发生时候的历史根源,但时移世易,在我们宣传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当下,是时候反思与清理这套既定的文学观念与生态构成了。
周明全:我极为赞同你的观点,我们有必要反思和清理目前的文学观念,甚至文学史的建构,文学是多样性、多元化的,不能按照一个单一的标准去评定和建构,人为地抹杀。你觉得当代的少数民族创作整体情况如何?少数民族作家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大先:整体创作情况是作品多、精品少,作家多、大家少,批评乏力,理论陈旧。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实绩,而是希望能够涌现出类似纳博科夫、布罗茨基、勒克莱齐奥、奈保尔那样出身少数族裔却改变了英语或法语文学整体格局那样的能重新构建中文文学生态的少数民族作家。
少数民族作家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三点:一是母语与翻译文学,中国55个少数民族,共使用100多种语言,许多民族也有着悠久的文字书写传统,即便现代汉语规范化以后,蒙、藏、维、哈、朝、彝等民族还有大量母语写作。民汉文学的相互翻译显然不仅包括文本字面的迻译,同时也是文化与美学的跨文化传播。翻译中常常会有对于源语言的归化,但文学的特异之处恰在于它在核心处的不可译性,这会将源语言中的差异性文化要素带入到译语中,这就带来了语言的陌生化,无目的而合目的地产生了特有的美学效果。二是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书写提供了有别于工具理性或市场功利的认知范式,比如伊斯兰教、藏传佛教之于穆斯林作家、藏族作家的写作,更多以弥散性宗教形式存在于各地的各类萨满教、道教分支、原始信仰(像云南就有白族的本主信仰、纳西族的东巴信仰等),在摆脱了“迷信”的污名化后,显示了在生态、人际关系和环境污染等全球性议题中独特的参考与借鉴价值。三是少数民族文学携带的地域差别,不仅是边缘目光的转换,同时也重新绘制了文学地图。我有专门论述过,就不展开了。
周明全: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作家都使用汉语进行创作,这在作品流通、传播上肯定是有益的,但你觉得这是否也会导致少数民族自己的文化特性因此被逐渐抹杀掉?
刘大先:就像巴厘岛旅游观光业的发展反倒带来了当地族群传统文化的复兴一样,我觉得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写作与自己文化特性的保持并不冲突。人类学上常讲“边界流动,核心稳定”,那些内含于精神与心灵深处的集体记忆、心理积淀、文化内核并没有那么容易动摇,而能够被改变的更多是外在的所谓“边界”部分。假使某一天族别仅仅成为无意义的名词,那也是民众自己的选择,我们也应该尊重历史。
周明全:你在《文学的共和》的后记里说,“文学的共和”意指通过敞亮“不同”的文学,而最终达到“和”的风貌,是对“和而不同”传统理念的再诠释,所谓千灯互照、美美与共;同时也是对“人民共和”到“文学共和”的一个扩展到推演。我不明白的是,文学“共和”了,差异性减少或消失了,文学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刘大先:“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我说的“共和”所要强调的正是差异性的共生,而不是抹杀它们。即我们在保持各种“不同”之间的对话,才能对抗同质化、一体化带来的活力丧失。“文学共和”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要表达对于不同美学理念、写作风格、文学观念差异性的尊重。
周明全:常年在少数民族地区做调查,给你的研究最大的启示是什么?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刘大先:我抒个情吧,那就是天高地迥、江山无限。萨义德说文学研究要走出“室内游戏”,确实如此。在各种不同族群地方做调查,能够获得仅停留在书斋生活所没有的鲜活体验,以及对于自身局限性的认知。那种甚至带有“文化震惊”效应的感受,能够让人更加谦卑,也更能激发求知的欲望。
“在时间的审判中,靠的是作品说话”
周明全:总有人说“70后”是被遮蔽的一个群体,其实以我最近的观察,“70后”批评家的实力是很强的,并非是被遮蔽的一个群体,作为“70后”批评家中最优秀的批评家,你是如何看待所谓的“70后”批评家被遮蔽这一说法?
刘大先:你的观察没错,“70后”确实有一大批实力型批评家,所谓“被遮蔽”可能只是在媒体上没有那么热闹。当他青春,他的严肃被上一拨人遮蔽,他的张扬则被下一拨人所淹没,这可能就是“70后”在大众媒体时代的尴尬。他们出场的时候,文学从公共文化中退场了,折返到日常、个人、情感、欲望等私领域,而他们还没有学会迅速适应汹涌而至的市场社会和文学产业化的消费浪潮。在“被遮蔽”的不满背后是“成名的焦虑”。其实,文学批评本身就是个冷门的行业,再出名也不过是文学圈寥寥数人知道,这个我觉得倒无需介怀,因为最后在时间的审判中,靠的是作品说话,而不是喧嚣的口水。
周明全:作为“70后”批评家中的一员,你觉得“70后”批评家这个群体的优势和劣势各是什么?应该如何克服劣势?
刘大先:“70后”本身是个复杂的星云式存在,他们共有的可能仅仅是出生的物理时间的相似性。当然,这样说又有些极端,但我实在无法给这群人进行总体性的概括与归纳。从直观上来说,“70后”成长期正是后文革时代而网络媒体还没有大行其道,这至少在两方面构成了他们的学养积累环境:一方面是崇高意识形态的解体所带来的对于个人、肉体、欲望、历史、资本、市场的再认识,但理想主义的残余依然焕发着微弱的光芒;另一方面是书面阅读还没有被碎片式阅读冲击得那么厉害,因而体系性的知识和细绎的方法还未被全然侵蚀,这反映在文本层面则是对于宏大命题的关怀,而不是“破碎思想的残编”。但这样的直观感受不具有普遍意义,文学批评终究是个人事业,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每个批评家都有他的个性,优劣得失也是因人而异。
周明全:记得2015年4月,上海作协、北岳文艺出版社等为上海四位年轻批评家召开研讨会后的某天,我们在一起喝酒,你说,真羡慕上海的批评家,有组织为他们的出道出力。但据我所知,业内不少人对“80后”批评家的“抱团取暖”式的出场是持批评立场的,你认为,年轻一代的批评家在成长中,外力的作用是否必不可少?年轻一代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出场?
刘大先:上海那次我不在,咱们应该是在呈贡聊到这个的吧。“80后”团体出场的机会,有前辈提携、有同道切磋,实在是人生幸事:一方面薪火相传,确实能够很快进入到话语场域;另一方面“独学无友则孤陋寡闻”,这也是很好的琢磨互进的机会。不过,有外力助推当然事半功倍,平台扩大,声音自然也会放大;但这种机缘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如果没有也无需抱怨。说到底,文学研究终究是个体性很强的寂寞事业,而毕竟出场的华丽并不一定代表谢幕的辉煌,就像《红旗谱》里面朱老忠说的“出水才看两腿泥”嘛。
周明全:最近不少前辈批评家撰写文章批评代际问题,你如何看待代际批评的划分?
刘大先:我觉得代际划分有利有弊,群体性形象出现容易形成规模和影响,同时也可能会在某种框架中埋没彼此之间的差别,能够从中打破山门出来的才是真正强者,毕竟每代人中间总会有鹤立鸡群的人物。另外,代际划分不应该是硬性的时间切割,比如“文革”结束到198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无论从生长、教育和传播环境都更像是一代人。当然,“70后”、“80后”这样的提法本身有着易于操作的策略性因素在里面,这个无可厚非,就是一种方便的说法,并不构成学理上的意义。
批评家应该具有“匠人精神”
周明全: 当下批评失语、批评失效一直是媒体的热门话题,你认为这个批评失语、失效了吗?
刘大先:笼统地谈“失语”、“失效”其实没有意义,是对大的政治变革无效了,还是无法影响到读者了,还是作家根本不理睬了呢?我觉得很大程度上,这种提法就是一种撒娇。现象意义上的观察,可能是批评再也无法像五六十年代批评《武训传》、《红楼梦》那样能够引发巨大的政治效应,或者也不可能如同八十年代那样对于“异化”、“人道主义”、“朦胧诗”、“先锋小说”那样能产生大范围的争议乃至文化理念和结构上的转型了。因为许多原本需要通过文学曲折表达的思想与观念,现在已经在更为宽松的环境中直接言说了。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吊诡的局面,依然掌握着话语通道的批评者失去了话语的权力:如果不掌握话语通道我们甚至连这种关于“失语”的抱怨都听不到,但是话语权力显然旁落了,因为绝大部分文学批评无人再当回事了。
这涉及到中国社会近三十年来整体性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思想的变迁,文学在这种大转型中被“边缘化”了,但是这种边缘化其实是文学不再是一种包打天下的普泛性话语,而是分化为社会与学术分科中的一种。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文学本体的“回归”,向着精细化、技术化、专业化方向发展。与之并行的是,文学批评的同构,出于对庸俗社会学批评和泛政治化的反拨,兴起的是“纯文学”式的个人主义、犬儒主义、消费主义的“向内转”式批评,主动放弃了言说重大问题的可能性。虽然它对狭义上的“文学”依然是有效的,但对更广阔意义上的社会文化的“失语”则是必然的。如果我们要在这个意义上,重新建立批评的有效性,就要实现它与政治和历史的对接,这并不是要重蹈某种“工具论”,而是要发明文学的潜力,重新界定批评的边界和空间,从而有效地介入到当代文化与思想生产的实践中去。
周明全:你认为文艺和政治应该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刘大先:这个问题关涉重大,真是很难一言以蔽之。不久前,在“中国文学博鳌论坛”上,我曾经对《人民日报》的记者谈过这个话题,可以简单概括一下。文学与政治一直都无法割裂开来,现代以来的文学尤其如此,它本身就是政治的产物。现代中国的主体是个中西融合的主体,文学在民族国家这样的“想象的共同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与主权国家的规划与建立密不可分。从19世纪中叶以来,从今文经学到洋务运动、从维新改良到国民革命,中国文学经历了逐步确定其现代内涵与外延的“政治化”过程。尽管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文学政治化运动过于激进而陷入困境,但是随后因为新一轮的向欧美学习而导致忽略了更广阔的全球不平衡问题,导致文学的“去政治化”,后果是个人、肉身与欲望至上弥漫在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话语之中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在全球权重中的上升,文化软实力的问题摆在议事日程之上,需要我们重提“政治化”,这个政治化不是简单的、机械的、图解式的政治化,而是指包含整体性视野、历史性关怀、现实感的萃取和未来性想象的“新主体性”。如果没有政治这一维度,那么文学就会沦为一种无足轻重的玩意儿。中国的“传统”有着自我更新、融合新知、应对时势嬗变的内在功能,我相信未来的中国文学一定会发生这样的变局。
周明全:我看你现在经常到外参加各类会议,这样会否走向你所批判的“表扬家”行列?在人情、作品的价值判断上,你是否能真正坚持以作品说话?
刘大先:哈哈,你太犀利了。我参加会议算是少的,更多是做田野调查,即便是参加某个作家作品研讨会,我也会从学理性的角度找到某个切入点来“六经注我”,而不是被它带着跑。人情关系与作家价值之间可能产生的落差,是当代文学批评欲说还休的常见问题。我想一个真正严肃的作家都不会拒绝善意哪怕是犀利的批评。当然现在有很多作家自我膨胀的厉害,对他们也不必客气。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一个研究者不应该懒惰到只读符合自己审美品位的作品,而应该观照哪怕从个人情感上来说根本就不喜欢的作品,这样才能观察到文学生态现场的全局。我的做法是对那些已经成名的作家本着“春秋责贤者”的态度要求高一些,对那些籍籍无名的作家则尽量发掘他独特的闪光点予以鼓励和期待。身在历史之中,一个当代批评家不可避免要面对的悲剧就是他所解读与评论的绝大多数作品终究会被历史淘洗得灰飞烟灭,而他就像那个披沙拣金的工匠,在无数脏杂凌乱的尘屑中,锻造属于自己也属于时间的蔷薇。
周明全:我看你在《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样的批评》中说,当下的批评家在败坏这些前辈苦心经营留下的遗产。那在你看来,我们应该如何承袭前辈批评家的遗产,又该如何重建批评的地位呢?
刘大先:凡是在文学史上留下声名的批评家,都具备广博的知识、漂亮的文本、与历史和现实的对话、以及启发性的一家之言。我们当然要读他们的著作,但借鉴不等于规行矩步、照猫画虎,囿于某种批评理念当中无力自拔,而更多的是要继承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有扬有弃,推陈出新。事实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批评者都有自己的对话对象,将他们的文本从其语境中抽离出来作为普世原理来传承就南辕北辙了。重建当代批评关键的问题是找到属于自己的对话对象,无论这个对象是美学、社会还是政治,都要以自己独特而不是前人的既有方式去回应对象所提出来的问题。
周明全:你认为好的文学批评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刘大先:首先它应该是明晰的,有自己的立场与观点并且能够将它们清通流畅地传递出来,能够形成让人愉悦的审美感受。其次,它应该富于真理性的启发意义,不仅仅是附着于作品或者现象的文本,而是个独立思想的成果,即便脱离开它的论述对象也具备足够的参考价值。第三,它还应该具有伦理上的诚实,以其自身的诚恳给人以道德上的教益,是善的流布,而不是恶劣趣味和品德败坏者的辩护人。
周明全:最后,想请教一下,你觉得一个好的批评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刘大先:我觉得他应该具有“专业性”,换句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所谓“匠人精神”,他要把这个活儿做好,而不是流于普通读者的感受。这包含的素质是多方面的,诸如敏感的观察力,不屈不挠的博学,理性清明的洞察,平等公正的善良,同情弱者与抗争不义的勇气,将自己的美学目的与判断付诸于实践的能力。要有一颗感恩的心,感谢那些曾经默默支持与帮助过自己的人,感谢那些曾经否定与指责过自己的人,因为他们提供了温情与改进的动力。最重要的是,还要有内在的激情,这种激情使得他不再停留于技术活的层面,而是把批评作为一种体验生命的方式。
周明全:谢谢大先兄。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