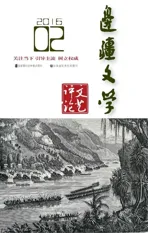夏天敏小说创作中的生态美学意义
2016-11-25郭冬勇
◎郭冬勇
昭通文学研究
夏天敏小说创作中的生态美学意义
◎郭冬勇
主持人语:夏天敏的小说以直面现实的苦难为主题意蕴,且故事曲折多变。郭冬勇的文章《夏天敏小说创作中的生态美学意义》,从生态美学的视角深入解析了夏天敏的作品,认为“夏天敏希望通过对生态美学的思考,展示出人类生活中应该发扬出来的温馨和谐的一面,而不只是单纯地生态问题的揭示。”这无凝是夏天敏小说研究的又一种新的认识和思考。张伟的《狂欢的诗意——论夏天敏小说中的传奇叙事与诗性张力》则从“传奇叙事与游戏笔墨”、“诙谐中的诗性张力”两个层面对夏天敏的小说作了较为中肯的评价。认为夏天敏的小说“在尘世的热闹中,扑面而来的是沉重和压抑,而感动读者的则是一份对生命的悲悯以及对苦难超越的情怀。”两篇文章相得益彰,各有千秋。(李骞)
在庞大的昭通作家队伍中,有影响力的作家不在少数,尤其是小说创作这一领域,自2004年夏天敏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之后,昭通文学的小说创作更是引起了全国文坛的关注,夏天敏在昭通文学小说创作上的领军人物地位,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然而,在认可之余,广大的读者和批评者们也迅速地为昭通作家们进行了标签式的定位,“苦难”书写似乎被看成了夏天敏及昭通其他作家的文学“名片”。但是在夏天敏的“苦难”创作背后,有没有其他东西存在呢,难道夏天敏就是为了表现“苦难”而写“苦难”吗?
纵观夏天敏的创作历程,就会清晰地发现,在伴随昭通文学近三十年的发展中,他的创作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侧重方向,分别是对传统文化的尊敬,对苦难生活的诉说以及对和谐生态的追求,虽然这三个方面的内容与他创作的时间历程不能截然的划分并一一对应,但是大致上却也可以看出存在着相契合的关系。作为一个扎根底层生活的作家,贫穷苦难的生活是他创作的大环境,对生活的描绘和反映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仅仅只能形成他创作总特征上内容方面的诉求,在这种“苦难”写作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一种整体上包含着生态美学的内涵精神,显露在文本的创作之中。通过对夏天敏不同阶段的创作进行梳理,去揭示这种生态美学的创作观念,对于更深入地认识夏天敏及其创作,乃至整个昭通文学小说的创作,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可以肯定地说,夏天敏的创作并不是一开始就直接进入“苦难”书写主题的,在他创作的初期阶段里,夏天敏一直是沿着新时期之后文学发展的主要思想潮流前进的,这是时代环境发展的大趋势。作为一个作家来说,其创作不可能不反映时代的脉搏,对于刚刚踏入文学创作领域的作家来说,更是如此。
夏天敏开始他的文学创作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时期正好是中国当代文学摆脱束缚,火热发展的时代。中国当代文学的“伤痕”还没有完全的愈合,对历史的“反思”正在展开,当代文学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寻根”的阶段。许多作家都以“文化寻根”为主题展开文学创作,他们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度挖掘,希望通过对民族文化心理的观照,揭示出人们对世界和生活的独特理解。特别是1985年韩少功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1]在这样的理论影响之下,反映传统文化意识的作品不断涌现,形成了文化寻根创作的热潮。而夏天敏开始发表小说是在1986年,恰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了自己的文学创作道路,因此,不可避免的使得他创作的初期阶段,主要的作品都反映着对传统文化的尊敬。
在夏天敏的第一部小说集《乡场上的皮匠》中,这种文化寻根的思路表现的尤为清晰。在这部集子中,主要收录了《乡场上的皮匠》、《四爷收徒》、《驼背轶事》、《残碑》、《乡场人物志》和《留在金沙江畔的传奇》等短篇小说,这些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致力于描绘出即将消失殆尽的,却仍然残存于边地人们心中的那一丝传统生活的诗意。在《乡场上的皮匠》这一短篇作品中,牛哥他家是几代的鞋匠,“据说他绱的鞋帮子湿了,里面都浸不进水;底子磨烂了,帮子还稳稳生在上头。据说他绱的鞋不走性,不变形,不夹脚,多穿一双袜子套不上,少穿一双就空脚”,“他做鞋没有规定的价格,别人给多少他收多少,不给也行。只要婚丧嫁娶,杀猪宰羊的时候喊他喝酒就行”。然而当他收留了外地漂泊至此带着新式机械加工方式的另一个皮匠之后,生计被剥夺了,但他毫无怨言,改行去做擀毡匠,“并且,他擀的毛毡渐渐成了这一带嫁姑娘娶媳妇的抢手货”;乡场上的另一位奇人“四爷”,家里几代人都是生猪交易的行家里手,掌握着鉴别生猪质量,有无“猪砂”的绝活,但是在他的心里,“德行”时刻都是收徒传艺的最高标准,“道义”和“利益”的对立中,“道义”是排在第一位的;驼背罗老师对公道人心的执着;陈诺之对刻有“宋乌蒙王殉难处”残碑的坚守:这些人物身上都彰显着作者对于文化精神的理解。特别是在社会伦理领域中,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成为检验人物身上“道”与“德”的参考性条件,不论是作皮匠的牛哥,鉴别生猪行家的四爷,还是驼背罗老师和守碑的陈诺之,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都遵循着顺天道,养德行,以德固道,以道培德的信念,这正是中国传统的哲学中“天人合一”智慧生动形象的表达。
毋庸置疑的是,“天人合一”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独特理解,即使是在今天,从生态美学的角度看,这一思想也可以看作是支撑当前社会伦理发展的核心内容。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夏天敏早期的作品,可以看做是对生态美学观进行实践的一种尝试性写作。
二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至本世纪初期的几年里,大约可以看做是夏天敏创作的第二个阶段。在这段时期里,夏天敏创作了为自己取得重大声誉的作品,如《好大一对羊》、《拯救文化站》、《乡村雕塑》、《断头桥》、《随水而逝》等,2004年,《好大一对羊》获得了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其他作品也曾获得不同的奖项。不断的获奖为夏天敏取得荣誉的同时,也让关注其创作的广大读者迅速地为其贴上了“苦难”写作的标签。
有学者曾论述新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在书写上存在“三大病症”,其中之一就是“苦难依赖症”,“在这类小说中,我们常看到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而导致物质极度匮乏,处在这种封闭落后虚空之中的乡村人背负着沉重的苦难。如云南作家夏天敏的小说《徘徊望云湖》把云南乌蒙高原的恶劣的生存环境和农民赤贫的生活勾勒得清清楚楚,触目惊心。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除了破败的村庄,还有面色如土的村民。这些被现代文明抛弃的农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吃的是野菜洋芋,烧的是海垡,睡的是茅草窝,穿的是破衣烂衫,什么都匮乏,唯一不缺的是时间”。[2]诚然,对于夏天敏这样的土生土长的本土作家来说,扎根于此,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怀着满腔的赤忱和热情,去拥抱赤贫的土地和时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并在自己的写作中,永远地背负着沉重,是他作为一位写作者不愿回避的责任,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把“苦难”作为自己的宝贵财富。
在这段时期内,夏天敏在贯彻自己“苦难”书写的思路的同时,还构思酝酿着两部长篇小说,分别为《极地边城》和《两个女人的古镇》。《极地边城》出版于2008年,《两个女人的古镇》出版于2010年,虽然在出版时间上稍显滞后,然而从字里行间弥漫的人文情怀中,却可以看出,夏天敏对于自己早期创作中传统文化优秀品格的继承和发展。经过“五四”的冲击和“文革”的摧残,中国传统文化在八十年代开始被人们正确地看待,传统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落后和糟粕,“男尊女卑”的思想虽然源远流长,但在历史的发展中,也不乏那些对“奇女子”的歌颂和赞扬。《极地边城》就以昭通地区解放前的历史为背景,围绕一位出生于名门望族的大小姐云霓的情感生活的波澜起伏和人生命运的坎坷曲折展开故事的叙述;而《两个女人的古镇》则以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为背景,以豆沙古镇上玉婉和蒋嫂两个女人的爱恨情仇为主要线索,再现着五尺道上的淳风和世间的人生百态。在这两部长篇小说中,主要女性人物身上都张扬着一种敢爱敢恨,个人家国同呼吸共命运的责任担当精神,在她们身上,融化着古老乌蒙大山大水的性格,只有这片土地才孕育出如此的人,既有大家闺秀的涵养,又有小家碧玉的淳朴,既遵循古老的教条,又有冲破禁区的豪情,人物的性格与自然山水相统一,古典文学中的传奇浪漫的女性身影在作品中得到重现。
从这两个长篇的创作上,可以看出,夏天敏虽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对边地生活的“苦难”诉说上,但是内心深处却也不曾放弃对传统价值的追求,“苦难”不是夏天敏在这段时间内创作的全部内容。尤为重要的是,在对“苦难”的书写中,夏天敏不是单纯地揭示物质生活的匮乏,更多地是刻画人物的精神,展现出生活中由于“现代”的冲击而带来的“异化”现象,而他对于边城古镇的传奇讲述,则通过对人物精神生态上的共融,表达着对“和谐”愿望。在此,夏天敏借用对传统的肯定,来实现自己对于现代文明所产生的破坏的矫正,实现自己心中生态美学的构建。
三
如果说,在之前的创作中,夏天敏的生态美学观念还处于隐蔽状态之中的话,那么在他获得鲁奖之后,他许多作品开始直接讲述自然生态在城市和乡村里被摧毁的残酷现实,在这一阶段的创作中,夏天敏对生活中“苦难”的书写,开始逐渐的淡去,即使偶有显现,也只是作品深层生态美学内涵的载体而已,整体书写的重心,已经转向了对生态和谐的诉说方面。
在《地缝》这一作品中,武副乡长被派去看守“地缝”,全乡33个村庄都处于滑坡、泥石流和岩崩地带上,在动员群众搬迁的过程中,武副乡长也被地缝吞没。作品的表层只是讲述发生在大山里一个悲剧,但是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则是生态环境的破坏;《漫过花园洋房的浓烟》则讲述了一个看似荒诞的笑话,刘经伦老汉被儿子接入城市,但他却要在带花园的洋房周围耕种四季作物,受到了重重阻力之后,最终他依然决定重新回到山村生活,刘老汉的无奈选择,其根本原因在于现代的城市在各个方面都扮演着自然的“敌人”这一角色。
而最集中体现夏天敏生态美学观的则是《猴结》和《好大一棵桂花树》这两个中篇。《猴结》讲述了一个带有魔幻色彩的传奇故事,猴群和人共同生活在一座大山之中,大山因为有了猴群,才有了生气,没有了猴群的山,那不叫山,当小猴子被麻五抓走,石崽的母亲蕨菜听到哀哀的叫声,也泪流满面,随着母猴的哀鸣伤心不已,蕨菜逼着麻五赎回小猴子,送回大山。主人公石崽对猴群的渴望是在他小时候被猴群救命的时候就连接在一起的,他和猴群之间的和谐共处在更大的程度上标明了自然与人的关系,山村的人靠山而活,人不能离开生活的自然。石崽的母亲蕨菜更是与大山和自然联系在一起,她不容许任何人去破坏这种和谐的平衡关系,拒绝麻五通过对大山的“阉割”而带给她的物质生活上的改善,蕨菜的这种态度不仅取决于人本身是从自然而来的属性,更是取决于人和自然共生的实际情况。作品在女性和自然之间建立了一种深刻的联系,表达着女性生态主义的立场,与这一作品相近的《好大一棵桂花树》中,那个叫桂花的女人,她所具有的对那个原本生长在山村里的桂花树的感情,不仅仅是因为那个桂花树曾治过她的病,更是因为那棵桂花树是整个山村的生命,是山村自然生命力的象征,山村里有棵桂花树,山村就有生气,没有了桂花树,山村的生气也跟着没有了,被移植到城市的桂花树和同样被迫漂流到城市的女人桂花,都同样地脱离了乡村,脱离了那个富于原生力量的自然,因而其生存发展必然面临挑战。
在这些作品中,夏天敏尝试着通过文学的方式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行艺术性地阐释,希望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走出一条新路子,毕竟不论是“自然中心论”也好,还是“人类中心论”也罢,截然的对立思维,都是不妥当。“人与自然的矛盾表现为社会发展和维护生态平衡的矛盾,从更深层次上说,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因为自然资源的分配关系和物与物的关系背后隐藏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3]长期以来,夏天敏扎根在乌蒙大山的热土之中,对于边穷地区的生活和社会发展,有着自己清晰的认识,一方面,现实中的人们急迫地要求改变落后的经济状态;另一方面,无休止的对自然的掠夺又造成了生态上的灾难。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带来的是双方的伤害,这不仅仅是现代化的城市与传统的乡村之间的矛盾,更为本质的是人在整体价值观上发生了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说,夏天敏希望通过对生态美学的思考,展示出人类生活中应该发扬出来的温馨和谐的一面,而不只是单纯地生态问题的揭示。因此,对于夏天敏这个阶段的创作,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本的表层,以一种定势思维去关注他作品中已经被淡化的边地物质生活的艰难困苦,从他对生态问题的思考中发现传统的人文情怀,那种对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相合相融的精神追求才是更为重要的价值所在。
四
在近三十年的文学创作之路上艰辛跋涉,夏天敏不仅仅收获了自己的文学声誉,还在创作中一直坚守文学的“良知”,让他能够深入扎根在乌蒙大地,“用热泪去抚慰孤立无助的心灵;用热血去浇灌荒芜的灵魂;用投枪和匕首,去鞭笞丑恶的行径;用仇恨和憎恶,去熔蚀一切卑污”。
事实上,这不但是夏天敏个人对自己创作思想的表达,在很大程度上,他的这种创作思想,也被昭通作家群的其他作家所认同。目前活跃在昭通的许多作家,在小说创作方面都受到夏天敏创作思路的深刻影响,如吕翼、刘平勇、沈洋等一些青年作家,在他们所创作的作品中,都有着贯彻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并且业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关注。
回过头来从整体上审视,不论夏天敏的创作在不同的阶段上侧重于什么内容,也不论作品中对生态美学追求的是显或者隐,剥离这些之后,赢得读者尊敬的是永远不变的创作“良知”。
【注释】
[1]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J】,1985年第4期,第2页
[2]雷鸣,《新世纪乡土小说的三大病症》,《文学评论》【J】,2010年第6期,第34页
[3]陆贵山,《文艺理论与文艺思潮》【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4页
(作者系昭通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程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