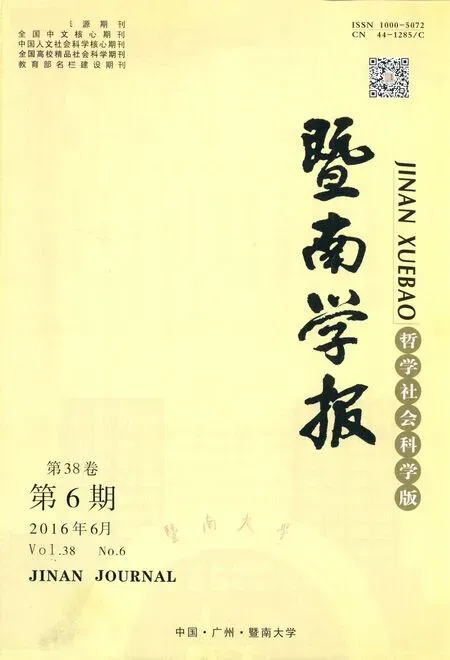刘鹗与太谷学派关系再考辨
2016-11-25陆楠楠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文学院北京100029
陆楠楠(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院,北京 100029)
刘鹗与太谷学派关系再考辨
陆楠楠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院,北京 100029)
刘鹗与太谷学派发生交集的时间有三十余年,其间,学派经历了不同传人的阐释与实践,刘鹗与学派之间的关系也处于发展变化之中,故这一问题应分阶段进行讨论,即李光炘时期、黄葆年时期,以及刘鹗殁后时期。以与刘鹗同时代人留下的文献资料为准,刘鹗与李光炘的关系仅限于三谒之晤,虽心念服膺,但并未深入,同代学派中人在著述中亦鲜少提及刘鹗;黄葆年时期他较为频密参与学派活动,但却与黄葆年和而不同,各执己见,并非学派的核心人物。他与太谷学派之间的关系因时而异,不可一概而论,应分阶段进行讨论。
刘鹗;太谷学派;黄葆年;姚锡光
一、引 言
刘鹗与太谷学派之间的关系历来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这既是由于《老残游记》在晚清文学史上的重要性,亦得益于太谷学派作为晚清民间儒家学派,渐渐进入学术界多个学科、领域的视野。但刘鹗对于学派活动的参与程度究竟如何,其在学派中的地位等问题,却云山雾绕,依然存在很大争议。
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文献记载不足。由于太谷学派秘密宗派的性质,自创始人周太谷开始,即严格规定言论思想以口耳相授的形式传布,著述亦以手抄,禁止刻印刊行,且仅限于学派内部传播。①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80页。因此它发生影响的时候文字记载并不多,②引发官府清剿的黄崖山事件有官方文献记载,这是由于学派此一时期的活动有强烈的社会实验性质,甚至已形成相对封闭的配备有一定武装力量的小社会,触碰到官方底线,因此受到官方压制。也正是由于这次正面冲突,此后太谷学派的分支与遗绪在活动时更加谨慎,其隐秘性也增强了。后世人注意到它时,其组织已不存。③有学者认为学派至今仍有后人,间歇偶有活动,但这依然无法否认学派已无周太谷、李光炘、黄葆年时期的社会影响力这一事实。朱季康:《近代华东民间秘密互助团体太谷学派的生存与信仰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王汎森称其为“道咸年间民间性儒家学派”,实为太谷学派在近代思想与学术的谱系中做了准确的定位。④王汎森:《道咸年间民间性儒家学派——太谷学派的研究》,《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谱系》,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版,第39—59页。介于“学派”与“宗教”之间的特殊性质,又使其在学术研究中面临归类的困难,故清末儒学与宗教学的专著均较少涉及。⑤近年来对于“淮扬文化”的研究将“太谷学派”纳入其中,提供了史学的视角。而就刘鹗本人来说,他生前的社会活动以经商实业为主,既无讲学经历,亦未留下与太谷学派相关的学术著作,仅存关于经学的只言片语,多是出自其小说人物之口。
以此为背景的研究呈现出以下两种取向:一类强调刘鹗与学派的密切关联,另一类则质疑刘鹗在学派中的重要性。前一类研究的立论基础存在材料可靠性的问题;后一类研究在方法上更为严谨,通过实证的方式对前一类研究提出质疑,但明确的针对性也导致其视角相对受限,在问题整体性的把握上还存在推进的空间。
第一类研究将刘鹗定位为太谷学派第三代传人中的核心成员,甚至是承龙川衣钵者。以刘蕙孙、方宝川等人为代表,亦可算是刘鹗与太谷学派研究的第一阶段。①如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收入《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0页。又如方宝川:《刘鹗与太谷学派关系考辨》,[日]《清末小说年刊》,1981年12月。太谷学派第三代传人黄葆年殁后,刘的后人并无能力聚众讲学,而黄仲素的号召力也远远无法与黄葆年相比,加上民国初年的乱世,旧有的秩序难以为继,太谷学派的活动几乎已告停止。刘鹗族中人主张将太谷学派遗书整理印行传世,而黄葆年之子黄仲素持不同意见,两家人心存芥蒂。②朱季康等学者对于太谷学派至今仍存的零散活动的访寻,事实上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太谷学派作为一个“民间儒家学派”的没落。聚众讲学是“民间儒家学派”活动的核心形态,朱季康著作中太谷学派今人活动的方式,正印证了由于缺少核心人物进行讲学、引导,这样的民间组织最终会变化为小范围的民间信仰式组织,最终只剩下学派中的一些秘密仪式和行为规范,更接近一种对先人的崇拜与信仰。最终遗书得以印行,并引发刘蕙孙等人后来撰文说明,这事实上形成了太谷学派活动的另一个时期(整理研究时期),刘鹗在太谷学派中的地位,也是在这一时期刘蕙孙等人的文章中被奠定下来。必须指出的是,刘大绅与刘蕙孙为刘鹗后人,作为历史亲历者,虽然为研究刘鹗提供了便利,但追述的方式也降低了其文章的学术性。刘大绅虽是在刘鹗身边长大的,但刘鹗过世时,大绅先生只有十几岁,所了解的情况有限;至于刘蕙孙,甚至没有见过刘鹗本人,关于刘鹗在太谷学派中的活动,多数是听家族中人转述所得。③刘蕙孙出生那年,即1909年,也正是刘鹗遭清廷流放,在迪化过世那一年。因为黄葆年一脉注重学派的秘密传统,故而黄葆年过世后,其后人并未整理文献或撰文传世,而刘鹗后人却发表了大量的相关研究,其对于太谷学派文献整理与出版、研究之事的贡献毋庸置疑,但也无形中加深了人们对于刘鹗与太谷学派之间关系密切的印象,其不言自明的权威性也引发了一系列以刘鹗论太谷学派,再反过来以太谷学派论证刘鹗的内循环研究,不仅无益于问题的深入,反而令真正的史实蒙尘。
另一类则基于前述研究基础之上,以王学钧等人为代表,多侧重文献考证,发掘了许多现存文献与刘鹗后人叙述中前后不一致的地方,由此对刘鹗在学派中的地位提出质疑,多有可观之处。④如王学钧等人。但由于较为明确的针对性,这一类研究因细致而零散,尚未能建立刘鹗与太谷学派关系的新脉络。从根本上来说,这是由于忽视了两者关系的不同阶段。刘鹗入门后的三十余年间,学派经历了两代传人不同的思想阐释与实践,刘鹗的参与程度亦因时而异。倘若一概而论,难免以偏概全,难窥其貌,陷入自相抵牾的泥淖。太谷学派的创始人为周太谷,自号空同子。周太谷讲学的方式不拘一格,往来之人亦不拘泥,乡野、士商皆有从其学者。周太谷殁后,张积中与李光炘承其遗命分别于山东、江浙等地继续传道。张积中于“黄崖山教案”中殒命,李光炘仍坚持在南方传道。⑤关于太谷学派早期活动的研究,目前史学界提供了更多新的资料,如周新国:《太谷学派史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此后,第三代传人黄葆年、蒋文田等创办归群草堂,实现南北合宗,又经历了短暂的繁荣时期。
刘鹗与太谷学派之间的关系研究,首先应注重材料的有效性,主要以与刘鹗同时期在门派中活动的人物所留下的文献记载为准,而不仅是依赖其后人的口述和追溯;事实上,包括刘鹗同乡好友的记载,甚至刘鹗本人的日记和书信在内,相关的资料尚未得到充分的挖掘和利用。此外,应考虑到两者关系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分阶段考查,具体来说,分为李光炘时期、黄葆年时期分别进行。
二、李光炘时期:成连一去海天空,二十年来任转蓬
(一)“从夫子之日甚浅”
刘鹗曾拜李光炘(1808—1885,号平山,晚号龙川)为师。由于李光炘是太谷学派第二代南宗传人,亦是学派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角色,因此,刘鹗与李光炘的关系,就成为刘鹗与太谷学派发生关联的关键线索。其中有两个问题尤为引人注意。一是刘鹗谒见李光炘的次数与场合;二是刘鹗是否是李光炘生前指定的承其衣钵者,也即“二巳传道”之说。
关于刘鹗与李光炘会面的次数,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三次说,最早源于刘鹗的继室郑安香夫人(1871—1952)。①刘蕙荪:《铁云先生年谱长编》,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12页。光绪六年(1880),刘鹗二十四岁条目:“继祖母郑说,曾经三次谒见龙川先生,第一次在扬州,第二次在泰州,二十四岁那年,即第三次,才在扬州拜从,同时拜门的有毛实君。”按照刘蕙孙记载,郑安香生于1871年,1900年进入刘鹗家,刘鹗将她引为“同学友”。另一种说法是三次以上,至少六次。②方宝川:《刘鹗与太谷学派关系考辨》,[日]清末小说年刊,1981年12月。两个人一生中究竟见过几次面,似乎不是要紧事,为什么竟会引起学者的关注,并引发严肃的讨论?这首先是因为李光炘是刘鹗的授业恩师,两人的会面次数与时间长短,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刘鹗与太谷学派之间关系的深浅。此外,亦是由于刘鹗此一时期并未深入太谷学派的活动,研究者们的着眼点只能越来越细节化。尽管人际关系不能以量化标准衡量,但鉴于完全置史料于不顾的各种任意揣测和附会甚多,只好以至少能够以事实为依据的见面次数为重要的参照之一。
第一种说法是关于刘鹗拜门的时间,现存三种不同的记载。一是来自追随李光炘多年的弟子谢逢源所编《龙川夫子年谱》:
八年壬午(1882)七十五岁,秋,张国英请游上海。丹徒刘鹗来,泰州高尔庚来。命授泰阶泰鼎读。
鹗字刘云抟,尔庚字星仲,州廪生。③谢逢源:《龙川夫子年谱》,方宝川编:《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三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第78页。
按照《龙川夫子年谱》体例,初次出现,且有籍贯、字、号、学位或官阶介绍者,表示此人正式被纳入龙川门下,此后再出现时,便只呼其名。
第二种说法出自刘鹗本人《述怀》一诗:“余年初弱冠,束脩事龙川。”④刘鹗:《述怀》,《芬陀利室存稿》,收入刘鹗著,刘惠荪标注:《铁云诗存》,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5页。若以“弱冠”计,刘鹗二十岁时入门,应为1876年。第三种说法来自刘蕙荪转引郑安香口述“三谒龙川”之说,即刘鹗是在第三次见龙川时,二十四岁那年才正式入门。又及,郑的口述亦提及刘鹗是与毛实君同时拜从,而依照年谱,毛是在1883年,也即刘鹗入门后次年拜从。⑤谢逢源:《龙川夫子年谱》,方宝川编:《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三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第78页。考虑到年谱作者谢逢源1859年即拜从龙川,“师夫子年最久,迹最亲”,且“丁丑(1877)而后,南北追随,未离左右”,⑥黄葆年修订:《李平山先生年谱》,方宝川编:《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三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第20页。是龙川最为亲近的几个弟子之一;而郑安香进刘鹗家时,李光炘已过世十五年之久,郑回忆、口述时又是在刘鹗过世数年之后,郑的记忆未必完全可靠,何况又是口述;此外,太谷学派注重仪式,以弟子入门为大事,收“束脩”,行礼,李光炘甚至设宴款待。⑦谢逢源:《龙川夫子年谱》,方宝川编:《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三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第58—59页。再则,《述怀》出自刘鹗本人自选诗集《芬陀利室存稿》,其中所收多为述怀言志之作,勾勒诗人思想脉承的意图十分明显,诗中“弱冠”,亦有可能只是虚指,实际说的是二十多岁,意在强调“事龙川”时日之久。
综合多种因素,似应以谢逢源记载为准。若要将三种说法统和起来,那很可能是刘鹗曾在正式入门前谒见过龙川,但其时并未有深入交流,亦不能算是入门弟子。王学钧以“三谒龙川”为准,还是较为中肯的。①王学钧:《刘鹗“三谒龙川”考》,《南京理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2卷第4期。
刘鹗第三次谒见李光炘,年谱亦有记载:
十年甲申七十七岁。四月,率陈士毅、黄葆年、谢逢源、黄樨、刘梦熊、刘鹗、赵成、拱铨游上海,寓西中和里。
……樨字木犀,梦熊字渭卿,鹗之兄也。师命各写经一部……②谢逢源:《龙川夫子年谱》,方宝川编:《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三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第80—81页。此次上海之行,李光炘或“徵歌酒市,或拥妓飞车”,虽率众弟子从游,但显然并非讲学的场合。连刘鹗本人提及此次拜见时,亦说“上海虽有数十日之聚,所议论者,观剧而已,看花而已”③刘德隆等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0页。。
1885年李光炘过世,“黄葆年、谢逢源、高尔庚、陈文铎、赵永年度地于青山之阳,夜中祷于周夫子林,乃得西冈紫泥洼,首卯趾酉,凹伏如脐……十二月十九日灵舆入山,风雪没径,诸子皆徒跣执绋以送。二十日安葬,三光并照,和煦如春,先后及门会葬者二十有七人焉。”④谢逢源:《龙川夫子年谱》,方宝川编:《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三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第93页。
这次重要的葬礼,刘鹗并未参加。不仅如此,他在1902年所作《题愚园雅集图抚本后并序》时,将李光炘的卒年留空,⑤王学钧:《刘鹗〈题愚园雅集图抚本后并序〉考辨——刘鹗与太谷学派之关系》,《文献》1990年第3期。而刘父与李光炘同年过世,若用“记不清”来解释,则未免牵强。种种迹象表明,刘鹗对于1884年谒见龙川之后的事,并不知情。
关于“二巳传道”之说,如今已得到学界共识,即刘鹗并非李光炘生前指定的学派传人。“二巳”应是指黄葆年与蒋文田。方宝川主编《太谷学派遗书》已采纳此说,新近出版的《太谷学派史稿》等亦从此说。事实上,对于李光炘生前是否指定了学派的传人,至今仍存在争议。⑥江峰:《太谷学派生命哲学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但无论有无正式的“遗命”,以刘鹗此一时期对于学派活动的参与情况来看,他都不可能是候选人。《龙川夫子年谱》对于李光炘的日常起居及交游皆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中只有前述两处提及刘鹗。此外,《龙川诗抄》中收录龙川诗作百余首,多为题赠之作,题赠对象包括陈士毅、谢逢源、黄葆年、蒋文田,以及许多往来密切的门人,但并无一首题赠刘鹗。李光炘在言语与诗句中曾数次暗示,陈、谢、黄、蒋四人应承其遗志,继续将其学说发扬光大,不乏赞扬溢美之辞。而刘鹗并无长期追随、受教的经历,亦不具备从事讲学的能力,李光炘过世后,他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晋、浙等地路、矿事的奔波上,与学派中人的往来基本中断。他在1902年愚园雅集后写给黄葆年的信中自陈“弟从夫子(李光炘)之日甚浅”,⑦刘德隆等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9页。貌似谦辞,实非虚言。
(二)学派人物影响力的外部证据:在场的缺席者
除来自李光炘的记录外,学派人物的影响力亦需要外部资料的旁证。其中,姚锡光写于1896年的一则日记尤为值得注意。
……龙川传其学教授于南。始设讲于扬州召伯湖滨之丁家伙,嗣粤匪犯扬州,乃移讲于扬州东北之仙女庙,主顾氏家,筑精舍、处生徒,即所谓龙川书院也。未几,黄崖难作,龙川乃韬晦,谢生徒,徙泰州居焉。其时至者,惟高弟子黄锡朋(葆年)、蒋子明辈数人。
方龙川居丁家伙时,先君子亦寓伙上,讲学术最契洽,朝夕相质证,待之在师友之间。未几吾家毁于兵,先君子挈家走泰州东乡之姜堰。时龙川讲学仙女庙,岁往过从。而泰州之黄葆年、蒋子明皆介先君子以见龙川,称高弟子。及黄崖事起,龙川徙泰州,先君子实左右之。今凡游龙川门下及师事蒋子明之再传弟子,如毛实君、刘伯浩、袁淡生诸君子,皆海内人望;亦可见龙川学术之正。而先君子调护之勤,为不可没也。小春同年亦颇师承龙川,因与历叙先君子与龙川交际,并龙川学术。及二鼓始归。”①姚锡光:《姚锡光江鄂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25—126页。
姚锡光(1857—?),江苏丹徒人,与刘鹗同乡。日记中提到的“先君子”即姚父,其与刘鹗父亲刘成忠亦为故交。1896年,由于得到张之洞的赏识,姚锡光入湖北任其督府幕僚。
日记写于1896年5月21日,其时刘鹗恰为筑路一事到湖北见张之洞,多次到访姚锡光处,两人过从甚密。这一日,姚锡光午间与人聚会,谈及龙川门人吴铁樵“因谈寇连才太监以言事获罪正法”,“正法时,犹神色不变,从容就义”,众人慨叹“此亦闻千古未有之奇”。宴毕,姚锡光冒雨往拜“刘云抟太守”(即刘鹗),两人商议上制府言铁路事之公文,姚并协助“商改数处”。之后姚离开,探访友人岳尧仙,被留晚饭,与吴小春“证龙川师承”。上述引用文字,就是“证龙川师承”后的一段题外补录。
补录先是详细叙述了龙川的师承与黄崖教案的始末,情形与《龙川夫子年谱》基本一致。其后讲述姚锡光“先君子”与龙川的交往。姚父与龙川为多年故交,两人不仅思想上多有契合,姚父在生活上对龙川亦颇为照顾。这段因缘,亦在黄葆年《黄氏遗书·记言》中得到证实:“予之知有夫子也,姚子始启之而蒋子终成之也。”②黄葆年:《黄氏遗书》,方宝川编:《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四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第47页。由此看来,姚锡光对于学派中事的解说,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当天日记中,造访刘鹗与谈论太谷学派都是重要事件,但记载颇不合常理。姚午间与友人论及龙川,下午见到刘鹗时,并未谈论此事;晚间与吴小春详谈太谷学派之渊源,述及蒋文田之后的第四代传人,又只字不提刘鹗。而刘鹗恰巧又是这段时间姚日记中的重要内容,依据姚日记体例,但凡刘鹗到访,姚必花费笔墨,详细记载,兼及到访事由,对话内容,甚至事后姚对刘鹗行事的看法,可谓巨细靡遗。姚显然深受龙川门人事迹感染,为何唯独没有与刘鹗提及此事?若为避讳,何以对吴小春等人口无遮拦?日记中,姚锡光对刘鹗以“太守”相称,表明两人之间的关系可能似近实远,因此交谈多涉及实务,未能真正深入,或许是记录中两人未就“太谷学派”相关事交流的原因。但姚的叙述仍然提供了与刘鹗同时代人的旁证,至少在姚所接触的学派门人中,并未将刘鹗纳入第三代传人的重要人物之中。许多学者强调刘鹗与龙川的关系,认为刘鹗是太谷学派第三代传人中的核心成员。若果真如此,姚锡光、吴小春等人不可能不知情,更不可能不借刘鹗到访的机会,与其请益学派之事。
另一方面,补录两次提到黄葆年、蒋文田两人,都以“高弟子”称之,这也进一步证实了两人在当时龙川门人眼中的特殊地位。姚锡光特别说明,如今“蒋子明之再传弟子”有毛实君(毛庆蕃)等人,亦包括当日晚上他造访的吴小春。此外,姚锡光叙述中将毛实君算作“蒋子明之再传弟子”,间接说明,毛等人可能是在龙川殁后才较多参与太谷学派活动的,也因此被当时人算作第三代传人蒋子明的弟子,即第四代弟子。从这个角度来讲,刘鹗与毛庆蕃处境相似,由于入门后不久龙川即过世,或被当时人归为黄、蒋等人弟子,确有一定道理。被提及的第四代弟子,显然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与声望,但都是以其他社会身份为重,毛庆蕃与刘鹗入门时间相差不过一年,而毛的身份地位(时任)是刘鹗远远不能相比的,李龙川与黄葆年皆曾为毛庆蕃题赠诗作,但仍然与传承龙川所学,收授弟子讲学的“高弟子”,有本质上的不同。再者,以刘鹗之身份,却并不在姚锡光提及的重要人物之列,是日两人适才碰面,刘鹗频繁出现于五月间的姚日记之中,这似乎不应该是偶然的遗忘所致。
1896年,龙川过世十一载。姚锡光作为另一位了解学派传承的自称“师承”龙川的门人,又是刘鹗的同乡好友,在频密联络的背景之下,这段记载也可说是提供了另一种旁证。
清末民初文廷式、刘师培、许宝蘅等人均曾注意到太谷学派,述及李光炘后,或言及蒋文田、黄葆年,但均未提刘鹗。惟汪康年曾提到刘鹗,亦是如此说明:今此派大弟子姓黄,在山东云。乔(树枬)此派,毛石君(庆蕃)此派,刘鹗亦此派。①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61—862页。
二、黄葆年时期:殊途同归,而未能共辄
(一)刘鹗眼中的黄葆年:云中引路人
1885年李光炘过世后,学派活动一度陷于停滞。②蒋文田:《龙溪先生文抄》,方宝川编:《太谷学派遗书》(第二辑第四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第13页。陈建安因病辞世,谢逢源告老还乡,黄葆年次年赴山东任县令,开始十七年的为官生涯,同时积极联络张积中一脉在山东的遗绪,并召集南宗弟子在山东聚会,承师命“还道于北”,力图实现“南北合宗”。学派由此进入黄葆年、蒋文田时期。期间组织过数次同门聚会,如1891年武阳夜集、1893年朝城聚会、1896年芝阳洞聚会、1898年重阳节聚会等,集结数位至数十位门人不等,1900年更举行“庚子第二花朝蝴蝶会”,意在纪念张积中六十年前举行的“第一花朝蝴蝶会”,在学派南北合宗历程中可谓意义重大。③关于上述聚会,收入《太谷学派遗书》中的《归群草堂诗集》中几乎都有题诗记载。
这些聚会,刘鹗都没有参加。他赴山东参与治理黄河、绘制河道图时(1888—1890)在济南见过黄葆年,具体情形不详,按照他1902年致黄葆年的信中所述,两人曾讨论“公(黄葆年)之吏治,弟之河工”。④《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0页。
直到1902年愚园雅集,黄、刘两人再次相聚,刘鹗重新开始参与学派活动。是时黄葆年辞官回到故里,决意专事讲学。在毛庆蕃(时任江南制造局总办)主持下,黄葆年在上海召集弟子聚会。刘鹗四月十七日出发,二十二日抵沪。次日即“携家兄至制造局,已知黄、蒋诸君皆在也……石溪(谢逢源)丰神如故,黄、蒋除略有白须外无老像。朱莲峰、杨蔚霞皆在也。怵怵之雨与清谈相应答。”⑤壬寅日记,四月二十三日,刘鹗著,刘德隆主编:《刘鹗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700页。显然,刘鹗与黄葆年,谢逢源、蒋文田等人已多年未见。两天后,“应实君(毛庆蕃)之约”,早起前往愚园,“凡两席,老辈九人,中辈十人,议作《愚园雅集图》”⑥壬寅日记,四月二十五日,刘鹗著,刘德隆主编:《刘鹗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700页。。
上海之行共十余天,刘鹗数度与黄、蒋等人会面。二十八日,他前往制造局:“黄三先生述梦,云升至极高之区。戚先生云:至此地位,盛衰二气俱脱粘矣。赵明湖衰气未脱粘,屈平之流也;刘□□盛气未脱粘,苏、张之流也,皆不可升孔孟之堂。闻之警悚。”⑦壬寅日记,四月二十八日,刘鹗著,刘德隆主编:《刘鹗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700页。戚先生所云,难免吹捧黄葆年之嫌,但刘鹗听到后以“警悚”表达自己的感受,似乎心下服膺,若有所悟。两天之后,他在徐园做东,邀请黄、蒋与诸同人午饭。之后,“黄三先生约同浴”。晚上与毛庆蕃等人碰面。离开上海之前,他又两度赴制造局辞行。
值得一提的是,刘鹗在乘船回京途中,竟然以自己的梦回应了黄葆年的梦:“梦至一高楼,月三立于侧。云:再上为催速转佛之居,黄三先生见过,作颂赞之矣。予升梯入,见佛紫面,大口,厚唇,与予握手为礼。予亦作颂赞之曰:天旋地转,有常度兮,不可催而速也。日月运行,寒暑往来,有恒节兮,不可催而速也。圣人去兮,人心弊兮,世运之转,不可缓也……”⑧壬寅日记,五月初七日,刘鹗著,刘德隆主编:《刘鹗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701页。这一梦似乎是为了印证黄葆年确已“升至极高之区”,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而日记与书信不同,并无写作给他人看的必要,似乎更能看出刘鹗对黄葆年发自内心的敬重,这不仅超出了姻亲之情,也超出了一般的师友之情,在刘鹗心目中,黄葆年的“修行”已达到一种神秘的至高境界,是凡人所不能及的,这也正是已在商界取得一定成就、衣食无忧的刘鹗此时最需要的,他迫切希望能够追随黄葆年这样的人,在心性的修炼上得到引导,受到承认。刘鹗一心向学的衷心,亦可见一斑。
愚园雅集再次明确了黄葆年在太谷学派“南北合宗”过程中的地位,开启了学派发展的另一个时期。对刘鹗来说,他重新建立了与学派之间的联系,坚定了追随圣贤之学的决心。同年十月的一封信中,他恳切地向黄葆年表白向学的衷心,不仅将其引为知己,还为两人对于学派的传承发展划分了不同的方向,认为黄葆年可以“教天下”,而他本人在清末的复杂时局中,应以实际举动“养天下”。①《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9—300页。这也是现存唯一一封刘鹗致黄葆年的书信。但表白衷心的恳切言辞背后,满含着委屈与愤懑,细心的读者不难察觉,刘鹗其实是在为自己得不到黄的理解而申辩。那么,黄葆年对刘鹗究竟有何评价?
(二)黄葆年眼中的刘鹗:狂奔疾驰,是为小家之欲
自1902年至1908年刘鹗被清廷流放新疆之前,刘鹗与太谷学派之间保持着较为频密的互动关系。由于曾经正式拜从李光炘,他仍然算是黄葆年、蒋文田的同门,较之黄、蒋等人新收受的弟子,地位自然不同。除此以外,刘鹗与黄葆年、毛庆蕃皆有姻亲关系(刘大女儿嫁与黄次子黄仲素),这更拉近了他与学派核心人物之间的距离。但就现存的文献来看,黄葆年对刘鹗却多有微辞。
刘德隆于1993年披露了一封黄葆年致刘鹗的书信,较为全面地表达了黄葆年对刘鹗的态度。信中,黄葆年以“士各有志,岂容相强”来解释他何以与刘鹗“不见十年,未通一字”。其后的一段话更是耐人寻味:“今接手书,披肝沥胆,吐气如长虹,直言仲负薪之劳;且苦思取而代之”。“仲”为黄葆年自称,因在家中排行第三,有黄三先生之称,黄葆年亦以“仲年”自称。“负薪之劳”,应是指黄葆年多年来为学派发展付出的辛劳。在他看来,刘鹗“狂奔十载”仅是为了生计。“宫室妻妾”等庸众之事或许可能“狂奔而得之”,但“取负薪之事而代之,此豪杰与圣贤之事也,非仅可以狂奔而得之也”②刘德隆:《一封黄葆年给刘鹗的信》,《文献》1993年第1期。。黄葆年又言刘鹗有“龙虎之气”,反复劝诫他做事应谨慎,才可能得道。
很明显,这封信是针对刘鹗去信所做出的回应,而且很可能道出了二人不睦的症结,但遗憾的是,信件落款只有月日(十月初八日),与现存刘鹗日记中接到黄葆年信的时间记载亦不相合,无法确定写信的具体时间,只能以“不见十年”大致推断为1890年至1902年间。③目前能够见到的刘鹗日记是根据刘德隆等刘氏后人所保存的四册日记过录而来,据说20世纪60年代尚存六册,分别为“辛丑日记”(1901年)、“壬寅日记”(1902年)、“乙巳日记”(1905年)、“戊申日记”(1908年),亦不全。详情见《刘鹗集》(上),第744页。但即便如此,依然能够与刘鹗1902年十月间写给黄葆年的信形成某种呼应。在黄葆年看来,刘鹗这些年的作为皆是为了一己之私,并不能为他积累“圣功”,反而可能妨碍他自身的修炼。虽然不确定黄葆年在信中何以言刘鹗欲“取而代之”,但根据现存刘鹗书信推断,刘很可能只是说明自己愿意负担更多学派事务的意愿。然而,刘鹗以“养天下”自居的情怀,并将自己多年来投资经商的举动与“圣功”相关联的理念,黄葆年并不认可。
这样的评价并非一时意气用事,黄葆年还曾在讲道时以刘鹗为例来说明得道与否,不在于根器之利钝,而在于能否发恨,能否分辨“真假”:“刘铁云误于成家学道两事双全,现在道既未成,家又何如”,并嘱咐弟子“汝等不可不赶紧醒梦也”。④刘龢:《归群草堂语录》之三,严薇青、方宝川主编:《太谷学派遗书》(第二辑第二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版,第19页。
直到1909年刘鹗过世,黄葆年为其做祭文,态度仍然有所保留,“君有游侠之豪,有长者之义,有亲师取友之学识,而以不能贫贱之故,卒至守法赴边以死。吾不能讳其罪也。吾不能不思其德也。吾不能不思其功也。记有之,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呜呼,其终不失为崆峒之人与!”
按照刘鹗后人追述,清廷批捕刘鹗之前,亲友已听得风声,特意请人送电至苏州当面交给黄仲素,请其通知刘鹗暂避。但黄仲素竟将此电压下,未送刘鹗。⑤刘蕙荪:《铁云先生年谱长编》,济南:齐鲁出版社1982年版,第145页。虽然看似不近人情,但如果考虑到在黄葆年看来,刘鹗是有罪之人,所作所为皆因“不能贫贱之故”,赴边乃为守法,那么黄仲素此举就不难理解了。
1924年黄葆年过世后,李光炘后人与黄仲素等人主持归群草堂,虽坚持讲学,但逐渐难以为继,再也未能达到黄葆年时期的影响力。
总的来说,黄葆年时期刘鹗与学派中人联系较为频密,虽就现存文献来看,两人的思想交流有限,但刘鹗并未深入归群草堂讲学活动。这也符合太谷学派的实际情形。虽以弘道为主,面向下层士人聚众讲学,同时也是一个同人组织,年资深者未必听其讲学,以其他方面联系为多。如门人之间多有姻亲之系,李光炘之孙娶黄葆年之女,黄葆年之子娶刘鹗之女,毛庆蕃之女嫁刘鹗之子等。
三、结 语
刘鹗与学派之间的关系,应分为不同阶段进行考辨与论证。刘鹗拜门后的三十余年间,学派的主导思想并不完全一致。与正统的儒家学说不同,太谷学派并无忠诚于某一学术传统的拘囿。其经历三代传人,历时超过百年,每一代传人的思想、主张都有所不同。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以程朱宋学为中心,逐步转向反宋学的倾向。周太谷更尊崇程朱学,但又特别重视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第二代弟子中,北宗张积中程朱学与阳明学并重,南宗李光炘重王学胜过程朱学。到了第三代弟子,黄葆年、蒋文田则强烈批判宋儒灭人欲。①王汎森:《道咸年间民间性儒家学派——太谷学派的研究》,《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49—50页。而李光炘晚年的狂放,与学派对于“欲”的强调是有内在一致性的。这也有可能是刘鹗1884年后一度与学派中人保持距离的原因之一。②也有学者认为李光炘晚年的狂放是一种伪装,是出于黄崖山事件后对于政治问题的回避所采取的策略。笔者认为这可能主要还是个性所致。张进:《李光炘与太谷学派南宗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39—241页。
自李光炘时代至黄葆年时代,学派的传播对象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周太谷时期讲学的对象较为广泛,且辅以“圣迹”,受众下及贩夫走卒之流。到李光炘时,由于受到“黄崖山事件”影响,早期规模有限,门人并无明确的门槛,但及至晚期,在泰州安顿下来,渐渐发展起一些地位较高的信众,尤其留意招揽士人群体。其宗教色彩和儒学的结合,也为一些官宦和富庶之人提供了特殊的思想资源。但黄葆年显然已大不相同,他个性强势,不仅自视甚高,亦自律甚严。虽仍秉持学派文献秘不示人的传统,但从《黄氏遗书》和《归群弟子记》来看,迷信色彩已淡化许多。这从他删修的《李平山先生年谱》中亦可看出。谢逢源为李光炘编修年谱时,保留了许多李光炘“一语成谶”的事迹,但黄葆年将其全部删去了。同时,也因为黄葆年十七年仕途的经历,他结交的对象地位更高,到其执掌的归群草堂时期,集结了一批在社会上知名度较高的人物,亦因此形成学派发展的另一个高潮。
尽管朱季康在考察太谷学派时曾特意提到其“义利并重”的生存理念,③朱季康:《近代华东民间秘密互助团体太谷学派的生存与信仰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8—143页。但从现存的著述和史料来看,学派主要的传承者轻商重仕的观念仍然是根深蒂固的。而由于传播对象以社会中下阶层为主,因此,具体的操作层面与学派中人的著述之间存在差异,亦在情理之中。换言之,利可为其所用,然逐利之人并不会因之受到尊重。黄葆年三度应试,后来又长期在山东为官,这段经历更提高了他在门人中的声望。而李光炘殁后,官居高位的毛庆蕃与黄葆年关系尤为密切,两人时有诗歌唱和往来,互相引为同道中人。毛在学派中的地位和影响也是后来一心从商的刘鹗所不能相比的。
刘鹗不同时期对于学派的参与程度,亦与其本人身份和心态的变化有关。早年仕途不顺,又颇有恃才放旷之气,虽治理黄河有功,但也因官场所见,颇觉失望。最终弃儒就贾,既是明清以降仕商合流的潮流与清末“经世救国”的特殊背景所致,也未尝不是个人选择。到1900年前后,路、矿事稍有所得,境况好转,而愚园雅集又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刘鹗再度参与学派活动。这时他已不是初出茅庐、一文不名、空怀一腔抱负的年轻人,而是银钱往来不断,与洋商交往密切的商人。由于并非阐释学派思想的核心人物,其社会身份对于其在学派中地位的影响就更加明显。虽然因经商有所成,以及入门年资的积累,成为黄葆年时期较为密切参与学派活动的主要人物,但也正是由于经商过程中引发的诸多争议,被视为不能安贫,为成家而误“得道”,无法得到黄葆年等人真正的赏识。作为刘鹗本人来讲,他确有对于圣贤之学的追求,这也使他仍然期冀能在官僚体系之外找到精神皈依,同时弥补他未能有经学研究的遗憾。正因如此,刘鹗与太谷学派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个面向:一方面是刘鹗以诗作、小说、书信屡次表白忠心,并与黄葆年、毛庆蕃等人结成姻亲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学派中人对他多有微辞,甚至并未留下足以印证其在学派中地位的文字材料。
刘鹗经商涉及多个领域,同时喜好收藏,其多重身份也使得他交游之人较为驳杂,与太谷学派中人的往来,只是他各种社会活动的一部分,他并不是太谷学派学术传承的核心人物,也并未留下任何相关的学术著作。在讨论刘鹗的思想时,我们也应考虑到清末的社会环境与思想背景。太谷学派亦是这个大背景中的一股暗流(并非逆潮而动),而且正体现了明清以降中下层儒生对于社会变动的反映。
此外,而黄葆年过世后,黄仲素又曾坚持讲学一段时间,但学派活动终于渐无声息,刘鹗后人刘大绅、刘蕙孙等人主动承担起传承学派思想的重任,并将家中所藏周太谷、张积中、李光炘等人遗稿印行传播,也由此维系了学派的思想余绪。虽是刘鹗身后事,学派活动已基本停止,以研究、翻印著述为主,但亦形成两者关系的另一个阶段,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责任编辑 王 桃 责任校对 池雷呜]
B249
A
1000-5072(2016)06-0114-09
2016-03-10
陆楠楠(1981—),女,宁夏银川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文学院讲师,清华大学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文学研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创新团队项目《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力》(批准号:CXTD5_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