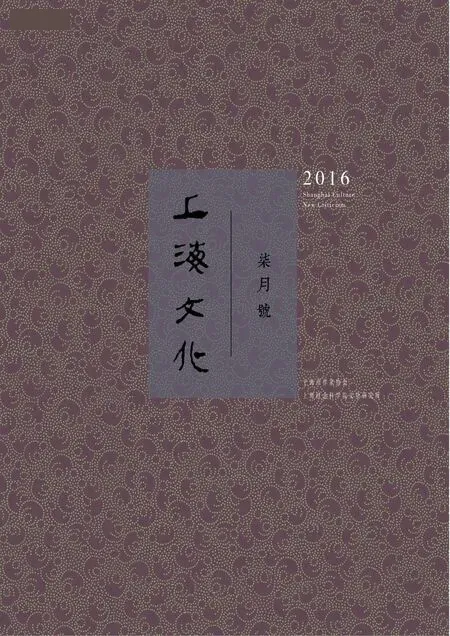雅典悲剧的观众
2016-11-25西蒙戈德希尔李平
西蒙·戈德希尔 李平 译
雅典悲剧的观众
西蒙·戈德希尔 李平 译
古希腊文化是一种表演性质的文化。这种文化凭借大规模的社会体制和行为规则,使得具有竞争性的公共表达具有了某种稳定性。举目可见充满男子气概的竞赛场,到处是歌声阵阵和演讲滔滔的会饮。剧场——由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崛起,希腊文化在地中海地区传播开来——成了希腊特性的关键符号。雅典文化在公元前5世纪的主要特征,就是发展了这些具有影响力的体制,而且可以说,已经发明了剧场。但是,在大多数方面,雅典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希腊城市。雅典民主政体的独一性,造成了一种表演文化的特殊类型。法庭和议会是民主政体的重要政治形式,是城市里冲突和辩论的主要场所,也是公民们获得权利的主要途径。法庭和议会充斥着大量的公民听众,因为那里会有演说家面对公众发表演讲。公民们则通过投票达成一个个决定和结果。民主制度使得公众争辩、集体决策和共同承担参与责任成为其政治实践的核心元素。作为参与者中的一员,不仅意味着你是城市社会结构中的一颗螺丝钉,而且本身就是一种基本的政治行为。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笔下的克里昂(Cleon,一位公元前5世纪持有不同看法的重要政治家),却不屑与此,曾把雅典人称为“演讲的看客”。雅典的政治意识形态自豪地强调,民主政体将实践把事件置于“公共领域讨论”的特殊承诺。任何一场关于希腊悲剧观众的讨论,都不能用现代戏剧经验的结构来审视之,而是要看到,它既体现了希腊文化表演价值的普遍性,又特别能显示民主制度特殊环境及其体制的特异性。这里,成为一名观众的要务,是担当起民主公民的角色。
社会戏剧与观众参与
在雅典的日程表上,戏剧是一项主要的政治事件。我所说的“政治”,不是今天理解的狭义,而是广义的“有关城邦的公共生活”的意思,就像保罗·卡特利杰(Paul Cartledge)在他的文章中已经概括过的那样:戏剧节是这样一种机制,公民的身份在这里被展示、定义、探索和质疑。这可以从规范戏剧的节日安排、仪式性演出和戏剧本身看出来。最重要的戏剧节是“大酒神节”,这里我将首先关注一下节日活动的不同类型,以展示大酒神节上观众中广泛存在的参与意识。
在日程表上,戏剧表演之前的事情不十分确定,然而它包括了:(a)举着狄俄尼索斯塑像的队伍前往通向伊柳塞拉(Eleutherae,靠近雅典的村庄)路上的一座神庙,然后再折回雅典的剧场区,在这里举行献祭活动并咏唱赞美诗。公元前2世纪,丁男(ephebes)——有正式成年人地位和全部公民义务的年轻男性——在这支队伍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许多学者据此推测,雅典的这个阶层在公元前5世纪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b)至少从公元前四百四十年开始,有一个演出前的仪式(proagōn):剧作家和演员被介绍给大众,戏剧的主题也会被宣布。目前尚不清楚这里的观众会是哪些人,但柏拉图确实在《会饮篇》(Symposium)里向剧作家阿伽通(Agathon)讲过,观众是一件令人烦心的事情;(c)这个仪式之后,是盛大的正式的游行(被称为pompē)活动,游行最终会导向献祭——在狄俄尼索斯祭坛内奉上公牛。这个活动的规模特别壮观,各路代表带来了各式各样的圣物和祭品。比如,一个被选出来的贵族血统的年轻女孩手捧一个盛装祭品的金篮;还有人捧着具有仪式意味的条状面包,它是男性生殖力的象征,通常与狄俄尼索斯崇拜有关。居住在这里的外来侨民和公民们都穿着特别的长袍游行。就是说,在节日中不扮演任何特殊角色的公民都能够参与到队列中去;(d)游行之后或许会有仪式性的纵酒,一场庆祝性质的狂欢。尽管并不清楚这是否与游行是一回事,或者说这仅仅是对游行和献祭的一个不太正式的描述。
这些开头的活动吸聚了许多雅典人,他们是城市里特殊阶层选出的代表,或者某些团体选出的代表,说大一点,就是雅典居民选出的代表。当队伍走向祭品和盛宴(以及狂欢)开始时,观众与游行者之间的界限一定会越来越模糊。这个节日让所有参与的雅典人成为了一体。
参与和展示的进程在剧场得以继续。至少是公元前5世纪中期开始,戏剧演出之前的四个显然相当重要的仪式就已经形成了:(a)十位将军——城邦的军政大员——往地上倾洒奠酒。从日程表上可以看出,被选出的官员们确实很少会像在这样的仪式上那样,表现得如此团结。它强调了城邦的力量和组织能力。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基础,这个盛大的节日才得以兴办;(b)有一份声明会通报一些公民的名字,这些公民通过特定的方式使城邦受益,所以也因为自己的服务而被授予皇冠。据演说家埃斯基涅斯(Aeschines)说,其时还曾发布过一些别的公告。比如,释放奴隶的公告,或那些来自别的城市的嘉奖的公告(他们通过一部法律限制对已经被自己市政当局嘉奖过的人的通报)。还有就是,这
样一来,城邦的政治结构就再一次被清晰地强调了;(c)有一个雅典帝国附属国的贡品展示。展示会上,所有的进贡财物都环绕陈列于剧场。这个仪式赞美了拥有强大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的雅典的荣光;(d)那里还会出现一批男青年,他们的父亲都为国捐躯了。这些孤儿是由国家出资抚养和教育的。现在他们成年了,穿着全套考究的军服出现在剧场,发誓保证像他们父亲当年那样,为国战死。军事国家的公民责任被仪式性地展现出来了。
这些仪式中的每一种都以不同的方式促进并凸显出国家公民的参与理念和理想,以及雅典城邦权力的形象。仪式通过这种公民活动使城邦获得了荣耀。戏剧的观众包括那些在先前仪式中挑选出来的人,剧场中的这一特殊时分有可能成为城市政治生活中极富激情的一刻。公元前三百三十年,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和埃斯基涅斯之间激烈的政治纠纷,很显然就是关于公元前三百三十六年在剧场授予德摩斯梯尼皇冠的颁奖仪式一事的,而德摩斯梯尼的演讲《反对美狄亚斯》(AgainstMeidias)则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美狄亚斯(Meidias)在剧场里打了德摩斯梯尼。德摩斯梯尼在酒神节上对美狄亚斯出现时的陈辞,清楚地显示了他在紧急时刻面对公民群体的那种个人荣誉意识:“酒神节上的观众们,当他进入剧场时,叱责他,向他喝倒彩,做出所有可能的事情来表示对他的极度厌恶……”演讲者的通篇言辞与戏剧语言一模一样。这出发生在剧场里的关于美狄亚斯的社会剧,后来还成为法庭上进一步辩论的主题。剧场成了这样一个空间:这里所有的公民都是演员——因为城市本身和它最重要的公民都在展示自我。
在希腊的创作中,合唱队指挥的身份所体现的作用常常是多方面的——有时仅仅是对富人征税从而使穷人受益的一种形式;有时则是让富人资助城市的绝好机会,就像所有的好公民应当做的。但清楚的是,合唱队指挥的身份提供了接受广大公民注目之荣誉的机会(正是在作为自己部族的颂歌合唱队指挥时,德摩斯梯尼被美狄亚斯打了,因此打人事件的公众影响非常激烈)。奢侈戏服的耀眼夺目,成功的可能性,庆祝活动时在城市集会前的隆重的个人露面,都是合唱队指挥提升自我地位的重要时机。因此,很自然地我们就听说了,亚西比德(Alcibiades),一个公元前5世纪的公民,身着紫色大袍漫步走过惊讶的公民人群,在众目睽睽之下显得非凡无比。我们还从(他的敌人)那里听说,他在竞赛中对裁判和公民的态度蛮横傲慢。大酒神节是男人们竞赛的节日,这不仅指戏剧或合唱队方面的竞争,也是合唱队的指挥争夺自己在城市里的地位的机会。
重大的节日里会上演戏剧,而这些节日本身也是一场社会剧。观众作为一个巨大的群体参与这场戏剧。在他们面前,也正是靠了他们,杰出的公民才显示出自己的了不起。由于整座城市和它的公民都仪式性地呈现在大酒神节的舞台上了,因此,观众就构成了那种所谓的“公民注视”(civic gaze)。
观众即城市
学者们是根据剧场大小来估计公民观众数量的——这是一项更艰难的任务,因为在公元前三百三十八年到公元前三百三十年间,莱克格斯(Lycurgus)用石头重建了剧场。学者们通常给出的可信观众数量在一万四千到一万七千之间。《会饮篇》中,柏拉图说:阿迦通在这场悲剧竞赛中的胜利,是在超过三万希腊人的见证下获得的。这一说法更多是为了显示大酒神节的威望和公众的赞誉,而不是其可能的观众数量。柏拉图之所以这样说,至少一部分原因是将三万视为雅典公民的常规数量,这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无论观众的事实数量和组成是怎样的,有这样一种说法不断被重复,那就是:“整座城市”,或更宏大地说,“整个希腊”都在剧场里。
一万四千名公民的正式集会,自然使得大酒神节成为不仅在雅典日程表上,而且在整个希腊都是最大且唯一将公民群体集合在一起的事件,奥林匹克运动会(数据不容易得到)或确实重大的战役也许除外。公元前5世纪公民大会(The Assembly)的参与者一般在六千人左右——也经常被称为“城市”或“整个城市”;法庭也是从这六千名公民中选取陪审团人员:陪审团成员的数量根据法院和案子的情况而定,但数量一定会大于今日陪审员——最少二百人,最多时达六千人。在规模和宏伟程度上唯一接近大酒神节活动的是“泛雅典娜节”,这个节日每四年举办一次。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泛雅典娜节是全雅典的节日,其核心事件,就是去往帕台农(Parthenon)神庙的大游行(pompē),城市里的所有团体都派代表出席。大游行的盛况可以在帕台农神庙的装饰性雕刻上见到。游行之后是体育竞赛、音乐和诗歌的比赛,选手是从整个希腊选拔出来的(这也是泛雅典娜节的一个泛希腊主义元素)。跟大酒神节一样,这些非常精彩的活动,突出并提升了雅典作为一个城邦的光辉地位——它向自己和外界展示了城市之为城市应有的样子。然而,即使在泛雅典娜节上,也缺少由舞台或庞大的公民观众所传递的那种关注。所以,大酒神节的超大规模赋予了自身这部社会戏剧以不同寻常的意蕴。
可以确定的是,大酒神节如此众多观众中的绝大部分是雅典公民——有选举权的成年男性。许多研究资料都将“合适或被期待”的悲剧观众视为公民团体。我会在后面考虑观众反应和悲剧的教育作用时讨论这件事的意义。现在我将首先来看看,公民团体在剧场内是如何被组织和安排的,其次也来看看观众中的其他人员。
在希腊的剧场里,席位被划分成若干个由座位(被称为kerkides)构成的楔形,即使在莱克格斯重建剧场之前,席位划分的方式也是迷人的。有一片席位被称为议会区,是专门留给议员们的。议会由五百名准备和实施那些制定政策的公民大会事务的公民组成。这五百名公民就像雅典民主制度下的大多数官员一样,由抽签任命。按规定,议员在地域上必须分散,每十个部族推选五十名议员。这里非常值得一提的是,狂热的竞争活动在各个部族由五十人组成的诸多合唱队中展开,每个部族还被要求提供一个名单,从中挑出竞赛的裁判——每部族一人,这也由抽签决定。这些组织规则,尤其是议员的特殊席位,一方面突出了民主国家官员的权威,另一方面也强调了民主制度之下的社会政治组织的正规性。
同样清楚的是,由于战争而成为孤儿的男青年,拥有展示自己身份的特殊荣誉席位。这与他们在大酒神节上传递神的雕像和开场献祭时的特殊角色相符。然而这,就像我已经提到的那样,只是在最新发现的时间较晚近的铭文上被证实而已。这种有关特殊男青年的正式机制是在变化的,如果由此推断,公元前2世纪真实的事情在公元前5世纪也同样真实,就显得不够明智。所以,无法认为这个阶层的所有公民都有特殊席位。不过有一点很明确,分配给作为战争孤儿的男青年的席位之所以与众不同,为的是在仪式和空间上突出显示:这是一个将以公民身份承担起全部职责的群体。
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其他的每一片席位都是为某个特定部族保留的。有三条证据可以支持这个假设。首先,(曾经)最近的铭文上有证据表明,在哈德良(Hadrian)时代——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去世五百多年之后——座位是按特定部族分配的。人们经常假设,也许更早之前就这么安排了;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用刻有公元前4世纪或者更早的部族名称的铅令牌做的剧场门票流传了下来。这可能意味着,很早以前部族联盟的席位安排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三点,也可能是最没说服力的,那就是亚历克西斯(Alexis)的喜剧《女性权力》(FemalePower)中的一个片段。在这个片段中,女发言人抱怨,不得不像外国人一样坐在位子的最后一排,似乎承认外国人有着特殊的席位。虽然这意味着外国人确实存在特定区域,但没有相关背景材料的支撑,这个片段还是让人着急。拿不出确定性的证据是可能的,这种关于部族席位的猜想,清晰地折射出人们对部族在节日中的组织方式,以及由空间呈现的社会政治区划问题的关注。
也有尊贵的席位(prohedrial)——位于每个区域的前排——是留给特定的祭司,尤其是酒神自己的祭司,以及特定的权贵的。民主制下的雅典,一方面是集体性努力、公民平等意识,强调国家高于个人;但另一方面,是个人对荣誉的渴望,看重个人展示与家族荣耀。这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张力。观众的空间区划——普通公民的区域、可以由尊贵的席位分辨出来的某些官方或代表性的团体的区域——戏剧性地展现了雅典社会生活中心的生动状态。因为大酒神节的观众构成了“公民注视”,所以,他们入座的方式绘出了一幅公民群体的结构图。可以说,大酒神节在仪式和空间上展现的,就是整座城市。
那么非公民呢?有哪些,又有多少非公民到了剧场?这些问题的部分答案是简单的,另一些则争议很大。这里有四个群体需要考虑:外国人(xenoi),外国侨民(metics),奴隶和女人。我将按顺序一一说来。
外国人确实出现在大酒神节上。随着这节日名气的扩散,剧场部门有了大量的文化资金,很可能有更多的人,特别是从邻国来的人出席了节日活动。然而,关于外国人的数量并没有牢靠的证据——宣布酒神节的活动是“面对整个希腊”的言论,不能被当作有大量外国人参加的凭证。无论外国人是否有一个分开的区域,我们都不知道入场是如何被组织的。不过大体上说,的确许多外国人都出席了,酒神节也特别被用来表彰外国权贵或国家的赞助人——这在某些情况下意味着外国大使的荣耀。他们坐在前排专门的位置上,看着自己国家被强制进贡的物品一一展现在剧场。城市在酒神节展现的那种国际感与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笔下的里尼亚节(Lenaea,一个中等规模的戏剧节)形成了反差。在那里,如同《阿卡尼亚人》(Acharnians)中的一个人物说的那样,“还没有外国人出现……我们只不过是一些自己人”。不能从字面上就得出里尼亚节上外国人完全缺席的意思;但它确实表明了,大酒神节对观众中的外国人尤其是外国官方代表出席的强化,提高了城市和公民将节日作为展示最大限度的公众自我意识和自我提升舞台的观念。
Metics——非公民的外国侨民——也会出席,酒神节和里尼亚节都会。并不知道他们是否有特殊席位,但是在泛雅典娜节和酒神节的游行上,他们可能会穿着特殊的长袍行进,他们是被雅典的作家们特别甄选出来并作为一个团体出席活动的。然而我们依然没有证据可以说明,是如何组织他们入场,以及有多少外侨出席了。
奴隶和女人让我们进入了更有争议的领域。有不少人说,奴隶绝对可以参加酒神节(尽管也常推测不会有许多奴隶参加)。有一条铭文证实:“议会的助理们”——八个在公共服务机构工作的奴隶——在剧场中有特别座位,大概跟议员们坐一块。然而仅有三个证据是关于其他奴隶的,虽然这些证据都是公元前4世纪的,但还远不是令人信服的。第一条也可用于酒神节上的妇女。在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Gorgias)中,苏格拉底申辩说:音乐和诗歌,与哲学不同,旨在让观众娱乐而不是教化;即使悲剧这种最严肃的艺术形式,也是一种“煽动”。这是在视诗歌和戏剧等同于修辞的情形下,关于修辞的极具修辞化的攻击中的一部分。苏格拉底在总结自己的艺术观时说:“因此,我们现在发现了一种意在吸引大众(dēmos)的文体,它将孩子、男人、女人、奴隶、自由民聚在一起,这是一种我不大欣赏的文体;我们已将它称为一种奉承(kolakiken)的形式。”他的结论不仅仅是关于悲剧的(而且完全没有提到任何演出的环境),尽管悲剧是苏格拉底所举的最终也是最困难的例子;确切地说,他是担心所有的艺术都成为煽动的形式。苏格拉底的结论,并不是暗示奴隶(或妇女)才是悲剧的观众,而是诋毁这种混杂和不道德的语言形式。他认为:这种语言只会迎合、取悦于自己的观众,这种(民主化的)语言形式没有适当区分不同的观众,也完全不懂如何提升观众。这种典型的(贵族化)希腊方式所表达的观点是基于这样的假设:悲剧语言混淆了阶级、社会的分层,而这种分层(成人/孩子、男性/女性、奴隶/自由民)通常是不能打乱的。
第二条证据来自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他在自己的作品《人物》(TheCharacter)中,把那种名为替外国人买票,而实际上带自己儿子和儿子的家庭教师去看戏的人称为“不知羞耻的人”。这里的带奴隶(甚至“他们的家庭教师”!)去剧场——当然了,这很可能是一个人“不知羞耻”的一部分——是一种罪孽,而不是雅典人行事的准则。
第三条也是最不重要的一条诉说文字,来自埃斯基涅斯,他声称:很多年以前,戏剧上演之前的时间是用来让公民宣布奴隶解放令的。因此,也许可以推论,奴隶们出席了这样的宣布仪式(当然了,尽管只是一些等待被解放的奴隶)。此外就再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奴隶会成为剧场的观众了。在古代的典籍中,奴隶的隐身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大难题。另外,在某些场合奴隶确实被要求去参加宗教活动(比如泛雅典娜节)的说法,也是有争议的。从这条证据很难得出这样切实的结论:奴隶们(公职人员除外)会参加酒神节。如果他们的确参加了,那么,他们就不会被我们知道的雅典作家描绘成是“应当而且合适”的观众。奴隶的隐身不仅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也具有社会的原因。
阅读越来越多有助于我们对观众以及戏剧演出本质理解的材料,就可以知道,妇女是否参加了大酒神节是一个多么具有争议的问题了。不幸的是,这里没有哪怕一条证据可以清楚而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因此,讨论就只能扩展一下,依赖那些对其他雅典节日的分析和妇女在雅典文化中扮演角色的总体估算,以及对于困难而模糊的材料的某些过于简单的解释上了。甚至,它们常常只是一些假设,也就是所谓的“直觉”。这里,我不可能去处理所有已经被用来解决这个题目的材料。我将首先概述一下几个没有争议的“事件中的事实”;其次,我将来看看那些古代作家的文件,这些相信妇女参加的文字被认为是最强有力的证据;再次,我将看看那些关于其他节日的分析,以及妇女在雅典的地位的不同意见;最后,我会审视一下对悲剧观众理解上的争议究竟意味着什么。
让我从那些我认为无可争议的事实开始。没有妇女直接参与到戏剧的写作、制作、演出或评论中去。没有妇女能够从赞助雅典公民参与戏剧的基金中申领到款项。至少有一个女性参加了仪式性的游行:一位被特别挑选出来的、出身好的(即公民)、未婚的女性,捧着神圣的篮子。除此以外,每一条负责任的材料都使问题具有不确定性。
那些用来证明妇女在古典时期参与戏剧活动的最重要的文本,来自于阿里斯托芬和柏拉图(后来的逸闻——比如一个有名的故事说,女人只要看一眼埃斯库罗斯笔下那进入剧场的的复仇女神(Aeschylus’Furies),就会流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因为毫无疑问,这里所说的妇女确实进入剧场的事是很久以后才发生的,而且再说,这些故事往往是后来的作家为了呼应剧本里面的特殊段落而编造出来的)。在阿里斯托芬的戏剧《和平》(Peace)中,主人和他的仆人正在把麦子扔向观众:“每个人都得到麦子了吗?”主人问道;“这里的每一个观众都得到了麦子”,奴隶答道;“但是妇女们一点也没有得到”,他的主人说;“不过,她们的丈夫今晚会把它给她们”,奴隶回答说。在希腊语中,“麦子”(krithai)这个词的复数形式与俚语中的“阳具”(krithē)这个词相同,因此这个笑话很容易被理解(尽管没有解释)成“所有的观众都有他们的麦子/阳具”,“妇女们没有麦子/阳具”,“她们的丈夫今晚‘会把它给她们’”。这段幽默的对话一点也不能说明妇女参与了戏剧活动。相反,这倒可以假设,妇女们坐得太远了,以至于麦子无法投到她们那儿。因此,这个笑话既表明了一个空间性,也有淫秽的意思。对于这些文字的两种阅读都是可以接受的。
批评家们已经发现,只要通过声称其中一个是比另一个“更好的笑话”来判定这段对话的意思还是可能的。但要通过这去充分证明妇女参加了戏剧活动或反驳说她们根本就没有参加,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另一段重要的论述来自柏拉图。我们已经读过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排斥悲剧和其他艺术——这些用在由孩子、妇女、男人、自由民和奴隶组成的群体身上的话语形式——的那些文字了。柏拉图《法律篇》(Law)的这段话也会时不时地被引用:“悲剧,是一种向‘孩子、妇女,乃至全体大众’宣讲的话语形式。”这段引语出自“雅典的外邦人”的演讲,此人是《法律篇》的主要人物,他构建了虚幻的国家大法,主张将一些创作想象性悲剧的诗人驱逐出城市。《法律篇》卷七中,他说:“因为我们也是诗人”——但法律就是我们的艺术——“不要设想我们会随便允许你们进入我们中间,从而在市场上搭建你们的舞台/展馆,把你们那些好嗓音(比我们声音洪亮)的演员带入,并且允许你们在孩子、妇女和所有人面前进行慷慨激昂的演讲。”这里尽管有很多柏拉图的诋毁性言论,但并未告诉我们关于大酒神节观众的任何事情。不能允许这些走来走去的表演家(用他们比“懂法律的诗人”——即哲学家——还要大的声音)在市场上建立舞台,去影响那些最有可能受到这些影响的人们——孩子、女人、大众。类似的,在《法律篇》卷二,柏拉图再次攻击娱乐和艺术的关系:那个雅典的外邦人明确地把悲剧视为“受过教育的女性、年轻男人,或者几乎所有的公民”的娱乐。暂且不谈柏拉图那些将女性、年轻男人和大众与悲剧联系起来的传统偏见,对“受过教育的女性”的这种规范,是否意味着只有受过教育的女性了解悲剧?如果这样的话,是否意味着她们是一群戏剧观众,或一群(受过教育的,因而是小规模的)读者呢?所以——这是一段不常被引用的文字——在《法律篇》卷七中,雅典的外邦人警告说:不要让任何自由民,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去学习喜剧,尽管他们必须通过看喜剧来学会区分“严肃”和“荒谬”。这里,柏拉图所关心的问题是,对智慧公民的培育以及文学的诱惑所带来的危险。他建议,应当只允许奴隶或外国人表演喜剧。因此,自由民完全不必认真对待它或者去学习它。雅典的外邦人关于乌托邦教育的这番说辞,显然不会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大酒神节的内容,但是,自由女性“了解喜剧”的说法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受过教育的女性”与悲剧的联系。
这就是被当作妇女参加大酒神节的最有力证据的一些章节,但它们并不是很有说服力的。尽管喜剧中有许多对各阶层男性的致辞,却没有对作为观众的女性的致辞。我们听说过女性参加其他节日活动的许多细节,但是却没有关于她们在剧场的说明。所以,总的问题可以被概括为:没有材料提及女性参加大酒神节,是受到我们那些多有疏漏的资料的影响呢,还是因为在希腊文化中确有男性在场女性则不出席的禁忌,所以在大多数公共场合都有女性缺席的礼仪?或者说,女性的不出场是大酒神节不同于泛雅典娜节的重要表征(在泛雅典娜节中,女性作为城市的代表以团体的形式列队行进)?换句话说,这不仅是一个由于缄默而造成争执的一般性难题,还是一个涉及“缄默的阴谋”(此与女性的历史特别有关)的更加特殊和重要的问题。
与其他节日或者我们知道的女性在雅典的角色作类比,能对我们有帮助吗?毫无疑问,女性是被排斥在某些主要的政治活动(比如公民大会)之外的。女性公民好像也不会作为证人出席法庭的活动,即使她们是事件的当事人。任何女性出庭的说法都是难以被证实的。她们也不能作为陪审员坐在法庭上。在这样一些公共场所,甚至在别人演讲的时候,都会有对女性露面的明显很强硬的禁忌。然而女性作为城市中的一个团体,在泛雅典娜节这属于整个城市的节日里参加仪式游行(Pompē)的事实是众所周知的。确实,在许多宗教区域,女性的参与都是必需的。因此,这里的剧场应该被认为是更像公民大会呢,还是更接近于泛雅典娜节?
让我们从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开始,去考虑一下仪式游行中女性的在场问题。杰弗瑞·亨德森(Jeffrey Henderson)写道:“很难相信,那个引导大酒神节进程的持篮者,是出席或被禁止观看戏剧的唯一女性。”他支持这样的说法:在对女性有常规限制的节日里,女性在宗教和休闲娱乐领域依然扮演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然而,在我们能够同意亨德森对这种可能性的呼吁之前,还有许多其他关于仪式游行的要素,以及妇女在宗教中的作用问题需要纳入考虑。首先,持篮者是一个处女(Parthenos),这是希腊思想中被特殊的禁忌所包围的一类人,只有在礼仪的保护下,她才会出现在男性的眼前,就像这里的情况。那么其他的处女呢?我们能否推测,她们也参加了这个活动?能否进一步假设:这个出身高贵的处女和其他公民的妻子和女儿在仪式游行的最后也参加了庆祝狂欢(Kōmos)活动(当他们不能参加会饮时)?为什么不去考虑在其他的宗教仪式中不提及个人或挑选出来的处女这件事呢?但即使女性的确参与了仪式游行,是否意味着什么关于戏剧本身的东西呢?很难看出女性在这里被说成以何种宗教角色去表演,或者说,公民的妻子和女儿是如何能够在没有得到宗教仪式的正式保护下,出现在公民注视中的。戏剧演出在不同的日子里举行,较少涉及明显的宗教活动。如果女人在场,她们坐在哪里,她们又是怎么去那里的?亨德森认为,后排有为妇女专设的席位(这是基于对阿里斯托芬的《和平》与亚历克西斯那些断简的高度怀疑得出的,这两人的观点前面都有引用)。虽然丈夫可能不会来看戏,或者带他们的妻子离开剧场,妇女也会在其他女性的陪伴下去观看戏剧。但亨德森的理论很难让我们相信,那些出身高贵的女人会和她们的朋友在剧场里逛进逛出。然而这种说法上的变换表明,它们只是建立在对妇女在雅典城和雅典不同的节日(它们使得妇女可能参与戏剧活动的观点有了立足点)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总体理解的基础之上的。不过,构成这种类推的可能的方法实在太多,故要做出支持或反对女性在场(这正是绝大多数学者正在做的)的切实结论十分艰难。
为什么学者都不太愿意去承认这些事实是很不确定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女性在剧场出现与否对于整个节日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戏剧的构架是由它的观众决定的。假如出现在剧场中的仅仅是男性和占统治地位的雅典公民,那么,这种戏剧对于性别政治、社会争议和城市中公民精致生活习俗的明显关注,就会形成一些面向公民大众这个整体的问题,因为公民是可能会被期待做出反应的观众。戏剧的议题是男性、成人和特权阶层所关注的对象,假如剧场里有女性出现的话,虽然那些“合适或被期待”的观众仍然是公民群体,但是对展示内容的看法就不一样了。这时公民们的判断仍然占主导地位,但区别就在于公民和他们的妻子一起观看了那些正在上演的戏剧。正因为如此,亨德森才写道:“阿里斯托芬的某些篇章真的就在呼唤和激发这样一群‘不合礼节、难以自控’女性的拉偏队的欢呼”。舞台上呈现出来的这种紧张气氛,犹如演员和观众在一起排练节目,而不是正式的演出。但这仍然是极其令人沮丧的:尽管这种解说的某些含义可以被大致描述出来,可是对于理解古希腊戏剧来说如此重要的问题,始终无法有一个确凿的答案。
这出发生在剧场里的社会戏剧,展示了一幅由观众构成的城市地图:无论认为妇女是地图上被沉默的在场者,抑或是缺席的符号,观众就是国家的代表。
教化城市
很可能是在伯里克利(Pericles)的领导下,城市设立了一项戏剧基金,以资助公民去参加戏剧活动。每一个被刻写在deme(指当地有组织的居民的城邦团体,在这个城邦里,每一个公民必须登记在册)名单上的公民,都可以索要戏票的费用(通常是两个奥波[古希腊银币],相当于一个非技术工人一天的工资)。这项基金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意图变更或修改基金是一宗可提起公诉的犯罪。很容易推断出,参加戏剧活动被认为是公民的义务、特权和要求。这种“戏剧是公民行为”的意识,被诗人反复声称“诗人是人民的教师”所强化了。的确,因为城邦的悲剧现状,柏拉图视悲剧为危险的煽动行为的攻击性话语至少在部分上是准确的。剧作家就是一个对城邦说话的智者(sophos)——一种富有特权和权威的声音。悲剧确实快速进入了正式和非正式的教化机构:人们通过会饮中的表演、阅读和研究来认识悲剧,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更是在整个希腊世界广泛传播开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我们的两个影响最广、用书写传达观众对悲剧教化反应的学者——对悲剧教化模式的评价是很不相同的。然而,他们都认识到悲剧对于观众的巨大力量,以及悲剧对公民建设做出的不同寻常的贡献。
我们也了解一些最新发现的关于野蛮的或不守规矩的观众反应的轶事,和某些立场偏激人群的事情——悲剧教育很显然没有使竞争和此类景象有所改善。剧场那种可供辩论和审议活动的半圆形式,就是为了邀请观众的参与。因此,演出本身也提供了一个令人眩目的景观,以激起演出与观众之间的活力。剧场里的集体——观众——对戏剧演出做出自己的反应,与舞台上的集体——歌队——反复与正在演出的事件作一种夸张性的互动,很相似。拉偏队的行为、不守规矩的举动,甚至戏剧场面本身,都与悲剧的教育力量形成了反差。如果悲剧有教化作用,那么,它肯定不只是戏剧声明或戏剧活动而已。对于古希腊悲剧观众的研究试图表明的是:通过参与节日所有层面的活动,雅典公民证明了自身的公民身份;通过节日的演出,这个城市也作为一个城市提升和突出展示了自身。雅典悲剧所引发的问题,促使人们去怀疑和探究:这种公民意识和城市意识,到底是否一直是这个民主制度非凡力量和开放的证明。
❶ 译自SIMON GOLDHILL.TheaudienceofAtheniantragedy, P.E.EASTERLING.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REEK TRAGED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编辑/张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