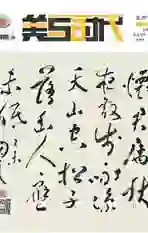从沈周《自画像》看其晚年心境与作品的情感表达
2016-11-22熊震
熊震

摘要:中国传统人物画的存在成为教化民众、弃恶扬善的工具。明代以后,人本主义的思想意识兴起,人物画创作亦逐渐摆脱思想教化的桎梏。尤其以沈周为代表的文人画中的人物题材,出现了表现性灵、抒发画家自身的情感、表述日常的生活细节、捕捉有情趣的瞬间等内容。这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在有意无意中改变着明代人物画的整体面貌。
关键词:人物画;沈周;情感表达
一直以来,中国传统绘画都兼具“教化人伦”的作用,“图画者,莫不明劝诫,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这是谢赫在《古画品录》中的记载,开宗明义地说出了绘画的功用,这种情况反映在人物画题材上尤其突出。
明以前与明以后,人物画作品面貌的不同,主要是由于人们价值取向的差异所造成。明以前,人物画主要被当成辅佐治国的宣传工具,被纳入治国和舆论造势的内容上来,只是在客观上有利于人物画的发展,在此风气的左右下,画家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社会教化的重任,人物画的存在成为教化民众、弃恶扬善的工具。明代以后人本主义的思想意识兴起,使得人物画创作亦逐渐摆脱思想教化的桎梏,画中的人物题材,出现了表现性灵、抒发画家自身的情感、表述日常的生活细节、捕捉有情趣的瞬间等内容,这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在有意无意中改变着明代人物画的整体面貌。
明代以后人物画开始逐渐向较为自由的方向处理,教化的功能也在逐渐消减,强调作品的意趣,注重作品主观意志的表达。当然在人物画的某些题材,比如写生方面,画家还是尊重对象的形象特征的,只是在明代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画家自身性情的表达与抒发成为绘画当中的主要因素,而这个主要因素的存在是由特定的现实环境所决定的。
“明四家”之一沈周的多才与博学在明中期江南地区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几乎达到了尽人皆知的程度,但是很多文献研究都集中在他的画作和诗作上,而对于沈周选择绘画和诗文的心理及意志层面的讨论相对较少,尤其是他的人物画方面。关于人物画,沈周74岁时的自画像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而74岁的沈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形象,画史上流传有他的作品。
明人陆楫撰写的《蒹葭堂稿》中有对沈周的描述:“沈周号石田,吴中名士也,博学工诗画,放浪山水间,隐居不求仕进。晚年言有持戒其子云:银灯剔尽谩咨嗟,富贵荣华有几家?白日难消头上雪,黄金都是眼前花,时来一似风行草,运退真如浪卷沙。说与吾儿须努力,大家寻个好生涯。”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沈周的个性,他身为吴中名士,工于诗画、不求仕进,放浪山水之间,但是却秉持家风,教育自己的孩子也拒绝做官。“白日难消头上雪,黄金都是眼前花”两句诗可以说是沈周的写照,从老年沈周的面貌特征中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学养深厚的画坛大家。从沈周自画像也可以得出这样的感觉,谦恭宽厚、乐隐山林,几乎成为沈周的标志性特征。
当我们仔细观察明代这些画家的人物画作品时,会发现他们的作品与前代大师的作品有很大的不同,这些差异性的存在不作为反映水平优劣的划分,只是由于各个时代整体性的社会风尚变迁而导致。过去的绘画作品多带有由“艺”入“道”的意味。《宣和画谱》记载:“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也者,虽志道之士所不能忘,然特游之而已,画亦艺也,进乎妙,则不知艺之为道,道之为艺。”也就是说,绘画之类的艺术门类,多包含着“道”的体现,前辈文人不论是抒发情趣的笔墨游戏,还是有意为之的作品,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带有经世治国、浓郁的出世色彩,其作品教化、寓意的特征明显。因为《宣和画谱》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观点是出自《论语?述而》篇,有着明确的指向性,将伦理学上的概念移植到绘画当中,把两个原本较远距离的客体融合在一起。由此论断看出,重视画面技术性表达的同时,又使得绘画成为了具有承载道德概念的载体。而这也是统治者愿意看见的一种状况,即绘画成为弘扬儒家仁义之“道”的具体体现。明代以前的传统人物画中,尤其在唐宋时期,如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与萧绎《职贡图》(宋摹本)等,也都有劝诫或歌颂的意味。但是到明代中期以后,世风日变,又以江南为盛,何良俊说原来他小时候家里请客,只是五色果品而已,只有贵客上宾来到时,才会添置鱼肉虾蟹等菜品,这种情况一年中也不过三四次而已;而今寻常的宴会,动辄就要十多个菜品,且水中、陆上的东西都要有,甚至去远处寻访珍品菜肴以会客,竟此作为,成为互相攀比之风,世间人人仿效之,成一恶俗(相关记载可见《四友斋丛说》)。明代文学家归有光也认为江南世风变化的轨迹是:“大抵始于城市,而后及于郊外;始于衣冠之家,而后及于城市。”从俭朴逐渐走向奢侈,这是当时的境况,而像沈周这种出身于世家的人物,生活在这般的环境当中,不可能不受到这样的影响,画作中传达的况味也自然不同于前代,这也是沈周当时所处的现实社会环境。因此,在沈周自画像中也自然重视其自我意识的表达,教化功能相应弱化,而记载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反映尘世生活的印记就成为画家创作的主要目的。
沈周晚年心境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即“名利不如闲”,这是明代文人士大夫的常用语,也是文人士大夫刻意追求的精神境界。从袁宏道所描述的五种快活方式来看,沈周的情况就是当时文人士大夫生活态度的一个典型。原有的“闲”的意思是不求名利,淡薄无为,自娱自足的状态,但是在明代,“闲”的观念也发生了概念性的改变,就是“趋俗”。文人的世俗化生活,主要体现在追求现实生活的幸福与享乐,对世俗生活有难以割舍的感情,他们耽于安逸舒适的物质生活,又在生活中贯彻闲雅的精神追求。文人在生活中的随意适从,有与友人间的唱和,不为衣食米盐所记挂,不为尘嚣所动心,安于诗画乐于独处;亦有与宾朋觥筹交错以忘其忧。我们可以从前文沈周的家世和交游状况了解到沈周等文人对于闲居隐逸的认识。他们认为只要志向在隐逸,则无须在实际生活中与常人拉开距离,也无须远遁山林;他们完全可以在游山玩水、治园修亭中获得隐居的乐趣,隐居而不绝尘,这是当时许多文人的自发选择。在“身隐”和“心隐”之间,他们更加重视“心隐”,对世间俗务不回避、不淡漠,因为这样才可以淡然面对生活,文人隐士才有“春时幽赏:虎跑泉试新茶,西溪楼啖煨笋,八卦田看茶花;夏时幽赏:空亭坐月鸣琴,飞来洞避暑;秋时幽赏:西泠桥畔醉红树,六和塔夜玩风潮;冬时幽赏:雪夜煨芋谈禅,扫雪烹茶玩画”的雅事。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沈周毕竟是当时江南优秀的文人画家之一,他绘画当中的教化作用虽然不可避免地在消减,但是他仍然在现实境遇的创作中传达自己的理想模式。只是沈周的理想模式中带有明确的现世重心,他在《石田诗选》卷八《自题小像》中云:“七十四年,我未识我。丹青一面,是否莫果。旁观曰真,我随可可。以真生假,唐临橘颗。以假即真,物化虫赢。真假杂揉,奚较琐琐。……呜呼老矣,岁月既移。茂松清泉,行歌笑坐。逍遥天地,一拙自荷。”沈周对自己的一生有着清晰的认识,终归于沉寂的生命意识在他的自画像中反复纠缠,亦真亦幻的表象交织在一起,丹青绘画也只是表现生命的一个瞬间而已。晚年的沈周在生活的真实与绘画的幻觉中,营造出属于自己的天地。
1502年,沈周76岁,其长子病逝,他悲痛至极。有诗记载:“佚老余生愿,失子末路悲。不幸衰飒年,数畸遭祸奇。独存朽无倚,如木去旁枝。剩此破门户,力疲叹叵持。屑屑衣食计,一一费心思。思深气血耗,痛瘁引百肢。多忘识虑浅,耳聩目兼眵。一旦一身内,有此众病滋。所若不敢诉,常畏老母知。小孙蠢不学,次儿诞而痴。后事不足观,百忧无一怡。吾性无妄好,执善信不疑。垂垂垂白乡,朝斯还夕斯。高高冥冥者,何物颇相欺?似我未蒙佑,反有灾害罹。滚滚人海中,黑白何可蠹?口亦不能问,理亦不能推。以死致度外,且活是便宜。今日尽今日,明日岂可期。亦复酌我酒,亦后吟我诗。我诗无好语,稿苴从散遗。儿在曾裒葺,今纸著泪糜。抱患天地间,空言亦奚为?”
晚年丧子让沈周悲苦难当,他在自己一力维持家业的同时,深感生活还有的现实与冷酷的一面,即便长寿也难以拥有真正的快乐,从年轻时候的意气风发,到中年的声明远播,直至老年的丧子之痛、亲友的离散之苦,都在沈周的自画像上有微妙的表现。面对如此境遇,老年沈周仍旧是笔耕不辍,其自画像的笔法丝毫不见颤栗之老态,反而呈现一派天高云淡、参透世事的禅意,在这张画像上,还有沈周83岁时的补遗:“似不似,真不真,纸上影,身外人。死生一梦,天地一尘,浮浮休休,吾怀自春。人谓眼差小,又锐颐太窄,但恐有失德。苟且八十年,今与死隔壁。七十四,八十三,我今在后,尔已在前。茫茫者人,悠悠者年。茫茫悠悠,寿夭偶焉。尔形于纸,我命在天,纸八百,或者有,天八百未然。生浮死休,似聊尽其全。陶潜之孤,李白之三杯酒,相对旷达犹仙。千载而下,我希二贤。”因此,现今我们才看到沈周的这张“乌巾赤舄,袖手凝立”的自画像,显出“道气盎然,极自得之趣”的面貌。
由上述可知,明代人物画在艺术创作上对于生活经历本身的关注更加密切。与此同时,创作者在艺术技巧和题材选择上虽受到前辈大师的影响,但是他们在创作过程当中,艺术家本体意识的加强使得他更加关注自身情感的表达也是不可忽略的方面。
作者单位: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