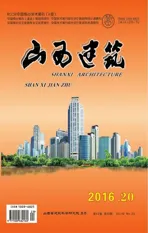儿童友好型城市公共空间研究
2016-11-22凃康玮
凃 康 玮
(湖北工业大学土木与建筑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8)
儿童友好型城市公共空间研究
凃 康 玮
(湖北工业大学土木与建筑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8)
结合我国城市儿童公共空间的现状,从可达性、安全性、自然性、多样性四方面,阐述了儿童友好型公共空间的设计策略,旨在创造出有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城市生活空间。
儿童,公共空间,活动场所,儿童友好型城市
0 引言
根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岁~14岁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6.6%。而正是这接近1/5总人口的健康成长与否,密切关系着祖国的发展与未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于1999年,2005年,2010年先后三次进行“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社会调查,结果表明网络已经成为少年儿童之间交流的主要途径。而正是这种过度的网络依赖,造成户外活动的急剧减少,随之带来一系列心理与生理健康问题——过度肥胖、孤独症、多动症、焦虑症、强迫症,这些听起来让人担心的病症在儿童群体身上出现的越来越多。
而过度的网络依赖—户外活动减少—儿童心理生理问题的产生,这样的因果关系逆推是否成立,过度的网络依赖是否是造成一系列儿童生理心理问题的唯一罪魁祸首,恐怕不尽然。“儿童专家逐渐地意识到建成环境对于儿童健康状况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责任,也开始关注建成环境是如何影响儿童心理和生理方面的”。与其说是网络让孩子们放弃户外活动的机会,不如说是城市中没有提供合适的、足够的户外活动场所。在我们常常思考孩子们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却忘记思考是不是我们的城市出了问题。
实际上,1996年联合国在召开的第二届人类居住会议上就发表了“儿童权利和居住”声明,提出了“儿童友好型城市”(CFC,Child Friendly Cities)的概念。之后在世界范围内,相继有400多个城市被认定为儿童友好型城市,但非常可惜的是,中国至今没有城市在列。
1 我国城市儿童公共空间现状
1.1 国家规划的儿童活动场地
回顾我国城市规划中对儿童公共空间的关注,最早始于1980年,北京市将儿童活动场地的建设写入居住区统建内容,之后的小区都依照此将儿童活动场地纳入建设项目中。2004年建设部公布的《居住区环境景观设计导则》,则对儿童活动场地进行了进一步更加详细的规范。这样的规划思路深受1920年代佩里提出的“邻里单元”的影响,认为城市规划中关注的儿童活动空间集中在运动场和公园,因此会在各社区单元预留出相应的活动场地。如我国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中明确指出,居住区应根据不同层级的规划组织结构设置居住区级、区级和组团级公共绿地,以及儿童游戏场和其他公共绿地。而在实际建设中,运动场和公园的性质却极大地限制了儿童活动空间的塑造,加上粗糙的施工,大部分儿童活动场地最后流于敷衍的形式交代,仅剩软质铺地加一堆或滑或爬的器械而已。
1.2 市场开发的儿童活动场所
从规模上看,国家层次自上而下规定的儿童活动场地一般局限于社区,尺度较小。随着儿童问题越来越多地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近年来自下而上的以儿童群体为主要受众的项目逐渐增多,且规模较大。从功能形态上对儿童公共空间做了一定的补充,但是由于理念落后,缺乏有效的约束管理,质量堪忧。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1)主题型儿童公园,这一类空间常常摈弃自然元素,极度人工化。过度追求视觉感官上的刺激,充斥着各种新鲜挑战的大型游乐设施,将儿童活动简单等同于儿童游乐,且普遍存在安全隐患。
2)以智力素质开发为卖点的娱乐教育儿童基地,如星期八小镇等。这一类空间常选择在室内,空气污浊。生硬的模拟情景设置无法代替真实的生活体验,且极大地破坏了儿童的创造力。过度灌输对儿童的培养教育,违背了其自然成长的天性。
总的来说,我国城市中的儿童公共空间还处在起步阶段,儿童特殊阶段的心理和生理需求没有得到城市公共空间的关注,孩子们的好奇心和精力也随之无法得到合理的释放。
2 儿童友好型公共空间分析及启示
城市中儿童公共空间缺乏的问题不单单只在我国。实际上世界范围内,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机动车交通的大量增加,步行空间受到挤压、绿地被强行割离,街道不复安全,儿童几乎找不到可以活动的公共空间。那么,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认证的“儿童友好型城市”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又是如何将城市定义为“儿童友好”的。
“儿童友好型城市是一个明智政府在城市所有方面履行儿童权利公约的结果,不论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或者社区,在公共事务中都应该给予儿童政治优先权,将儿童纳入到决策体系中(UNICEF,2004)”。从联合国基金会对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定义中我们不难看出,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创建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它关乎公共政策到管理实施的方方面面。我们现只就城市物质空间环境这一环节展开讨论。与此相关的CFCI和GUIC计划提到,儿童友好型城市需满足儿童以下需求:“拥有健康生活、学习、发展和玩耍的空间;远离暴力,拥有安全、和平的环境;拥有能与大自然接触的干净、便捷的公共空间”。再综合被认证的国外“儿童友好型城市”案例经验,在城市物质空间环境上想要达到“友好”标准,必须具备“可达性”“自然性”“安全性”“多样性”四种要素。结合我国目前现状,逐一分析如下。
2.1 可达性
城市设计导致活动场所分离,城市居住区高密度,对交通依赖程度明显提高。另外,家长普遍认为汽车对儿童造成十分严重的威胁。因此城市儿童步行进入公共空间越来越困难。
提高城市儿童公共空间的可达性,首先要加大公共空间的分布密度。德国城市规划明确规定,学龄儿童的步行距离一般为300 m~400 m,12岁以上少年儿童由于能骑自行车,距离可延伸至1 000 m,而幼儿则必须在父母监管范围内,即住宅周围。因此有必要按照年龄段,对城市儿童公共空间进行相应距离的等级划分,如分别以50 m,300 m~500 m,1 000 m为半径,以社区单元为中心,高密度分布儿童活动场所。
其次要改善城市中的儿童步行交通环境。“全球儿童安全网络”报告显示,“中国每年有近16 000名少年儿童步行者因道路交通事故受伤或死亡,年龄段以5岁~9岁最为集中,事故高发时段为中/下午放学时段”。儿童步行交通环境改善迫在眉睫。新西兰广泛开展的“步行校车”(WSB)计划可以提供借鉴意义:在上学和放学途中设定专门步行线路,在其中指定儿童可进入和出行的停止点,在成人监护下儿童以队列的方式穿行城市道路。其产生的积极意义不仅仅在于减少了儿童步行出行的危险,还减少了机动车交通拥挤,增加社区凝聚力。
2.2 安全性
公共环境近来越来越难提供安全感,这也是“称职”的家长为了保障子女的安全,减少城市公共空间使用频率的原因。危险的陌生人和绑架拐卖让45%的家长认为公共环境对儿童产生巨大威胁。因此,增加孩子们在户外使用公共空间的机会,首先要打破这种不安全感。中村攻在其著作《儿童易遭侵犯空间的分析及其对策》中,就对不合理规划区域作了分类,主要为三种类型:产业发生巨大变化的区域、车站及周边区域、住宅小区内的危险空间(如图1~图4所示)。这就要求城市规划相关从业者,在空间设计的初始就要主动规避掉这些易对儿童造成伤害的危险空间。


另外值得强调的是,要加大城市儿童公共空间的开放性和可见度,利于成人对危险和犯罪活动的警觉和监管。特别是可以适当促进多种人群共同使用空间,如儿童与妇女,儿童与老人,对不同的活动进行合理分区规划,既互不影响又能相互照应。
2.3 自然性
2010年,网易以国内近7 000名4岁~13岁儿童为对象展开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儿童幸福感远远低于农村儿童。究其根本,在于儿童与自然的亲疏关系。康奈尔大学环境心理学家的报告更是证实:“生活越贴近自然的孩子在面临生活中的压力时会产生越少的心理负担。孩子的家庭周围自然环境越多,孩子就越少会出现多动、焦虑或消沉等行为”。与之相反,则会如“The Last Child in the wood”的作者所说,“远离自然是造成儿童诸多心理病痛和行为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由此产生“Nature-Deficint Disorder”自然缺乏失调症。
所以在城市中,应相应的增加自然空间。可以借鉴的做法,如日本儿童教育界流行的体验型教育模式——“乡村留学”项目。其成功的代表如“森之幼儿园”,没有采用传统意义的幼儿教学模式,而是让孩子们身处森林之中,自由自在地玩耍。没有刻意的学习目标和目的,反而让儿童发挥自主能动性,在观察自然、聆听自然、触摸自然、感悟自然中自觉提高各项素质与能力。而对于大部分城市,自然空间有限,则可以学习欧洲城市屋顶花园的经验,在城市第五立面增加孩子们接触自然的机会。
2.4 多样性
由于不同年龄段儿童具有不同的行为需求特点,如0岁~2岁儿童需要成人辅助才能活动,感知力强;3岁~5岁儿童需在成人看护下活动,喜欢模仿和体验;6岁~7岁儿童需在成人视线范围内活动,个体表达强烈;8岁~14岁儿童可独立行动,积累多方文化信息。因此,在城市儿童公共空间的设计上要“因材施教”“量体裁衣”。
其次,研究显示儿童需要至少四种游戏选择才能避免不被其他使用者排挤(Kritchevsky,1977),贝里(Berry,1993)发现年幼儿童一旦掌握一种基本技能,他们在一个固定式攀爬设施上逗留时间不超过4 min。儿童对那些具有创新可能的游戏机会充满兴趣——一个狭窄的空间无法做到这点。这就要求设计者在设计儿童活动空间时要预留出足够大的位置,并努力创造多种多样能够吸引孩子们的活动项目。这与国内目前单调乏味的活动空间距离甚远。比较成功的例子如伦敦戴安娜王妃威尔士纪念游乐场和圣弗朗西斯科Lafayette儿童活动场。后者游乐设施的设计综合了儿童冒险、运动、娱乐、益智等多种方面。
3 结语
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创立绝不是一朝一夕,除了从空间设计的领域注意以上要素的掌控,还需要从制度管理上明确儿童在城市空间的基本权益。中村攻在谈到游戏场所的基本条件时说到,“由于受社会变迁的影响,儿童的游戏场所必须作为社会制度来考量。而在城市规划中,建筑中的公园绿地就变成一种制度。像这样被整备的公园绿地就成为近代都市居住环境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儿童友好型城市公共空间必须在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图中明确表示出来,并确保预留出足够的活动空间供未来发展需要。另一方面,国家层面的儿童公共空间设计指引也应尽早出台,对活动空间选址、功能使用、实施建造方方面面应形成统一的标准,以利于在全国范围推广,共同促进儿童友好型城市在我国落地开花。
[1] 中村攻.儿童易遭侵犯空间的分析及其对策[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2] 布伦丹格利森·尼尔西普.创建儿童友好型城市[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
[3] M.欧伯雷瑟·芬柯.城市——设计少年儿童友好型城市开放空间[J].吴玮琼,译.中国园林,2008(9):49-55.
[4] 钟 乐,龚 鹏,古新仁.基于儿童安全的城市开放空间研究述评[J].国际城市规划,2016,31(2):96-98.
Research on children’s friendly city space
Tu Kangwei
(CivilEngineeringandConstructionInstitute,HubeiIndustrialUniversity,Wuhan430068,China)
Combining with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our cities children public space, from the accessibility, security, naturalness, diversity four aspects, this paper elaborated the design strategy of children’s friendly public space, aimed to create an urban living space conducive to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children, public space, activity, children’s friendly city
1009-6825(2016)20-0010-03
2016-05-06
凃康玮(1987- ),女,讲师
TU-024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