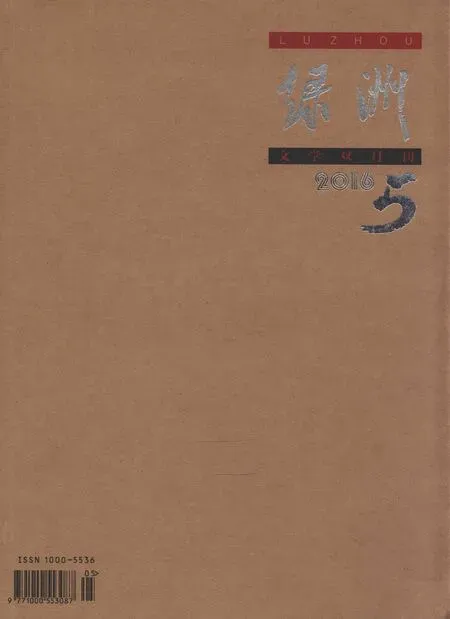噪音
2016-11-22王新梅
王新梅
噪音
王新梅
下班时间刚到,华丽就关了电脑。她几乎差不多是第一个离开单位的。最近单位开始酝酿评选好职工的活动,好多人都爱上了加班。华丽也想装一会,可她不行,她得回去给家里的高中生做饭去。
深秋的傍晚,可以嗅到初冬的气息。那丝气息陌生而熟悉。华丽想起才结婚那阵,一下班她就和闺蜜去广场转转,悠闲自在地晃一个下午。可现在,她过的差不多是复印机的日子,赶车、上班,下班、赶车,单调而重复。一切都会准时准点地出现和发生,毫无例外。比如现在,站在车站不到两分钟,6路车会准时晃晃悠悠地从前方出来,车上的人都会很安静,他们都会举着手机沉默无声。华丽差不多都坐在倒数第二排靠窗户的座位上。椅子上总会坐着一个学生。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穿着实验学校的校服。车行驶时发出的轰鸣声让人昏昏欲睡。华丽试图抵制自己拿出手机的念头,但最后还是掏了出来。浏览了一圈微信微博,她才关了手机装好。她眯起眼想等会下车后买点什么菜,做什么饭。继而就想到儿子。车是往市中心走的,越走两边越繁华。过西大桥的时候,华丽无视路边璀璨的灯光和一个又一个的亮化造型,心情糟糕起来。昨天和儿子吵了一架。高中了,儿子像变了一个人,变得敏感脆弱。还有一个不好说出来的状态,一副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的样子。她知道孩子压力大,也是忍了又忍。可一晃几个月过去了,儿子还是那副样子。
车停在清泉市最繁华的地方北门时,华丽下了车。住了几个月了,严重路盲的华丽才学会在密集的建筑里找到回家的捷径。先拐进一家小区再路过一段菜市场,然后才绕到她家的巷子里。刚来时,东南西北搞不清楚,好长时间她都是以那个医院住院部的高楼为参照物,磕磕绊绊地摸回去。一个多小时的站程,换两次车,绕来绕去,拐进巷子时华丽觉得自己可以去那个医院躺着了。
华丽租住房子的小区在最里面。巷子像所有的老巷子一样狭窄弯曲。他们找房子的时候还是夏天,狭窄的巷子里有穿堂而过的风和浓绿的树荫,古里古气的巷子看上去也怪怡人的。房子旧租金高。可儿子要上的是人人羡慕的重点高中呀,华丽一家心情蛮好。一切困难都被涂饰得别有励志意味,他们很快就决定租住在这里。秋天这个老巷子就面目沧桑了,黑乎乎的楼、斑驳的墙、角落里的垃圾、无家可归的老猫,像卸了妆的老女人,到处透着末日的暮色之气。主要后来儿子的学习并不像他们以为的那么顺利。总之,华丽到现在也没完全适应一个租客身份。你说,住得这么别别扭扭,无非是为了孩子。可这孩子他咋就不争气呢。一想起孩子,华丽好像就是个长时间充满气的气球,随时可以爆炸和崩溃掉。
菜店里面拥满了买菜的男男女女。躺了一天的菜都有些萎靡不振的样子,好像工作了一天的人。华丽买了点儿子爱吃的菜和水果后向家里走去。菜市场毗邻一个大垃圾箱,垃圾箱毗邻一个公厕。华丽憋着气不呼吸,快跑了几步。
一到家,华丽就忘记了疲惫,赶紧给孩子做饭。
饭做熟,孩子还没回来。她给何志打了个电话。何志正在洗澡,接了电话,声音闷闷的。她能想到他的样子,关了水龙头擦了手拿电话,手机在窗台上放着。他是单位搞营销的,24小时开机。她说米快没了。他那边说,喔,还能做两顿吧。她含含糊糊地嗯着。其实是能做两顿的。可还能说什么,告诉他自己心情不好,问他怎么教育儿子,还是说点单位的勾心斗角——像以前那样。他问,还有什么事吗?他急着洗澡,然后看球赛,然后看电影。不看球赛的话,他就去和别人打乒乓球。反正他会把自己放假这周的时间利用得足足的。真正过起单身汉的日子。她说没有了。语气明显淡下来。她就是这样,人家若对她好,她会还人家更多的好。若人家冷淡,她只要察觉,就会凉得更快。她先挂了电话,何志还没有放下,似乎想解释什么。她没有给他机会。她和他是自由恋爱的,曾经也热烈地爱慕过。何志年轻时候精神头倍足,甜言蜜语也是说过一箩筐的。可现在,何志的精气神只留给上班时游说客户用了。回到家后,沉默得像个思想家。从什么时候淡了下来呢。这个问题常会在某个时候突然冒出来。房子里很静。就在这个时候,她听到了那个声音。是录音机里播放的声音,是一些儿歌,接着是一连串的叫声。猫叫狗叫还有各种分辨不清的声音。声音是从旁边的邻居家里传来的。这新搬来的人家她没怎么见过。以前是一位老太太和孙子住着。七月份孙子考了大学搬走后,房子空了几个月。大约是因为房东涨了房租。房东涨房租是因为儿子那所著名高中去年又拿了全省最好的高考成绩,一千余人的学校,清华北大的就五六十个。每年慕名而来的外地好学生好几百个。不单是百年名校,大名鼎鼎的医院,还有这个城市最繁华的商业圈都在这巷子四周。这里再高的楼层再贵的房租都能租出去。房东相信,大家也都相信。这不果真就租出去了。旁边住了个什么人呢?华丽好奇起来。说起来,早出晚归的,除了看大门的,她还不认识小区一个人,对一墙之隔的新邻居也一无所知。全省最大的电器商场出巷子不到五百米,那儿上班的年轻人为了方便也会合租在这里。莫非在附近上班的年轻的三口之家?
邻居的声音继续夸张地持续着,还有哈哈的大笑声。这让华丽的心情不爽起来。华丽原来当过十几年的老师,留下了职业病,在学校听多了学生叽叽喳喳的吵闹声,家里就想静一静。邻居不管不顾地欢快地吵闹着。做作,孩子也不是这样哄的。相似的声音,勾起了她快乐的记忆,那个时候儿子多可爱呀,丈夫也总是那么温柔。她把房间的地拖了拖,窗台上的灰尘擦了擦,耐着性子等待墙那边安静下来。可那边的声音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反复的播放中,儿歌的歌词华丽都记起来了。其间还有一个女人发出的声音,好像在教孩子说话,声音大而夸张。倒也听不出来说的是什么,但真的是喊,那音量。
她解下围裙,来到阳台打开窗户。昏暗中,各类嘈杂声立刻涌过来。他们搬来时老公给房东提的唯一要求和建议就是,把沿街这面的窗户换成三层的。后来,他们真为这个建议暗自庆幸。三层玻璃的窗户果然不一样。外面是闹市,关了窗户,屋子里就是一方清静。他们很少开窗户,也避免制造杂音。老公也在时,孩子写作业,他们走路都得猫着步子,说话就打哑语。一点也不夸张,同事说他们家儿子高三时,两口子都是散步到半夜才回去的。
热闹是有侵略性的,站在窗户边,就什么也不可能想了。可这个时候,她偏偏在嘈杂声中分明听到了邻居家发来的声音。这让华丽对自己敏感的神经有点郁闷,毕竟人家哄孩子也很正常。
儿子回来的时候,她还在窗户边站着。听到关门声——她一直留心着开门声音。她急急忙忙地关了窗户。刚还恍惚的人立刻身手灵敏矫捷起来,菜、饭,还有一个汤一一端出来,苹果也削好了。洗了把手的儿子拿了筷子来吃饭。她没拿筷子,让儿子自己拿筷子。因为学习,儿子差不多快成了那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人。吃饭自己拿筷子,洗脚自己端水,成了华丽教育孩子为数不多的一点坚持。她看到儿子门口的鞋子乱七八糟地躺着。就为这点小事,她也说过儿子好多遍。她真有些烦躁呢。可她烦躁没用。决定家里气氛好坏的要看儿子的心情。儿子要是在学校心情不好,回来一般脸都绷紧的。单位领导训话的时候,脸上就是这副表情。上班看领导脸色,下班看儿子脸色,这让她很有失败感。她有时候真想骂人。
怕发胖,华丽下午很少吃饭。儿子已经习惯母亲照顾自己的这一周,自己一个人吃饭。他自顾自地吃着。华丽想听听儿子说说班里的事,就像儿子小时候那样。可儿子的眼睛只看着菜了,腮帮子一鼓一鼓地起伏着。外面的车驶过发出的声音小了下来,隔壁好像也安静下来,唯有儿子清亮的咀嚼声。吃饱后,儿子心情好了许多,接过妈妈递过来的苹果,说了些班里趣事。儿子原本也是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可上了初中再上了高中后,话也越来越少了,像一个疲惫的大人。华丽有时会有种莫名的伤感。她得不时想想,儿子的学校是全省最好的学校,在全国都排名前三十了,今年清华北大就考了五十多个。像一种药一样,这些会让她心里舒服一些。
按照惯例,儿子一进房子,她就停止走动。她躺倒在沙发上看书。楼上看电视的声音隐约传来。那么小的房子看电视的就只能是没有孩子上学的老住户了。租房的人几乎都不看电视。华丽家那种四平八稳看电视的日子,在儿子上初中后就结束了。他们来这里的目的就一个,一切为了孩子考个好大学。
没看几页,她又听到邻居发出了声音。好像是一个女人在逗弄孩子,一会唱一会笑,很尽兴的感觉。大声地说话和嬉笑,肆意地歌唱和看电视,多幸福呀,一种俗世的幸福。她想起儿子小时候家里也充满了这样的笑声,禁不住开始猜测这家孩子有多大。这样哄的能有多大?一岁?不到一岁?好在很少听到孩子哭。也许哭过。白天哭?
书举在半空,一行字也没读完。她懊恼地发现,自己全部的神经都被隔壁的声音吸引了。忽然,想起什么,她轻手轻脚地起身,站在儿子门口,站定了听。她想知道这声音吵到儿子了没。是小一点,但她还是打算将儿子房间有点虚掩的门拉紧些。她的手刚挨着门框,儿子嗖地转身,椅子和地面因为快速的摩擦发出尖利的声音,吓了她一跳,再看儿子,目光里满是警惕。她顿了下,打开门,冲一样地跨步到儿子桌前。果然,孩子没有在学习。他在玩手机。可手机她明明要回来藏起来了呀。她眼前出现了儿子趁她不在,翻箱倒柜找手机的情景。不知怎么的,她就想起那些吸毒的人狼狈窘迫饥渴的样子。一股热气冲上脑袋,你怎么把自己弄得跟贼一样?她吼道。儿子低下了头。有那么一两秒,所有的东西好像都被华丽的一声大吼给吓住了,僵在了原地。只有华丽气呼呼的喘气声。她看到儿子窝窝囊囊的样子更加来气了。咱们到这干啥来了?儿子也曾抱怨这里的居住条件不好。她的意思是咱们这么辛苦为了啥?不是我要来的,是你们——儿子想都没想抬起头吼起来。好像这个答案早就在他那里等着。她愣了一下。想起来这句话不是第一次问儿子了。以前儿子不吭气,但这个反驳或许早就在孩子心里装着。是呀,说起来还真是他们两口子拼了大力气花钱找人才进了这名校。儿子是一开始就不和他们在统一战线上。跑这干啥来了?不就是为了儿子能接受最好的教育资源,考上一所相对理想的大学。然后,好工作,好人生。这良性循环、等量代换不是谁都晓得的吗?儿子却并不领这个情。他觉得自己是一只跑进骆驼群的羊,实在有些吃力。儿子长大了,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好像成了真理的代言人,总会义正辞严地反驳华丽的质问。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她无话可说,也不想再多争执,一把拽过手机,狠狠地瞪了儿子一眼。
儿子也不依不饶地生着气,华丽刚出门,他气呼呼地用力把房间的门推紧。有拒绝母亲再进来的暗示。“哐”的一声,华丽好像哪里被门夹着了一样,身体抽搐了一下。
她重新躺在沙发上,生着闷气。她也懒得吵了。不仅在家,就是在单位,她也懒得和别人争执。觉得世界上一定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泾渭分明的都是幼稚的判断。有什么可吵的。她有时想起结婚时因为婚纱的肥瘦问题,一言不合就和婚纱店的老板吵了一架。其泼辣其暴躁看不出来第二天就是要当粉嫩新娘的人。想想真好玩。那个傻瓜当时想啥呢?像回忆别人的囧事一样思量着当时那个自己。
“战争”过后,屋子里更安静了。隔壁邻居的声音更加吵了。是不是这噪音吵到了儿子,让他不能静下心来。她基本判定邻居一家是在对孩子进行早教。这么小就这样折腾,他们是要把孩子培养成神童吗?唉,满世界都是不服输的人。她又为儿子懒散的状态发起愁来。
书看不进去了。她拿起手机看。微信里是热闹而忙碌的光景。卖面膜卖包的,发自拍发心情的,晒孩子晒晚餐的,这算活泼有趣的,大部分是一些人生鸡汤、治世宝典。领导的、朋友的,该点的赞点完,华丽就有些瞌睡了。早晨起得早,忙忙活活的一天。可她如果睡了,儿子怕是才高兴呢。她想老公在干什么。因为房子小,来回奔波也很辛苦,是老公出的主意,他们俩轮着来。像排班一样,一人一周。他们自己的家和单位都在三十公里外的另一个小城。两个人来回跑,实在没必要。双份的车钱,双份的劳累。不划算,何志说。这个办法好吧?他试着和华丽商量,脸上却是一副发现新大陆的激动。想着可以连续一周不用起早贪黑地赶路,可以干点自己想干的事,比如和闺蜜去广场那个小山坡转转,每年秋天的菊花展会持续好长时间。她已经好久没去过广场了。她就同意了建议。可很快她发现也有很多的不好。比如,她和老公在一起的时间少了。她脆弱起来是想黏着老公的,可她不好意思说明。老公单位也很忙,顾不上她那些小情绪是常有的事。还有闺蜜也整天围着孩子转,根本没有时间和她闲情雅致。许多喜怒哀乐,华丽只好试着自我消化。
晚上,她被一些声音弄醒。半夜三更哪来的声音?清醒过来确定不是在梦里,确实是旁边邻居家里的声音。她皱了下眉头瞟了眼那墙,似乎怪墙没有堵住那些肆无忌惮的噪音。邻居家的门打开又关上。有人出去了。很快她听到鞋子摩擦地面的声音,几声轻咳。是个男人,华丽判断着。她拿起手机看,才四点多。这个时候干什么去呢?这家人真奇怪。
只能继续睡。还是睡不着。神经越发灵敏起来。
秋天的夜和别的季节不同。风总是暗自潜入。风声里,还传来瓶子易拉罐被惊扰后发出的清脆的呐喊声——那是有人在院门口的垃圾箱翻捡垃圾。好多个夜晚,瓶子被惊醒,她也被惊醒了。现在她又听到了它们的叫声。
好在半夜睡着的儿子是吵不醒的。他睡得太沉了。每晚,那呼吸声都像潮水一般均匀有力。
那天早晨因为开会,华丽走得迟一点,在楼道里碰到邻居。是一个老奶奶推门出来,提了一袋垃圾。华丽想抓住这个机会说点什么,比如,奶奶你们家晚上有点吵。可华丽看到的是奶奶温和的微笑。华丽不好意思了,也抿了抿嘴,友好地微笑了。接下来更让华丽不好意思的是,老奶奶弯腰拿走了华丽前晚放到门口的垃圾。华丽这才想起以前门口的垃圾也会突然不在。她一直以为是打扫卫生的人顺便拿走的。华丽赶忙去抢。老人家还摆了摆手,示意华丽去忙。
周一,华丽早早地先回了自己的家。带回来些脏衣服要放过去洗。老公还没起来。一看她回来了,脸上浮出一丝笑意。那笑就是暗示。他们彼此都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了。也有时候,她去迟了老公已经穿好白衬衣蓝裤子的单位制服。他推搡着她进了卧室。三下五除二地剥光自己的下身,俯在她身上活动着。华丽一条腿上的裤子也没来得及脱,为了节约时间。丈夫上半身的白衬衣蓝色领带在她眼前晃呀晃。这让她总有一些幻觉,觉得是在和另一个男人亲热。床有时会发出声响,大或者小,取决于丈夫的激情。
到了单位,她和早来的人一起打扫办公室。一间大办公室里满满地坐了六个人。六个电脑六个人脑以外就是柜子和沙发。三个电话偶尔会同时响起来,他们捂着话筒大声重复着说话。闲下来时,也有人来串门。有的大明大亮地往沙发上一坐开始聊天,声音大而肆意。有的进来倚在某个人的办公桌上,嘤嘤嗡嗡地说着什么,或者说到什么关键事,甲的嘴和乙的耳朵就凑在一起了。华丽暗自把他们这种聊天方式叫静音模式,把前者喊做震动模式。是静音还是震动,内容差别大了去。
今天华丽可以在办公室多赖一会了。丈夫回去了,这周他值班。他们把回清泉市照顾孩子叫值班。楼道总是比外面的天先暗下来。她把门打开,让别人知道她也在加班——像那几个天天加班的人一样。鬼才知道他们干什么呢。当然,她也没有干正事。搜个电影看,或者进几个网站转转。关了声音就行,有字幕。不用急着回去做饭,真是自由和轻松呀!
直到十点,华丽才往自己家赶。拉开灯,她打量着空房子。电冰箱压缩机发出喘息一般的声音。房子里残留着丈夫的味道。她把手机上下载的好听的歌用最大音量放开。歌声中,她漫不经心地洗脸刷牙。有时她会哼上两句。睡觉的时候,她才把声音关掉。
周三的时候,她给清泉的两个男人打电话。丈夫压低声音说,一切正常,儿子在做作业。她想再听他说点别的。最终也没说。儿子一写作业,他们的电话就是短平快。
一周很快就过去了。周一下午她又回到了清泉市租住的房子。开门的时候,想起那些噪音,华丽有意识地瞥了眼邻居家的门。这家房东装修费了心思,把门也换了,新崭崭的。房东是个讲究人,门上还不忘贴个福字,大大的,在黑乎乎的楼道里突兀地金光四溢着。
晚上,儿子写作业,她看书。像之前的每一个夜晚一样。
果不其然,声音又传来。她给丈夫打了个电话。今天他们分手的时候,丈夫抱了下她。她还没从那个拥抱里抽出身来,语气温柔了许多,她问丈夫,你听到旁边的声音了吗?丈夫被问蒙了,停顿了会才想起来说,好像有点。男人到底粗枝大叶,又在看球赛,漫不经心的说话声听不出来这噪音干扰到他了。
那天晚上她水喝多了点,起夜时听到那家又发出了声音。像唱歌又像在哭,到底是唱歌还是在哭,琢磨了半天也没辨清。一琢磨,又失眠了半夜。可巧,那天在路上竟碰到年轻时喜欢过的一个男人。华丽为此懊丧了片刻。
不过后面几天邻居家安静极了。她关了窗户听,也没有听到一周前听到的那些莫名其妙的声音。这幸福的一家人大约旅游去了,她想。
儿子月考前几天,又是她陪儿子的那一周。那天没想着和孩子吵架,但因为儿子偷偷看小说,她说了儿子。儿子又烦了,两人不欢而散。之后,她只好没意思地窝在沙发上看书。就在这个时候,她又听到了噪音。她早就把它们定义为噪音。心情不好的时候一切的声音都是噪音,即便那些声音听上去欢快而有节奏,就像现在。儿子那边一声不吭地沉默着,没打算给被母亲道歉。她呢,像所有这个时候气愤的母亲一样,生着闷气。那边的声音更大了,还能听到几个人在笑。过了一会儿还嫌不够热闹,又放开了录音机。心情不好的华丽觉得这家人很烦很不自觉。有点公德吗?这又不是在荒郊野岭住着,你们不知道这四周都住着上学的孩子吗?
她最终决定要去这个邻居家里看看,是又过了几天。那天是周末,她和孩子正睡午觉。他们计划好的,午觉起来后,儿子读半个小时的英语,背两篇文言文,做两张卷子。然后他们一起去公园跑步。你说,做这么多事情,如果能提前休息一个小时多好。专家都说了,孩子休息好了,会超常发挥的。儿子那天还算配合,脱了鞋子就躺倒在床上。一个和谐的下午就要开始了。华丽心情好起来。
声音是在半个小时后响了起来。那可是大中午的时候,这半个楼上的人应该都在睡午觉。你们不睡午觉,让别人也不睡吗?她觉得这家人有问题,自私、无耻。她想骂人了。
她换了鞋子,临出门照了下脸。因为是被吵醒的,脸上的疲倦还未撤去。头发有点乱,她也没梳。她觉得这样也好,充分表现自己被吵到后的不耐烦。她还看到了自己脸上的一丝怒气。她不想等平静下来。她已经犹豫和等待过好久了。总以为这噪音马上就会消失。但没有。生活考验人耐心的地方太多了。她不希望自己再对一个不知道收敛反复打搅自己的噪音忍耐下去了。
她抬起胳膊,越过那个福字,用了点力敲门。几下后,邻居家的门才打开。打开的那一瞬间,除了录音机里的歌声还在继续,屋子的人都走过来看她。是两个老人和一个年轻点的女人。他们有点闷头闷脑的样子,疑惑地打望着华丽。华丽也打望着他们。两个老人衣着寒酸,表情木讷。华丽还认出那个男老人曾经趴在垃圾箱边找过瓶子。后面赶来的那个年轻女人也是一脸枯萎。女人问,你找谁?一听就不是这个城市的声音。她站在离华丽一米外的地方,身上穿着一件旧睡衣,睡衣上布满碎花。睡衣上的小黄花已经不新鲜了,每一朵上都有若干个小毛球。她身后的一个角落里,堆了三个装满的尿素袋子,几个瓶子露出了脑袋。华丽呆住了。进来之前,她一直以为这是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幸福美好到忘记了周围还有人在煎熬。华丽迅速地整理了自己的思路,她说,你们家怎么总这么吵?她按原计划发出了疑问,声音像责备犯了错误的儿子那样的口气。对面的三个人愣住了,因为个子矮小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们的下巴都有点向前伸的意思,似乎是仰着头看华丽的,眼睛里装满了胆怯。华丽想起自己看到领导时候就是这副怂下去的样子。可华丽却无法像领导那样不动声色。她张了下嘴又闭住了。好在他们很快反应过来,交换了眼神。华丽顺着其中一个人的眼光向里面看去。里面一张床上躺了个人,是个孩子,但眼睛紧紧闭着,似乎睡着了。
后来华丽走近了孩子。华丽当过老师,还有个职业病,看到谁家孩子不对劲,都会有点……怎么说呢,多管闲事,或者说爱操心。
穿睡衣的女人普通话里始终残留着固执的地方口音,这声音絮絮叨叨地说着。华丽也听不出来到底是哪个地方的,或者他们说了,但华丽忘了。进到华丽脑子里的是别的。这床上的女孩是她的女儿,今年夏天出了车祸,成了植物人。医生说有康复的希望。她从床边拿了一堆单子,让华丽看孩子检查的指标。他们看出来华丽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医生让我们每天给孩子放点小时候听过的东西。孩子小时候学过钢琴,经常听的,我们想着……华丽还知道,车祸赔的钱快花光了,为了治病,孩子父亲在别的城市打工,一个月寄点钱回来。女人还想解释什么,华丽已经在女孩的床边坐了下来,那是十一二岁大小的女孩。皮肤白皙的脸上稚气未脱。她捋了下孩子的头发,又揉了孩子的手腕——从小她就给儿子这样揉。书上说,这样有利于孩子的末梢神经发育。孩子奶奶坚持说孩子得的是“睡病”,就是睡着了。在孩子奶奶看来,孩子不是植物,是人。老人手里一直在织毛衣,毛线是嫩嫩的粉色。女人说为了节省药费,他们只在孩子治疗时才去医院住。华丽知道他们说的那家医院。那医院在全国都赫赫有名,名气大效益好,政府去年拆了一些老巷道,在旁边又盖了栋二十层高的楼房。二十层的高度远远就能看见,华丽才搬到这个城市时,下车不辨方向,是循着它最顶的红十字才能辨清东南西北,然后晕头胀脑地摸回家。女人说,为了使用机器辅助治疗,每隔二十八天住一次院。为了方便,也为了省钱,他们租了这房子。老少三代住在这了。华丽想不出来他们怎么住下的。她不好意思乱瞅。余光里,她看到一个简单到清贫的家。除了床就是床,吃饭的桌子是院子里搬家走的人扔掉不要的。其余什么都没有,好像要随时撤走那么简单。女人说,这里太贵了,他们已经打算重新找房子。
华丽从邻居家走出来的时候,距离她进去的时间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她忘记了自己在那里都干了什么。但记得在邻居家她说了好多话。孩子的妈妈奶奶爷爷也说了许多话。说话间余,她一直偷偷地打量着孩子的眼皮。儿子睡着的时候偶尔眼皮会动一下,好像在梦里梦到了什么。女孩枕头边有一个毛绒小狗,滴溜溜地大睁着两只眼。华丽想女孩要是睁开了眼睛是什么样子呢?女孩的爷爷奶奶说了孩子好多以前的趣事。孩子喜欢小狗、爱吃香蕉,钢琴已经过七级了……说到什么,华丽也会插上几句话,说些儿子小时候的趣事……四个大人一会高兴一会伤感。女孩静静地躺在旁边,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像一张白纸一样空白。华丽第一次离一个植物人这么近。她偷偷地瞄了几次,孩子的眼皮始终一动不动。华丽学着那个女人的说法,孩子只是睡着了。
出门的时候,那个女人说,真不好意思,我们以后会把声音放小点。华丽连忙摆手,没关系,我家儿子听不到。她又说,对不起,不好意思……
从邻居家里出来,华丽没有回去,她知道儿子还在睡觉。只要不喊,儿子可以睡好久。睡吧,孩子多累呀,她想起儿子睡着的样子,又想起那个女孩一动不动的眼睛。她在院子里的一个木椅子上坐下,愣了会神。过了会,又站起身来往巷子里走。巷子拐弯的地方有个修鞋的。修鞋的老人低着头在机器上给一双鞋子轧线。发出的咋咋咋声里,一只老猫在旁边打起了瞌睡。几个上了岁数的人从不睡午觉,他们总坐在那处石阶上一起谈古论今。他们头顶的上方是树梢,树梢上有残留的叶子随风摆动,发出似有若无的声音。再往外走,就听到巷子外车水马龙的声音。
回去的时候,那只猫跟在了华丽身后。轻手轻脚的样子,安静又温柔。华丽还第一次在小院废弃的花园里发现几株月季。月季花已经败了,不过叶子依旧浓绿舒展。她拿出手机给叶子拍了照片发了个微信。微信配的文字是,冬天还早呢。
责任编辑刘永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