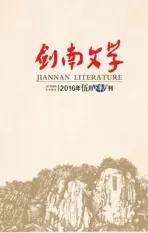浅谈明清两性作家在才子佳人作品中寄寓的“佳人之德”
——以《牡丹亭》和《再生缘》为例
2016-11-21□魏玲
□魏 玲
浅谈明清两性作家在才子佳人作品中寄寓的“佳人之德”
——以《牡丹亭》和《再生缘》为例
□魏玲
明清男性文人所创作的才子佳人故事如《牡丹亭》中,女性虽表现出一定的追求恋爱自由的反抗意识,但其角色设定仍是依附于男性的“菟丝花”,仍遵守着三从四德的女性规范;而女作家陈端生的作品《再生缘》中,女主角孟丽君却如同一颗以“树的形象”和男性站在一起分庭抗礼的“木棉”。作者借助这一形象及其经历所表达的反抗意识,可视为女性在男性拥有话语权背景下的一种发声。本文拟从“德行”方面,对两性作家所塑造的这两个角色进行简要比较。
一、杜丽娘之德
明清才子佳人作品的主流是发乎情、止乎礼的道德化的情感。佳人作为大家闺秀,虽然为了追求理想的爱情,能冲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束缚,但她们仍需要一份被社会认可、也被自己接受的完整婚姻,因而其行为往往自觉遵从于礼教。
勇于献身的至情佳人杜丽娘,在复生后便拒绝了柳梦梅的成婚要求,因为没有媒人,父母不在跟前。在杜丽娘看来,“鬼可虚情,人须实礼”,再度为人是不可草草成婚的,她希望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使自己的婚姻取得社会的认可。
谢雍君在《杜丽娘的婚姻追求与明清女性情爱教育》一文中提出:“在《牡丹亭》中,‘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情’,固然是杜丽娘理想情爱的主要内涵,但却不是唯一的内涵。在杜丽娘的‘理想情爱’字典里,除了两性之情,也包含着合乎伦理道德的夫妇之情。易言之,杜丽娘追求的是一种‘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理想情爱。”
鲁迅先生则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表示:“才子佳人的遇合,就每以题诗为媒介。这似乎很有悖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对于旧习惯则有些反对的意思的,但到团圆时节,又常奉旨成婚,就知道作者是寻到了更大的帽子。”
从某种意义上说,男性文人纵然可以使笔下的佳人表现出恋爱自由的反抗意识,但在自觉不自觉间,她们仍维护着父权社会的伦理秩序,仍是“三从四德”的女性规范的代言人。
二、孟丽君之德
作为女性作家笔下的女主角,孟丽君才貌双全,云南总督之子皇甫少华与元戎侯爵之子刘奎璧均欲聘娶她,后经比试,皇甫少华胜出。刘奎璧不甘心,便陷害皇甫一家,并倚仗权势迫使孟丽君改适。为了“全节”,孟丽君只得离家出走。此时的孟丽君堪称传统意义上的大家闺秀,因其目的是“从一而终”。
然而,扮男装后,孟丽君凭借才智官至丞相,已使皇甫一家沉冤得雪,完成了出走时的初衷。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她已不愿回归女性身份,再度成为男性的附庸。为此,她甘冒欺君大罪,拒不与亲人相认,致母思女成疾,父被罚半年俸禄。
孟丽君的所作所为堪称惊世骇俗。这种强烈的反三纲五常的叛逆心理,受到了很多人,包括女性读者的批评。
这并不难理解。男权制文化不仅使妇女处于社会底层,且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在这种“愚妇”政策的熏陶下,女性本身也将这种约束内化为自身的价值取向,正如波伏娃所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因而与陈端生同时代的女性如侯芝、邱心如等,均对孟丽君有所批判。然而,这些逆反行为,却正是陈寅恪先生所称道的:“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
邹颖在《从对〈牡丹亭〉的回应看〈再生缘〉的女性书写及其文学史意义》一文中提出:“以状元夫人的身份,杜丽娘最终为家庭、朝廷、社会所认可,她获得了社会所能给予女性的最高地位,并对此感到满足,将之视这一种自我实现。相反,孟丽君却并不认同这样的社会地位,当杜丽娘竭尽全力想要证明她就是杜丽娘时,孟丽君却尽力显示她不是真的孟丽君。”
以女性“三从四德”的规范来衡量,孟丽君不守闺仪,辱父欺君,显然不具备“妇德”。但这种独立的人格却正是孟丽君魅力之所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