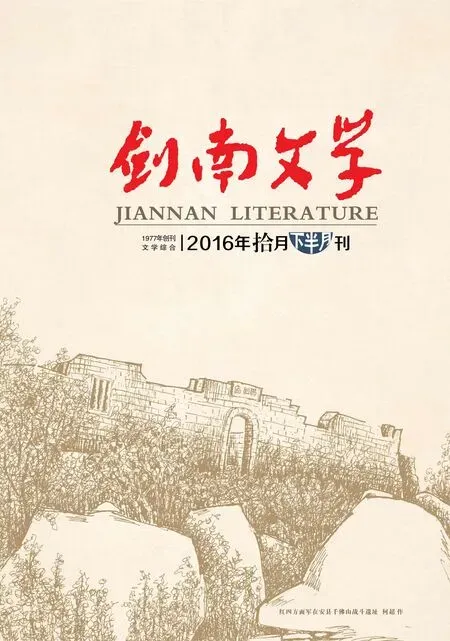新诗散文化与“赋”传统的现代生成——兼论散文化作为新诗诗体的可能性
2016-11-21徐传东
□徐传东
新诗散文化与“赋”传统的现代生成——兼论散文化作为新诗诗体的可能性
□徐传东
新诗散文化是百年新诗发展的核心关注点之一,以往论者多将其视为新诗的一个语言问题,而对其诗体上的文本意义考查较少。笔者通过新诗史的角度,认为新诗散文化先后派生出了散文诗、口语诗等诗体,作为与新诗纯诗化、现代主义化等方向并行的一大新诗演进脉络,其独立的诗体意义已昭然若揭。而新诗散文化对中国古典诗歌“赋”传统的资源征引与现代转换则双向强化了其合法性,并具有更大的诗性营造空间。
新诗诞生百年来,其语言、诗性生成机制等都是核心命题,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发生了诸多变迁,包括往返回复。而围绕新诗的散文化,这些问题的冲突更为凸显,涉及了新诗的合法性、新诗建设等命门。具体而言,包括从新诗发生的角度观察文与诗的问题、新诗散文化与散文诗分野及其联系的问题、新诗散文化与口语诗的牵扯、从中国诗歌“赋”传统的视角考察新诗散文化的问题等。
一、新诗散文化之为问题
在标举“白话诗革命”大旗的时候,胡适故意打破传统诗、文的界限,提倡“作诗如作文”,一再强调白话诗之变不在于语言,而是别出新裁,确立一种“活”的语言、“活”的诗歌、“活”的文学。胡适的《尝试集》引起的争议一直比较大,不过正反两派都认为他动摇了旧诗的语言系统和基本法则。钱玄同对胡适使用大量文言词汇有点“小小不满意”,但正是文白相杂的糅合突破了传统的“诗之文字”,而当代学者康林则认为胡适的实践“用古代散文的语言系统全面改造古典诗歌的语言系统,使后者散文化”。可以这么说,由于新诗的内在精神即是“自由”,新诗的散文化便是其内在气质追求的重要途径之一。
另一方面,从新诗的语言表现形式来说,散文化同样具有某种天然性。叶公超就曾指出:“在文言里,尤其在文言诗里,单个字的势力比较大,但在说话的时候,语词的势力比较大,故新诗的节奏单位多半是由二乃至四个或五个字的语词组织成功的,而不复是单音了,虽然复音的语词中夹着少数的单音。”当代学者张桃洲进一步指出,“在现代汉语的句子成分(关系词等的介入)日见完备的情形下,当一句诗要表达一个完整的文意时,句式必然拉长,句法也必然趋于繁复化,这样就大大刺激了新诗的句式结构,使得新诗出现了大量长短不一、参差错落的自由句式,也使得新诗的口语化、散文化不可避免。”
既然新诗在精神气质、语言形式上都有着天然的散文化的因子,似乎新诗的散文化是堂而皇之的,但恰恰这一点成为新诗百年发展过程中不断被诟病、被质疑的一大问题。一是不少人认为新诗散文化,病根正在于因之胡适的“作诗如作文”,模糊了诗与文的界限。他们认为,如果说胡适打破文言文学的条条框框,重新划分诗文界河,“作诗如作文”还有一定合理性,而在新的文学语境下,诗歌必然要与其他文学门类相区分,那么诗歌散文化就是一种“诗病”。二是一些人虽然认为自由诗天然具有散的因子,但是诗歌散文化造成的长句子、长篇幅,连带所衍生的叙事性、生活化等却对新诗的诗性构成了伤害和破坏,而没有意识到新诗散文化能在新诗的王国中自成一派,成为一种独立的新诗门类,他们依然将诗歌散文化视之为新诗的一种语言问题,而对新诗散文化独立独特的诗学意义探索不够。
二、新诗散文化与散文诗
要探讨新诗散文化的诗学问题,首先得弄明白新诗散文化与散文诗的区别及联系。关于散文诗,李健吾曾说,“散文诗,不是看做一种介于诗与散文的中间产物”,这一论断成为最为主流的见解,如《辞海》对散文诗的定义是:“兼有散文和诗歌特点的一种文学体裁”,学者王光明认为“散文诗不是有诗意的散文,也不是散文化了的诗”,张俊山认为散文诗“既不依附于散文、也不依附于诗的独立文体种属,它的产生几乎可以追溯到与散文和诗同样久远的年代”。
不过主张散文诗是“诗之一体”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在2011年12月召开的“当代散文诗的发展暨“我们”文库学术研讨会上,学者邹岳汉、树才等人便主张散文诗即是诗,“不要再诗之外寻求一个散文诗”。
跳出文体归属的争议,这一点是大家都公认的,即散文诗本质上是诗歌的,形式上是散文的,这是使得散文诗和诗歌,尤其是散文化的诗歌重合的因素。从来源来讲,新诗与散文诗是同源的,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到,“英国诗体极多,且有不限音节、不限押韵之散文诗”,彼时,散文诗与散文化的诗便没有明显的区分,散文诗的确经历了从散文化的诗、诗化的散文中脱胎而来的历史阶段。前者可以沈尹默《月夜》为代表,后者则可以鲁迅《野草》为开端。
被第一部新诗年选集《新诗年选》认作是“中国现代第一首散文诗”的《月夜》,保留了诗歌的韵律和排列,而鲁迅从不认为《野草》中的篇章是诗,他自认是“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说是“散文诗”,只是一种夸大了的说法。不过,从这两个肇始的实例来说,却显露了散文诗内在的堂奥之谜。虽然后来的散文诗没有像《月夜》那样自觉或刻意的用韵,但是却从诗歌那里继承了音乐性,而且这一文体特征的认识上,其与新诗对格律、节奏、音乐性的把握基本上是同步的。另一方面,鲁迅口中的“小感触”,则外化为散文诗从新诗那里学习得来的抒情性。主情被认为是中国诗歌传统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抒情性与音乐性的结合,基本上就构成了散文诗与散文最基本的区别。
散文诗从散文那里获得的一大特征就是“形散文不散”,“形质合一”,这也是它区别于新诗,散文化新诗的根本所在。从形式上来说,散文诗的外形面貌与散文一致,主要以段落的形式呈现意义单元,而新诗则以断句分行的形式表现。从组织上来说,散文诗虽然也具有情思、想象的跳跃性,但是总的来说,受限于语法形式,它的行文比诗歌更加绵密,更加服从语法、意义的逻辑。
另外一个较为关键的辨识区间在于,由于散文诗的立足基点便在于兼具的“诗形”和“散文形”都是新诗和散文最为核心的特征,这使得它在形式的发展上实际上是趋于保守的。以散文诗与散文化新诗而言,散文诗在保持抒情性、音乐性、含蓄蕴藉等诗性特质上较于散文化新诗更为坚持,散文化新诗则可立足于“诗乃文体之母”,“诗歌是一切文学之源”,“新诗是自由诗”的认识获得先锋探索的合法性,从而更为激进地实践一些诗学主张。而如果放在诗歌史的角度来看,散文诗正是新诗在散文化实践中派生出的,而且散文化新诗仍在派生不同的诗体面貌,如其在上世纪20年代、80年代两度派生出口语诗、于坚《零档案》那样的实验文本和柏桦等人近年创作的笔记、小品文式的诗体等。
三、新诗散文化与口语诗
口语诗也是新诗散文化过程中派生出来的,因其如此,在许多人的认识中常将二者的概念混同。在《朗读与诗》一文中,朱自清认为,“新诗的语言不是民间的语言,而是欧化的或现代化的语言”,在另一篇文章《抗战与诗》中,朱自清又指认,“抗战以来的新诗的一个趋势,似乎是散文化。抗战以前新诗的发展可以说是从散文化逐渐走向纯诗化的路。”其实,新诗的散文化和口语化在甫一开始即分流而行。当时,朱我农向胡适写信质疑其“白话”不过是“笔写的白话”,而不是“口说的白话”,他批评道,“所以先生等名为文言改为白话的白话,——就是我称为‘笔写的白话’的——其实依旧是文言,不过不是那种王敬轩所崇拜的文言罢了”。
朱自清所说的“散文化”大致等同于朱我农所谓“笔写的白话”,这种新诗语言“不是民间的语言,而是欧化或现代化的语言”。朱自清同时考察到,当时新诗的建设主要是在散文化方面再向“纯诗化”发力,即包括新月派诗人的“格律化”,李金发等人的“象征派”,还有时兴的“小诗”等,而抗战以来,民间形式崛起,民间语言、口语入诗的现象蔚然成观,新诗另一个维度的“散文化”又繁荣起来。其实,这里的“散文化”即口语化。不过,朱自清随即又对“用的是一般民众的口语的标准”的抗战“诗朗诵运动”作了修正,认为“这固然不失为诗的一体,但要将诗一概朗诵化就很难”,“文化的进展使我们朗读不全靠耳朵,也兼靠眼睛”,这“兼靠眼睛”的“朗诵诗”也即书面语化的散文化。
从新诗发生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新诗散文化和新诗口语化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二者的语言,一个是欧化的或现代化的书面语,一个则是民间的、民族的、民众的口语。但是口语诗的发展并非沿着口语在演进,因为中国方言众多,各地的口语自身也在不断变迁,最主要是受到国语/普通话的侵蚀,故而照此路径演绎,口语诗的领地要么不断萎缩,要么则相对于书面语的新诗而言会翻转成为一种封闭的,文言文化的活化石诗歌,反而失去自由、大众、鲜活等诗歌身份。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口语诗不等同于口语化。
四、新诗散文化与中国诗歌中“赋”的传统
在整个新诗的源流图谱上,除了散文化,大致还有纯诗化,包括格律诗运动、民谣化,部分象征主义、意象派、古典主义等的追求;此外还有现代主义化,即与世界文学主潮,现代世界诗歌接轨的冲动,包括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改造,当然这些外来的刺激与影响在新诗其他的诗体上也产生了作用,这里为了分清枝干而特指其对自由诗的重新塑形。
我们可以看到,新诗的散文化、纯诗化、现代主义化,其合法性的立足点、诗体建设援引的资源、诗歌美学的追求等都各不相同或各有侧重,纯诗化侧重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所援引的外部资源也多为前现代的范畴;现代主义化主要立足于援引外部现代主义资源,并发现中国诗歌资源中的现代性因子,在融合中书写现代主义文学的中国版本;而与现代主义自由诗侧重“现代”不同,同属自由诗阵营的散文化新诗则侧重于“自由”。
由于散文化长期被视作新诗的一种语言倾向,学界、诗歌界对其辨识一直不甚清晰。在新诗史上,散文化一度是白话诗、自由诗的同名词,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散文诗从中独立出来,口语诗从中脱离出来,纯诗化也分门别户形成了庞大的子家族(抒情诗、格律诗、象征派、小诗等),现代主义诗歌也获得了命名,而作为母体的散文化则一直没有自身单一的身份。而在其他诗体相继确立之后,笔者认为,是时候该对散文化诗体做出重估了。在其他诗体“分家”之后,散文化新诗还剩下什么呢?首先是形,除了散文诗以外,其他诗体都采分行断句的陈列方式,且对字数长短比较敏感,而散文化诗则较为自由,趋向于长句分行,或一行承载多个句子。
其次是神,在对待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资源、诗歌资源、美学体系上,散文化诗采取的是兼蓄并收、各采所长的态度。虽然没有将散文化上升到诗体的角度,学者王泽龙也指出,“新诗散文化的开放性思维能容纳和改造传统,又易于接纳新的诗体形式,散文化的诗式是一种开放型的诗式”。在具体某首诗歌的表现上,散文化诗或综合或集中突出一二,并带有一定的实验性、先锋性,但即使是集中使用一两种表现手法或援引资源,散文化诗也保持着某种克制,特别是对抒情、口语、意象、象征等可能改变作品性状的因素保持着警惕。
在所有的援引资源里,散文化诗对“赋”传统的征引可谓最为青睐。在这里,“赋”传统主要包含两大体系,一是中国诗歌传统中源自诗经“六义”的“赋比兴”之“赋”,也即“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朱熹《诗集传》),一般认为是诗歌中的叙事性和铺陈的手法,在后世又融入了如白居易“歌诗合为事而作”、杜甫“诗史”等“缘事”的诗学主张;一是以汉赋为代表、诗赋并举之“赋”,作为一种文体,相对于“诗”的草根性、民间性,赋居于庙堂之上,属于精英文学,其特点在于辞藻繁丽、铺陈渲染,学者徐公持曾详述了诗赋从彼此疏离,到赋中系诗,再到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出现赋的诗化和诗的赋化的文学源流,其对汉语诗歌的句法、空间之营造、修辞手段、诗教功能等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同时也承上启下,形成了一个文人歌诗的传统。
就散文化新诗而言,自由、句式散漫、打破中国古典诗歌的组织体系是其对接现代语境、与世界主流文学潮流对话的立足点,而“赋”传统则是沟通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与现代文学现实的最直接、最方便的桥梁。既然“赋”在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身负表现手段、诗赋同源的诗体形式两种身份,其在新诗语境里同样也能实现这样的置换,并相对于其在古典诗歌中角色来说具有更大的空间,更充分的合法性。
近年来,作为诗体命名的一个新词——“小长诗”受到了诸如诗人温经天、杨炼等人的大力倡导。所谓“小长诗”指的是行数在50~100行的自由诗,温经天在其新浪博客(2013年9月26日)说:“我们的确需要长一些的句子来表达自我和外物之间的关系和需要”,他比较小长诗与长诗和短诗认为,“短诗凝练含蓄,适合有限通达无限的艺术意识去操弄,而长诗则过于宏大,往往激情在浇筑过程里形成雷同的石柱和架构”,“对于丰沛情怀和自由之翼而言,既要得当的艺术展示之淋漓感,又要理性旋转的叙事思辨性,小长诗则是一种很妥帖的选择”。应该说,“小长诗”的艺术内涵与“散文化诗”十分接近,但是,小长诗主要是从篇幅体量去界定的,则又使得其统筹的范围及其诗学特征受到了限制和蒙蔽。
与长短的自由诗相比,除了前述断句分行上二者长短有别外,我们也看到,散文化诗更加注重“赋”的力量,散文化不仅是一种语言风格,也是一种诗歌组织的方法、一种文化的、美学的倾向和追求,它同样开辟了诗歌的疆域,具有独特的诗学意义。
(四川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