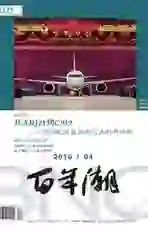中顾委七位老大姐讲故事
2016-11-19黎虹
黎虹
中央顾问委员会于1982年党的十二大成立,到1992年十四大撤销,历时十年。中顾委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加快新老交替,逐步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同时也鉴于老同志是我们党的骨干,还需有个过渡性组织继续发挥作用,成为“中央委员会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十年间,中顾委委员作过两次调整,有进有出。年老多病的退出中顾委,仍在一线工作的老同志分批进入中顾委。据统计,先后进入中顾委的委员共有287位,其中有七位老大姐,她们是曾志、夏之栩、帅孟奇、区梦觉、李贞、李坚真、章蕴。她们都是建党初期的老革命家,经过血与火的考验,有着不平凡的经历和传奇人生。我在中顾委担任副秘书长八年,有幸和她们接触,聆听她们的感人故事。
曾志和她的四个孩子
曾志,1911年生,1998年逝世。湖南省宜章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随后上了井冈山,担任红四军后方总医院党总支书记。1929年后,历任闽西特委书记、闽南和闽东特委组织部长等职。1939年赴延安,先在马列学院学习,后任中央妇委秘书长。1945年到东北,任沈阳市委委员兼铁西区委书记、地委组织部长,是中共七大候补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书记处候补书记、中组部副部长等职。1982年任中顾委委员。
1986年,我陪同新闻出版界的同志去采访曾志,请她谈谈对青年一代的希望。由于事先有约,采访直奔主题。一开始,她就深有感慨地说:“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在改革开放年代有多么幸福啊!看看战争年代的孩子,他们经历了多大的苦难,甚至断送了生命。我就从我的几个孩子谈起吧!”
曾志说,她生过四个孩子,三个送了人,最小的也差一点不要了。前三个孩子都是男孩,他们的父亲是革命烈士蔡协民。第一个男孩生于1928年11月初,那时正是创建中国工农红军最艰苦的年代,孩子生在井冈山后方留守处。产后不久,曾志就参加建造红军后方医院的劳动,天天上山刮杉树皮、抬木料。她说,杉树皮剥下来很有用处,晒干后可以盖屋顶,也可以当床板。我们大家睡的床,就是把一张张晒干的杉树皮铺在房间的泥地上,七八张杉树皮围成一个圈,冬天中间烧一堆柴火取暖。我们都没有被子、褥子这些东西,因为中间有燃烧的柴火,躺在杉树皮上也不觉得冷。可是井冈山人多、田少,吃的东西非常匮乏,粮食、蔬菜全靠到山下去背、去挑。大家经常吃辣椒干做的汤,吃南瓜就是会餐了。此外,还要天天打仗,而且是游击战、麻雀战,一会儿化整为零,一会儿化零为整,环境非常艰苦。在这种情况下,养活一个孩子是很困难的,加上曾志当时还不满18岁,自己不愿放弃工作去带孩子。经过思想斗争,不得不把小生命送给当地老百姓去抚养。可是,孩子送给谁呢?当地群众都很穷苦,谁还会要孩子?曾志正为此事发愁时,恰好王佐部队的一位连长夫人来看她,这位连长夫人就是井冈山茅坪村人,曾志便请她帮忙找个人家收养这个孩子。她说:“我的孩子三年前死了,正想要个孩子,你就把孩子给我吧。”听说孩子有人要了,曾志当时非常高兴,过了一会,又难过起来。曾志说:“当孩子被抱走时,我不知怎的,顿时又难过起来,眼泪直淌。他毕竟是我的骨肉啊!我带他生活了26天,真是难分难舍。这大概就是母亲的天
性吧!”
说到这里,曾志有些动情。她用纸巾擦了擦眼泪,接着说:“我的第二个孩子生于1931年,大概也是11月。我怀孕后,写信告诉母亲,她老人家来信,要我把孩子送回家,由她抚养,并寄来40块现洋作路费。孩子刚生不久,才40天,我奉命调到厦门工作。我到了厦门后,正准备请假送孩子回家,厦门市委负责同志找我谈话,劝我不要带孩子回家,一是路途遥远,孩子也折腾不起;二是回家来去要几个月,影响工作。我当即表示,同意组织上的意见,于是把这个孩子送给了一户人家。不幸的是,由于当时卫生条件差,孩子只活了20多天就得了天花而夭折。”
曾志谈到第三个孩子时说:“我的第三个孩子生于1933年2月左右。临产了,没有钱请助产士,我急忙拿了一块旧毛毯,去当铺当了两块钱,请来一名家庭接生婆。她动作粗鲁,不讲卫生,孩子虽然平安出生了,我却因严重感染,得了妇科病。这孩子生下来13天,就送给一位同志的婶婶。她是个寡妇,没有儿女,家在湖北,在福州做盐商亏了本,家境贫穷。这个孩子11个月时,我去看了一次,瘦得皮包骨,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四岁时,因营养不良,患淋巴腺结核病,身上的淋巴流脓、流血,家里人都讨厌他。他十四五岁时,因养母是基督教徒,福州教会医院免费为他做了手术,去掉了两根肋骨和一个肾,成了瘸腿跛子、半残疾人。1950年我去汉口找他,一见面,哪里像十六七岁的小伙子,还不如十岁孩子高。他告诉我,哪怕是寒冬腊月,他也从来没有穿过鞋袜,没有念过一天书。为了糊口,他磨牛角梳子做手工,走街串巷叫卖香烟、花生、瓜子,赚点钱养家糊口。这孩子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吃了不少苦头。”
接着,曾志讲了第四个孩子的情况。她说:“第四个孩子是女孩,她的父亲是陶铸。1941年4月生在延安,她是幸运儿,出生在延安中央医院,还有男保姆抚养她。1945年,孩子才四岁,我和陶铸同志随部队到两湖两广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当时我们作了五年十年的打算,于是把孩子交给公家。没有料到刚离开延安两个月,日本就投降了。这时中央命令我们日夜兼程,赶赴东北。保姆叔叔知道我们在东北,带着女儿去东北找我们。沿途转战一年,遇到不少危险,经过不少艰辛,1947年初,陶铸同志和我同女儿见
面了。”
曾志讲完四个孩子童年的遭遇后,我问她:“现在这几个孩子情况怎样?”她说:“大儿子现仍在井冈山山区当农民。1950年我委托中央到井冈山的慰问团帮我找到孩子。1952年底,我把孩子接到广州。那时他24岁,我想让他进工厂,一方面当工人,一方面业余学习文化,可是他不愿意,要回井冈山去。当时他家有十几亩地,还有五亩山林。他老婆很能干,养的鸡鸭成群,日子过得挺不错。孩子说,是养父母和祖母把他拉扯大,现在他们虽然故去,若离开,就没有人为他们烧香上坟。我觉得他回去也好,当工人、农民都一样,都能为国家作贡献。于是他回了井冈山。直到现在,他仍在井冈山山区当农民。他已儿孙满堂,我也有了第四代,但没有同堂。第三个孩子,新中国成立后先在武汉子弟小学念书,后来进了工农速成中学,毕业后考取了西安化工工业技术学校,从那里毕业后,分配到东北辽阳制造无烟火药的工厂任技术员,60年代入了党。1972年分配到广东省乐昌县山沟沟里。粉碎‘四人帮后被分配到县环保办公室,当了助理工程师。儿媳是劳动妇女,50年代入团,在食堂当勤杂工。他们工资虽不高,儿子每月70多元,儿媳每月40多元,但生活还过得去。他有三个孩子,大儿子19岁,初中毕业后当工人,还有两个孩子在念书。他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一贯积极努力,尤其是儿子,半残疾人,工作上从来不落后于人。他们不依靠我,完全靠自己双手劳动,自食其力。”
在谈到女儿时,曾志说:“我的女儿,虽然是生在战争年代,但成长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从小学、中学、大学到现在,都靠自己奋斗。她当了近20年的医生,1964年入党,有了22年的党龄。我和女儿也经常不在一起,她上中学时大半在北京,上大学时在上海,直到1972年,组织上把我从广东农村安排到陕西临潼干休所时,经毛主席和周总理批示,女儿调到我身边工作。”
在谈到如何对待儿女时,曾志说:“我对儿女,无论是学习和工作,都靠他们自己奋斗,靠他们自食其力,听组织安排。我和陶铸从来没有为他们走过什么后门。例如,女儿一次考高中没有考上,她自己就去上补习学校,去农场劳动锻炼,直到考取高中。所以,我的孩子们现在有的仍然能当农民,有的仍然是最低级的技术员,有的只是一般的医生。”
曾志最后提出:“是不是我对儿女太缺情了呢?”她又接着说:“从我入党那天起,党就教育我,一个党员,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为了革命事业,为了真理,要牺牲一切,甚至生命。党员誓词,我在入党仪式上是宣誓了的。只要生命不息,我就要遵守。儿女是自己的骨肉,爱儿女是父母的天性,但是,我总想一个共产党员,首先爱的应该是亿万劳动人民。爱自己的儿女,要服从于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每当给儿女做些什么时,要想想千千万万人民的儿女,想想国家社会的需要,想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孩子不单是家庭的,也是国家社会的,不能把孩子据为己有,为他们做些违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政策原则的事,也不要使儿女躺在父母身上,事事依赖,让儿女自食其力,自己奋斗。”这就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人生观和家庭观,值得我们学习和深思。
夏之栩以革命先烈的
事迹激励后人
夏之栩,1906年生,1987年逝世。浙江海宁人。1922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9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2年回国。历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处长、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长、轻工业部副部长等职,是中共七大、八大代表。她的母亲也是一名老党员,是被称为革命母亲的夏娘娘。她的丈夫赵世炎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列主义传播者和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1927年不幸被捕,英勇
牺牲。
1986年,夏之栩80寿辰时,我曾受中顾委领导委托去看望她,随后又陪同新闻出版界的同志去采访她,她同我们谈了许多往事,并以赵世炎烈士的英勇事迹激励后人,寄语青年一代。
夏之栩说:“我已经是80岁的老人了。从1922年参加革命活动,到现在已度过了风风雨雨63个春秋。回首往事,我经常怀念那许许多多曾经和我一起战斗过的先烈,特别是我的丈夫赵世炎,他的事迹一直在激励我,使我终生铭记。他是1901年出生,长我五岁,1915年考入北平国立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五四运动中被师大附中学生推选为学生会干事长,并结识了革命先驱李大钊。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人在法国建立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少年共产党,被推为书记。1923年赴苏联学习,第二年回国,参加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工作,协助李大钊领导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1926年与周恩来一道在上海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后被捕牺牲。”
夏之栩还向我们讲述了赵世炎被捕、就义的详细过程。她说:“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后,白色恐怖笼罩上海,几乎每天都有同志被捕牺牲。6月下旬,江苏省委秘书长韩步先无耻叛变,出卖了陈延年和赵世炎,供出了我们家的住处。7月2日下午,倾盆大雨,国民党特务突然闯进我们的住所,由于赵世炎外出未归,敌人就在屋内蹲守。我和母亲焦急万分,母亲急中生智,她机警地把窗外边用以作为警号的花盆推了下去,把它摔碎在马路上,以便引起世炎归来时的注意。可是风雨太大,天色昏暗,世炎没有看见,仍走了进来,结果被捕。但他神色镇定,趁敌人翻箱倒柜的瞬间,悄悄把王若飞的地址告诉我,要我通知他迅速转移。世炎被抓走后,我立即冒雨找到王若飞同志。他得知世炎被捕后,流下了眼泪。但时间不允许我们有哭的自由,若飞和我迅速分头通知有关同志转移,并研究营救世炎的方法。敌人知道迟则生变,所以很快就决定处决世炎。他被捕后第17天,即7月19日清晨,就被押解到上海枫林桥畔的刑场。他在凶残的敌人面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面对敌人的屠刀,他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把26岁的闪光青春和满腔热血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接着,夏之栩向我们叙述了两个孩子的情况。她说:“在世炎牺牲后的第二年春天,我生下了第二个儿子。根据组织安排,1929年我带着两个孩子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时大儿子三岁,小儿子才一岁多。到苏联后,儿子寄养在国际儿童院。周恩来、邓颖超曾去国际儿童院看望他们,为他们取了中文名字。邓颖超为大儿子取名为赵令超,认作自己的儿子。周恩来为二儿子取名为赵施格,意思是发扬父亲赵施英(笔名)的革命风格。1929年我回国时,两个孩子都留在苏联。不幸的是,大儿子令超13岁时就病逝了,永远留在了异国他乡。二儿子施格在苏联生活了25个春秋,直到1954年我们母子才见面。”夏大姐动情地说:“谁说革命者没有亲情?我既是革命者,又是母亲,血浓于水,亲情是割不断的。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为了革命的需要,我们不得不天各一方,无法享受天伦之乐。”
夏之栩最后激动地说:“世炎和无数烈士当年舍生忘死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早已昂首屹立于世界东方。他们的鲜血在祖国大地上已经开花结果。作为一个幸存者的我,经常在思考,也经常和青年朋友谈论。现在国家富强了,人民富裕了,各方面条件好了,可是千万不要忘记,新中国的建立,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没有他们的牺牲,不可能有幸福的今天。我要再次告诉青年朋友们,你们应该珍惜今天,坚定地踏着先烈们前进的脚步,把我们伟大祖国建设好,以告慰我们的
先烈。”
帅孟奇的坚贞与爱心
帅孟奇,1897年生,1998年逝世。湖南汉寿人。1922年在家乡从事妇女解放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汉寿县委组织部代部长、汉阳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江苏省委妇女部部长、湖南工委秘书长、中共上海浦东区委组织部部长、江苏省委委员等职。1939年赴延安,任中共中央农村运动委员会秘书、妇委代理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组织部副处长、外交外贸处处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纪委常委。她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会议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
帅孟奇是中顾委委员中年龄最大的两位委员之一。她1982年进入中顾委时已经85岁。每逢春节或生日前夕,我都要受中顾委领导委托去看望她。1987年,帅大姐得知中顾委要为她祝贺90寿辰时,就有意躲开,和刘英大姐去湖南暂住。但她回京后,宋任穷和我去看望了她。
她住在西单附近的一个僻静院子里,无儿无女,平时只有秘书陈双璧陪伴。我每次去看望,她都坐在轮椅上,虽然双目失明,听力很差,但脑子非常清楚。宋老去看望时,她一再表示感谢。宋老和帅大姐都是湖南人,又长期同在组织部门工作,所以帅大姐那天特别高兴,谈了许多往事。
我每次去,陈秘书都要向我介绍一些帅大姐的情况。后来上海《萌芽》杂志又通过我采访帅大姐,使我对她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帅大姐一生遭遇过不少磨难。她1927年去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先后在武汉、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2年,由于叛徒顾顺章的出卖,她被捕入狱。在狱中,帅大姐受尽酷刑,往鼻子里灌煤油、辣椒水,坐老虎凳……致使左眼失明,右腿骨折。但她坚贞不屈,英勇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她被判了无期徒刑,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经李克农同志多方努力,由她父亲托人取保,才得以出院治病,后被地下党组织护送到延安。
她的丈夫许之桢也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曾任湖南工人运动讲习所所长。后来也被送到苏联学习。本来他俩感情很好,可是一别十年,断了联系,许之桢便在异国他乡建立了新的家庭。帅大姐入狱前,他们有个13岁的女儿,后来在孤儿院里被敌人残忍地毒死。谈到这段往事时,帅大姐却表现得非常坚强,她说:“我是在特殊情况下造成没有丈夫、没有女儿的。一个革命者为了革命事业,抛弃个人的家庭利益也是常有的事。不少革命者都是如此,甚至还牺牲了个人生命。我们这一代人是注定要多受苦多做牺牲的。”
到延安以后,帅大姐见到了已经结婚的许之桢。许向她又解释,又道歉。帅大姐见他真诚窘困的样子,爽朗地说:“行啦!行啦!不必多说啦,我都能理解。以后不要叫我孟奇孟奇的,也跟同志们一样叫我帅大姐吧,我本来就是你的大姐吆!”
帅大姐没有再结婚,却享受着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她收养和照顾了许多烈士子女,从精神到物质给了他们许多的爱,也得到了他们温暖的回报。她说:“我虽没有亲生儿女,可我并不孤独啊!我家里逢年过节或假日,许多烈士子女来看我,还有我的侄儿侄女来来往往,他们就如同我的亲生儿女一样。其实,我是孩子最多的家庭,家里热热闹闹。”
帅大姐很注意对烈士子女的教育。她多次对他们说: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大厦千间,夜眠八尺。有的人要那么多房子有什么用?只会脱离群众,害了子女。心里只有儿子、孙子,没有人民,人民就会抛弃他!
她的爱心不仅给了烈士子女们,也给了许许多多的困难群众。有一次,陈秘书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塑皮的日记本,扉页上写着“捐献簿”三个大字。我翻了翻,大约有60多笔捐款,少则数百元,多则上万元,其中有帮助灾区小学盖校舍的,有资助失学儿童的,有捐给希望工程的……
帅大姐就像一束永不熄灭的生命之光,征服黑暗,温暖人间。
区梦觉与向秀丽精神
区梦觉,1906年生,1992年逝世,广东省南海县人。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广东妇女解放协会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妇女部长。1927年出席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参加广州起义。1935年赴延安,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解放战争期间,任中共松江省委妇女部部长、佳木斯市委书记、全国民主妇联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华南局组织部副部长、纪委书记、广东省妇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常务书记、广东省政协主席等职。她是中共七大代表,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会议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
1986年5月,区梦觉80寿辰,我受中顾委领导委派,去广州转达中顾委领导对区大姐的生日祝贺。我们虽开会时见过面,但从来没有交谈过。我知道区大姐长期从事妇女工作,也很关心青少年的成长,很重视在青年中弘扬党的优良传统。我们的话题离不开这方面的情况。她向我介绍改革开放以后,广东地区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建设大大发展,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但人们的道德风尚却大不如前,一切向钱看的风气蔓延滋长,她对此深感忧虑。她特别怀念50年代人们的精神风貌,尤其向我介绍了向秀丽的英雄事迹。
她说,向秀丽出生在广州的一个贫穷家庭,九岁给地主家当婢女,12岁进火柴厂当童工。解放初期,她才16岁,就去广州一家制药厂当包装工人。1958年12月,她所在的车间因酒精瓶破裂,酒精蔓延起火,危及烈性易爆品的金属钠。一旦金属钠爆炸,将引起整个厂房及附近居民区的重大火灾。在千钧一发之际,向秀丽不顾个人安危,立刻侧身躺地,用身体截住燃烧的酒精,避免了一场爆炸事故的发生。而向秀丽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于1959年1月不幸离世。终年才25岁。当时广东省委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追认她为革命烈士。中央领导同志林伯渠、董必武、陈毅、郭沫若和广东省委的陶铸、朱光等都为向秀丽写诗题词,区梦觉也写诗悼念。《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对向秀丽的事迹都作了报道。
接着,区大姐深情地说:“这件事已过去多年,但向秀丽精神永远值得全社会学习。这件事发生在广州,但现在广州的年轻人却很少有人知道,因此,我逢会必讲向秀丽的英雄事迹,倡导他们学习向秀丽精神,也就是学习雷锋精神。”区大姐认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非常必要的,也要看到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在不断侵蚀着我们青年一代。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在大力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要大力发展精神文明。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健康发展,社会才能全面进步。我作为一名老党员,要带头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听了区大姐的一席话,我深为她忧国忧民的情怀所感动。她的这些话语,正是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区大姐于1992年逝世,可以告慰她的是,她生前所极力倡导的向向秀丽英雄事迹学习的活动在各级党委的支持下已逐步展开。向秀丽所在的广州何济公制药厂如今已成为广州制药集团的一部分,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地举行纪念向秀丽的活动。集团本部和所属23个企业都成立了“向向秀丽、雷锋学习服务队”,积极开展抗震救灾、扶贫济困等公益活动。向秀丽精神已成为企业文化的重要部分。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向秀丽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名新中国成立以后感动中国人物”。2012年,广东清远市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学习弘扬向秀丽精神的倡议》;广东连山检察院以实际行动学习向秀丽精神,全体干警一致表示,弘扬向秀丽精神,就是要做到一身正气,执法为民,不怕牺牲,无私奉献,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国梦保驾护航。2014年是向秀丽逝世55周年,广州工会、共青团广州市委、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广州青运史研究会,在向秀丽烈士陵园隆重集会,1000多名职工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党的好女儿、人民的女英雄向秀丽同志。他们还举办向秀丽事迹展览、印发向秀丽丛书,广泛宣传向秀丽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涓涓细流,汇成大海,现在广东越来越多的单位掀起学习和宣传向秀丽精神的高潮。
李贞坚持“寒酸”不改
李贞,1908年生,1990年逝世。湖南浏阳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历任浏东游击队士兵委员会委员长、红六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二方面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八路军一二〇师直属政治处主任、晋绥军区政治部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区政治部秘书长、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秘书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开国将军中唯一的女将军。她是中共七大候补代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会议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
中顾委成立后不久,我作为中顾委副秘书长去看望李贞大姐。她当时住在香山干休所一座年久失修的平房里。我走进平房,只见房子非常破旧,墙皮脱落,家里只有几件旧家居,没有一件像样的摆设。我忍不住问她有什么困难?要不要中顾委帮忙做些什么?她连声说:“没有困难,没有困难,我生活得很好。我这个人从小就受苦,勤俭的日子过惯了,没有必要把家里搞得富丽堂皇的。现在的生活已经够好了,我很满足。再说,我一个孤老婆子,能将就就将就嘛!”这时,一旁的工作人员插话说:“首长也太将就了。组织上动员她换房子她不换,组织上动员她换车她也不换。一辆国产轿车开了好多年,经常出事故,她就是不同意换。多少年来,未见她买过一件新衣服、一双新鞋。衬衣补了又补,领子袖子已不像样了,还照样穿。我们劝她,你作为大军区副职的高级干部,也得注意点形象啊!”李大姐听后不高兴地说:“一个人的形象在于品格和本质,不在于新衣新鞋。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艰苦奋斗的作风,更不能忘本。作为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真正的形象在老百姓心上,而不在于个人表面。”接着,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她的老战友张启龙有一次去看她,说她太“寒酸”。张启龙指着她客厅里的沙发、藤椅、书柜、办公桌,风趣地说:“这四条腿的东西,像战场上的伤兵一样,都已经缺胳膊少腿了,缠着绷带。过几天我去反映,请组织上更换新的。”李贞笑了笑说:“这就不劳您大驾了,这些‘伤兵还能发挥作用,能将就行了。”张启龙对她也没法,就说她是“吝啬鬼”。李贞回他一句:“用公家的财物还是吝啬一点好。”
接着,李大姐给我讲了她的童年苦难和革命经历。她告诉我,她出生在湖南浏阳县的一个贫困家庭,父母有六个孩子,她是老二。在她六岁那年,因家贫养不起这么多孩子,就把她送给了一个姓古的医生家当童养媳。她在古家受尽了虐待,过着奴役般的生活。18岁那年,北伐军来了,共产党来了,她才脱离苦海,参加了革命队伍,加入了共产党。她参加过秋收起义、反“围剿”斗争、长征、保卫延安和解放大西北等重大战役,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最后她深情地说:“新中国来之不易,新生活来之不易。作为过来之人,我宁可把日子过得寒酸一些,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决不当败家子。”
李贞无儿无女,却抚养了20多位烈士遗孤。1990年去世时,我去协助她所在单位办理丧事,得知她临终遗言,把为数不多的存款和国库券一分为二,一半捐献给家乡的贫苦群众,一半交了党费。
李坚真被称为
“蛮大姐”的来历
李坚真,1907年生,1992年逝世。广东丰顺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闽西汀东、长汀县委书记,闽西特委书记、福建省委妇女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参加了长征。后任中共陕北省委委员、江西省委妇女部部长、中共中央东南局妇女部部长、山东分局妇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妇委书记、中共粤中区委第一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她是中共八届、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一至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会议上当选为中顾委
委员。
李坚真是一位身材高大、性格豪爽、精明干练的人,在中顾委有人称她“李大姐”,有人称她“蛮大姐”。1986年我去广州祝贺她80寿辰时,曾好奇地问她,为什么有人称你“蛮大姐”?她爽朗地回答:“这要从我小时候说起。我出生在粤东山区一个贫困家庭,出生才八个月,便因生活所迫,被父母卖给人家做童养媳,养父家也是以种田为生,生活并不富裕。我五六岁时就开始做家务,十五六岁成了家里主要劳力。我从小性格倔强,敢闯敢干,有一股不服输的蛮劲。1926年那年,我20岁,遇到了彭湃同志。在我的坚决要求下,参加了农民运动,并于192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参加丰顺农民武装暴动,随游击队打游击。由于作战勇敢,不怕牺牲,同年冬天被选为丰顺县革命委员会副委员长。后来又当汀东县和长汀县县委书记,受到毛主席的称赞。毛主席说我这个人不简单,是苏区的第一个女县委书记。在长征出发前,毛主席把我调到瑞金,担任中央直属机关的民运科科长兼地方工作队队长,长征时又担任特殊连队的指导员,负责找粮食,找向导,运伤员。这个任务十分艰巨,我就靠着善于做群众工作和不屈不挠的劲头,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接着,李大姐讲了在长征途中,就是凭着一股蛮劲,救了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团长姚喆和团政委钟赤兵(新中国成立后都被授予中将军衔),而得到“蛮大姐”这个称呼。她说:“攻打娄山关之前,姚喆同志腿部受了重伤,因一时找不到民夫,我就毫不犹豫地和警卫员抬担架走了几十里路,到野战医院把他救了回来。”也是在这次战斗争中,钟赤兵因右腿受伤被截肢,在行进途中,抬担架的民夫听到敌人枪响便扔下钟赤兵自己跑了。李坚真见状奋不顾身,背起钟赤兵就跑。敌人在后头不断射击,子弹从头顶、身边呼啸而过,而她全然不顾,终于救了钟赤兵一命。老红军们都称赞李坚真真有一股蛮劲,说她勇猛顽强,敢拼敢闯,豁出命来干革命,亲切地称她“蛮大姐”。
李坚真讲完这个故事后,对我说:“我可蛮得很哪!这几十年我就是靠这股蛮劲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我所讲蛮劲不是蛮干,而是追求信仰的一种勇气,一种精神!”
章蕴“未敢白头言倦”
章蕴,1904年生,1995年逝世。湖南长沙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汉口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长、区委宣传部长。1927年后,任中共武昌市委组织部部长,后在南京从事地下工作,任湖南省妇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湘潭中心县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妇委委员,江南区委民运部部长,苏中区第二地委书记,苏中区党委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华中分局委员兼妇女部部长,豫皖苏区党委副书记,第三野战军妇女干校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华东局妇委书记,全国妇联秘书长、副主席,中央妇委第三书记,中组部顾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她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届委员和常委。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会议上当选为中顾委
委员。
章大姐在进入中顾委之前,我就听说她是个一生正气、疾恶如仇、刚正不阿、勇于担当的“女包公”,平常不苟言笑,给人的印象很难接近。可是到了中顾委以后,我和她接触过几次,觉得她平易近人,善于言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大姐,完全改变了我原来的印象。她向我谈过她的革命经历、她丈夫英勇牺牲的情况,说过她的子女,谈过到中纪委办案的情况,也谈过她就党风建设多次发表的文章等等。听后给我的印象是,章大姐是一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人,特别是担任中纪委副书记期间,她为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而东奔西跑、日夜操劳,使长期蒙受冤屈的干部得以平反。一位新疆干部,拖延长达七年的冤案,她经手七天就解决了。在打击经济犯罪中,她敢于碰硬,严肃处理了几起大案,如北京市的陈梦猇诈骗案、黑龙江的广天章案、河南“汽车大王”案等。尤其是去福建办案,曾得到邓小平的称赞。邓小平在中顾委会议上说:“前一段章蕴同志到福建工作了两个多月,她在那里就搞得很好嘛!”
1983年底,章大姐被中顾委派到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工作,担任中央机关整党指导小组组长。她不顾年迈多病,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为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为探索新时期党的建设尽心竭力,先后发了多篇文章和调查报告。中顾委成立之初,曾规定每位委员每年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并尽可能地写出调查报告。章大姐是委员中写得最多的一个,而且很多观点颇有见地。由于我分管这方面的工作,她送给我看的文章和调查报告有近十篇。如《严格要求自己,欢迎群众监督》《增强党性,争取党风根本好转》《关于京、津、鲁三省市部分整党试点的调查报告》《在整党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大兴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增强党性,克服派性》《全面提高党员素质是党风根本好转的坚实基础》等。我看后向她建议:这些文章和调查报告最好汇集成册,公开出版或内部发行。后来听说这些文章和报告已汇编成《章蕴谈党的建设》一书,成为党员学习的重要资料。
就在她逝世前一个月,我去看她,这位91岁高龄的老党员还在关心、惦记着王宝森案件的处理。随后,她无比气愤地奋笔写道:“腐败风气是实施二十字方针的死敌(笔者按:指1994年初中央提出的‘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二十字方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死敌。反腐倡廉要与二十字方针同步进行,要坚持到底。”她期待并相信:“消灭贫困,达到共同富裕,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色的目标,到了成功之日,全世界人民视之都会向往。”殷殷之情,跃然纸上。
章大姐这种对党的责任感和奋斗不止的精神令我十分感动。有一次我问她:你年高身弱,视力又差,是什么力量在支持你?她给我讲了半个世纪以前的故事。她说:“1927年初,我在武汉工作时,我和武汉特区书记李耘生同志从相识到相恋、结婚。他是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我们结婚后,组织上就派我们去南京做地下工作。1932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他被捕入狱。同年6月8日,他在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27岁。在临行之前,他写了一张纸条托人带给我,上面只写了一句话:‘过去一百斤的担子两人分担,以后只有你一人挑了。我明白他的意思,就是革命工作和抚养孩子这两副担子都由我一人挑了。几十年来,我一天也没有忘记这个重任。”
接着,章大姐又谈道:1982年6月,是耘生同志牺牲50周年,她带着子女从北京到南京雨花台,沉痛悼念为革命献出生命的亲人。祭奠归来,她心潮澎湃,久久难平,连夜以“告英灵”为题,填《如梦令》四阕,其中第一阕云:“回首雨花台,别语匆匆遗愿。五十易春秋,日月双肩担,双担,双担,未敢白头言倦。”章大姐正是遵照党的重托和亲人的遗愿,数十年如一日挑起“双担”“未敢白头言倦”。
(编辑 叶 松)
(作者是中顾委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