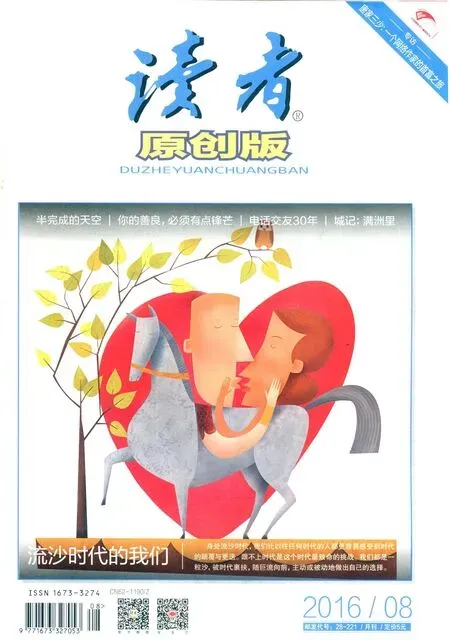移植
2016-11-14刘云芳
文_刘云芳
移植
文_刘云芳
小时候,我常把山顶上的松树、柏树移植到门前的菜园里,也移植野韭菜、野薄荷,让远处的风景成为我们家的景观。十几岁时,在纸上写下“把母亲的火炉移植到天边”,没想到会一语成谶,我真的成了一个“移植者”。
我先把自己移植到了远方,在那里扎下根。接着,把故乡的天空移植到了笔下。我还移植了父亲裤腿上的泥土、栅栏上站立的鸟、一头初生的盲牛、村头的老路和路上的行人……他们都变成了我文字庄园里的一砖一瓦。而在通往远方的路上,生活里的那些遇见也慢慢磨成它应有的形状,在这庄园里扮演着各种角色。
这些年,我经常掰开过去的时间,从脑海里取出记忆,一些消逝的声音和影像忽然再次回来。有人读到这些文字,从里面看见曾经遇到的一只鸟,或者某个熟悉的黄昏。他们给予我的回应成了庄园上空的炊烟,它让庄园活了。是的,我逐渐成了移植文字的人。
很多年前,我从故乡看我现在生活的城市就像天边一样遥远。而现在,像许多客居他乡的人一样,我开始勾勒自己的故乡和亲人。这样做的时候,我确定,我就是那个一直抱着“母亲火炉”的人。我终于把她对我的爱和温暖从那个镶嵌在吕梁山脉里的小村落移植到了眼前。
移植的过程中,我不可避免地搬来了泥沙、树的伤疤和盗取它汁液的蚂蚁。那些让我惧怕的不幸慢慢凝结成树,长在庄园里了。我因此学会了面对,并且明白,所有的事情终究会成为营养,滋养生命。
这两年,我一次次自问写作的意义,我发现从生活里提炼、积累的其实是另一个我,我的文字庄园其实是我的精神图像。我曾经移植的那些野韭菜,最终会失去山林的味道,它们举着白色花朵在风里摇晃的样子越来越像我采它们回来的那个下午的样子。于我而言,写作就是生命里的一场移植,它让一些流逝的东西变成我的。
我知道自己还不是移植文字的好手,但我要感谢那些注视过我的文字的目光。我相信,文字与心灵的碰撞兴许会成为另一场移植的开始。感谢《读者·原创版》,为这移植提供了最好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