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茨威格笔下没有兑现的“未来之国”
2016-11-10龙成鹏
□ 文·图 / 龙成鹏
巴西茨威格笔下没有兑现的“未来之国”
□ 文·图 / 龙成鹏
8月的奥运会,让我们看到巴西混乱的一面。但70年前,它却是另一番景象。在茨威格所著《巴西:未来之国》一书中,巴西是一个等待实现的理想国。对于经历“二战”创伤的欧洲,茨威格看到了巴西被人忽略的“精神”价值。
没有种族主义的巴西
把茨威格的名著《巴西:未来之国》拿在这里介绍,并不全是应奥运会这个景,还因为茨威格的言论,对认识今天的巴西,乃至当代世界,都有不少价值。
我们先来看一段话,这是茨威格写巴西的动机。“我最想说的,也是对现今世界各国最为重要的,是巴西在精神与道德层面的意义。”
这个意义是什么?
“在这个世界上,不同阶级、种族、肤色、信仰的人怎样才能和平共处?”这是每个国家,每一代人的难题。
巴西面对的情况更复杂,“但巴西处理得最好、最值得称道。”茨威格说,“我有幸见证了这点,并由此写下了这本书。”
巴西是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的?最重要的一环是反对种族主义,提倡各种族(民族)的通婚、接触与融合。
巴西民族由不同的种族(民族)融合而成。和很多美洲国家一样,它有土著的“印第安人”(分很多部落),有欧洲的殖民者的后代,还有非洲黑奴后裔,以及亚洲移民。
如此多元的人种结构,“如果也采取欧洲民族主义与种族的愚昧政策,势必四分五裂、战乱不止”,“如果按照欧洲人的思维模式,这里的每一个群体都会对其他群体保持敌意,先来者反对后来者,白人压迫黑人,巴西人驱逐欧洲人,白种人、土著人和混血人一同对付黄种人,多数派与少数派冤冤相报,为捍卫自己的权利不断争斗”。
但事实却是,“在这里的所有种族,尽管肤色不同,却能和睦相处;虽然出身各异,但却齐心协力。他们致力于尽快消除彼此的差异,成为完完全全的巴西人,共同建立一个团结的新国家”。
巴西为什么有这样的局面?茨威格追溯了巴西民族形成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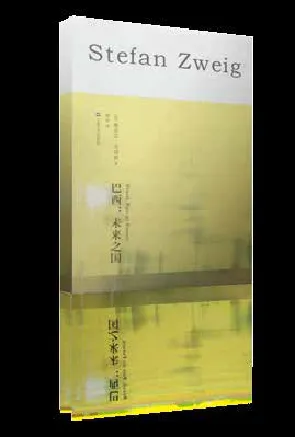
葡萄牙从1500年征服巴西开始,就鼓励(也是不得已)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之间通婚,由此造成了巴西没有一个纯正的种族,进而也就没有种族主义存在的基础。
种族的融合,“成为整合民族文化的有效途径”。
此外,巴西民族的形成,还得益于统一语言(葡萄牙语)的形成和基督教的传播。作为葡萄牙殖民的文化遗产,语言和宗教的普及, “最终将巴西由分离的元素变成了有机的整体,从互斥的散沙变成了统一的国家”。
基督教对巴西的影响,茨威格在书中也有浓墨重彩的阐述。他认为:巴西文化是全新的文化,在殖民征服之前,巴西土著并没有创造值得称颂的本土文明——茨威格写到这里时,应该想到了美洲其他地方出现过的文明古国,比如玛雅文明、印加帝国等。巴西是一张白纸,葡萄牙人在上面复印了欧洲文明。而其中,茨威格最为称颂的就是传教士带去的基督教精神。
基督教在巴西的传播始于1549年,距离葡萄牙殖民者发现里约刚好49年,这一年也是葡萄牙向巴西正式派驻总督的开始。
与6名耶稣会传教士同行的有巴西总督和600名士兵及400名囚犯。但在巴西民族、国家的塑造上,茨威格强调,这些人加起来都不如6名传教士重要,这些传教士“创造了真正的巴西”。
早期的殖民征服,其血腥与残酷,我们不陌生。但与这种无政府的行为不同,传教士主张建立道德秩序,主张通过教化去改变巴西,在他们眼中,土著民族是上帝的潜在的“选民”(把他们变成基督徒,体现在民族上,就是民族平等的主张),而不是变成掠夺、奴役的对象。
茨威格特别看重传教士那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以及他们对巴西文化的推动。但这种传教士究竟能带来多少具体的变化,茨威格也不能肯定。因为,对于从事文明教化工作的传教士来说,最难教化的对象,不是土著,而是欧洲殖民者及其野蛮后裔。而传教士后来被赶出巴西,也正好说明传教士与殖民者之间的矛盾冲突。
传教士并没有实现理想,但却给巴西未来发展奠定了某种“平衡”。茨威格这个判断特别重要,体现了茨威格对历史的深刻洞察。
对巴西来说,这种“平衡”体现在历史上各种对立因素之间的博弈,比如奴役与和解(巴西后来也废除非洲黑奴制度,且成效比美国更彻底)、等级与平等、暴力与和平,等等。这些博弈的结果,虽然未必就像茨威格说的“从这一刻起,他们在这片新大陆上,在所有人之间,树立起了互相平等的精神信念”,但却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一个和谐巴西。
反战,反“文明”
茨威格虽然赞颂传教士的精神,但他写巴西的意图跟传教士刚好相反。传教士是教化他者,而茨威格则是借“他者”教化自己,也就是教化欧洲。这点很容易被忽略,但又是这本书的关键所在。
在《巴西:未来之国》中,茨威格描述的那个“未来之国”,与其说是巴西的未来,不如说是欧洲的未来,因为茨威格想通过巴西经验的总结,去探索欧洲文明的出路。
茨威格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这要从《巴西:未来之国》的时代背景入手。这本书的出版时间是1941年,正好是欧洲各国陷入“二战”深渊的年代。“二战”对犹太作家茨威格来说,不仅仅是一场世界大战,也是欧洲文明自我毁灭这种绝症的表征(“欧洲亲手杀死自己”)。
而欧洲文明为什么会自我毁灭,茨威格也有明确的看法。
他认为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是症结之一。他们“妄图创造出最‘纯粹’的人种,就像培育赛马或者名犬一样”。这种极端的种族主义,最后导致互相仇恨,而结果就是种族大清洗和你死我活的战争。种族主义的悲剧,茨威格亲身经历过。他是奥地利人,因为欧洲1930年代愈演愈烈的“反犹运动”,他被迫离开故乡,最后流亡巴西。他的亲人、朋友,有不少受到运动牵连,甚至死于非命。
种族主义是否是“二战”的根源,历史学者可能有另外的看法,但“二战”期间及之前,欧洲种族主义的确发展到十分极端的程度,并最终导致了600多万犹太人被屠杀。这种现象如果深究,的确可以视为欧洲文明的内在缺陷。所以,茨威格想从巴西处理种族关系的历史经验中找到解决办法。
在书中,茨威格透露了一种思想,认为人类在种族性之上还有人性,相比种族的狭隘,人性则是人类共同体宽容、理解以及和解的基础。所以,对于“二战”,茨威格持有鲜明的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这种观念在“二战”中响应者寥寥,但“二战”之后,却成了世界的主流,并影响至今。
茨威格写巴西还受一种思想影响,这种思想是一种新的文明观。茨威格说,这种新文明观的出现是“近年来”的事情。与之相反的是旧文明观,旧文明把文明“简单归之于‘秩序’或者‘舒适’”。这种文明观实际上就是工业文明的产物,“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数据”,这些数据只看重国家财富、公民财产,“按照这些数据,文明也就意味着生产力、消费以及金钱”。
但这些功利主义的数据“却缺乏了一项重要因素:即人类的精神财富”。所以,茨威格断言:“最顶尖的体制(指欧洲文明)不但没有赋予人民人道主义精神,反倒将他们带上了野蛮的道路。”
意思就是,欧洲的工业文明那套,不是把人类变得更文明,而是变得更野蛮,因此,相比而言,“落后”的巴西,反而让茨威格看到另一种文明。
茨威格的这种文明观,在“二战”后同样得到发扬光大,从今天世界范围内如火如荼的“非遗”保护,从乡村旅游的发展趋势等等方面,都可以看出这种主张。
不过,另一方面,茨威格所批评的欧洲工业文明,同样在世界范围得到广泛传播。今天的巴西,之所以被人诟病,其原因之一就是它粗暴地学习了欧洲的工业文明,最终用环境破坏、贫富分化、社会矛盾加剧作为发展的代价。
“一切暴力、野蛮、残忍都与巴西格格不入”
对照今天的巴西,《巴西:未来之国》最有趣的内容是关于巴西民族的性格。
“民众在自娱自乐时也十分平静内敛;正因为缺乏力量与野蛮,他们才能享受到平静的欢愉。在巴西,高声喧嚣或是疯狂舞动都属于不合习俗的愉悦……”
……
茨威格的这些描述,很容易唤起我们对中国南方的一些印象,但却很难与今天那个充斥着欺诈、暴力、毒品与犯罪的巴西联系在一起。不过,回到该书的时代语境,这些巴西人的每一个优良品质,都可以对应一个欧洲人的致命缺陷。茨威格清楚地展示了他对巴西的爱,与对欧洲的恨。
茨威格眼中,巴西那么好,连今天臭名昭著的贫民窟,都熠熠生辉。
“贫民窟就建在里约城中的山坡之上,好似摇摇欲坠的鸟巢。……开始的时候,我承认,我以为这里会像欧洲无产者的街区,人们会以愤怒的眼神望着我,或者在我背后恶语相加。可是对于这些善良的居民来说,一个外国人不辞辛劳爬上山坡,就应像客人甚至朋友那样受到欢迎;一个拿着水罐的黑人看到我,他笑了笑,向我展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并帮助我登上光滑的台阶……”
在茨威格笔下,贫富不均、民族矛盾这些现代世界(也是人类历史)的顽疾,在巴西统统都不成问题。在茨威格的理想中,只要给足够的时间,巴西将会成为一个“最值得我们尊敬,最值得我们效仿的国家”。
然而,历史的发展却并不如此。
远逝的天堂
令人遗憾的是,茨威格描述的巴西“理想国”并没有出现,他笔下那个知足常乐平和的巴西,正在被各种欲望缠绕,被政治混乱、环境污染、贫富不均、暴力犯罪等等社会问题缠绕。今年里约举办的奥运会,被网友描述成“里约大冒险”就代表了当下普遍的声音。
④地下水水位的预测方法包括水均衡法、解析法、数值法和数理统计方法,本次节水增粮行动项目水资源论证主要采用了均衡法和解析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由此可见,茨威格在1941年对巴西的“正名”(当时欧洲以为巴西“野蛮”)至今依然没有完成。
茨威格的巴西,怎么变成今天的巴西?说来话长,所以,我们只好借另一本书来勾勒一下巴西的社会变迁。这本书叫《远逝的天堂——一个巴西小社区的全球化》,作者是美国人类学家康拉德·科塔克。就像书的标题提醒的,巴西的某种美好,正在失去。
这本书是作者从1962年到2004年40年间,在巴西东部一个小渔村(阿伦贝皮)进行田野调查的总结,他记录的小社区的变迁,可以视为巴西整个变迁的缩影。
1962年,阿伦贝皮的村民以打渔为生,“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几乎与世隔绝。
1965年以后,阿伦贝皮发生了改变,嬉皮文化侵入,社区旅游开始发展。
1973年,阿伦贝皮的环境随着工业发展,开始污染。“所有这一切都在1973年开始改变,曾经湛蓝的潟湖水(海边的淡水湖),如今变成漂浮着腐烂之花的一潭死水。”
这种污染,显然延续至今。但另一方面,1973年前后,为中产阶级和富人建造的海滨度假屋也开始大量出现,房租增长了5倍,“阿伦贝皮俨然成为一个附近城市旅游目的地新宠”。
这时候,“传统的发明”也开始被外来的嬉皮士推动进行。那些原本来过逍遥日子的嬉皮士开始搞“土著”手工艺品。村民开始搬迁,住到了新的聚集点,而老房子粉刷之后被嬉皮士租下来。
1973年左右,另一个关键变化也开始了——这里不再安全。“‘带枪吧’,一些村民告诉我们,强盗们肯定会来抢劫‘有钱的美国人’。……有人警告我们从萨尔瓦多来的警察当天正在搜寻两个持枪劫匪。”
茨威格眼中那些远离暴力且心情平和的巴西人开始消失,巴西社会朝着越来越不安定的方向变化,直到成为今天这个连奥运会运动员都会被抢的地方。
1980年之后的阿伦贝皮,变化虽然加剧,但“所有变化的雏形都已在1973年奠定”,此后的一切变化,“只是在充实这个框架”。
康拉德总结说:“短短20年,阿伦贝皮从一个相对孤立、平等主义和同质的社区,变成一个职业分化、信仰多样、社会阶级与地位存在高下的社会。”而这种变化,是20年间完成的。
(责任编辑 黄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