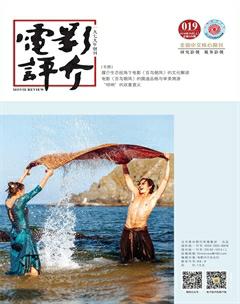从影片《幸运是我》看当今社会的家庭多元化现象
2016-11-08侯晓银
侯晓银
从影片《幸运是我》看当今社会的家庭多元化现象
侯晓银
香港家庭片《幸运是我》由罗耀辉执导,这位有着“金牌编剧”之称的电影人,首次尝试执导电影,便获得了香港与内地观众的一致好评。本片从独居老人芬姨的角度出发,讲述了一个她与港漂小厨师阿旭之间互相陪伴的故事,二人萍水相逢,非亲非故,却在朝夕相处中产生了家人般的依赖与真情。在IP改编潮流席卷国内市场的当下,这类质朴温情的家庭小品尤其难得。《幸运是我》直面人口老龄化现状,聚焦认知障碍问题,将“多元成家”的概念带入了公众视野。

电影《幸运是我》海报
一、 家庭破碎造成角色的性格弱点
影片的两位主人公,阿旭(陈家乐饰)与芬姨(惠英红饰),二人年龄差距巨大,在生活习惯方面也有很大差异,但是,他们的家庭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非常相似的,不幸的家庭生活造就了二人性格中的相似性。正是这种相似性,让阿旭和芬姨一拍即合,成为忘年知己,最终升华成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影片的开篇镜头便是阿旭捧着骨灰盒的双手,二十出头的年纪,别人还享受着父母的照顾,在大学中肆意玩乐,阿旭却一无所有,母亲的溘然离世,让他只得孤身前往香港寻找父亲。阿旭的寻父经历一波三折,从广州来到完全陌生的香港,他的处境,用“举目无亲”来形容也丝毫不过分。为了养活自己,他来到一家小餐馆打工,厨师的工作非常辛苦,老板娘对这位外来的打工仔毫无耐心,稍有过错便大肆责骂,阿旭一气之下辞了工作,祸不单行,他又因为拖欠房租被房东痛打一顿,赶出家门。从此,阿旭处境更加艰难,睡过露天大街,偷过女友钱包,阿旭身上完全没有所谓的“主角光环”,而是一个活在你我身边的落魄青年。当他千辛万苦找到父亲,却发现父亲早已组建了新的家庭,拒绝承认自己,甚至以骚扰罪名报警。在生活的压力面前,血浓于水的亲情竟如此不堪一击,父亲的逃避态度,让阿旭彻底认清了现实,他变得阴郁,一言不合就满口脏话,这也是阿旭内心自卑的表现,越是外表强硬,就越说明这个青年失落的心需要关爱。
芬姨同样也生活在平民阶层,买鸡蛋要为了几元钱掂量半天,出门舍不得坐计程车坚持步行,这个形象非常贴近真实,反映出了香港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情景。她年轻时做过歌手,出过黑胶唱片,却抵挡不住时间的洗礼,岁月的沧桑让她容颜不再,颠沛的经历让她孤独至今。没有丈夫,没有孩子,芬姨每天除了吸烟、发呆、听收音机便再无事情可做。这个角色正是现实中无数孤寡老人的写照,她不懂现代科技,不愿接受新鲜事物,每日奔波于柴米油盐的琐事之间,只为填满时间的缝隙,让自己显得不那么孤独,她同样缺少亲情、缺乏关爱。
两个角色都有着典型的双重人格,即外表和内心的极度反差。阿旭染着一头个性张扬的黄发,说话之间尽是少年的狂放,而他的内心却很自卑、脆弱。阿旭这个角色的设定并非尽善尽美,也不具有邪恶的劣根性,尽管有过不道德的行为,例如为了盗窃名贵酸枝椅接近芬姨,但影片也将阿旭重感情、善良的性格特点表露无遗。他带着同父异母的弟弟进游戏厅玩耍,用自己微薄的工资给弟弟买玩具、买冰激凌,家庭二字在阿旭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正是因为在乎亲情,他才会对一个名义上的弟弟如此慷慨、关切。芬姨同样如此,她非常符合一个传统意义上包租婆的形象,唠叨、暴躁,在钱的问题上斤斤计较。但是,当阿旭好心办错事,导致弟弟花生过敏,连夜送进急诊室,从小最崇拜的父亲当众责打阿旭,此时,只有芬姨站在他的身边,用拥抱和话语安慰了少年。她不易接近的外表下隐藏的是一颗敏感而善良的心,总是默默帮阿旭分担生活中的烦恼与辛苦。
拒绝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温情而不煽情,《幸运是我》将两位主要角色置于最平凡的生活中,用点滴小事引起观众共鸣,用侧面烘托的方式展现了主人公的双重性格,为阿旭和芬姨在冷色的都市中重拾人间温暖做了铺垫。
二、 由家庭到社会直面人口老龄化
在车水马龙的大都市中,总有一些需要关爱的弱势群体,随着医疗水平的进步,许多亚洲国家的老年人口比例迅速上升,“老有所依”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电影作为一种有效的大众传媒手段,在关爱孤寡老人问题上理应有所作为,《幸运是我》没有避讳现实,深入描绘了独居老人的生活点滴,将重点放在芬姨所患的阿尔兹海默症上,展现了人生岔路口上的悲欢离合。
阿尔兹海默症是多发于老年群体中的一种疾病,俗称认知障碍,随着病情的加重,患者的记忆力会逐渐降低。近年来,全球阿尔兹海默患者数量呈上升趋势,这个弱势群体需要更多的理解与帮助。欧美影片《爱》、台湾电影《漂浪青春》均涉及认知障碍患者,特别是奥斯卡佳作《依然爱丽丝》上映后,社会对他们的关注度有了大幅度提升。在《幸运是我》中,芬姨也被认知障碍带来的无奈和痛苦深深困扰着,她变得越来越脆弱无助。面对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老人,阿旭需要做出人生中重要的抉择。出于道义与情感考虑,他不能丢下孤苦伶仃的芬姨,眼睁睁的看她走向死亡,但理智和现实条件又让阿旭非常犹豫,在这个高消费、快节奏的都市,连一个健康的青年都还没找到立足之地,又怎能让一个素昧平生的老人拖累自己的追梦脚步?
在影片开头,芬姨的病症已表现的比较明显,她时常会忘记自己买过菜、做过饭,转身又去买来一袋鸡蛋,开火又准备做一顿饭,面对着冰箱里满满的鸡蛋失神。芬姨已经有所察觉,但倔强好强的性格让她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无助,随着病情的渐渐加重,她的记忆周期开始进一步的缩短,走在街上会突然忘记回家的路,给阿旭做了一碗粥,竟然忘记了放米。这些细节看似漫不经心,却处处戳中观众内心深处的感伤,导演的镜头不留痕迹,没有任何刻意的夸张,仅用写实的白描手法,就将角色的无助和落寞表现得恰到好处。当阿旭得知房东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他一度消失,不敢与芬姨见面,这正是人性弱点的体现,阿旭没有义无反顾地照料芬姨,也没有就此撒手不管,承担责任还是就此放弃,不断地徘徊、犹豫,两种心理在此消彼长。这时的芬姨,带着染了一半的头发出现在街头,沿着二人每天买菜途经的坡道,昏暗的路灯下,一个老妇踽踽独行。这个镜头是全片最令人痛心的场景之一,阿旭帮芬姨染白头发,途中却忽然消失,染了一半的白发刚好象征着阿旭与芬姨的关系,二人已经十分友好默契,是成为陪伴一生的亲人,还是就此分道扬镳,阿旭站在了人生的岔路口。
芬姨的扮演者惠英红在接受采访时黯然流泪,她在片中的精湛演技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真情流露,她的母亲也患有同样的病症,而为了事业打拼的自己却没能多陪伴母亲一些时间。在影片中,阿旭有一段没有结果的恋情,女主角也是一位港漂,从内地来到香港做义工的女孩小月(刘雅瑟饰)与阿旭在社区服务中心相识,同样的漂泊经历将两个年轻人的心连在了一起。对于在外打拼、四处漂泊的游子而言,家人的陪伴是如此珍贵,为了事业,他们牺牲了很多与父母相处的时间,珍惜亲情,才不会在它倏然远逝的瞬间感到悔恨。
《幸运是我》直面了社会问题,以阿尔兹海默症为入口,意图唤起社会对孤寡老人的关爱,深挚的情感,精致的演技,将人性弱点如此形象的展示出来。阿旭面对患病芬姨的态度非常写实,让观众感同身受,照料孤寡老人的任务,即使在能力之外,也应在情理之中。
三、 现代社会中的“多元成家”思想
这个故事发生在香港,在这个现代化风口浪尖的大都市,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的思想也在悄然变化。高速发展的社会给了每个人更为沉重的生活压力,现代人往往重视对家庭的责任,而忽略了“家”的本质是简单的沟通与陪伴。芬姨和阿旭正是通过彼此间的交流,弥补了对方心灵的缺口,同时也改变了自己对生活的态度。
最初的阿旭,由于长时间得不到家庭的温暖,他对周遭一切都缺乏耐心,脾气暴躁,不信任他人,在与芬姨的相处中,他慢慢学会了包容他人。尽管也有许多摩擦,比如他为芬姨买了新的电视,却没想到芬姨根本不领情,理由更让他出乎意料,老人看了一辈子旧电视,记不住新电视的频道。但是阿旭心里明白,芬姨的出现为他的人生增添了新的色彩,他把从芬姨身上学到的人生智慧,传递给更多的人,而不是再对身边的人恶语相加。他们不仅彼此相伴,还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对方,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
两人每天去买菜,必经之路上有一个陡峭的坡道,阿旭总是关切地问芬姨需不需要帮忙,芬姨总是笑着答应。人生有时正是如此,就算没有血缘关系,两个陌生人互帮互助,又何尝不可?即使无法阻挡人生必然的变故,也可以坚定的陪在彼此身边。在影片结尾,芬姨终于重拾画笔,想为阿旭创造一张画作,在她的笔下,阿旭耳后的胎记非常突出,芬姨正是要用这个特点,永远的记住阿旭。此外,胎记也是血缘最神秘的象征,两个没有血缘的人,因为命运的牵系而相识相知,最后结为全新的家庭,这种牵绊,与胎记一样神秘而妙不可言。阿旭与芬姨的故事,解析了一种全新的家庭模式,即现代社会独有的“多元成家”。在血缘家庭中找不到温暖的他们,勇敢地跨过陌生人的间隙,成为相依相伴的亲人,比起血亲给予的凉薄,他们才是彼此最合适的家人。认真地为家人染头发,用心地为家人做早餐,两个煎蛋,一片培根搭配一杯红茶,虽然简单,却回味无穷。茶余饭后,围炉夜谈,坐在沙发上看冯宝宝的《万家灯火》,阿旭与芬姨一家的日常生活,是那样平淡温馨,对于长时间生活在家庭不幸的中二人而言,这不仅是一种解脱,更是彼此的救赎。
“多元成家”作为一种新型的家庭概念,早已在许多影片中都有所体现,同样以香港为背景,许鞍华在作品《得闲炒饭》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理念。现代社会在快节奏、高压力的同时,也赋予了我们每个人更多的自由,让我们有机会选择和表达。摒弃虚伪的束缚,选择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关怀,能得到这样的机会,称得上是一种难得的幸运。
结语
本片主题曲中有这样一句歌词:“曾尝遍失意时,却找到快乐匙。”一对老少失意人,在彼此的陪伴中,找到了人生最可贵的色彩。《幸运是我》没有过多的商业色彩,而是将真实的市民生活赋予光影,用深挚的情感唤起了观众的共鸣。在众多的视觉系电影的冲击下,质朴平实的《幸运是我》突出重围,成为了今年暑期档影片中的一股清流。
侯晓银,女,陕西富平县人,西安石油大学人文学院设计系讲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