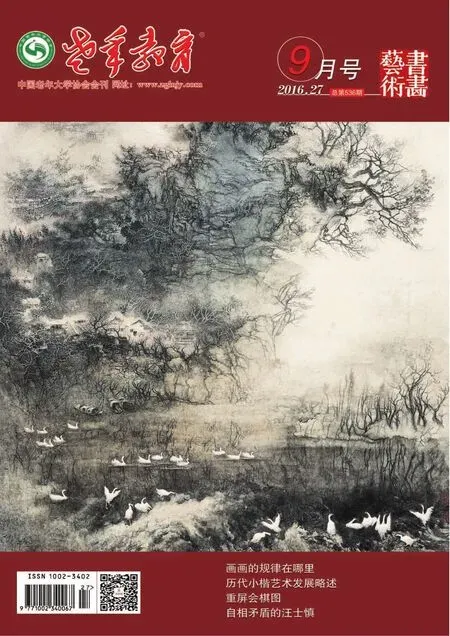我的艺术之路
2016-10-27李孝萱
□李孝萱
我的艺术之路
□李孝萱

小时候,常见大哥闲暇之余弄几笔梅、兰、竹、菊的玩意儿。我不懂好坏,自然很佩服。也许是那时萌生的兴趣,凡关乎画的东西,都要动手尝试一下。因为我更喜欢人物画,他便找了本俄罗斯的“素描教学”给我看,那本书差不多让我翻烂了,里面的画也几乎临遍了。然后,我就按其方法对着真人写生,于是,家人都成了我的模特儿。
那时,一册小书《工农兵形象选》和蒋兆和先生的《毛主席和少年儿童在一起》的画页,是我唯一的学习资料,其它根本不知晓。恢复高考那年,我考上了天津美院,学中国画,以写意人物为主。那时,教与学只有“写实”一个标准。学校里有一批老先生,都是从前老“湖社”一派的画家。他们言传身教,重视临摹,重视笔墨传统。一位老先生曾对我们如何用功垂训八字:“瞻前顾后、东张西望。”此深刻悟道之言,使我受益颇深。
大学四年,除了速写、素描、国画写生这些解决人物造型必要的课程外,我对传统绘画的研习、临摹占去了大半,仅对永乐宫壁画原作的临摹就达三个月。从历代壁画到历代大师名作,我都仔细认真地反复临摹。课堂上,老师对每个环节都不放松,严格的程度超出了今天学生的想象力。老师教诲我们,一定要先理解,后动手,临成什么样,就能画成什么样。临摹课的持续使我对传统绘画有了新的理解和体会,它不但没让我厌烦,反而在我心里发生了深刻影响,哪怕后来沉浸在对都市人生的表达,问途于西方艺术的经验,都始终没有忘记中国艺术的博大。
随着对写意人物画研究、写生的不断深入,我渐渐觉得自己的胃口不及从前消化好了,慢慢地开始有了挑剔感,过去曾经心手膜拜的一些人物画家,一下子从大脑里隐退。最后,筛来筛去只剩下了徐悲鸿、蒋兆和、方增先和王子武等先生。我找来他们的画临摹、琢磨,发现徐、蒋一脉一般人理解的不外是“兼容中西”的空架子,其实,徐先生把西方重形构的东西拿来,才是他真正成为改造中国画第一人的原因。虽然,徐先生的人物画仍停留在工笔的某些方式上,没能达到以写的方式里外通和,但他给写意人物画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再说蒋先生的用笔如屋漏痕,力透纸背,变化多端的线条以一根直线立住,不显花哨,朴素单纯又磊落大方;方先生则吸收写意花鸟画的语言,补充了人物画在笔墨变化和趣味上的不足;王先生的人物肖像且不言,仅他的《曹雪芹小像》,就令我大开眼界。我即刻把所学用到自己的写生中,面对模特儿,不用起稿,从眼睛着笔;不弃性格,在形构中强调笔墨,在块面中提炼线条,能用一笔,不用两笔,并尝试着抛开块面和光影,完全以线表达,虽不成熟,却透露着我当时的追求。
大学四年级(1981年),是我学习写意人物画感受最多、收益最大的一年。大约是那年5月,我去了山西省永济市,在黄河岸边的一个村落住下,一下子画了近六十多张人物写生。闲下来静观谛视,又觉得长进了许多。人物的刻画去掉了课堂上的呆板,身份特征也明朗起来,线的变化有了轻重疾缓,墨的浓淡干湿处理也有了“手气”,只是线条的使转、力度、味道、生涩劲总是达不到自己的意愿。打开随身携带的王子武先生的画册,对照着,忽生一念:去拜访他!于是坐上火车,直向西安。敲开先生的门,只见他满脸疲惫,微声弱力地以朴素的方言问:“你是谁?”我便介绍了来历。先生说他一会儿有事,想来对一个素不相识的访客,先生虽不便固拒,但只能说勉强接待。而当我打开画夹子,他即刻现出惊喜:“你画得好,你的笔墨好,造型好。”想必先生的惊喜不是出于我对他的模仿,而是出于长者对晚辈的厚爱吧。不善言辞的他与我聊了起来。我设法把话题引向自己的画,问到如何着色,先生反倒赞赏起我的用色,询问过程,并予记录。然后,他铺上宣纸,亲手磨墨,坐在椅子上居然让我为他画像。在先生面前丢失了胆量的我,真不知如何是好。运笔间,他不时站起来,热诚鼓励之余,又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中午留我饱食一顿,还拿出原作让我一饱眼福。最后,先生从他的画中挑了一幅,落上款送给我,真让我万分感动。
返津的路上,脑子浸在王先生其人其画中,无了无休。难怪先生能臆造出堪称美术史经典之作的《曹雪芹小像》。从我敲门那一刻,无论是隐姓埋名、清心寡欲和动手记下一个无名小卒的着色情景,还是充当模特儿的角色在我眼前矗立,这当中留给我的只有感动。不单单是先生的画,他的朴素、平和、高贵的艺术品质和人格上的魅力完全俘虏了我。
这次对王子武先生的拜访,亲炙他的光仪,得到他的帮助,其意义远远超出了绘画本身,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从未经过思考的东西。假如没有像王先生他们这样的人对艺术的持守,真正有教养的中国画语言和作品就无处可寻。除了这些先生,还有再远一些的,像八大山人、齐白石、徐悲鸿、黄宾虹、蒋兆和诸先生,对我后来写意人物画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真万言难述。总之,我学他们到了饥渴的程度,甚于强夺,尤其是齐白石先生,从我小时候在街头看到他的漫画起到现在三十多年,那影响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我花掉了大部分生活费买他的书,哪怕为了一页都要买下来。要是齐老先生健在,就是还有一口气,我爬也要爬到见他一面为止。对这些先生,我不只是感激和崇拜,更多的是悼念和敬意!我衷心地感谢明清人的记载和收藏,如没有他们的作品,没有他们真实可信的传说,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坏、什么叫好,也就不知道什么叫公道。
1985年底,蒙师长垂爱,特别是在陈冬至、白庚延先生的吁请下,我被调回了母校任教。在外漂泊的几年,一次次艰难和心痛,神经遭到猝不及防的强力撕扯后,虽然仍保鲜着大学的记忆,当我重新拿起笔时,在一刹那间,彻底颠覆了我原先积累的艺术经验。这些发生在我人生经历上的对抗,反倒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快意和自由。
我画画的动机,是为了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或真实感情。能够具有独创性的理解和运用个人语言,对于画家而言,本身就不太容易。尤其是写意人物画,刚刚找到一个区别于传统、区别于困扰我的偶像,把自己的图式面貌打碎了重新捏合,再来一番大的割舍,无疑需要勇气。这时候,我又遇到了大学时的中国美术史老师、著名美术批评家郎绍君先生。他针对我的想法,语重心长地给予了肯定。先生在理论上的建树和对传统笔墨精神的高度重视,给我提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和最大的精神援助。我激情跃然,画了《大轿车》 《赤裸的喧哗》《我们吃力——时刻忘不掉的呼吸》等巨幅画作。记得1985年的一个冬天,我的心犹如当时的天气一样寒冷。生命没有着落,四处奔波,想给自己寻个出路,带着一卷画和曾经被批判的毕业创作照片去见先生,先生为我遭受的厄运同情有加,关爱垂示,并在当时的《中国美术报》上发表了题为《我看—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晨》的评论文章。就是这篇字数不多的短文,却让我暂时吸了口新鲜空气。在与郎先生往来的近20年中,都是先生给我巨大的心理支撑,保持着底气,始终不减。还有一点我非常庆幸,数年来一直伴随在我身边的几个怪人——寒碧、何家英、闫秉会、李津,令我不觉孤独。我们彼此会心,砥砺为学。正如何心隐所言:“道而学尽于友之交。”我想,没有老师的教诲、提掖,没有朋友的相互切磋,独学无侣,是很难在艺术上找到正途并有所提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