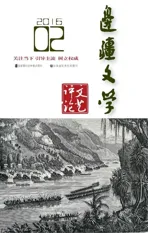柏桦:“第三代”诗人中的“异类”
2016-10-21刘文涛
◎刘文涛
学人观点
柏桦:“第三代”诗人中的“异类”
◎刘文涛
主持人语:文学史在描述某个时期的文学创作时,总喜欢用思潮、流派、社团等术语来概括这个时期的文学风貌,“第三代诗”就是这样一个在当代诗歌史上引人注目的诗学概念。一个作家或诗人,一旦被文学史家纳入某个流派时,他就获得了这个流派的共同美学标签。有的作家因为归属于某个流派而存名,有的作家则因为流派而淹没了自己创作的个人性。刘文涛所论述的柏桦就是这样一个被“第三代诗”的标签淹没了个人风格的诗人。在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中,一般都认为“第三代诗”的总体审美指向是“反文化”、“反美学”,这样的标签用在柏桦身上,
实在贴错了对象。如刘文涛所述,柏桦的诗歌显然与“第三代诗”的诗学追求相距甚远,他是当代文学史中的“异类”。刘文涛的这篇评论不仅是为柏桦“正名”,而且也提醒我们反思文学史叙述存在的“不可靠”。
张雷是云南已故的青年诗人。作为张雷的老师,知名学者张直心先生在为张雷诗集所写的序中,回顾了他们令人感喟的师生之谊,并将“追寻黑豹”描述为张雷诗歌的精神指向。张直心先生的序虽然简短,但却颇为传神地道出了张雷诗歌的内在品质。我想,倘张雷地下有灵,一定会感到安慰的。(胡彦)
第三代诗人是以“pass北岛”的反叛姿态出现的,“他们”“非非主义”“撒娇派”“莽汉”等等社团都在用现代或后现代的理论武装着自己,结社、出版地下诗刊成为当时流行的诗歌事件,诗人们不断聚集分散,谈诗论事。进入1990年代,诗歌的论争和发展依然如火如荼。在一个用诗歌流派或结社来显示诗人身份的年代里,柏桦算是其中的“异类”。他虽然与张枣、周忠陵创办过《日日新》杂志,但在多数情况下他依然游离在这些社团之外,对于1980年代的诗歌史而言,他是个体性的存在,不属于任何流派。这一方面与柏桦的个人气质和经历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柏桦的诗歌自觉有关。
一、男人身体“女人心”
敬文东说“柏桦是一位有着浓厚女性气质的男性诗人。”[1]柏桦在反思自己早期诗学理念时,写到:“就一般而言,我有些怀疑真正的男性是否真正读得懂诗歌,但我从不怀疑女性或带有女性气质的男性。”接着,柏桦继续写到:“她们寂寞、懒散、体弱和敏感的气质使得她们天生不自觉地沉湎于诗的旋律。”[2]怎样的经验让柏桦如此反思自己的诗歌写作经验?在《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里,他不止一次写到,他的内在是“母亲激情”,外表是“父亲形式”,也就是说,他外表虽然是个男性样貌,但在内心深处却隐藏着一个女性——“母亲”——给予他的性格特征。也可以这样说,柏桦作为一个诗人,尤其在1992年之前的创作生涯中,他是男人身体“女人心”的存在。
柏桦以这样一种特殊的诗人身份进行着尖叫与呐喊。探究这种身份形成的过程也许比结果更加重要。按照柏桦在传记中讲述的童年记忆来看,笔者认为这种身份的形成与他童年时期的心理创伤密切相关。在很多研究者看来,心理创伤是由任何一种突然发生的和潜在的生活危险事件造成的。弗洛伊德作为心理创伤理论的奠基者,他认为心理创伤是“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到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3]心理创伤可以发生在个体成长的任何时期,然而,儿童期的心理创伤将以潜意识的方式影响到个体成长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个体性格。以儿童心理创伤理论来解释柏桦的性格特质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它可以为探究柏桦的写作风格以及柏桦其人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撑。
在《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柏桦对于儿童及青少年阶段的回忆文章,极少谈论其父亲,然而却用极大的篇幅叙述他与母亲之间的对立,以及小学时遇到的“多毛症”的女教师。“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童年全被母亲的‘下午’所笼罩,被她的‘词汇之塔’所紧闭。”[4]母亲在他的儿童时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母亲常会在下午训斥他,“时间一长,我会产生幻觉,喉咙发痒,血管里奔涌着尖叫……突然,热衷的下午又极速变化为冰里的下午,我不知多少次仅仅只差一秒钟就疯掉了。”[5]母亲尖锐的声音始终环绕在柏桦的童年记忆里,“蛋糕事件”使他与母亲走向了对立面,本是一个孩童的顽皮或者口舌之欲,却成为母亲喋喋不休的理由,他在恐惧和不安中度过了那个下午,却走不出母亲的影子。当时的柏桦知道自己会被母亲训斥,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行为让母亲暴怒。在一般情况下,孩子都是母亲的心头肉,即便是做错事,教育完也会把母性温柔的一面展现给孩子,但是柏桦的母亲没有,这对儿童期的柏桦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少年时期,由于一个脾气古怪的女教师的苛责,他离家出走,这样的经历让他感受到了寒冷和女性带给他的恐惧与厌恶。记忆或者说留存在内心深处的创伤是很难被抹去的,但也正是这样的童年记忆在未来成就了柏桦身上所独有的精神和心理特质。柏桦写到“9岁的我虽不会抒情,不知道这‘愤怒’所酝酿着的‘精神分析学’的被伤害感和被抛弃感,但没有这一夜我就不会在15年之后与波德莱尔的《露台》相遇,我就不会以我后来的‘冲锋的青春’歌唱我的生活。”[6]
柏桦的性格和精神特质是儿童时期的成年女性给予他的,这种男人身体“女人心”,更多地表现在心理和创作层面,极度敏感、情感充沛、阳刚被遮蔽;往回走,不断处理童年,青年的经历,使得这种身份更加凸显。然而,就像精神分析学所关注的,诗人和精神病就在一线之间,或者说两者在某些方面是同质的,观照柏桦的诗歌,他虽然被灼烧,但从没有迷失。
柏桦在成为诗人的道路上,逐渐将这种儿童时期的心理创伤转化为诗歌语言流淌在纸张上和双唇间,不论是激情的缓慢的讽刺的,都有效地释放了他对于记忆的敏感度和复仇心理。这种转移是一种移情,他顺利地把那种有可能扭曲的感情转移到了诗歌写作上,一个敏感的男人把目光投向诗歌时,天才出现了,最优秀的抒情诗人诞生了。对于一个抒情诗人而言,对生活的敏感是必不可少的性格特征之一,儿童时期所留下的心理创伤,没有毁灭柏桦,却恰好成就了柏桦。柏桦的性格是独特的,诗歌也是独特的,而在当代文学史中,柏桦的“尴尬”地位也从另一个方面变现了柏桦的特异性。
二、当代文学史中的“异类”
文学史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它是对文学发展作科学的、历史的鸟瞰、描述、概括和总结,是编写者(研究者)以宏微观结合的历史眼光,审视、概括和阐发文学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从而科学地总结出文学在其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或某个历史阶段中)的特点、规律或经验。”[7]也就是说,写中国文学史,“便要采取‘文学’的观念、按照‘历史’的时间顺序,来描述中国文学的过去”[8]。在古代传统中是没有“文学史”这样的命名的,“文学史”是个舶来品,由西方转道日本而来,与中国现代性的进程密不可分,它按照西方对于“文学史”的定义对中国文学进行溯源、描述和评论。而中国当代文学史也就60多年,在这60多年中,前30多年文学的文学性值得商榷,后30多年是文学多元化发展的历史,它还在继续演变和发展。在笔者的考察中,当下流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不论教材还是专著),一般以1949年为开端,最远述及时间为2009年,文学史写作的时间性问题在这里凸显。文学史写作的特点,决定了它必须与现实世界保持一定的时间距离,以便对过去发生的事件进行客观和准确的描述与评价。
文学史终究是人(集体或个体)叙述的,它直接或者间接地体现了写作者的审美趣味,对于某些个体是否具备纳入文学史的价值,写作者之间也有不同的看法。同时,在时代的制约下,文学史的写作也与时代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相联系。1980年代末,对于“重写文学史”的争论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文学史与时代、政治、个人错综复杂的关系。之前的文学史,由于与政治存在暧昧,使得无法从纯文学的角度来评价文学作品、作家以及文学事件,政治正确性成了文学史的主线,因此,陈思和与王晓明在讨论中说道:“只有把一切研究都推到学术起跑线上,才能够对以前成果作一番认真的清理,使前一时期或者更早些的时期,出于种种非文学观点而被搞得膨胀了的现代文学史作一次审美意义上的拨乱反正。”[9]“重写文学史”具开创性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挖掘出了许多不为文学史所接纳的文学事件,延续了文学史的传承性,为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打开了一扇门。
在文学史中,文学思潮、文学事件、作家、作品等等,是必不可少的框架性要素。那么,什么样的作家作品才能进入文学史?对于当代文学史而言,历史对于作家作品的检验时间相对较短,如何衡量一个作家或者文学事件的历史价值,是每一个文学史家都必须考虑的问题,当然,上文说过,文学史是人写的,写作者的审美价值是通过其选用的作家、作品体现的,这样,文学史所具有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就不言而喻。笔者在考查当代文学史著作时发现,诗人柏桦作为第三代诗人很少出现在文学史的叙述中,这里暂且不讨论其中的原因,先看一看文学史是如何描述的。
笔者参考了19部当代文学史著作[10],4部诗歌史著作,其中涉及柏桦的文学史有4部,诗歌史有2部。张志忠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60年》第七章《西部风景:‘新边塞诗’、昌耀与巴蜀诗群》中写到“在社团、流派林立的巴蜀诗群中,柏桦并没有明确的‘归属’。”[11]然后简要介绍了柏桦以及其代表作,同时引用柏桦的《表达》和《在清朝》中的诗歌段落分析柏桦的诗歌创作,“他的这些诗,在构词和句法上具有苦心经营与猝然迸发相交融的特点,显出某种浑然天成的美感。”[12]这是涉及诗人柏桦较多的一部当代文学史。赵树勤、李运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49—2012)》中在第二十二章概述中提到柏桦作为第三代诗人的身份。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第十八章《朦胧诗及其他》中写道:“此外,八九十年代较有影响的青年诗人还有海子、骆一禾、柏桦、伊沙、朱文、臧棣等。”[13]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第五部分《新时期文学(1978—2000)》第三节《第三代诗人》中写道:“四川诗群实际上包括了1986年参加‘现代诗群大展’的‘非非主义’和‘莽汉主义’、‘整体主义’等诗人,其中的欧阳江河、翟永明、钟鸣和柏桦较早知名。”[14]不难看出,柏桦与这些文学史著作只是打了个照面。在当代诗歌史著作中,程光炜的《中国当代诗歌史》写到“四川五君子”,他说:“80年代中期后,欧阳江河从新传统主义中分裂出来,与翟永明、柏桦、钟鸣和孙文波组成了松散的诗歌小联盟”[15],这就是“四川五君子”。洪子诚、刘登翰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中认为柏桦是第三代诗人,文章写道:“在1982年,‘打倒北岛’的口号已经喊出,当年,钟鸣等在成都创办的‘民刊’《次生林》,所载柏桦、欧阳江河、翟永明等的诗作,已经明显有别于北岛、舒婷式的朦胧诗。”[16]同时引用柏桦的《表达》来说明。这就是文学史对柏桦的叙述。笔者考查的资料也许不够全面,但20部文学史,只有4部提到柏桦,起码能说明柏桦在文学史中尴尬的位置。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柏桦远离文学史?
笔者认为,首先,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有一套既定的规范,如:在描述新时期诗歌时,大多采用通过流派来描述诗人,从“归来诗人”、“新边塞诗派”、“朦胧诗”到第三代诗人群,文学史中出现的诗人大多都隶属于某一个诗歌流派,而对于柏桦来说,他与第三代诗人群中的许多诗人都有交流,但却不属于任何一个诗歌流派,这对于文学史的写作者就比较棘手,叙述这样一个诗人的价值何在?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学术考虑和美学追求,如何叙述也需要考察这些写作者的价值取向。柏桦成名于1980年代,正当自己诗歌生涯辉煌之时,他却在1992年之后选择了从诗坛“隐退”,进入自我的天堂,之后,鲜有诗歌问世,没有了作品支撑的诗人,怎样去表现自己的影响力和价值,便成了疑问。这样,在考察作家创作的延续性时,柏桦就被排除在外了。其次,进入新世纪之后,柏桦的写作可谓是喷涌而出,一系列的诗歌文本呈现在读者面前,而文学史也没有过多关注。为什么?诗人、作品只有经受了时间的检验之后,在历史的长河中积淀下来才有可能被文学史家发现,进而进入文学史。文学史对于新世纪的诗歌事件的描述大多是对第三代诗人中若干人的跟踪以及对网络诗歌、“70后”“80后”写作等的关注。柏桦属于第三代诗人中诗歌写作延续性较差的一个,而且新世纪出版的诗歌文本中,如《水绘仙侣》,“史记”系列、《一点墨》等在风格上都在试图挑战以往和当下的诗歌写作,这样的创新对于文学史家、评论界以及诗歌界的接受来说都需要一定的时间,用什么样的话语去评述?怎样定位?如何理解?都是读者以及文学史家面临的问题。最后,柏桦特有的男人身体“女人心”的性格,使得他过于个体化,它的诗歌是自我感受的表述,如《一点墨》中的诗歌,其个人化的风格极端明显,他在诗歌中回望,却忘记了时代的期望,他诗歌中表现的与当下的权利话语有着很大的距离,这种距离也在他与文学史家之间画出了一条鸿沟。笔者在阅读中,感受到柏桦的诗歌世界似乎与这个时代有很大的距离,他故意的回头,在过去的时间里建构着他的诗歌王国。正是这些原因,让他成为当代文学史中的“异类”,其中有客观原因,也有柏桦作为一个个体自身的原因,但是起码可以看到,柏桦作为一个诗人,有他自己的态度,有他自己对于诗歌的执着。
文学史只是评价作家、作品的一种平台,文学史中的“异类”不等于说就没有价值。诗意往往在别处,受不到意识形态的关注,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可能是一种幸运,他们能够在最自由的限度里写作诗歌。柏桦近年来的文本正是这样一种尝试,他不断突破自己,突破体裁的限制,试图在现代、后现代主义盛行的当下,以一种返回的姿态反抗和反思当下的诗歌写作,建立自己的诗学观念,创造属于一代人的诗歌风格。
三、结语
柏桦作为第三代诗人中的一员,儿童时期的心理创伤使他变得敏感、激烈,内心中充满火一般的狂奔突进,从这一点来说,柏桦显得更加私人化,在那个个人为时代代言的年代里,他却在向内走,在写自己,在表达“个人既时代”的诗学观。这样一个抒情诗人在文学史中鲜有被提及,“尴尬”的文学史地位使他又一次游离在主流话语权之外。一个独特的个体性格、一个“尴尬”的文学史定位使他不像大多数第三代诗人那样活跃,然而正是这种看来非正常性的现象成就了柏桦,成就了柏桦的诗歌。
【注释】
[1] 敬文东.中国当代诗歌的精神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45.
[2] 柏 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92.
[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17.
[4] 柏 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3.
[5] 柏 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4.
[6] 柏 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9.
[7] 徐志啸.文学史研究的启示与思考——以《剑桥中国文学史》为例[J].文学评论,2015(1).
[8] 戴 燕.文学史的权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5.
[9] 陈思和,王晓明.关于”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对话[J].上海文论,1989年第6期.
[10] 考虑到文学史著作的有效性,故笔者参考的文学史著作多出版于2000年之后。特此说明。
[11] 张志忠主编.中国当代文学60年[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115.
[12] 张志忠主编.中国当代文学60年[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115.
[13] 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512.
[14] 丁 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416.
[15] 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96.
[16] 洪子城,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47.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2013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杨 林

桃花斑鸠图 桂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