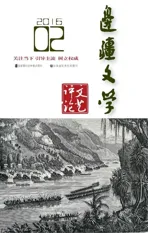在语言中构建一种更高的艺术真实
——甫跃辉小说浅论
2016-10-21朱彩梅
◎朱彩梅
在语言中构建一种更高的艺术真实
——甫跃辉小说浅论
◎朱彩梅
第一次读到甫跃辉的小说,是在2012年底第四届高黎贡文学节举办时,作为八位提名作家之一,文学节作品集选入他两部中篇小说《丢失者》、《动物园》的片段。因是节选,情节不免突兀,但读了没几段,就能感觉到特别之处,其语言的清晰、简洁、准确,字里行间的从容、平和、中正,与之前风行一时的很多80后偶像作家矫饰、油滑、戏谑,或是决绝、残酷、任性的笔调,可谓大相径庭。而且,他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青年最易犯的伤感病——那种情感泛滥、语言夸张、装腔作势的唯美文艺腔和千篇一律、俗不可耐、毫无节制的成长叙事。对于一位年轻小说家来说,难能可贵。虽然还在探索阶段,但作者具有强烈的叙事自觉和经典意识,其写作是“取法乎上”的。
之后在昆明圆通影院会场上见到他,正和云南青年诗人符二聊得高兴,一脸笑容淳朴、灿烂。现场交流时,谈到复旦大学文学写作专业导师王安忆对自己写作训练要求之严苛,他声音沉稳,语调庄严,笑容不见了。可想见,导师对于他的写作意义之重大。自此留了意,再看到他的作品,自然就特别关注些。之后又发现,他的创作量也很惊人,从2006年到2015年,每年持续发表多篇小说,先后出版了《少年游》《刻舟记》《动物园》《鱼王》《散佚的族谱》《每一间房舍都是一座烛台》《安娜的火车》等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且写作视野日渐开阔,品质不断提升。
小说的真实性
甫跃辉创作已十年,整体来看,他文学感受敏锐、细微,善于组织素材,能为呈现不同类型的故事、生活找到对应的叙事节奏、表达方式;诗化语言的适度运用,有助于经营意象,营造氛围,在他笔下,一些细节被赋予了深厚的意蕴;若说其语调的自在、从容,有三分来自性格的温和、淡定,倒有七分源自他对写作永恒意义的坚定信念。这些元素、态度使得他的小说贴近生活,与现实世界息息相关、彼此照见,具有了可感知、可触摸的真实性、生动性;同时,他又具有一种超越的视角——不断审视生活,审视自己,时时反省、思考如何看待世界,理解世界。这种“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的写作,很有希望通往一种超越现实的、充满力量的真实,那是更高的艺术真实。
好的小说,具有不可抵抗的召唤力。读上几句,深海般的吸引力会使读者不由自主想进入它的内部世界,读下去,一直读下去。这种召唤力源于作品所创造的真实。所谓真实,不是内容方面单纯的遵照现实,也不是写作手法的照相式如实描摹。作家创作时,尽可展开想象,大胆虚构,但想象与虚构里面,须含有另一种更高的艺术真实。小说的生命之所在,正是这样的真实。就像一个人的行事,只有当此事是其性格使然,源于内心深处的渴求,非外力强迫或对体制、权威的屈服,他所做的一切,才会焕发出活泼、迷人的光彩。小说亦如此,当它遵循自己内在的结构来运行,才会获得真实性。真实蕴含人性的丰富、存在的无穷,真实使小说产生令人信服的动人效果。这样的作品,不是向读者讲述、传达什么,而是使读者直接体验。读者身在书房,却能经历各种人生,享有丰富的生命体验。
甫跃辉深知艺术真实的重要性。他的创作,正如其所言:“我所有的小说加起来,真实经历的痕迹还占不到百分之十。但是,它们千真万确又是真实的。它们是我想象中的真实。如果真实经历是一棵树,它们便是树的影子。我的写作更多的瞄准的是影子,在我看来,影子比树本身更迷人,甚至,也更真实。”[1]的确,不管空间背景是乡村、小镇、城市,还是模糊的远方,他都试图在记忆与想象中构建关于它们的真实。《安娜的火车》腰封上这句话,可看作他的创作谈:“我记得那些广阔且沉寂的乡村,混乱而蓬勃的小镇,繁华也破败的城市,陌生又熟悉的远方;我也记得,在那些乡村、小镇、城市和远方里,浮现又消失的面孔。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2]“我记得”,“我也记得”,一切关联都源于记忆,记忆的海水深处,是庞大的感觉、情绪、经验之冰山。它们“都与我有关”,这种相关,更多是作者的关切——对身边事物、存在的深切关注。他的写作,就是起于这些“与我有关”的物、事、人。在对这些息息相关之物倾注心神、笔力时,作者得以不断构建外在世界与内心图景的真实。
的确,真实是小说的生命之所在。当小说家遵循作品内在的情节逻辑和人物的性格逻辑,找到独具个性的讲述方式,其语言与内容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独立自主的生命体,此时,小说是真实的。而真实在广度、深度、厚度方面可作不同层级的区分,由此亦可辨别一部作品的艺术价值。甫跃辉的小说,虽不可单纯以题材内容来划分,但就“真实性”而言,他的作品在乡土叙事和都市叙事两个维度,却明显呈现出迥异的特质。
在黑暗中显影:对乡土世界的构建
乡土叙事是甫跃辉写作的一个核心,他一直围绕这个核心经营自己的园地,多年来收获的成果有《父亲的手指》《红马》《雀跃》《初岁》《鱼王》《鬼雀》《乱雪》《母亲的旗帜》《滚石河》等。这类小说且不必细论其结构安排、人物形象塑造、人性挖掘等,写作技艺对正在摸索“狐狸多知”[3]阶段的甫跃辉来说,已达到实属不易的程度。若要论成熟、完美,那是另一个需要交给时间来回答的问题。在此,只谈他在乡土叙事中所构建的“真实性”。
甫跃辉的乡土叙事语言平实、故事朴素。他笔下的那些土地、景物、人,以及人物的话语、神情,都是鲜活的,叙述充满了在场的实感,读之如在眼前。他语言中的“有”之物,常能召唤出“无”的在场,氤氲出故乡的氛围。
这种在场、实感是有其深层来源的。一来作者具有云南边地乡村的生活记忆和家族背景,熟悉乡土经验。云南地理环境特殊,人们常年散居或聚集于山间平缓之地的村落,饱尝山村生活之苦乐。即使是城市,也多基于群山环抱之中的一个个“坝子”经年累月慢慢发展起来,与大自然亲密相依。自小生活于此的人,天然地保留着与宇宙天地浑然一体的整体感,他们成为作家后,作品里就自然地散发着一股活泼泼的生命气息。这股生命气息,在于坚、海男、雷平阳的诗歌和范稳等作家的小说中,是扑面而来的。这股生命气息,在甫跃辉的小说中也挥之不去。他描绘的乡土世界,充溢着来自民间、荒野的野性力量和神秘气息,酣畅淋漓的生命元气弥漫出苍茫大地的混沌气象。
二来作者身在异地,而对故乡、童年常怀无限追忆。不管从地理空间看,还是从出生地与成长的意义上说,甫跃辉和当下的很多青年一样,都是名副其实的流亡者。他从乡村流亡到城市,从云南流亡到上海。如布罗茨基所述,“在促使一位流亡作家紧盯着过去的诸多因素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追忆”,“追忆”会“使他不知不觉地受到稍感陌生的环境之触动。有时,一片枫叶的形状就足以使他感怀,而每棵树上则有着成千上万片的枫叶。……无论过去是愉快还是悲伤,它永远是一块安全的领地,这仅仅因为它已被体验;人类复归、回头的能力非常之强,……这种复归、回头的能力简直能使我们无视我们所面临的现实。”[4]甫跃辉不断追忆过去,追忆儿时的生活,成长的村庄,追忆村里的那棵香樟树,那座小桥,那条河……“追忆”使他同逝去的岁月发生联系。
怀着深深的追忆,甫跃辉在故乡村庄与童年岁月中,构建起意味无穷的诗性言说空间。如颇具象征意味的《鱼王》,外来者老刁承包了白水湖养鱼,尽管他谙熟原住乡民的生活习性与交往之道,但随着乡村文化形态中的原始性、自在性被打破,乡民本性深处的排外、狭隘、盲目、跟风、贪婪、粗野统统被激发出来。矛盾、冲突终于演化出一场声势浩大的抓鱼、抢鱼事件,此时,“鱼王”出现了。值得玩味的是,传说中的鱼王,只在孩子、老人、傻子的世界中存在。“鱼王的传说虚无缥缈,又实实在在,鱼王无迹可寻,又无处不在。许多年后我们才知道,村里人年轻时无一不找寻过鱼王,又都一一遭到挫败。有一天,他们忽然明白,鱼王是没有的,他们便长成这个村子最最普通的一员了。可等他们辗转一个大圈子,又渐渐地认为,鱼王是有的,他们没缘遇见罢了,那时他们已经是老人,快要离开这个村子了。”
鱼王是什么?这个追问还得回到故乡。云南各少数民族对神山神石、神树神林、神泉神湖的敬畏,在世代生活中,与崇尚天人合一的汉民族文化相互融合、渗透,使得云南人至今还保留着敬畏自然,亲近自然,尊重天地万物,以及“各美其美,美人所美,美美与共”的美好传统,这传统和人类童年的率性纯真一起流淌在居民的血脉中。在云南,“人与宇宙万物同处于大地上。人并不高于万物。万物各得其所。”[5]对甫跃辉来说,故乡不只是一个空间,更是一个饱含万般生命情绪与体验的生命场,自小浸润在云南的多元文化中,使他对自然、神秘之物心怀敬畏。在这里,“鱼王的传说不知哪年开始的。父辈们小时候听祖辈们说,我们小时候又听父辈们说……”但随着鱼王被捕,鱼王已死,“白水湖还是我们的,我们却再也没有鱼王的故事讲给那些很小的小孩听了。”
海天离开时,带走了鱼王骨架上一根巨大的刺。甫跃辉离开云南时,也带走了鱼王骨架上一根巨大的刺。这根刺,流溢着云南大地粗犷、野蛮、原始的美。这根刺,能否承载他在现代都市中对乡土世界的追忆、怀念?能否养护故乡赋予他的生命元气?这根刺,能否在他的文字中复活、生长为另一个“鱼王”,唤醒读者对自然、神秘之物的向往、敬畏?
记忆是一间漆黑的暗室,甫跃辉对乡土世界的构建,就是在黑暗中,使故乡的底片慢慢显影。显影历历在目、真实可触,而追忆的视角,使其乡土世界被怀旧的色调与氛围深深笼罩。身在都市,却执着于不断地回头、追忆,这回头有着惊人的价值:“如果走运,它会聚集起强烈的感受,于是我们便真的可以得到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了。”[6]
在街拍中剪影:对都市异乡人的透视
空间的改变带来心灵的变化。乡村生活与流动于山川、田野、河流之间的天地灵气相贯通,身在都市,生活便捷、舒适,但世界的自然性、丰富性、差异性却逐渐消失。现代化城市更改生命的存在方式,更改人们对世界、时空的感知系统。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原来星星点点稀疏坐落在大地上的小城,一夜之间变为庞然大物,转头吞噬四周的山川、河流、森林、田野。城市把人从自然之家中切割出来,将花草树木小心培植在街道旁、公园里、阳台上,将飞禽鸟兽豢养在动物园、铁栅栏、鸟笼里。在钢筋混凝土的人造世界中,城市景观设计师总想保留一丝人类原始自然之家的气息,但现代化科学技术能移植小桥流水的形、体、物,却难以养护小桥流水的气、神、魂;高楼大厦能满足城市爆炸式增长人口的居住之需,却未必给人以天井庭院那种天地人相通的自在、踏实。人们惶惶不可终日,莫名地焦虑、害怕。难怪当下的都市叙事中,常常流露出生命的茫然无措感、时空错位感、身心分裂的疼痛感。
被窒息在密不透风的网中,谈何营造生命的大气象。甫跃辉也深陷在里面:“乡村叙事中,我们还能看到天地万物的影子。城市叙事中,坦然存在和恣意生长的天地万物已让位给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城市坚硬的现实长不出神话故事,也长不出鬼怪传说。我自己也深陷在这现实里。”[7]深陷在现实里的甫跃辉,只能寄情、寄想象于动物园、猴子、巨象、老鼠、香樟树……聊以慰藉无处安放的乡愁、失落。他作品中的主人公顾零洲们,大多从乡村、小镇而来,客居城市求学、求生。他们游离在异乡,漂浮在都市,仿佛玻璃罩里的一粒尘埃,悬浮游荡,无着无落,窒息而绝望。他们既难融入城市,故乡也已回不去,一个个成了离土之树、离水之鱼,不得其所。在系统的高等教育中,顾零洲们获得较为广阔的人文视野,知道世界上存在着别种别样更加精致、奢华,更加富足、美好,更加自由、尊严的生活,但那种生活不属于他们。他们是被故乡放逐、被城市排斥的一代,内心充满被挤在边缘、排斥在外围的无奈、焦虑、失落和隐秘的愤恨,以及对自己的卑微、渺小、碌碌无为、人生毫无意义的巨大恐惧。残酷冰冷的现实、孤立无援的状态、无足轻重的感觉……一起交织为难言的痛苦,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们,而他们又被自身的欲望重重包围。向外,无力突围,向内,难于据守。终于,不得不臣服于汹涌的欲望,成为伤害更弱小者的施害者。
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中,作家面对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挖掘、处理社会现实提供的丰富素材,书写这个时代。云南大学宋家宏教授在《重说文学创作的“思想性”》一文中指出:“急剧的转型时期的生活为文学提供了空前的精彩与荒谬,数百年的人类历史进程被压缩成一堆,在短短的一二十年间轰然降临于中国社会,它的丰富性、复杂性在世界史上也是少有的,这正是文学的用武之时,从社会现实状态来看,正是出现伟大作品的时代。”[8]在这样一个转型期,无数个体都是这个时代的“顾零洲”,作者、笔者也都是其中的一员,小说人物的处境也正是我们自身的处境。顾零洲们将如何面对现代化、全球化对故乡世界的摧毁?如何在警惕、审视、反省现代文明的同时,去发现、领会身处其中的城市之美?在现实困境中,这一代人是否能萌生出一种拯救自我的抵抗意识?在卑微、尴尬的境遇中,他们,也是我们,如何对现实社会的驯化、潜规则进行有效、有力的抵抗?……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的精神即复杂性。塑造人物是小说的核心问题,可惜在甫跃辉的都市叙事中,也许和作者自身的经验、视角有关,这些人物大底单薄、空泛了些,他们是来自数码相机的街拍剪影,聚焦是表面的,透视是浅层的。他们的卑微与渺小,孤独与绝望,是作为局外人的旁观所见,作者和人物内心虽有一些同感,但还是很隔离,所以小说叙述没能很好地营造出人物活动那个“场”的氛围,没能发出人物灵魂深处的声音,缺乏出自人物骨髓深处的切肤之痛。小说写出了人物此时的状态、困境,却未写出造成他们如此这般的复杂根源。到底是什么因素、际遇促使顾零洲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是什么不可抗拒的力量使他不得不臣服,不得不沉沦于欲望世界,难道仅仅因为他们出生在农村?小说写出了人物的无奈、无助,却还未写出他们的命运。不过这倒并非作者无心于此,而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这一代人,大都还年轻,他们的生活眼下是无望的,但依然充满各种可能性。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他们将面临什么,会做何选择,他们的人生会发生什么变化。此时的一个个顾零洲,是继续无力、无助地绝望下去,还是会出现另一种转机?在充满变数的生活中,什么力量会继续强化或逐渐改变他们的性格,有没有一种内在的心灵觉醒、精神支柱最终支撑他们走出生命的困境?
顾零洲应该是一个人物系列,而不是一种人物类型。他们是多样的,复杂的,是充满各种矛盾的。顾零洲们与其他一些作家,如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卫慧的《上海宝贝》、马小淘的《毛坯夫妻》等塑造的人物,都是城市新人。对于这些人物未知的命运,读者充满好奇、期待。而甫跃辉与韩寒、张悦然、郭敬明、春树、马小淘等80后作家的家族背景、成长经历都大不一样,他具有书写顾零洲的天然优势,加之其不凡的文学才能、经典意识和写作热情,他笔下的顾零洲当会越来越立体、多样,越来越丰富、饱满。
两相比较,“追忆”使甫跃辉的乡土叙事真实可触,那个遥远乡土世界里的人物、故事是从他的生命里流淌而出的,全出自他的内心,故而清晰、动人,但怀旧先天带有理想化、纯净化的美颜、过滤功能。怀旧之乡土与现实之乡土的关联、比照,是值得作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追忆”使他对城市文明保持警觉,同时也无法全身心融入城市,对置身其中的生活世界,反而隔雾看花,故其都市叙事处于悬浮状态,挣扎于都市边缘的顾零洲们——这些具有时代特征和典型意义的人物新形象,显得模糊、单薄,落不到实处,只约摸可见个影像。近年来,文学批评家关于乡土资源与都市资源孰优孰劣的讨论,一直甚为火热。笔者以为,这不是乡土与都市的问题,而是作者的生命、经验、感受、体悟、思考和艺术的挖掘力、表现力能深入、拓展到何处的问题。切近的生活,与生命主体血肉相联,若未经体验、发酵,虽近,却远。记忆中的岁月,经过时间过滤,虽远而更近,但在追忆、怀旧的光芒笼罩中却容易失真,与现实脱节。所谓写作,不管是数码相机街拍的及时呈现,还是在黑暗中使生活的底片慢慢显影,都需要作者敢于正视现实,敢于渗透自己的思考。
作为一位80后作家,甫跃辉有直面、关照社会的意识、勇气,但他的笔墨间又常露出犹豫不决的神色,这透露出其内心的紧迫、焦虑,也呈现出技艺探索、打磨中的艰难。作家最可珍贵的,正是这种犹豫,这种对写作的慎重。文学之存在,其意义不仅在于见证、描述一个时代外在的存在状态,内在的人心世相,更高的意义还在于作品中蕴含的内省精神——那种基于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与意义对当下进行审视的内省精神,那种热力——激发人向死而生、永不疲倦的生命热力,那种力量——唤醒读者、震撼其心灵的情感力量。不知甫跃辉能否确立起内在的主体性和真正的自我意识,能否打开视野、格局,回到现场,洞察社会与人生的差异性、复杂性,以文学的方式,有力地表达出这一代人对于自己生活于其中这个时代的思考、体验和审视?笔者期待在他未来的小说中,感受到一个闪耀着内省精神、散发着生命热望、充满心灵力量的动人世界,那将是更高的存在之真实、艺术之真实。文汇出版社,2012年12月版,后记。
【注释】
[1]甫跃辉:《时光若水,刻舟求剑》,见《刻舟记》,
[2]甫跃辉:《安娜的火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10月版,腰封。
[3]甫跃辉引古希腊谚语“狐狸多知,但刺猬有一大知”表达自己的写作状态、路径,见《刺猬,还是狐狸?》,《动物园》,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后记。
[4]【美】布罗茨基,刘文飞译,《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或曰浮起的橡实》,《悲伤与理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4月版,第29-30页。
[5]于坚:《在汉语中思考诗》,《红岩》,2010年第2期。
[6]【美】布罗茨基,刘文飞译,《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或曰浮起的橡实》,《悲伤与理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4月版,第30页。
[7]甫跃辉:《鱼王》,北京铁葫芦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12月版,序言。
[8]宋家宏:《重说文学创作的“思想性”》,《边疆文学·文艺评论》,2015年第5期。
(作者系青年文艺评论家,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杨 林
青年批评家
主持人语:大先黝黑的脸上,永远挂着笑容。那种感染人的、有甜味的笑。和大先在一起,无论是聊天,还是喝酒,总有他欢快的笑伴随,也总被他的笑所感染。
可能爱笑的人,或者说活泼的人,文章也会受感染,大先的文章,无论是做电影研究、当代文学研究,还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都不呆板。理论文章读起来,多少都会有生硬感,但大先的文章却很润,有暖暖的气藏匿在文字间。
大先近年被批评界广为称道的是他一直行走在少数民族地区,潜心研究少数民族文学,提出许多有理论深度的见解。我曾和一位学界大佬聊天,他直言,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新的认知,都来自大先的文章。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提倡作家、艺术家要深入生活,却很少说批评家要深入生活,在绝大多数人看来,批评家面对文本就足够了。这或许是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越走越窄的一个因素吧。以我之浅见,批评家中,目前只有大先,云南的冉隆中两位才是真正深入生活的批评家。这是他们的批评文章有灵气,接地气的根之所在。
但正如批评家孟庆澍所言,从本质上说,大先是一个有情的、内心饱含诗意的批评家。(周明全)

刘大先(1978-),文学博士,生于安徽省六安市,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曾访学及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杂志编辑部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已出版有作品《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文学的共和》《时光的木乃伊》、《无情世界的感情》《未眠书》《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合著)等六种,译著有《陈查理传奇:一个中国侦探在美国》,主编有《本土的张力:比较视野下的民族文学研究》等。两部专著分别译为日文和英文,多篇论文翻译成哈萨克文、蒙古文、维吾尔文,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作协民族文学年度评论奖、全国青年作家批评家峰会“2013年度青年批评家”、第四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