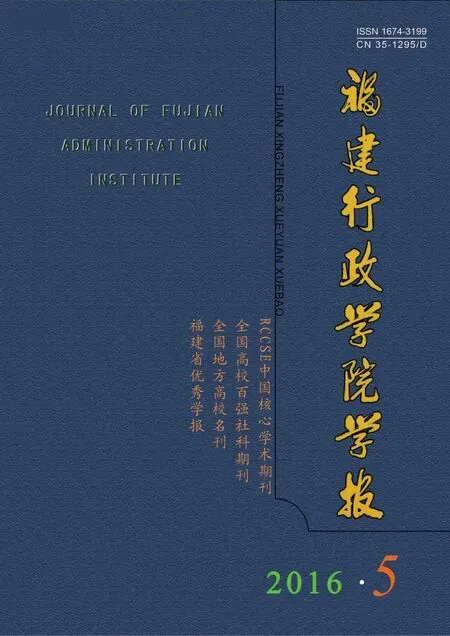论法律与习惯的关系
——以理性主义哲学为视角
2016-10-17钱炜江
钱炜江
(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论法律与习惯的关系
——以理性主义哲学为视角
钱炜江
(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我国研究法律与习惯关系的主要进路大致可以概括为“普遍与个别”的关系。但仅仅从这一进路进行思考是不够的。事实上,从“理性与非理性”对立的角度去思考法律与习惯的关系是更有思想深度的进路。这一进路大致要遵循黑格尔辩证法之要求,以“正、反、合”的方式,扬弃法律与习惯的对立,而寻求同时能包容两者的更高者。循此思路法律与习惯的关系大致可以表述为:法律塑造习惯,习惯亦参与法律判断之最终形成。
法律;习惯;理性主义哲学;黑格尔哲学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我国对于习惯以及习惯法研究的文献层出不穷,可谓汗牛充栋。但这些文献多半集中在具体习惯法的研究上——如张洪涛教授所指出的:“中国是对策研究与外部研究多于理论研究与内部研究,不是像西方那样从内部来研究习惯的概念及其民主法治自由等价值。”[1]而且,纵然是认真对法律与习惯的理论关系加以研究的学者也都只是过于偏重特定方面——一提到法律与习惯的关系,常常只能想到国家对于习惯法是否尊重、中央法规与地方习惯如何互动等等这类问题,对这一关系的其他方面往往疏于思考。如果我们可以用一对西方哲学的范畴对当今中国学界关于法律与习惯关系的研究范式加以概括的话,那么无疑就是“普遍与个别”,即把法律视为国家层面的更普遍的规范,而把习惯看作地方乃至个人层面的更为特殊化的规范,然后讨论普遍性如何与个别性协调的问题。然而,在笔者看来仅仅限于使用“普遍与个别”这对范畴对于法律与习惯的关系进行思考,仍是不够的。因为法律与习惯的关系并不仅仅是普遍与个别的关系——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在国家层面也有习惯,国家的宪法惯例也应该可以被看作习惯。但依照我国对于法律与习惯的研究方式——所谓“上层的国家法”与“民间的习惯”这样的思考进路却完全无法处理这一主题。
因此,我们可以在西方看到对于同一问题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而这是用“普遍与个别”这对范畴完全不能把握的一种思考方式。此种方式以马克斯·韦伯对法律与习惯的思考为典型。他在《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一书中特别定义了法律与习惯的区别,他指出,所谓习惯是“广大的群众参与者虽然遵照法律规范行事……因为整个周遭环境认可这种行为并非难相反的行径,或者仅仅是对规则性生活一种无自觉的、惯性的反应。”[2]197而法律则是“有一个强制机构迫使人们遵从上述的秩序”。韦伯这一观点很容易被解读为法律与习惯的关系仅仅在于“有无强制力”。[3]但事实上,韦伯的理论远非如此简单。首先我们对韦伯的理论稍加观察即可发现:根据韦伯这一定义,任何一个层面都可能存在“习惯”,只要存在通过“无自觉的、惯性的反应”来遵守的规范。同样的,任何一个层面也都能存在“法律”,只要存在一个由专门的强制机关来执行的规范。因此,韦伯为了强调自己的“法律”概念的不同,还特别使用了“国家法”一词指一般所谓国家制定法。[2]199很容易看出,此处韦伯关于法律与习惯的定义与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难以对接。如罗昶教授发现:“《古麦村村规民约》规定,村民委干部和执约小组有权利执行本村规民约规定的罚款权利。”[4]此村规在基于“普遍与个别”研究范式的我国学者眼中显然是典型的习惯,但在韦伯看来该规定却是“法律”而绝不是“习惯”。因为韦伯此处关于法律的定义就是“如果在某个场合里,有一个强制机构迫使人们遵从上述的秩序”。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与我国学者不同,在韦伯看来,法律与习惯关键性的区别是“在何种程度上被意识到”;法律比习惯高明并不在于它是国家法,而是它被更为清楚、理性地意识到——它甚至拥有机构实现自身,并且韦伯此观点在西方并不孤立——一个最显明的事实就是与“习惯法”对应的并不只是“国家法”,而且还会是“制定法”或“成文法”。
在笔者看来,以韦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与我国学者的本质性差别在于:两者研究基于的范畴的差异——我国学者所基于的乃是“普遍与个别”这一对范畴,而韦伯用以研究法律与习惯的却是“理性与非理性”这对范畴。在韦伯那里,习惯对人而言是一种自发的、直接的、不清晰的甚至没有被意识到的规范。而法律则相反,是一种后天产生的,因此是间接的,是理性参与制定并参与执行的规范。笔者认为,基于“理性与非理性”的立场对于法律与习惯的关系加以研究是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主要进路,却恰好是我国目前较为缺乏的。我国的研究过于偏重“普遍与个别”这对范畴,而忽略了“理性与非理性”这一更有思想深度的研究进路。因此对于这一进路从哲学理论到我国实践的各种关系加以思考必定有利于加深我国对于法律与习惯关系的认识。
二、西方哲学里的理性与习惯
对西方思想史进行简单梳理即可发现,“理性与非理性”这对范畴和法律与习惯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几乎所有主张人类理性有限的或者对人类理性抱着怀疑态度的思想家全都主张尊重习惯,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大卫·休谟。
(一)休谟对理性的怀疑和对习惯的赞美
休谟严格说来是经验论者,但他把经验论推向了极端,由此进入了反对理性的怀疑主义。他首先反复强调我们的一切观念都来自于经验,他指出:“一切自然法则和物体的一切作用,无例外的,都只是借经验才为我们所知晓的。”[5]29此种论点本无问题,但他将此观点推向极端,认为我们所有观点都必须来自于经验,如实体性、因果性等观念因为经验当中找不到,所以他全部加以否认。如“因为有火焰所以热起来”这个说法在休谟看来根本不成立,因他认为“热与焰”不过是一种“恒常汇合”,换言之,只是它们一贯来连续发生,所以我们做了一个习惯性联想罢了。[5]41
但如此,就产生了一个基本问题:因为诸如实体、因果等理性范畴是我们生活必要的范畴,现在休谟把这些都摧毁了——他告诉我们没有所谓“因果关系”了——那么我们如何生活呢?对于这个问题,休谟给出的答案就是“习惯是人生最大的指导。”[5]43他认为人的理性的种种范畴既然并不可靠,我们就应该遵循经验给我们的指导。他指出:“控制自然途径的那些力量虽是我们所完全不能知晓的,可是我们看到,我们的思想和构想正和自然的前一种作品在同样程序中进行着。这种互相符合之成立,正是凭借于所谓习惯的原则;习惯在人生各种情节下,各种事件中,对于维系种族,指导人生,原是这样必要的。”[5]51
休谟对习惯的态度是支持习惯的西方思想家的典型态度,即认为人的理性是不可靠的,而习惯对人是直接的、现成的东西,必须加以接受,作为个人,乃至整个种族的指导原则。如果我们对其他支持习惯的思想家的理论加以抽象,其实无不能得出类似态度。如卢梭在其名著《社会契约论》中对习惯推崇至极,称之为“一切之中最重要的一种法律”[6]。但如果我们细究卢梭的思想体系,会发现卢梭的思想里的确存在着某种对人类理性的不信任因素。他的成名作即是所谓的《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他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人类的道德水平是毫无帮助的。而他的另一部名著《爱弥儿》同样要求把儿童带到远离人群的地方加以教育。又如哈耶克亦可以用这种思路加以把握。他推崇习惯,正在于他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用理性去规制经济,认为理性并无此能力,而要求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当然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其实是非常复杂的,远非仅仅几句话能加以全面概括,但既然本文的目的是从理性主义哲学的角度对法律与习惯的关系加以研究,当然以目前的考察就够了。
(二)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与他对雅典习惯的破坏
与前面相反,在西方凡是推崇人类理性的思想家多不喜欢社会习惯,甚至破坏社会习惯,这以苏格拉底为典型。论及苏格拉底,人们多愿意联想他的那句名言即“自知其无知”。哈耶克甚至利用他为自己的“自生自发秩序”做辩护——他在《自由秩序原理》中这样说道:“苏格拉底认为,承认我们的无知,乃是开启智慧之母。苏氏的此一名言对于我们理解和认识社会有着深刻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理解社会的首要条件。”[7]但是,哈耶克此种对于苏格拉底的引用多少是有问题的。首先,我们可以立即发现的是,苏格拉底所谓“自知无知”的对象与哈耶克有限理性的对象正好是相反的——苏格拉底使用理性对象是“什么是善、什么是正义”,他终生探索的正是人类秩序本身,要保持无知的则是自然事物;而哈耶克则恰好认为人的理性不足以去建构人类社会的秩序。当然,此种分别还远远不够,以下我们还要进一步考察苏格拉底与理性主义的关系。
苏格拉底所谓“自知其无知”主要出自柏拉图的《申辩篇》。在该篇中,苏格拉底指出:“真正的智慧是神的财产,而我们人的智慧是很少的或是没有价值的……。”[8]但这是不是苏格拉底要求放弃理性地追求真理呢?其实并非如此。柏拉图在《斐德诺篇》让苏格拉底对《申辩篇》的论断做了补充:“我还不能做到德尔斐神谕所告诫的‘认识你自己’,只要我还处在对自己无知的状态,要去研究那些不相关的事情(指天上地下的自然事物)那就太可笑了。所以我不去操心这些事,而是接受人们流行的看法。”[9]139因此苏格拉底的基本立场是:人首先要研究自己,包括“什么是善”“什么是正义”这类问题。等到这类问题清楚才能去研究自然。因此,苏格拉底绝非要给理性划出限度,而只是划定了一个顺序——而且在他的这个顺序中,探求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倒是优先的。是故,苏格拉底的活动明显表现出理性主义倾向,从而对雅典传统习惯造成破坏——这实为他受到雅典人民审判的根本原因。
一般观点多认为,雅典人对苏格拉底判死刑乃是典型的不正义的恶法。但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中提出一个深刻的观点即:雅典人处死苏格拉底是完全正当的,原因就是苏格拉底的思维方式实为雅典传统习惯的破坏者。[10]90对于苏格拉底思考的基本方法,邓晓芒教授精辟指出:苏格拉底询问的“重点不在于‘正确的’而在于‘有什么证据’因而不是否认这件事的正确性,而是否认……提供的理由。”[11]换言之,苏格拉底询问的原则并不在于强加某些观点给对方(赞同或者反对某个具体观点,很多时候对苏格拉底是无所谓的),而在于引导对方自行思考,让对方基于理性的理由得出答案。苏格拉底谓之“精神接生术”。[9]661而在自己的事物处理上,苏格拉底也奉行同样的原则——他不求助于雅典人习惯遵守的神谕占卜而是依靠自己的思考和他内在的所谓“灵异”。但是苏格拉底此种理性的精神恰好解构了雅典社会的基础,即雅典人的习惯——“雅典人民的精神本身、它的法制、它的整个生活,是建立在伦理上面,建立在宗教上面,建立在一种自在自为的、固定的、坚固的东西上面”[10]96——雅典人原来是采取非理性的态度对待他们伦理生活中的一切:比如儿子服从父亲、公民服从国家、凡人服从神明。但苏格拉底却引入了理性的原则,要求人们思考为什么要服从——这种思考的结果就是儿子不再服从父亲,公民也不愿服从国家,神明也得不到人们应有的礼敬。正如黑格尔强调的,“苏格拉底现在把真理放在内在意识的决定里面;他拿这个原则教人,使这个原则进入生活之中。因此他与雅典人民所认为的公正和真理发生对立;因此他是有理由被控告的。”[10]90
从苏格拉底的例子可以看出,持有理性主义观念的思想家往往会与社会习惯相冲突。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对立在社会规范领域往往会体现为法律与习惯的冲突,这正是韦伯习惯—法律理论的根本来源,而理性主义的巅峰正是黑格尔哲学。
(三)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哲学:“人死于习惯”
事实上,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起就有强烈的理性主义倾向。康德主张:善良只能是意志的善良、自觉的善良,那种依靠本能习惯的善良绝非善良。[12]而黑格尔哲学正是秉承苏格拉底、康德的这一理性主义的传统立场,坚决提倡依赖人类理性而拒斥依赖于直接的感觉、直觉等等东西。他在《精神现象学》中强调:“真理唯有在概念里才获得它的实存要素”[13]——这就是说我们必须通过理性的概念思考真理,而不是通过直接的“直觉”。
而基于这一哲学立场,黑格尔对于习惯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因为习惯似乎是人类感性生活的直接结果,而不是理性反思的结果,以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要求当然必须加以反对。事实上黑格尔也的确有很多对于习惯的批评。一方面,他指出:“人死于习惯,这就是说,当他完全习惯于生活,精神和肉体都已变得迟钝,而且主观意识和精神活动之间的对立也已消失了,这时他就死了。”[14]171在黑格尔看来,人之所以为人正在于其主观意识与客观活动的对立,在于他对现实的不满,他要努力去把主观的东西变成客观的事实。而一旦这种对立消失,人服从于他的习惯,那么在黑格尔看来,他已经死了——这就是说他已经失去了人的基本活力。另一方面,他坚决要求区别“统一的、没有反省的习惯和风俗”和“有反省的、有个性的,有一种主观的和独立的生存的个人”。[15]30他认为前者是没有价值的。而在法律与习惯的关系上,黑格尔也主张立法,而非仅以习惯进行治理。他指出:“当习惯法一旦被汇编而集合起来——在稍开化的民族中必然会发生的——这一汇编就是法典。正因为它仅仅是一种汇编,所以它显然是畸形的、模糊的和残缺的。它同一部真正所谓法典的区别主要在于,真正的法典是从思维上来把握并表达法的各种原则的普遍性。”[14]219此外,他还对萨维尼的反法典化要求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否认一个文明民族和它的法学界具有编纂法典的能力,这是对这一民族和它的法学界莫大的侮辱”。而其理由正是黑格尔所持有的理性主义立场:“因为这里的问题并不是要建立一个其内容是崭新的法律体系,而是认识即思维地理解现行法律内容的被规定了的普遍性,然后把它适用于特殊事物。”[14]220
但是须注意的是,黑格尔作为理性主义的巅峰,并不在于他把理性主义推向了极端,刚好相反,他利用古希腊哲学对德国古典哲学进一步改造使之具有某种弹性,能够包容对立的哲学如经验论甚至非理性主义的立场。在法律与习惯的问题上也是如此。黑格尔表面上持绝对理性主义立场,但他实际上并非没有给习惯留下空间。我们同样可以从他的著作中找到相反态度即强调习惯作用的论断。比如他指出:“国家直接存在于风俗习惯中,而间接存在于单个人的自我意识和他的知识和活动中。”[14]253“国家……主要是依靠风俗习惯的力量和它的各种制度内在合理性的力量,来减少和克服反常状态和国家严格主张它自身权利之间的差别的地位。”[14]273
解决黑格尔对待习惯这一看似矛盾的立场必须从黑格尔辩证法的一对关键性范畴着手,即直接性与间接性的辩证法。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指出:“无论在天上、在自然中、在精神中或任何地方,都没有什么东西不同时包含直接性和间接性,所以这两种规定不曾分离过,也不可分离,而它们的对立便什么也不是。”[15]52习惯对人固然是直接的东西,人无须思索便可按照习惯行事,然而这个习惯却是历史上理性的产物,因此是间接的。比如黑格尔指出,“对伦理事物的习惯,成为取代最初纯粹自然意志的第二天性”。[14]170就自然的人而言,其实并不天然就习惯伦理,他之习惯伦理恰好是后天教育的结果。但这个结果却使得伦理变成了他的“自然天性”、变成了纯粹直接的“习惯”了。
三、理性主义法哲学视角下的法律与习惯
当然,黑格尔的哲学理论对于法律与习惯的思考还是比较抽象的,如果我们需要更为具体的应用,则需要观察法学家们的法律与习惯的关系理论。就此,笔者认为英国法社会学家麦考密克(Neil MacCormick)以及德国法学家普赫塔(Georg Friedrich Puchta)的法律与习惯的关系理论与黑格尔的哲学理论有着某种程度上的亲和性,值得提出作为我们进一步阐明观点的基础。
(一)麦考密克:规则塑造习惯
麦考密克在面临规则与习惯的关系时,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之前梳理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他指出:一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真正的好人必须习惯于做好事,而非因深思熟虑而做好事。[16]63另一方面,康德与之相反,坚持做好事必须基于自觉的善良的意志。[16]64而麦考密克的意图明显是协调理性与非理性的两种不同立场,得出他自己的规则-习惯理论。
麦考密克的理论建构的基本出发点是哈特所谓“规则的内在观点”。他指出,哈特在其著作《法律的概念》中提出:对于法律不仅有外在的观点,更有内在的观点,也即对于开车过红绿灯这件事的观察不仅可以从外在角度统计有多少人在红灯前面停住了,也可以从内在的角度直截了当地指出“红灯停,绿灯行”乃是一条规则。但麦考密克认为,哈特可能会面临如下很难反驳的指责:当我在红灯面前停止的时候,我并未对规则加以考虑,我就是看见红灯然后停下来了而已。所以在我这里并没有内在的观点。[16]62而麦考密克替哈特提出的反驳即是:认知科学指出,规则塑造习惯。[16]66他以学习开车为例说明了这种塑造。他强调当我们学习驾驶的时候,任何一个信号灯的变化都足以让我们手忙脚乱。因为此时我们还在利用理性适应规则,还没有足够熟悉。但是当初学者的驾驶技术足够熟练,这些规则就逐渐内化为他们的习惯。[16]67麦考密克通过此说明,哈特的所谓“规则内在观点”的真实的内在过程即从理性的规则到无意识的习惯。
但麦考密克在这个基础上走的更远。他把理性与规则比作“维特根斯坦的梯子,当爬上去以后就扔掉了”——换而言之,理性与规则只是一种工具,而守法的习惯和本能才是真正目的。这正如我们学习的交通规则只是一种工具,真正的目的是学得驾驶的技能。他甚至把这种模式推向其他一切领域,以至于认为:“人类或者人脑的作用模式要求……学习技能,然后忘记获得技能所需攀爬的脚手架。”[16]67所以,正如李锦辉博士所强调的,麦考密克“法律规则的理想标准”乃是“法律必须被遗忘”。[17]
可以说麦考密克的观点是大致符合黑格尔关于习惯的哲学观点的。但其理论相对黑格尔而言仍有缺陷。黑格尔的理论可说是一个圆圈:理性塑造习惯,但理性永远不会安于现有的习惯,它会永远向前。这也是恩格斯解读黑格尔时说的“凡是现存的,都是要灭亡的”的含义之一。但麦考密克却人为地设定了一个理想状态,即习惯守法——“法律必须被遗忘”。这一设定看似合理,但最大问题在于把理性变成了工具(脚手架、梯子),培养守法习惯才是目的——对此,我们须牢牢记住黑格尔的教训:“人死于习惯”。现代人区别于古人的最大优点正在于他能够反思自己的守法习惯,乃至法律本身。只知习惯守法的公民必将会沦为恶法之工具。如果我们认为现代民主制度已然保证了良法的话,我们只要回忆一下希特勒就可以消灭这种幻想——这位独裁者正是现代民主制度的产物。二战以后颇有诸如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为专制主义张目之类的批评,但事实上失去自由的原因绝非某种特别的思想的影响而是人们丧失了自己思想的能力。因此麦考密克的理想状态应当修正如下:法律必须被遗忘,但同时必须被时时记起。
(二)普赫塔:从习惯法到概念金字塔
作为概念法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普赫塔的理性主义立场应无疑问。但普赫塔的主要著作除了他那著名的《潘德克顿教科书》(Pandekten)外,就是两卷的著作《习惯法》(Das Gewohnheitsrecht)——可见习惯法理论在普赫塔的体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故,对普赫塔关于法律与习惯的看法实值得加以研究。
普赫塔首先区别了“历史或者理论性的习惯法判断”以及“实践上的习惯法判断”。[18]58而此种区别的目的主要是摆脱繁琐的具体习惯法研究,而直接阐述他对于习惯法的形而上学的见解。换言之,普赫塔对于习惯法的见解主要是理论化、哲学化的。
普赫塔对于习惯法的基本定位是:所谓习惯法只是法律的导论。普赫塔为此专门区别了法律的认识渊源以及法律渊源。[18]78他认为习惯只是法律的认识渊源,而非法律渊源本身。换言之,我们可以从习惯中认识法律究竟为何,但却不能认为习惯本身就是法律,因为习惯要成为法律须待理性的加工。而习惯法虽然其效力无须制定法承认,但也可以被制定法所废除。[18]86习惯法要最终向更为理性的法律家法发展。[18]161此观点本不甚出奇,但普赫塔接下来提出了一个深刻的观点,他指出:制定法本身也只是法律的认识渊源。他认为真正的法律渊源只能是民族信念(Volksüberzeugung),而制定法与习惯法都只是认识民族信念的手段。[19]298-338制定法必须足够理性化才能真正体现出他所谓的民族信念。换言之,在普赫塔这里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并不是表现为制定法与习惯法的对立,而是表现为一切法律的认识渊源(习惯、制定法)与真正的法律渊源民族信念的对立——只有民族信念才是真正的理性本身。一切因素,只有趋向理性才是有价值的。如普赫塔还区别了惯常做法(Herkommen)与习惯法(Recht der Gewohnheiten)。普赫塔认为所谓惯常做法只是不自觉的,从而是空虚的、无灵魂的东西(Etwas ganz leeres,geistloses)。[19]298-338而习惯法则理性程度较高,较能体现民族精神的要求。
至于如何才能进一步理性化而达到更高的民族信念,普赫塔在别处指出:“科学现在的任务在于,在体系性的关联上去认识法条,认识这些彼此互为条件且相互衍生的法条,以便能够从个别的系谱学向上追溯至其原则,并且同样地可以从这个原则向下衍生至最外部的分支。在这样的工作上,法条被带进意识里并且从隐藏在民族精神中被发掘出来,所以法条不是从民族成员的直接确信及其行动中产生,法条也不是出现在立法者的格言里,法条一直是在作为科学演绎的产物上,才能看得到。”[20]在这里普赫塔清楚地看到,从习惯到法律的理性化并不是一个一次完成的工作,而是一个不断理性化的过程。这种理性化的工作其实是普赫塔工作的重点,而他的成果即是所谓“概念金字塔”。谢晖教授曾经这样说过,他打算“在未来准备做的一项学术努力,就是设法把‘民间法’和法律方法的研究结合起来”。[21]然而我们清楚地知道早在近200年前,普赫塔已然这样做过。而他的主要工作成果所谓概念金字塔,正如那真正的金字塔一样,我们虽然知道,在它之中,多少包含着些古人的迷信和无知,但每当我们站在下面仰视它的时候,我们都会不由自主地感到敬畏,感到人类精神的伟大。
四、理性主义哲学视野下法律与习惯研究的基本思路
前已述及,法律与习惯的研究可以分为基于“个别与普遍”这对范畴为出发点的研究以及基于“理性与非理性”为出发点的研究。当然,如果对某个具体的事实进行研究,这两种出发点所涉及研究思路难免有所重合。但是我们从“理性与非理性”对立的角度仍可以提出一些新的思路以拓宽研究的视角。根据我们前面对于理性主义哲学家以及法学家的理论的梳理,现大致可以提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基本思路:第一,须注意法律或者其他理性因素对于习惯的塑造。任何习惯都不是绝对天然的,都是人类理性塑造的结果。第二,这种塑造的结果并不是一切都向着制定法发展,因法律也不是理性本身。相反,因为法律本身也需要理性化、系统化,它也需要趋向更高的理性整体,所以它可能反过来吸收习惯。
(一)理性因素对于习惯的塑造
习惯就其本身而言必定是直接的,近乎本能的。但是根据黑格尔“直接性与间接性”的辩证法,人类的一切似乎是现成的、自然的东西其实都是理性塑造的结果。如果不注意这一点而认为习惯就是天生的、自然的,便会在研究中遇到许多问题,以下将对此问题详细讨论。
第一,法律以外的理性因素对于习惯的塑造。喻中教授曾对中国农村传统的殡葬习惯以及政府在农村推广新式殡葬的状况进行了考察。对于“乡村社会为什么排斥新式葬礼?”这个问题,喻中教授声称他“曾经询问过一个临死的老人,为什么拒绝火葬。她的理由是:火烧会很痛。”喻中教授认为这种说法是因为老人害怕身体的灭失,并且认为旧式殡葬体现了对人的尊重。[22]喻中教授的这种研究方法很有典型性:田野调查、直接询问当事人——这似乎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的标志。但如果用理性主义哲学的视角看这个问题,会发现喻中教授的方法其实不无值得商榷之处。
我们知道习惯是近乎本能的,所以习惯的主体其实往往并不知道自己的习惯是哪里来的——尤其是殡葬习惯这样历史久远的习惯。如果采取一般社会学调查方法询问本人,实际上是逼迫他本人将原本直接的、近乎本能的习惯理性化,也即让他给出一个“理由”。但由于习惯主体的理性化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他给出的答案往往是有问题的。如喻中教授提到的“临死老人”的“火烧会很痛”的理由。喻中教授也注意到这里理由的难以成立,于是他用自身的学识对该理由进一步理性化:“老人害怕身体的灭失”,并且认为“旧式殡葬体现了对人的尊重。”但喻中教授这一论断仍然是有问题的。对此,我们只需要稍稍考察一下中国的殡葬史就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其实有一次与新中国殡葬改革相反的改革。在明朝初年,当时许多人家习惯于火葬。而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强制禁止火葬,推行土葬:“古有掩骼埋胔之令,近世狃元俗,死者或以火焚,而投其骨于水。伤恩败俗,莫此为甚,其禁止之。”若按喻中教授的说法,人们觉得火烧会“痛”、土葬“尊重人”云云,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明朝人就不觉得火葬痛,为什么就不懂得“尊重人”?反而要杀人如麻、滥用酷刑的朱元璋来提倡“尊重人”?
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必须认识到:习惯虽然看似是直接的,体现为当事人的近乎本能的反应,但其发展和成型却恰好是历史理性塑造的结果。殡葬习惯就是如此。殡葬问题其实是一个宗教问题,必须从一般宗教的角度加以理解。在明朝初年,由于之前的元朝统治者信奉佛教,所以佛教在民间极其兴盛。而佛教对于躯体的理解乃是“臭皮囊”——对于佛教而言身体本身只有否定的价值。佛教所追求的境界“涅槃”就是要抛弃身体乃至自我意识,进入一种虚无的状态。所以对于佛教信徒而言,死后火葬乃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但与之相对的中国官方宗教——儒教,却对身体持有完全相反的看法。因为儒教本身就是现世的宗教,它没有彼岸世界,生前如何,死后就将如何,甚至没有死后的报应之说。[23]对于儒教而言就算报恶报善也都是现世报。正如《易传》所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而儒教的孝道也极其重视身体,《孝经》有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轻易毁之。”因此对于儒教的宗教观念而言,火葬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而朱元璋本人虽然当过和尚,但他深深明白,统治中国只能靠儒教。[24]佛教的因果轮回业报之说,虽然也有利于统治,但佛教还要求人们修“空”,这就容易引导人们放弃社会义务,必须加以约束。因此明朝那次禁止火葬的运动其实质不外是一次宗教观念的更新:重新树立儒教观念为中国社会的正统。与之前的历次对于佛教的迫害,其实并无本质的区别。而新中国的殡葬改革本质上同样是一次宗教观念的更新。因为新中国的官方宗教意识形态是无神论。既是无神论,那么死后如何安葬本身其实是无关紧要的,更多的是考虑实际的卫生、用地问题。因此这一次殡葬改革虽然以卫生、用地等理由提出,但究其实质是用新中国的无神论去替代儒教的祖先崇拜和天崇拜。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几乎可以说没有那种绝对自然的社会习惯。我们对于社会习惯的研究必须包括习惯以及与之相关的理性因素,否则得出的结论难免流于肤浅。
第二,法律对于习惯的塑造。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多数社会习惯都是理性塑造的结果。而在法律与习惯的关系上,我们须明白与法律有关的习惯大多都是法律本身塑造的结果——可能是历史上的法律,也可以是现代的法律——当然也可能是其他理性因素塑造的结果。就此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法律可以通过人的接受和重复内化成为人的习惯。典型的例子就是酒驾入刑后,人们形成“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习惯。另一方面,法律将习惯作为自身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此尚可举马士基公司诉瀛海公司案为例说明。此案中马士基公司为国际班轮运输公司,其后因故与瀛海公司发生纠纷,所以拒绝继续接受瀛海公司托运的集装箱。瀛海公司诉至法院要求马士基公司按照交易惯例接受其集装箱托运请求。此案看似是一个法院是否采纳交易习惯的问题,但实际上,法院与双方当事人都十分清楚,这其实是一个如何适用规范的问题。瀛海公司主张: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九条,马士基公司作为“公共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换而言之,马士基公司之所以有义务尊重交易惯例并不是仅仅因为该交易惯例是“习惯”,而且还在于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公共承运人”有依照交易惯例的强制缔约义务。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自然就转向了马士基公司是否是“公共承运人”。马士基公司提出抗辩的核心理由就是其并非“公共承运人”,因此没有按照交易惯例的强制缔约义务。而最后法院亦是循此思路判决。二审福建省高院认定“马士基公司的海上运输行为除了具有商业性外,还因其面向社会大众而具有公益性,因此,马士基公司属于公共承运人。”据此判决“责令马士基公司……不得拒绝瀛海公司依业务惯例要求的订舱和相关运输服务。”而最高法院的意见则与此相反:认为班轮运输没有垄断性和公共性。所以最高法院就此认定马士基公司不能作为《合同法》所谓的“公共承运人”,是故撤销了二审福建高院的判决,改判驳回瀛海公司的诉讼请求。
综上所述,虽不能断言习惯俱是法律塑造的结果,但现代社会中的习惯其实多源于法律的塑造。在实践中,司法是否接受习惯的关键并不在于该“习惯”是不是习惯,而是基于该习惯的形成是接受何种理性因素的塑造、其发展是以何种法律规范为前提。这一因素的查明才是习惯能否被尊重,尊重到何种程度的关键所在。拒绝考察作为习惯基础的法律因素,而简单地把习惯接受下来的做法是不能把握事情本质的。
(二)习惯反作用于法律的途径

1.法律文义与习惯。关于习惯在法律中的适用问题,若法律明文规定适用习惯,自无问题,甚至如瑞士民法典或者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那样概括性地规定“法无规定依习惯”亦可。但若此类规定俱无,如何适用颇成问题。但大部分学者都承认,仅在法律文义无规定或规定不明确时才能考虑适用习惯。但实践中的问题往往是:以为法律与习惯的关系中处处存有缺陷和漏洞,而未能意识到法律是一个系统整体。尤其是我国现行《民法》正是采用普赫塔之潘德克顿体系,其在概念上被设为一个无缺陷的整体。在实践中当然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陷,但也断不会到漏洞俯拾皆是的地步。正当的做法应当是循整个法律体系对于法律规定进行全面的检索,方才适宜断言漏洞存在。
谢晖教授所举的“红白喜事纠纷案”即为典型。谢晖教授指出:“红白喜事同时同店规定方面都基本上是空白,但法院既然受理了这样的案件.就必须设法进行裁判,由于法律中没有现成答案,法官不得不另辟蹊径,而在其他社会规范特别是民间法中寻求并引用以作为裁判规范。”[26]但笔者认为,此事并不用“另辟蹊径”,在法律范围内即可解决。设甲在丙开设的酒店办喜事,而乙则在同一酒店办理丧事。甲完全可以起诉丙要求其退还酒席费用并赔偿损失。因《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而丙在与甲签订合同允许在自己店内办喜宴后,竟然又允许乙在同一时间在自己店内办丧事,显然使得甲难以达成其合同目的,属于履行不适格,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并可认为构成加害给付,应当负有赔偿责任。
2.通过习惯突破法律文义的规定。当然,在实践中,的确可以发现在某些情况下必须突破法律文义的规定。但须指出的是:虽突破法律文义,但也要尽量在法律体系的框架内为之。此时突破法律文义的与其说是习惯,倒不如说是包含习惯在内的法律的整体要求。
如姜世波教授所举的案例:“陈某、唐某夫妇生有两子五女,长子陈某志,次子陈某德……陈某夫妇因家庭生活琐事与长子矛盾重重,经亲朋好友出面调解,于2004年达成‘陈某、唐某夫妇与次子共同生活,并由次子负责办理百年之后的丧葬事宜’等内容的协议。后次子陈某德将长子告上法庭,要求法院明确两人的百年事宜由次子陈某德办理。因当地风俗习惯长子主持父母百年事宜,如果法院对该协议迳行判决予以确认,不仅会受到当地群众的议论、指责,还可能在将来办理陈某、唐某丧事引发子女们之间的矛盾,于是法院以无法律依据为由,驳回陈某、唐某要求‘由次子负责办理其百年后的丧葬事宜’的诉讼请求”。此案被姜世波教授奉为法院尊重民间习惯的典范,认为它“顺民意,得民心”。但我们认为此案判决严重不当,因为它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破坏了法律的安定性。而该案的法官却丝毫不见“穷尽法条”的努力。
首先,该判决违反了法律的文义。该判决的理由“以无法律依据”驳回诉讼。但该起诉却是显而易见有法律依据的。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另一方有权要求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而在本案中,陈某德基于有效协议向法院起诉,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当然可以支持。其次,此判决在突破法律文义的同时却没有兼顾体系性思考要求,没有把对习惯的尊重放到法学界可以接受的轨道上来——因此是一种野蛮的违法判决。当然姜世波教授自己也认识到这点,他指出:“主审法官面临着既定法规定与农村风俗习惯的选择,双方签订的协议并无欺诈、胁迫的情形,协议也没有损害国家及社会公共利益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内容,一般情况下应当尊重。”[27]但姜世波教授认为,这种情况下,因为考虑到社会稳定和对风俗习惯的尊重,违法是可以接受的。但笔者认为这种违法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存在可以达成同样效果的合法判决,至少是在法律体系内的判决,此时为这种毫无必要的违法判决实为不智。第一,以姜世波教授的原文而言,“陈某夫妇因家庭生活琐事与长子于2004年达成协议。”可见,该协议是陈某夫妇与其长子达成的,而最后起诉的却是次子陈某德——这属于诉讼主体不适格,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第二,退一步说,纵然该协议确系长子陈某志与次子陈某德达成,法院也可以以“该协议剥夺了长子主持葬礼的习惯性权利”,从而违反了《民法通则》第七条所确定的公序良俗原则,因此协议应当被认定为无效。据此可以驳回次子陈某德的诉讼请求。虽然此种判决手段仍不无疑义,但其至少在形式上实现了合法。事实上,最高法院再三强调“善良风俗”在涉及习惯法的民事审判中的作用,正是因为此法律原则恰好是法律与风俗习惯的一个有效衔接点。[28]
五、结 语
亚里士多德有言: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者,乃在于人有理性。[29]这就是说,人能对直接现成的自身习惯加以反思,从而使得改进成为可能。而也正因如此,他才是一个人——一个永不知改变自身现状,以前如此便永远如此的人,实不配被叫做“人”。是故,理性精神实可看作人之本质,我们须时时借助理性对于习惯加以反省——如苏格拉底所言: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然而,这并非要我们用法律去吞没习惯、拒斥习惯,而是相反,我们必须在法律与习惯的对立中,找到那个第三者、那个合题、那个代表更高理性的整体,唯有如此,才能正确处理好法律与习惯的关系。
[1]张洪涛.边缘抑或中心:大历史视野中习惯法命运研究[J].法学家,2011(4):15-28.
[2]马克斯·韦伯.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M].康乐,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张镭.论习惯的法权本质[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7(6):20-24.
[4]罗昶.村规民约的实施与固有习惯法[J].现代法学,2011(4):19.
[5]休谟.人类理解研究[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6]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70.
[7]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M].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19.
[8]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1卷[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9.
[9]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2卷[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0]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11]邓晓芒.儒家伦理新批判[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8.
[12]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M].李秋零,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03-405.
[13]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
[1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15]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16]Neil Mac Cormick. Institutions of Law: An Essay in Legal Theory[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7]李锦辉.法律的微循环与法治[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4):89-92.
[18]G.F.Puchta.Das Gewohnheitsrecht:Vol1[M].Erlangen:in der palm’schen Verlagsbuchhandlung,1828.
[19]K.Moriya.Zum römischen Gewohnheitsrecht bei Georg Friedrich Puchta[J].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 für Rechtsgeschichte. 2011(1).
[20]吴从周.概念法学、利益法学与价值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4.
[21]谢晖.大、小传统的沟通理性[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10.
[22]喻中.乡村丧礼的逻辑:一个法人类学的考察[J].比较法研究,2011(4):132-143.
[23]李申.中国儒教史:上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2-34.
[24]潘桂明.中国佛教思想史稿:第3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454-457.
[25]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45-247.
[26]谢晖.民间法与裁判规范[J].法学研究,2011(2):173-181.
[27]姜世波.习惯法规则的形成机制及其查明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45-46.
[28]汤建国,高其才.习惯在民事审判中的运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10-12.
[29]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384-386.
[责任编辑:郑继汤]
On Relationship of Laws with Customs:From Perspective of Rationalistic Philosophy
QIAN Wei-jiang
(School of Law,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Hangzhou 310018, Zhejiang, China)
The main pattern of China for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of laws with customs can be generally summarized a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general and the individual. But it is not adequate to think along the pattern only. As a matter of fact, it is a profound pattern for 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of laws with custo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pposition of “rationalism with non-rationalism”. The pattern just follows the requirements of Hegelian dialectics in the form of “thesis, anti-thesis and synthesis”, to give up the opposition of laws with customs and pursue a higher one to contain both. Such high one can be described as follows: law shape customs and customs are also involved in the formation of final legal judgments.
laws; customs; rationalism; Hegel philosophy
2016-03-2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6YJC820028)
钱炜江(1982-),男,浙江桐庐人,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博士。
D90
A
1674-3199(2016)05-005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