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鸡蛋上跳舞的人
2016-10-13乌耕
乌耕
王端给生产队喂驴,兼看场院。我老家地处平原,上世纪六十年代曾经养过牛。七十年代以后,大队终于有了一台缺胳膊少腿的拖拉机,虽经常趴窝,但耕地还是能对付,牛就卖掉了。驴的作用,主要是秋播,平时基本赋闲,所以在我记忆中,我们第三生产队最多时也只养过两头驴。
每个生产队都有喂驴的,也都是老头,一般是老光棍儿,我老家叫“光棍子”。
既然喂驴,自然住在场院里,“看场院”是捎带的,似乎只具象征意义。那时,偷窃的事情鲜有,但那么多集体财产,总得有个活人守着吧。
所谓场院,就是一个几亩地大的打麦场,一间很大的仓库,一排烘菸(yān)屋,一间地窨子,一个农具棚加驴棚。紧挨着农具棚,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小黑屋,王端就住在那里。
场院是孩子们的天堂,即使是晚上,或者寒冷的冬季。至于麦收或秋收时节,场院永远都像一口沸腾的锅。
孩子们疯够了玩腻了时,会逗王端玩儿,似乎是一种调节或休息,也几乎成为一天的收官之战。这是个雷同的剧目,每天都要上演,王端也很配合。
孩子们站在小屋前,扯着嗓子一块喊:“王端王端,腚上冒烟,用手一摸,薄屎没干——”
王端很快就从小黑屋出来了,手中拎一截手腕粗细两拃来长的木棍,伴随着一声低沉的国骂,他把木棍掷向孩子们。
他掷不远,大约七八米的样子。孩子们哄笑着撤退七八米,又站定了一起喊。王端蹒跚着奔向他的“武器”,捡起来再掷,如是者三,或如是者五。等孩子们对这个游戏也腻味了时,肚子便开始叫,天也黑透了,母亲长长短短的唤声传来,孩子们就散了。
热衷于这个游戏的,都是些很小的孩子,最大的也不过七八岁,我没有加入过。叫人纳闷的是,王端从来没有伤过一个孩子,我想,唯一的解释应该是他的善意。一个孤寂的老人,内心一定渴望子嗣或者温情吧,他跟孩子们的默契,意味着在这个近乎恶作剧的游戏中,他收获了某种人性的满足。
我读四年级那一年,腊月初七午后,王端光着腚跑出来了。我们刚放学,一大帮同学跟在他屁股后边跑,包括女同学,大家兴奋得就像过年一样。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裸体的成年男人,很震撼,最大的直感是丑。
据说王端宰了一只鸡准备过年,让侄女给他收拾,而侄女拒绝。王端有个早已过世的弟弟,留下了一子三女,最大的侄女已嫁,最小的一个叫改。
还有一个说法是,王端让改给他收拾鸡是假,其实是对改有想法,并动手动脚。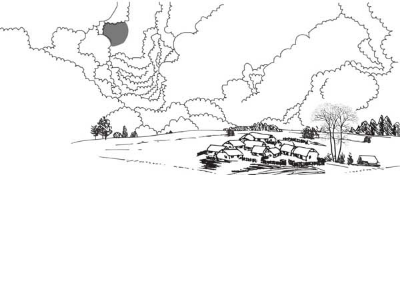
真相如何,已经不可考。但有一点是可考的,那就是独身一生的男人,老了不免会裸奔,这在农村很常见。年轻时,他还能用理性的缰绳拴住自己,老到一定程度后,力比多会跑出来做功。就在这天晚上,王端灌进了一瓶白酒,口鼻流血,活活醉死了。
落了一夜大雪,天亮时积雪没膝。按农村惯例,停灵三日才出殡,但王端这样的光棍子,跟弟媳一家也形同陌路,腊月初八就给抬出去埋了。
一些看殡的老人叹息道:这个人,那二年多么吃人!唉,就这样走了……
在我老家的语汇中,形容一个人牛时,往往用“吃人”二字。试想,人都能吃且敢吃,当然是牛的最高级。
王端是个有故事的人,曾做过我们村的“农救会长”。
顾名思义,农救会应该是“农民救国会”,是八路军搞的村民组织。大家都知道,抗战后期,山东有两个著名的根据地,一是临沂,一是胶东,而我老家不在这个范围内,但又离得很近,且介于二者之间。这种微妙的地缘关系,决定了微妙的地缘政治——拉锯与观望:富人盼着国军来,穷人盼着八路来,但盼来盼去,二者谁也没有实力长期驻扎。对这种朝秦暮楚的局面,阎锡山在抗战初曾有过一个形象而透辟的比喻:我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
阎锡山老谋深算,阎的三个鸡蛋是:国军,共军,日本人,他打量并掂量着这三个鸡蛋,依形势变化而俯仰。
我老家有条母亲河叫弥河,绕县城而过,从抗战后期到1948年,大致的军事格局是,河东属于还乡团,河西属于八路军,我们村在河西。八路军一般都是晚上来,包括搞土改,天亮就撤了,很多胆小的农民,甚至不敢要地主的土地和浮财。可以想见,在这种一夕数惊的形势下,出头为八路军做事,那是提着脑袋在刀刃上走。王端当时三十来岁,一身胆子与蛮力,于是他做了我们村的农救会长。
这是王端一生中唯一的辉煌,有很多关于他的轶事。那时没有扩音器,据说王端给村民训话,邻村都能听得到,可见他的身体状况与底气。只要王端一训话,晚上就有人给他送东西,当然都是政治上有问题的。最拉风的,是王端有一头走驴,通体乌黑,四蹄与两个鼻孔雪白,脖子上挂有响铃,只要一听铃铛响,村民就知道王端回来了。我们村很小,仅有的一家地主也是个小地主,他都没骑过驴。
王端的这段经历,没有成为他的资本,时移事去之后,他很快又回到落寞,而且越老越凄凉。于是他像流星一样,划过历史的夜空。从他那张从来就不洗也很少有表情的脸上,你既读不出曾经的辉煌,也读不到沧桑。
我对这段历史的兴趣,绝非仅仅是好奇,而是它深深地砌入了我的命运。
——我姥爷也曾给八路军做过事。
姥爷的村子也在河西,但非常大,大约就是这个原因,它成为八路军工作的重点,所以村里驻了一个八路军。在阴晴不定的形势下,那些给八路军做事的人,是首鼠两端的,在形势突然变得恶劣的情况下,几个人偷偷一商量,决定把那个八路军送到河东去。这是彻底的背叛。
姥爷是个商人,大多时间不在家。他的口碑和口才应该不错,只负责给村民调解纠纷,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另外,叛变的阴谋他一无所知,但行动的那天晚上,他恰好在家,几个人隔着墙喊他,他开始是拒绝,但拗不过众人,最后也跟着去了。
成群结队,是农民最大的本能,尤其是面对凶险时。在策划者,多一个人可以壮胆,也可分担未知的风险;在我姥爷,我猜则主要是从众,乡里乡亲的,你很难逆众而行。不过,骑墙心理是共同的,万一还乡团杀回来并坐了天下呢。
那个被五花大绑送到河东的八路军,被还乡团杀害了。
在建国初期的镇反运动中,那几个主要的策划并参与者,都被枪毙了。我姥爷是“从犯”,被从轻发落,但却留下了再也擦不掉的历史污点,而且他在惊吓之下很快就得了重病,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
这个历史污点的正式结论是什么,已经是个永远的谜。孩子的直感是发达的,很小我就感觉到了它的存在,但爹娘讳莫如深。直到读中学时,我因为姥爷的历史问题不能入团,才坐实了此前的直感,那个影影绰绰的梦魇,一下变得清晰。
能够从容地谈论姥爷的历史问题,已经是我读大学以后,不过,智商过人的老爹,依旧说不清姥爷的最后结论是什么。
当然,说清楚也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它影响了我的人生态度与价值选择。比如我亲近文学并一头扎进历史或哲学,并非始于兴趣或书本概念,而是穿着母亲做的平底布鞋,背着巨大的原罪感,从那个无名的小村和自己的伤口出发的。
